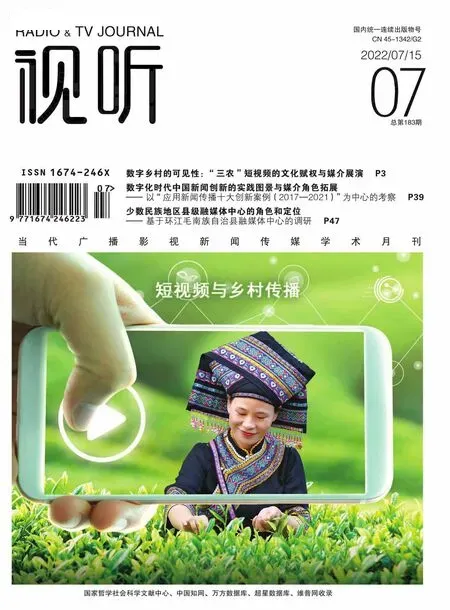文化工業理論視角下懷舊型消費空間的生產與傳播
——以超級文和友為例
張 文
“文化工業”一般指的是憑借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大規模地復制、傳播文化產品的娛樂工業體系①。被稱為“餐飲界迪士尼”的超級文和友僅用8年的時間,就從路邊攤蛻變為“市井文化綜合體”,并將“長沙模式”推廣至全國。“文和友現象”引起業界的極大關注。然而,在發展過程中,超級文和友卻按照文化工業標準化、程式化、商業化去生產文化產品,利用社交媒體的特性壓榨分享型消費者的剩余價值,這些舉措致使其產品在部分地區“遇冷”。本文以超級文和友為案例,試圖通過文化工業視角對其生產和傳播作深入探討,從而揭示懷舊型消費空間當下面臨的運作困境。
一、懷舊型消費空間的火爆出圈
不斷加劇的現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催生了當代的懷舊現象,懷舊已經擺脫了最初的醫學起源,內涵延伸到與感懷往日、消失的地方感、對地方的渴望和依戀等相關內容,成為當下的一種文化實踐②。懷舊型消費空間的興起得益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情感型補償助推懷舊消費勃興
對于當下一批具有雄厚購買力的消費者來說,懷舊文化不再是通過書本和影視被動式輸入的文本,它能沉淀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和心智共識。懷舊消費源于受眾群體對既往的追憶與思念,其觸發條件一般分為兩類情感補償機制。一是內生型情感補償,是基于受眾內在生理和心理機制之上的一種心理傾向和性格特征;二是外源性情感補充,通過有形或無形的品牌資產作為誘因,在企業的空間搭建與感官營銷等外部刺激物中將個體的記憶帶入產品或服務。
(二)新媒體賦權懷舊消費結構化擴張
在新媒體的加持和大眾對文化需求升級的環境下,城市成為懷舊型消費滋生的土壤,為其提供精神文化價值確立和互動的場域。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工業體現在文化產品的流水線生產上,而新媒體語境下這一模式呈現出“IP—泛娛樂的整合營銷”更加高級的擴張形態。相較于需要持續性內容生產與“輸血”的文化項目,懷舊型消費空間在生產和傳播上均有革新。一方面,新媒體語境下懷舊型消費空間在創造之初便將自身置于接受市場審視與檢驗的地位,將品牌資源轉化為規模性的經濟效益,使得“文化品牌”這一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有了充分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懷舊型消費空間以過去“單點式”經營為突破口,在此基礎上實現“結構式”規模化擴張。在遵循現代市場原則的前提下,有效調度政府資金與媒體資源,有序開發文化產品及其衍生品,有意搭建新媒體自有渠道,擴大品牌的互聯網聲量。
作為集餐飲、娛樂和觀覽功能于一體的商業空間,超級文和友是懷舊型消費空間的典型代表。2019年,這一商業綜合體脫胎于老長沙油炸路邊攤,在長沙海信廣場盛大開幕。超級文和友以還原市井煙火氣和維系人文底色為宗旨,僅用1年時間便將其觸角伸向廣州、深圳,創始人表示有望于2021年末啟動包括重慶、上海、天津、北京在內的超級文和友。迅速擴張的背后,卻被打上“性價比不高”“裝修沒誠意”“不能代表廣州本土文化”的標簽。隨著客流量銳減、“流量冠軍”茶顏悅色的撤離以及接二連三的餐飲商戶搬遷,曾經號稱要“定義全國人民煙火氣息”的超級文和友如今面臨著尷尬的境遇,無論是深圳文和友還是廣州文和友,都沒能逃脫“曇花一現”的命運。
二、懷舊型消費空間的生產之虞
從文化工業理論視角來看,懷舊型消費空間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和操控性。欺騙性是指通過不斷地對消費者進行說服和許諾,為其營造懷舊空間的假象以麻痹消費者;操控性則是將原本內涵淺薄的產品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并當作合理的模式灌輸給消費者。
(一)符號嫁接:情感異托邦的打造
在本雅明看來,城市是消費文化審美幻象的滋生地。在這里,“各種各樣的陳列商品的巨大幻覺效應經常被轉化為資本家和現代主義者的一部分尋求新奇的動機,成為夢幻影像的源泉。”③隨著城市成為文化消費的主陣地,懷舊型消費空間成為具有符號意義的隱性消費品。為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懷舊型消費空間通常會忽視與其文化屬性配套的空間環境,多選址在客流量可觀的繁華商圈。自我標榜為“市井文化博物館”的超級文和友,將“戶外”裝進“室內”,以長沙海信廣場代替市井文化的“原生家園”長沙街頭巷弄,使之淪為城市文化的附庸。超級文和友的店面裝修會有意營造破舊粗糙的氛圍,例如,采用早已被淘汰的馬賽克瓷磚、老式燈箱店招牌、處處可見的吊燈和八仙桌,以期將參觀的游客拉入生產者打造的“市井街頭”。而市井文化,這一屬于個體性靈感的審美烏托邦和文明的避難所,卻在高樓大廈間通過懷舊物什的堆砌喚起人群的懷舊之心,“在眼花繚亂的符號的嫁接或掩蓋下,竭力描繪一個割裂現實社會的現代性‘異托邦’。”④
(二)偽個性化:淺薄內涵產品的復制
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曾指出,音樂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使用音樂器材和滑動音技巧——甚至沒有任何意義和美感。某些產品一旦取得成功,就會在文化工業下被大肆渲染。懷舊型消費空間正是如此,由于生產方多為本土新生企業,在沒有足夠深厚的文化底蘊支撐的前提之下,產品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受到現實因素和客觀情況的限制。以超級文和友為例,在長沙店推出與長沙話相關的展覽與市集,在廣州店推出“講什么——廣州語言觀察展覽”“‘廣州城相’許培武影像展覽”,表面上做到了本土文化的滲透,似乎是以差異化的文化重構吸引不同地區的消費者,但實際上都是地方方言的露出和模式化復制。懷舊型消費空間本身及其產業鏈下游的展覽、戲劇、市集多是一次性的,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衍生周邊產品在沒有周期性沉淀的情況下被大規模生產。在商業價值成為產業追逐的唯一目標下,文化產品的藝術風格日漸消失,大眾的審美意識逐漸弱化,解讀能力不斷退化,最終只剩下機械的物質娛樂感官⑤。超級文和友吸納紛繁多樣的市井生活,在文化工業的揉碎、拼湊下變為僅具有抽象屬性的商品,使之成為無法“反魅”的貨物。
(三)消費異化:人與社會文化的危機
在現代,消費不再是純粹為了滿足人的生活需要,而是人們借助商品符號試圖展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超級文和友構建的商業邏輯里,20世紀80年代的市井生活被消費者審美化,成為被消費的一部分。從根本上看,人們不再消費物質產品,而是消費符號。一方面,不斷加劇的現代化讓人們直面生活的乏味和枯燥,過去的愉悅和幻想無法被追隨與感知。因此,創始人文賓將個體的懷舊情結與社會的懷舊現象加以聯結,使消費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懷舊符號也成為自我身份的彰顯,進而符號消費的過程也可以看作是自我消費的過程。另一方面,超級文和友的懷舊符號可以為消費者消除不安,使之“在符號的掩護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況下生活著,奇跡般安全”。當過去的美好不再存在時,人們將自身對意境的追求轉換為對懷舊符號的消費,從不斷的“購買”行為中產生安全感。
三、懷舊型消費空間的傳播之困
在傳播層面,懷舊消費的空間性傳播可以更多地吸引到熱衷于打卡的年輕群體,也決定了一般懷舊消費的核心受眾是外地游客,其消費多是一次性的。而就時間性傳播來說,長期的網紅屬性與非持續性的生產能力導致懷舊型消費空間無法深耕本地用戶。因此,懷舊型消費空間的空間性傳播與時間性傳播實際上是不對等的。
(一)產消合一:虛擬空間傳播者剩余價值被資本壓榨
同多數形態的文化產業一樣,超級文和友的傳播可概括為“實體空間+虛擬空間”雙管齊下:實體空間表現為文和友臭豆腐博物館、文和友美術館得以實現跨越時間的傳播,虛擬空間則表現為“兩微一抖”的渠道建設和小紅書、知乎等平臺賬號的運營。超級文和友享受了許多新媒體為它帶來的紅利,通過一則則“市井文化博物館”“帶你回到80年代”“老長沙人的共同回憶”的高贊回答與帖子,打出感情牌,一躍成為網紅打卡的新寵。但是在爆紅的背后值得思考的是,大眾媒介通過“種草文案”將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合二為一,人們在消費后自發、無償地進行創作,實際上附加的行為被平臺資本當作商品。通過社交媒體,依靠大眾的消費行為,向大眾傳輸文化與意識形態,這種方式已成為注意力經濟下的“利器”。
商品的符號價值必須借助大眾傳媒傳播才能形成,因此,大眾傳媒成了推行消費主義話語的得力助手。大眾傳媒的鼓吹和渲染加大了符號消費的誘惑力,廣告制造了商品符號的幻境,“激起每個人對物化世界的神話產生欲望”。與產品廣告不同,超級文和友的廣告聚焦的不是商品實體本身,而是重在渲染20世紀80年代的市井氛圍,將信息當作商品去賦值。例如,“老長沙的柴米油鹽”“五講四美三熱愛”,通過拼貼高意向的城市符號,形成構圖場景化和儀式化,成就了一場喧嘩的、炫耀的、釋放消費欲望和快感的表演儀式。消費社會下商品源源不斷地生產,與此同時,廣告也許諾可以“通過觀覽與消費重回上世紀80年代”。盡管消費者已經“看穿”了廣告的套路與伎倆,但出于對自我彰顯和安全感的考量,依然會選擇參與整個消費過程。
(二)個體游蕩:懷舊型消費空間全球化風潮和地方性抵抗
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本身在操縱大眾的嘗試中,已變得與它想要控制的社會一樣內在地含有了對抗性⑥。文化工業中也蘊含著大眾抵抗與批判的積極潛能,“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含有自己謊言的解毒劑。”
在“十四五”政策背書和數字技術賦能的“兩輪齊驅”下,中國文旅發展進入4.0時代,懷舊型消費空間在全球掀起熱潮,是引領文化產業未來發展的熱點方向。然而,在懷舊型消費空間全國擴張戰略實施的過程中,“單一模式”卻被認為不再適用,甚至出現地方性抵抗行為。首先是地方消費者的抵抗。自超級文和友發軔以來,其發展軌跡便與長沙這座城市深度捆綁,造成后續城市很難與超級文和友這一“外來品牌”產生強關聯,消費者難以產生強黏性。例如,廣州文和友力圖打破桎梏,“一城一策”地推出廣州茶點,卻被廣州本土消費者稱“形似而神不似”,背離了講究務實精致和“平靚正”的廣州飲食文化,實際上還是“長沙模式”的翻版再利用。其次是地方商家的抵抗。擴張的文和友一直打出“招商三定律”旗號,即入駐的商家必須有十年資質,是生意好的非連鎖店。而在廣州、深圳具備以上條件的商家已具有一定的區域影響力,為何要再加盟超級文和友,去面對一系列未知的風險挑戰與競爭威脅?
四、基于懷舊型消費熱潮的理性思考
在現代化信息社會越來越仰仗創意與風格的前提下,懷舊消費面臨著潛在危機:由于被利益與資本裹挾著,懷舊消費逐漸與“重現經典”的初衷和藝術價值背道而馳。隨著流水線生產和工業化傳播愈演愈烈,懷舊文化將淪為千篇一律的文化工業產品。
(一)流水線生產損害“光韻”
法蘭克福學派的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時代之前的藝術充滿了“光韻”(aura)。超級文和友將原本不堪盈握的虛空和轉瞬即逝的體驗以工業復制的形式留存,受眾原有的“留白”被各式社交媒體的“種草”、打卡填充,文化參觀活動變成異化的勞動延伸。通過空間搭建重現市井文化不是“光韻”的復原,只是“拾荒者”進行“自我救贖”的努力嘗試。在工具理性凌駕于藝術價值的情況下,懷舊消費空間放棄挖掘原本的文化內涵,而是選擇效仿好萊塢的生產流水線。超級文和友在廣州的發展策略與長沙如出一轍:選取當地特色建筑作為載體,搜集當地具有懷舊因素的老物件堆砌在商業綜合體中,依據“招商三定律”選拔當地小吃。這時的懷舊文化已經蛻變為“物化”的文化。縱觀懷舊型消費空間,多數都只是“馬賽克式”拼貼的景觀符號。
(二)“大規模定制”泯滅個性
“大規模定制”是數字信息時代文化工業產品的新型生產方式,為了應對逐漸細分的受眾市場,凸顯定制的“個性”與風格,更具迷惑性⑦。整個懷舊型消費空間產業鏈按照“后福特制”式商品市場的邏輯運轉,源源不斷地遵循模式化公式去生產個性化內容與消費品。超級文和友的底層邏輯附著文化變現,而文化變現又是依托城市戰略的。當開拓新的城市店面時,超級文和友針對地方消費者采取“類長沙模式”:將外形打造為當地風格的建筑以期喚起共鳴,利用“招商三定律”吸引地方特色小吃,開展當地方言主題大觀與展覽會。在此情況下,文化活動儼然成為一種有序的歸類活動。
“大規模定制”實際上仍是對個性和創造性的扼殺,是虛假的“個人主義”,將被意識形態標準化了的情感承載在文化傳播產品之中,并將其作為大眾的消費對象。包括超級文和友在內,懷舊型消費空間的廣告幾乎都會模糊產品本身,很少會提到他們所供應的餐飲或是文創商品,取而代之的是對老一代記憶的描摹,這也使得廣告在任何地區都可以適用。
五、結語
文化工業下的懷舊文化正在通過地方缺乏真實性的擬仿、“大規模定制”和千篇一律的“種草”傳播來實現對消費者的蒙蔽與操控,消費者的私人閑暇空間也由此被技術世界的現實侵犯和壓縮。然而,真正的懷舊文化不應將全部動機都放在對利益的追逐上,而應是有溫度、有價值且能滿足受眾需求的藝術。文化工業環境之下的懷舊型消費空間雖然代表全新的文化表達形式,但其本質上仍是人類文明發展與前進的一環,需要我們理性看待,挖掘文化中真正可視、可感的價值。
注釋:
①劉金風,吳寧.論當代中國青年的流行文化——基于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3(04):29-34.
②Bonnett A.Left in the past:radic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M].London,UK:Bloomsbury Academic,2020.
③[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劉精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33.
④福柯,王喆法.另類空間[J].世界哲學,2006(06):52-57.
⑤李小華,祝琳婷.文化工業視域下的IP電影熱潮思考[J].中國出版,2016(18):28-31.
⑥[美]馬丁·杰.阿多諾[M].瞿鐵鵬,張賽美,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59.
⑦郝雨,郭崢.傳播新科技的隱性異化與魔力控制——“文化工業理論”新媒體生產再批判[J].社會科學,2019(05):17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