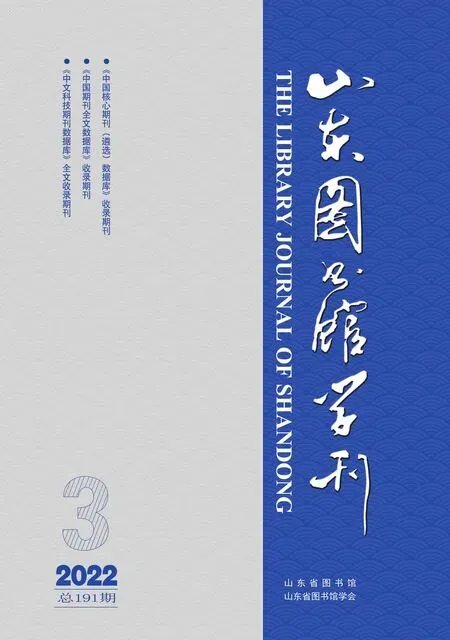阿英與膠東圖書館
唐桂艷
(山東省圖書館,山東濟南 250100)
阿英(1900-1977),錢杏邨的筆名,原名錢德富,安徽蕪湖人。 192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與蔣光慈等組織太陽社,宣傳革命文學。 1930 年當選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常委。 抗日戰爭期間,在上海從事救亡文藝活動。 1941 年應陳毅之請去蘇北參加新四軍革命文藝工作。 1947 年4 月任中共華東局文委書記。 建國后任華北文聯主席,中國文聯副秘書長。
阿英是中國現代屈指可數的大藏書家,被認為僅次鄭振鐸一人。 他一生愛書,即使在戰斗激烈的歲月,也總是擠出時間訪書、購書。 自1947 年初,他隨北撤部隊進入山東魯南山區,到9 月26 日離開山東抵達大連,在山東九個月時間內,他一路訪書、購書,與山東結下了不解書緣。 其中,最大的收獲,莫過于兩次到訪膠東圖書館。 在此,他見到了山東解放區最大的專門圖書館,這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圖書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為這個館做了很多工作。
1 筆墨勾勒膠東圖書館概貌
創建于炮火硝煙中的膠東圖書館,是山東共產黨人創辦的山東最早、最大、最具特色的圖書館,它以收集根據地的新舊圖書、文物為目的,保存了大量的珍貴文獻和革命文獻,在山東革命發展史、山東圖書館發展史、山東文物保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關于膠東圖書館的歷史資料,至今能夠見到的、唯一較為全面的,即是阿英《敵后日記》①阿英:《敵后日記》,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年8 月第1 版,后收入《阿英全集》第12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7 月第1 版。中的記載,他以一個訪書者的身份,記錄下了1947 年6 月間膠東圖書館的情況,雖然是相對隨意的散記,但足以讓我們一窺其當時的盛況,也為我們解決了諸多關于膠東圖書館的疑惑。
1.1 關于創建時間
關于膠東圖書館成立的時間,查檢資料,共有四處記載。 《山東省志·山東文物事業大事記(1840-1999)》:“(1943 年)10 月,中共膠東區黨委、膠東行署成立圖書館,任命王景宋為館長。 其任務是收集根據地的圖書和文物。”[1]《山東省新編地方志總目提要》“山東省志文物志”條下[2]及于芹、張媛《山東博物館藏甲骨述要》一文[3]亦同此說,即1943 年10月成立。 阿英亦有記載。 阿英1947 年6 月訪膠東圖書館,在與代理館務的倪同志交流后記錄:“該館成立于一九四三年。”[4]未說明具體月份,只確認1943 年成立。 作為日記資料,這個時間是可靠的,只是不知前三條來源何處,應該有更確鑿的證據。
1.2 關于館址
膠東圖書館初創于棲霞,具體位置不明,未見任何資料談及。 在阿英訪館之前,尤其是日軍投降前,膠東區黨、政、軍各機關為了應對日偽軍的瘋狂反撲頻繁遷移辦公處所,像1944 年3 月開始,膠東區行政公署就經歷了乳山田家村——乳山馬石店——海陽北申家——棲霞方格莊——海陽取水崖——海陽郭城——萊陽城西南楊家疃村(均為現縣屬)的數次遷徙,由膠東區委、行政公署聯合成立的膠東圖書館有沒有遷移? 當時的各報社印刷廠均能夠驢馱馬擔、車輪滾滾地負輜重輾轉遷徙,何況膠東圖書館初創之時,藏書不可能太多,加之長期革命斗爭的經驗——“就地埋書”,遷移不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膠東圖書館到底曾走過哪些地方? 現知有兩處記載,一是阿英日記中記錄的海陽西魯家夼,時在1947 年6 月;一是《山東省志·山東文物事業大事記(1840-1999)》中記錄的棲霞陶家夼,時在1947年秋季①按:山東省文物事業管理局編《山東省志·山東文物事業大事記(1840-1999)》第79 頁記載:“(1947 年)秋,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 膠東區行署為確保文物安全,事先抽調干部、民兵,將文物裝成 300 余筐(箱),從棲霞陶家夼取出,人抬、肩挑、車推,轉移至海陽縣安全地帶。 國民黨軍隊進攻失敗后,局勢趨于緩和,又將多數文物運至乳山縣司馬莊保存,另一部分隨行署機關轉移到萊陽縣河頭店村。1949 年春,兩部分文物又集中到萊陽縣沐浴店統一保存。”。
西魯家夼村位于海陽市東北部,在與棲霞接壤的群山之中。 此村向南十里為郭城,再向南十五里是戰場泊,戰場泊向南八里即膠東行署所在地湖西村。 時阿英住萊陽夏格莊,西約十里為省文協駐地北張夼,西北約十里為膠東文協駐地石硼,石硼正北約五里為膠東區黨委駐地石橋夼。 阿英第一次訪館,即是從區黨委石橋夼出發的,先是沿沙河東北十里上公路,至野侯(野后),再行十五里至徐家店,“飯后向東南,七里至侯家,下山時,四面如花壇,風景極佳。 有盲人聯合會人在此作宣傳。 旋即入崎嶇山道,又凡十八里,數過山,到一小莊,在此煮茶,因天甚熱。 又四里,到西魯家夼——圖書館所在地(小莊名姜家)。”[5]這是所謂的“西路”。 阿英回駐地時走的是“南路”,即由館里向南行二十里至戰場泊,西行七里至姜家(北姜格莊),再西行十五里至發城,再西行九里至夏格莊村。 第二次訪館,阿英是南路去,西路回。 阿英一日步行五十里,其中的崎嶇山路十八里,要過數山,可知西魯家夼村的地形地勢確是易守難攻的,膠東圖書館的藏書在此應是非常安全。
1.3 關于館舍
阿英首次訪館,先是參觀,他見到了圖書館有八間屋子。 第一、二、三、五四個房間,全是舊書。 另有新書一室,雜志一室,報紙一室,又裝訂一室。
在阿英記載的圖書整理過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舊書是以經、史、子、集、叢分藏在四個房間的。第一室存經部、叢部書,內有《自警編》及明版書數部;第二室存史部書,內有不少地方志和金石類書,有《岱史》及明版書數部,有《明狀元圖考》《語石》《國朝經籍志》,還有部分劉鶚的藏書;第五室存子部、集部書,子部書有嘉靖本、萬歷本《藝文類聚》各一部,《太平御覽》日本影宋刻本一部,清嘉慶鮑崇城刻本兩部,還有《桃花影》《茶經》《留青日(扎)〔札〕》《金瓶梅》等,集部書中清刻本佳者較多。 阿英整理的主要是第二室、第五室,時第一室由王昆玉老先生在整理,未言第三室之事,據館藏品類及阿英小兒子錢厚祥整理過書畫、碑帖,猜測第三室存的是書畫、碑帖。
1.4 關于人員與管理
關于膠東圖書館的人員設置,大多數只提到館長為王景宋。 或創館初期,工作人員寥寥無幾。 我們從阿英記載中了解到,其兩次訪館,王景宋館長均不在,有一倪姓女同志代理館務,第一次見到了萊陽人王昆玉,第二次拜訪過曲姓、徐姓二位工作人員。知1947 年時,館里的工作人員至少為五人。
從阿英日記中透露出的若干訪書流程,我們知道,膠東圖書館的古書不是想看就看的,要有膠東行政公署的介紹信。
阿英兩次訪館,均由膠東行署出具介紹信。 第一次是1947 年5 月26 日阿英訪膠東軍區司令部金政委,由金政委作介紹書給行署主任曹漫之,講阿英欲參觀膠東圖書館[6]。 5 月31 日,阿英至膠東區黨委教育科李濟民科長處,取得行署所寫膠東圖書館介紹信[7]。 第二次,也是8 日提前至區黨委李科長處,請其向行署要介紹信,陪吳秘書長等往圖書館,10 日由“李科長送介紹吳秘書長等往圖書館參觀函來”[8]②按:吳秘書長即吳仲超,時任中共華中分局秘書長。。 可知,在閱書這方面,膠東圖書館是有嚴格規定的,與今天的古籍閱覽制度有相合之處。
1.5 關于藏書數量與質量
膠東圖書館到底存了多少書? 有多大的規模?具體有哪些書? 由于膠東圖書館很少在舊書上鈐蓋館藏章③按:鈐“膠東圖書館藏書之章”的古籍,目前所見僅一部:清何秋濤撰《朔方備乘》,清刻本。,多在新出版的革命文獻中鈐章,故其藏書數量、質量無法得知。 而這些,阿英日記中都有詳細記載,這是對膠東圖書館藏書數量與質量的唯一記載。
先說數量。 阿英經與代理館務的倪同志交談,并據1946 年底館里所作的總結,記下膠東圖書館的書刊藏書總量有110253 冊,其中舊書82397 冊,新書21064 冊,舊刊物3379 冊,新刊物3453 冊。 報紙有32 種450 本。 輿圖127 份。 金石拓片千余份。古物三,包括造像一、漢瓦二。 書板有二十余種。 另有照片、戰時郵票、宣傳畫等,未作統計[9]。 這大概是膠東圖書館最盛時的藏書數量。
關于藏書質量,阿英筆墨間透露得最多。 當時,阿英之子錢厚祥所整理的書畫中就有高鳳翰、何焯、阮元、翁方綱、許瀚、左宗棠等名家書畫精品。 關于三箱碑帖,“皆大漢碑,無舊拓本,然草草檢視,可能遺漏也。 有唐伯虎所繪張仙像拓本,原拓甚精”[10]。
其實,阿英去膠東圖書館的主要目的,是看善本書。 所以,在他筆下的舊書,全部是珍稀版本。 其中,明本有《藝文類聚》《岱史》《殊域周咨錄》《弗告堂集》等,稀見本有《留青日(扎)〔札〕》,此書“刻本甚稀——在滬僅見到振鐸買有此書抄本”[11],同樣在上海未見過的還有一部《永樂大典》書目。 阿英所見抄本《亳州牡丹史》四卷,明薛鳳翔撰,此書現存版本并不多,南京圖書館、蘇州圖書館有明萬歷間刻本,國家圖書館有清初刻本,北京師范大學有清抄本,吉林省圖書館有清末抄本。 對于清刻本,阿英認為“佳者較多”:“《玉蟾集》內刻像,《離六堂集》插圖卷,都極佳。”[12]
2 辛勤編纂膠東圖書館善本簡目
阿英兩次到訪膠東圖書館,數天時間,過眼數萬冊古籍,邊看邊挑選善本,最后為圖書館留下了一部善本簡目。
阿英第一次在膠東圖書館呆了整整四天,除去參觀及交流時間,真正的整理圖書有三天時間。 第一天整理子部書,邊挑邊著錄。 接著整理集部書,先挑選,后著錄了一部分。 當日,經部書、叢部書亦著錄精本完畢。 第二天由整理地方志開始,中午即告結束,發現一批劉鶚的藏書。 下午繼續著錄前一天集部未著錄完的書。 第三天查漏補缺,并看了書畫、拓片。 當晚,“燈下,整理完本目錄初稿,次序尚未排定,明晨還須再寫一過,始克交付圖書館。”[13]第四天一早,“晨起,謄寫善本簡目,交與圖書館。”[14]完成善本目錄的編纂后,阿英始起身回程。
回住處后,阿英為了完善這本書目繼續做了很多工作:
第2 天,“午飯后,將善本目分類粘貼,后又整寫,迄晚不完。”[15]
第3 天,“晨起,續抄書目。”[16]
第4 天,晚上,“燈下,續抄善本書目,不完。”[17]
第5 天,“晨起后,領報紙十張,補整書目,迄十時寫完,裝訂成冊,以備帶至圖書館校正。 私意如將清本并整一個,可成一卷完整書也。”[18]
以上可以看出,從6 月1 日至9 日,阿英一直在作膠東圖書館的善本簡目,無論是在館內還是回到住處,他利用的都是早晨、午后、晚上的時間,可見其用功之勤,亦見其責任心所在。
第二次去,阿英呆了兩天,分別在地方志室、集部室發現《岱史》《弗告堂集》等珍本及明版書數部,第二日亦在叢書室發現明版本數部,并自廢書中檢出書目兩部,似劉鶚手筆,一題《六一閣藏書目》。 當日晚上,“燈下,整理此番所發現明版書目錄。”[19]
這應該是膠東圖書館的唯一一部善本目錄。 在這之前,藏書家黃縣杜明甫、萊陽王昆玉均受聘整理館藏,大概是對全部圖書進行初步分類、著錄,尚未形成館藏目錄①按:王昆玉后來在山東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期間有《線裝書籍分類表》一書,孫鵬翔抄本。 此書書衣墨筆題:“文管會王昆玉依江蘇圖書館目修,文史館孫鵬翔錄。”從此書可知,王昆玉精于古書的分類。。 阿英編纂的是膠東圖書館的館藏善本目錄,是一部分精品。 對于這個善本目錄,世人少知,那世平《阿英書目成果梳理研究》一文亦未談及。 從阿英的日記中,我們可以得知,此目錄應該有兩本,一在膠東圖書館,未完善本,即未修訂,亦未補充第二次發現的明本。 另一本即完善本當在阿英手中,但目前,此二本均未找到,實屬遺憾。
3 面談函書留下寶貴意見
阿英是一位革命的藏書家,黨交給他的任務之一便是搶救古籍、文物,戰火中的經歷,讓他不僅對書有發言權,更對圖書館有相當的思考。
早在上海“孤島”時期,阿英就在北京路一家通易信托公司大辦公樓陰暗的地下室里主持編纂《文獻》月刊,發表抗戰救國運動的各式文獻,包括從地下黨電臺傳送來的延安資料,樓適夷認為這是“在孤島與最大敵后根據地之間裝上一條熱線。”“他辦公室墻邊堆了一大堆線裝書,我翻翻,全是唐五代宋元明清的詞集。 他低聲說:‘這是延安毛主席要的,專門收了給他送進去的。’”[20]
阿英的老書友王松泉回憶說:“一九三八年,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從延安輾轉帶來毛主席的一封信……是托阿英代買一些古典詞曲的書其中有開明書店出版的汲古閣本六十種曲。”[21]有些書一時買不到,阿英從自己的收藏中補齊了不少。
阿英從孤島到蘇北后,在隨部隊流動的五年中,戰火中搶救的文物、古籍、書畫,都跟著他一起流動,“十輛八輛雞公車,吱啕吱啕跟他在一起‘跑反’。”[22]
抗戰勝利后,阿英對圖書館的建設有了更強烈的意識。
1947 年5 月1 日,他在赴膠東路上,因思念在鹽阜犧牲的大兒子錢毅,計劃“擬集大眾文學書數萬冊成一‘錢毅圖書館’,以紀念之”[23]。
5 月2 日,他到達諸城相州,晚間起草工作規劃,《關于研究工作》:“為著保證研究材料的充分,及不散失,必須健全資料室的組織,并進行科學管理,以免散失。 也必須宣傳部給予必要書籍、期刊、報紙之經費。”[24]此時,是他剛任中共華東局文委書記不足十日。
6 月18 日,阿英第二次從膠東圖書館回來后,就想到“厚祥可創一農村圖書館”[25]。
阿英這種對圖書館的重視,一直延續至建國后。1956 年,“阿英同志倡議文聯成立專門的文學藝術圖書資料館,周揚同志和我都支持他。 他為此約各協會的有關同志開過會。 他提出要自己擔任館長,并把他珍藏的圖書資料捐獻出來。”[26]
阿英這種對書的鐘愛,對圖書館的鐘情,從一進膠東地界就可看出。 1947 年5 月9 日,在古峴,“地主家沒收字畫古董,聞大都在膠東行署——在區黨委附近。 如有機緣,頗想一看。”[27]這里說的就是由膠東行署主管的膠東圖書館,當時膠東解放區還有膠東山區圖書館、區黨委圖書館、膠東軍區圖書館,但所藏皆為新出版的書。 在日記中,阿英記載曾到訪國防劇團資料室,對于區黨委圖書館,只記載了“離此(按:區委)二十余里,有書二萬余冊。”[28]以收藏晚清文獻為主的阿英,其最大的興趣當然在膠東圖書館的舊書。
第一次到館時,阿英便與代理館務的倪女士交談,從她口中得知膠東圖書館的館藏數量、館藏品種,以及該館的歷史,知舊書來自膠東有名的藏書家杜明甫。 不知二人交談的內容還有哪些,只是在6月9 日的日記中,他記道:“午后,函金政委,轉倪同志信,并說明對圖書館意見。”[29]想必是倪女士寫了一封信給膠東軍區金政委,阿英在代轉時亦表達了對圖書館的意見。
阿英在訪書之余還與館里工作人員交談。 第一次去,是與萊陽王昆玉老先生談。 王昆玉 (1890-1969),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先后任省立六中、省立女師、萊陽中學、蓬萊八中、山大附中、煙臺八中等十余處學校的國文教員,在山大附中時,季羨林是他的優秀學生。 1946 年6 月任膠東圖書館職員。 1952年,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任圖書組組長。 1953 年8月,被聘為山東文史研究館館員。 兩人相見時,王昆玉在第一室整理舊書,阿英稱其為“參議員王先生”,想必王昆玉曾當選膠東區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在阿英離開膠東圖書館前一天的晚上,兩人曾有過一次交談。
第二次到館,也是在離開的前一晚,“圖書館同志們來談,十一時辭去。”[30]由于日記記載不詳,我們無法得知阿英與王老先生、同志們談至深夜的內容。
返回的第二天,阿英寫了一封詳函,給當時的膠東行署主任曹漫之,談圖書館工作問題,約四千余言。
阿英之所以給曹漫之寫信,因為他知道,曹漫之是一個懂書的人。 曹漫之(1913-1991),山東榮成人。 膠東根據地的重要領導者、建設者。 他在榮成縣立一小任教員時,在師生中大量推薦魯迅、郭沫若、茅盾、蔣光赤、殷夫及其他進步作家所著作的小說、詩歌、論文給大家讀,“還傳播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綱》、陳豹隱翻譯的《資本論》,在這之前還成立了一個地下圖書館。”[31]在榮成民眾教育館夜校任教員時,通過館員李耀文,他們“用民眾教育館的經費購進了大批的進步刊物”[32]。 曹漫之不僅懂書,還對圖書、文物有正確的認識:“早在抗日戰爭時期,膠東行署主任曹漫之就作過指示:在斗地主和打敵人時,得到的浮財可以分,但文物圖書不能分,因為那屬于國家資財,并成立了膠東圖書館和膠東文管會。”[33]
面對膠東圖書館的創辦者,對于如何辦好這個館,阿英肯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 所以盡管不知此函的具體內容,我們亦可以想見阿英的意見絕對是中肯的,比如,他就認為館里有關膠東材料的新書不多:“新書——特殊是膠東材料甚少。”[34]
4 盡情享受文化盛宴
對阿英來說,膠東圖書館可謂是山東解放區的文化寶庫,8 萬多冊的古舊圖書,在當時的延安以及其他解放區,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存在。 在館數日,阿英如饑似渴地抄錄珍稀資料,盡情享受這場文化的饕餮盛宴。
阿英所抄之書有《留青日(扎)〔札〕》《桃花影》《牡丹史》《殊域周咨錄》,以及《岱史》第十三卷《香稅志》約三千言,《弗告堂集》中《金陵花品詠》一卷,劉鶚《六一閣藏書目》中的宋元明部分。 我們從他安排時間之緊湊,可知其對這些書的渴望:
第一日,借《留青日(扎)〔札〕》回住處閱錄。晚飯后,燈下讀《留青日(扎)〔札〕》盡。 第三天晨,摘抄《留青日(扎)〔札〕》盡。
第二日,從第五室的子部書發現稀見本《桃花影》傳奇,午后,著錄《桃花影》傳奇,至二時,不完。歸后,繼續閱抄《桃花影》材料,至晚畢。
第三日,發現《牡丹史》抄本一部,乃借回著錄。飯后借佛曲歸,就燈下與厚祥、小惠等著其曲牌名字,至十時許,未完而寢。
第四日,侵晨起,繼續摘抄佛曲曲牌名完,又選出兩篇作品,交小惠抄寫。 早飯后至第五室進行著錄工作。 做《孝順事實》材料筆記,到午未完,帶回續記完。 午后,至第一室找王老先生,借《自警編》作筆記。 完后復至第五室,找遺漏材料,便錄數則。 借《明狀元圖考》及《茶經》歸作札記,至黃昏時摘錄終結。
第二次去:
第一日,抄《岱史》第十三卷《香稅志》約三千言。 因為此卷“為后來所無,并可見當時剝削情形”[35]。 午后,在集部室,發現“《弗告堂集》中有《金陵花品詠》一卷,頗冷僻,亦將其抄出,至晚而盡。 借《殊域周咨錄》歸,燈下擇抄。”[36]
第二日晨起,續抄《殊域周咨錄》不完。 上午在叢書室,“自廢書中檢出書目兩部,似系鐵云手筆,一題《六一閣藏書目》。 不及全抄,乃錄其中之宋元明部分,成《六一閣藏宋元明善本書目》一卷。 將來如有機緣,擬借其全帙錄之。”[37]午后,“乃就清華圖書館增刊一——二〇〇期中,錄其不經見曲子數種目,并將《周咨錄》材料錄完,歸去。”[38]
阿英不分晝夜地抄書,可以想見膠東圖書館藏品的特點與質量,想見這座寶庫對讀書人的作用。阿英在享受膠東圖書館提供給他的文化盛宴的同時,筆墨流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藏書家眼中的圖書館,一個由共產黨人創建的以收集古舊圖書為主的圖書館,一個兼具博物館功能的圖書館。 阿英日記中留下的這些珍貴史料,不僅為進一步全面研究膠東圖書館提供了基礎材料,也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戰火硝煙中搶救文物、為保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