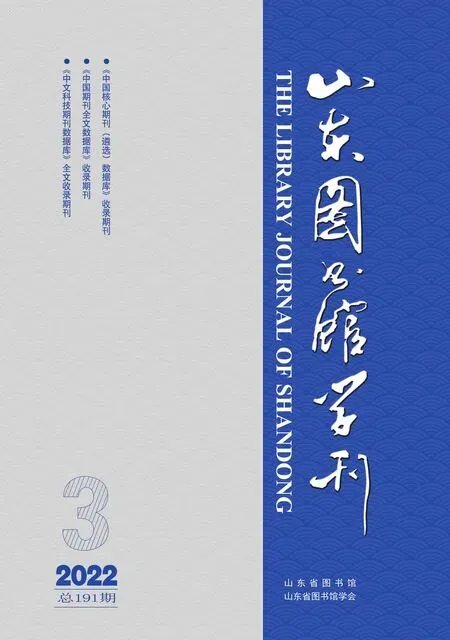國外圖書館數字人文館員能力素養(yǎng)要求及其啟示
齊維穎
(福建省圖書館,福建福州 350001)
隨著數字中國的加速構建,“數字人文”成為近幾年的研究熱點之一,展現出廣闊的發(fā)展前景。2021 年3 月,我國在“十四五”規(guī)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指出,要推進“公共服務機構資源數字化,加大開放共享和應用力度。”2020 年,中國人民大學信管學院開始增設二級學科數字人文。 在第一屆全國數字人文年會成功舉辦后,2020 年第二屆中國數字人文年會吸引了眾多國內外知名學者參會。 與會期間,在專設的“館長圓桌論壇”上,各地圖書館館長們就如何深化與人文學者的合作以及促進中華文化傳承的問題積極獻言獻策,達成“圖檔博機構應在數字人文研究領域中占據明顯地位”的一致共識。 圖檔博機構是數字人文基礎設施的主要構成,數字人文館員的服務能推動這些設施更好地開放。 因此,借鑒國外培養(yǎng)數字人文館員的成功經驗,可以承前啟后,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的數字人文館員隊伍建設。
1 相關概念與國內外研究述評
1.1 數字人文的發(fā)展
數字人文實踐最早始于1949 年意大利神父羅伯特·布薩組織的《神學大全》的數據庫建設,互聯網的出現使其進入了加速發(fā)展階段。 21 世紀初,學界開始進行大量相關研究。 隨后,國外不少知名高校,如哈佛大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都開設了數字人文專業(yè),使其成為獨立的學科。1989 開始,越來越多的國家積極參與一年一屆的國際性會議——“數字人文年會”,這是該領域“最知名的國際性學術會議”[1]。 2019 年,“中國十大學術熱點”評選更是將數字人文研究列入其中。
國外對數字人文最早的定義是美國學者Smith Rumsey 提出的“利用數字證據和數字查詢、研究、出版和保存的方法來實現學術研究目標”。 國內學者賴茂生在《數字化時代圖書館發(fā)展六問》中提出相似觀點——“數字人文就是人文科學領域利用數字化的技術手段開展學習研究等”[2]。 利用數字技術手段對館藏文獻和歷史資料進行加工處理并予以保存利用,已經成為一種發(fā)展趨勢,同時這也是圖書館進入新的數字化發(fā)展階段,為讀者和社會提供新型知識服務的基礎。
1.2 數字人文館員的研究
在數字人文館員的實踐方面,高校圖書館比公共圖書館更早開始發(fā)展,尤其是美國的高校圖書館在培養(yǎng)數字人文館員的實踐上處于領先水平。 2013年國際圖聯就已把數字人文納入圖書館研究的重要方向;2016 年,數字人文已成為全美大部分學術圖書館的研究新趨勢。 根據李國剛等人統(tǒng)計,到2018年8 月,數字人文館員占全美圖書館員的平均比率已達到35.1%[3]。 國內學者葉煥輝發(fā)現,我國的高校圖書館中,武漢大學和臺灣大學兩所高校最早開設數字人文中心[4],現在南京大學等個別高校也開始設立類似的研究中心。 蘇敏、許春漫發(fā)現,目前國內有招聘數字人文館員的圖書館尚屬少見[5]。2017 年9 月,武漢大學圖書館率先公開招聘熟悉數字人文服務的館員,要求同時具備圖書館學和計算機及信息管理相關專業(yè)背景。
關于我國數字人文館員的研究狀況,筆者采用文獻調查方式了解,以主題詞“digital humanities”AND“l(fā)ibrarian”,“數字人文”AND“圖書館員”,檢索了中國知網、維普、萬方等國內知名數據庫(檢索日期:2022 年1 月26 日),發(fā)現我國第一篇關于數字人文時代圖書館員如何作為的文章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圖書館的周瓊、胡禮忠在2012 年發(fā)表的“圖書館員在‘數字人文’中的作為——‘2011 數字人文國際大會’后的感想”[6]。 可見我國對于數字人文與圖書館館員的研究始于2012 年,從2016 年開始相關研究有明顯增加,2019 年的相關研究發(fā)表量達到近三年的頂峰。 國內首位定義數字人文館員的是學者葉煥輝:數字人文館員是經過圖書情報專業(yè)培養(yǎng)的,具有深厚的理論知識與扎實的技術能力,能肩負起數字人文項目服務、館藏建設、數字人文技術培訓與專業(yè)教學等職責,了解學科研究前沿,有能力進行學術交流服務以及能擔負參考咨詢等工作的圖書館館員[7]。
筆者對檢索到的100 多篇文獻,逐一核對文獻內容,發(fā)現其中真正符合數字人文與圖書館員兩大主題詞的文章實際數量為120 篇,其年度發(fā)表趨勢如下:

圖1 文獻年度發(fā)表趨勢圖
關于國外圖書館數字人文館員的文獻共48 篇,在全部文獻中占40%;其中有41 篇文獻提及美國高校圖書館的范例,占海外圖書館數字人文實踐范例文獻的85.4%。 可見國外圖書館,尤其是美國高校圖書館在數字人文館員培養(yǎng)方面有不少值得我國圖書館借鑒之處。
2 國外數字人文館員培養(yǎng)實踐概況
圖書館的工作涵蓋了三個要素:書(知識信息資源)、人(知識信息受眾)、找(知識服務方法)[8]。國外數字人文館員的培養(yǎng)實踐,同樣可以按上述要素概括。
2.1 建設數字人文資源項目
國外數字人文館員參與的數字人文資源項目,涵蓋了藝術、歷史、地理等各個人文領域。 如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館員,在疫情期間仍積極將館藏的中國近現代史資源制作成數字音像資源,供讀者學習研究之用。 他們構建了線上虛擬的閱覽室;設計了一款同步索引軟件,可以檢索并聆聽口述史的錄音,這些元數據對于從事民國史研究的學者來說非常關鍵[9]。 法國國家圖書館與索尼集團等音樂發(fā)行代理商合作,將36000 多份唱片進行數字化,大大完善了近代音樂庫數字人文資源;和日本的印刷界龍頭公司合作,將55 份特藏世界地圖數字化,以3D 立體形式儲存。 此外,它還與其他歐洲國家合作,參與多項國際數字人文建設項目[10]。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選取本土特色人文資源制作新加坡數字美食數字地圖,用戶可以在使用界面直接看到該國不同地域的特色美食標簽,并可以通過標簽的顏色變化對同一美食在不同地區(qū)的價格高低一目了然。
通過建設數字人文資源項目,既鍛煉了數字人文館員的資源建設能力,又為后續(xù)進行數字人文服務提供資源儲備。
2.2 提升人文學者數字人文素養(yǎng)
人文學者是與數字人文館員合作交流最密切的用戶群體,也是數字人文館員的主要服務對象。 提升人文學者的數字素養(yǎng),有助于數字人文館員更好地提供知識服務。
2012 年,美國圖書館協會(ALA)率先對數字素養(yǎng)做出正式的定義:一種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去獲取、吸收、評價、傳播數字化信息資源的能力,并指出數字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需要概念學習和實踐操作兩方面共同進行。 同年,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協會(IMLS)斥資25 萬美元用于國家圖書館數字素養(yǎng)培訓計劃。到2014 年,接近九成的全美公共圖書館已經能夠提供常用計算機軟硬件服務,幫助人文學者更加便捷地研究[11]。 無獨有偶,歐盟在2013 年也制定并頒布了歐洲公民數字能力框架DigComp1. 0,2016 年更新至2.0。 它要求公民具備:①信息和數據的素養(yǎng)。 如瀏覽檢索和評估數字內容的能力,和管理數字信息的能力;②數字技術方面的溝通協作能力。如能夠將數字技術共享,進行互動合作,能夠管理自身數字身份;③數字內容創(chuàng)作能力。 如能開發(fā)、整合和重新配置數字內容;④保護數字安全的能力;⑤解決數字技術問題的能力[12]。
除上述的普遍要求,國外高校還重視人文學者數字學術能力的培育,包括信息獲取能力,運用技術能力和學術交流能力。 如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為在校師生提供校數字資源的指南,開展信息檢索的培訓,培養(yǎng)學生使用數字工具解決問題的能力[13]。 此外國外諸多知名高校成立了數字人文研究中心,提供一個更好的平臺,推動人文研究學者更好地將研究進展及時結合數字化手段分析保存[14]。
2.3 培育數字人文館員服務能力
許多國外高校圖書館會以設置專業(yè)數字人文機構的形式,組建并歷練一支專業(yè)的數字人文團隊。如密歇根大學早在1997 年就成立數字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 又如在耶魯大學圖書館的數字人文實驗室,該校的碩博研究生有機會獲得數字人文的教育培訓機會,也能將自己專業(yè)特長用于協助實驗室建設。 實驗室會開展工作坊形式的培訓,邀請專業(yè)學者指導館員提升數字人文的服務能力[15]。 據2007年成立的國際數字人文中心聯盟網站(Center Net)統(tǒng)計,到2021 年5 月,全球共202 家數字人文中心建立,絕大多數位于北美和歐洲國家[16]。
我國臺灣大學于2008 年成立“數位人文研究中心”[17],而大陸首家此類研究中心是2011 年5 月武漢大學的數字人文研究中心[18],在國際數字人文中心網絡(Center Net)上可查的目前只有5 家[19]。許多數字人文中心已是高校獨立的機構,兼聘圖情人員參與工作;也有如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數字人文中心由圖書館負責管理。
3 國外圖書館數字人文館員的能力素養(yǎng)要求
結合上述國外數字人文館員培育的相關實踐,綜合李潔[20],鄭麗央[21]等人的文獻,國外數字人文館員的能力素養(yǎng)建設方向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3.1 強調數字資源創(chuàng)建和管理能力
數字人文館員首要的重任是能夠整合數字人文資源,并能夠熟練使用這些資源以提供相應服務。國內外圖書館都注重擇取數字資源建設對象和培養(yǎng)建設能力,其中國外圖書館甚至對館員運營數字人文項目的整體能力還有進一步要求。

表1 國外圖書館數字人文館員學術服務能力要求
國內圖書館對數字人文館員的要求與國外圖書館方向大致相同,但能力水平要求相對基礎。 近幾年,我國數字人文館員同樣重視充分利用本館或當地現有特色資源,以及館際合作。 如上海圖書館推出“上海年華項目”展示當地百年風土人情,還有國家圖書館和哈佛燕京圖書館合作,將中文善本數字化供全球讀者檢索瀏覽,實現大量海外漢籍的數字化回歸。 再如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聯合制作的“數字敦煌”項目。
3.2 重視數字人文館員的人際表達能力
數字人文館員和學術人員的有效溝通大大影響著其數字人文服務的效用。 此外,他們還是知識的傳遞者,負有向大眾傳播數字人文知識的義務。
國內數字人文館員招聘信息中,基本都有提及對團隊合作能力的要求,但相對來說描述得較為簡單。 目前國內招聘尚未明確提及項目管理經理一職,只能從一些招聘信息中看出類似項目管理的要求:“能夠建設數字人文團隊,培養(yǎng)數字人文人才。”[26]在培訓輔導能力方面,國內僅提及兼任人文學科或信息學科的教學工作,如上海師范大學相關招聘要求應聘者同時進行中文或歷史的教學工作,或講授信息資源課程[27]。 但國內對引領行業(yè)學術研討的能力尚未提出具體要求,這與國外數字人文館員能夠自主開展交流研討活動,還存在差距。

表2 國外圖書館數字人文館員人際表達能力要求
3.3 完善數字人文館員的教培考評
數字人文館員需要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和學科素養(yǎng),因而在國內外的前置學歷要求都比較高,且必須有終身學習的理念。 在這一點上,國內外圖書館認知一致,只是我國起步較晚,相關培訓體系尚未完善。

表3 國外圖書館數字人文館員教培考評情況
國內數字人文工作人員招聘同樣有高學歷的要求,傾向復合學歷。 近年來,我國也舉辦了不少數字人文交流年會。 如上海圖書館學會召開的“數字人文與語義技術”研討會,北京大學圖書館聯合哈佛大學召開的“數字人文論壇”等。 在專業(yè)性授課方面,中國人民大學于2020 年開設了數字人文專業(yè)。但總體而言,培訓的次數和多樣性均不如國外圖書館。
數字人文館員的教培考評還包括其考核評估體系。 美國高校圖書館對數字學術館員的評定比較全面和長效。 如耶魯大學圖書館借鑒職業(yè)生涯測試工具對館員進行四維評估。 除了校內自行開展考核評估,校外的專業(yè)機構協會也會開展調查評估。 2009年,美國圖書館協會ALA 就對全美圖書館員的核心能力提出了八大要求,包含圖書館學的職業(yè)基礎,信息資源處理能力、用戶服務能力、學術研究能力、終身學習能力和其他管理能力等[29]。 美國的數字人文館員還能得到包括校內和校外的資金機會。 與之相比,我國圖書館對于數字人文館員的考核評估體系尚未完整,還存在不少空白。
4 對我國圖書館培養(yǎng)數字人文館員能力素養(yǎng)的啟示
繼阮岡納贊提出經典的“圖書館學五定律”之后,1995 年美國圖書館學家克勞福德與戈爾曼提出了“圖書館學新五律”:①圖書館服務于全人類;②重視各種知識傳播方式;③明智地利用科技手段提高服務品質;④確保知識的自由存取;⑤尊重過去,開創(chuàng)未來。 以“新五律”為指導,結合國外數字人文館員的實踐和能力素養(yǎng)要求,我國數字人文館員的建設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4.1 增設數字人文中心
我國的數字人文中新心數量目前還比較少,且其中具備國際知名度的僅有前文提及的臺灣數位人文中心和武漢大學的數字人文中心等少數機構。 我國應扶持更多有條件的高校或公共機構開辦數字人文中心,對于校內外人文學者的數字素養(yǎng)培訓,也可以依托這些中心展開。 對于已經獨立于圖書館運營的大型數字人文中心,圖書館應加強與其合作交流,積極培養(yǎng)館內的數字人文館員,有能力的圖書館可以創(chuàng)建自己的數字人文中心——可以由專職的館員組成,也可以由如信息技術部、地方文獻部、古籍部等各部門人員兼任,還可以吸納外部學術單位的指導人員加入。
在開發(fā)數字人文資源時,館藏資源包括紙質書籍、報刊、古籍文物等,是傳統(tǒng)數字化建設的重要對象。 與此同時,許多圖情專家在2020 年的上海數字人文年會上也指出,數字人文資源的建設不應再局限傳統(tǒng)館藏,而要注重特定數據集和數據整理。 數字人文建設的題中之義既包括尋找開發(fā)資源,也包括整合管理資源。 如對數字資源進行文本挖掘,通過詞頻統(tǒng)計、實體識別、情感分析等方式使得這些數字資源能夠被充分利用。 此外,數字人文資源的開發(fā)應結合本館的定位和特色,發(fā)掘特色人文資源。如上海市圖書館建設的華人家譜平臺,對收集到的家譜進行數字化加工,出版了專題聯合目錄,實現從文獻服務到數字人文服務的轉型。 建設地方特色資源項目也有助于吸引到更多的外部支持,讓各館在數字人文時代的激烈競爭中找到一席之地。
4.2 提供嵌入式數字人文服務
數字人文館員要提供嵌入式服務,就要做到“兩個合作”。 其一是與人文學者合作提供嵌入式學科服務。 參與具體的數字人文學科項目中,主動地打破邊界、打破孤島,去研究需求導向,著重以研究項目的完成效果和研究人員滿意程度為標準;其二是館際合作。 如公共圖書館可與高校圖書館和科研院所專業(yè)圖書館合作。 后者針對學科進行采購,擁有珍貴的特色館藏資源,還擁有相關領域的專業(yè)研究人員可以推動資源專業(yè)化的采集、存儲和描述。其中高校圖書館相對擁有更悠久的人文歷史資源,它們在數字人文中已經處于先行先試的地位,盡管也遇到了自身的困境,但具備的相關軟硬件設施和實踐平臺,仍然值得公共圖書館學習借鑒。
上述兩類合作可謂是互利共贏:一方面,圖書館的數字人文館員能夠充分利用館藏資源幫助人文學者深入系統(tǒng)地研究,并能運用計算機技術處理能力對專題學術予以輔助的評判和分析;另一方面,科研學者的參與能夠促進數字人文館藏的建設。 在對數字資源的內容揀選與整合上,可以借助他們專業(yè)的眼光來保證這些資源的學術價值和與時俱進的更新,最終形成一套非常有體系、有價值的專業(yè)數字人文館藏資源。
4.3 推動數字人文館員的成長
將館員劃分為專業(yè)館員和大眾館員,在招聘專業(yè)數字人文館員時,鼓勵信息類和人文類雙學位的應聘者。 設立專項資金支持,適當提高數字人文館員薪酬,同時注重評估,形成激勵和約束并行的長效管理機制。
對于數字人文館員的繼續(xù)教育,應涵蓋分析和使用數字資源的培訓,還應包括歷史學、傳播學等人文領域的知識,同時也不能偏廢圖書館學、文獻學等相關學科的基礎教育。 數字人文繼續(xù)教育的形式,有圖書館專門的崗位培訓,也包含館員的自我學習,以及“走出去”的交流學習,如利用外部資源和網絡資源,積極參與現有的數字人文學會、高校圖書館等的講座,或是聆聽數字人文年會、慕課(MOOC)等網絡課程資源。 除了這些顯性的職業(yè)技能培養(yǎng),數字人文館員還要注重自身職業(yè)道德和職業(yè)意識的隱性職業(yè)素養(yǎng)的提高。 同時,要在社會層面倡導人才的培養(yǎng),借鑒中國人大設立數字人文二級學科的做法,發(fā)揮高校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的教學優(yōu)勢,制定人才培養(yǎng)計劃,將數字人文課程融入高校課堂,為數字人文館員做好高學歷人員的儲備。
5 結語
美國杰出的圖書館學情報學家杰西·謝拉曾說“圖書館學理論,隨著它的發(fā)展,定將包括所有形式的人類活動,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 這不僅因為圖書館書架上保存著人類經歷的記載,而且還因為這些保存物體現著和能夠滿足所有人類生活的需要”。 隨著數字人文的快速發(fā)展,圖書館館員所提供的知識服務面臨更大的機遇,也面臨更高的要求。只有建設好數字人文館員隊伍,才能在新的時代發(fā)展中不被淘汰,甚至成為全人類的大腦,讓人們得以從我們保存和傳播的數字人文智慧中尋回遺忘,發(fā)現未知,擁抱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