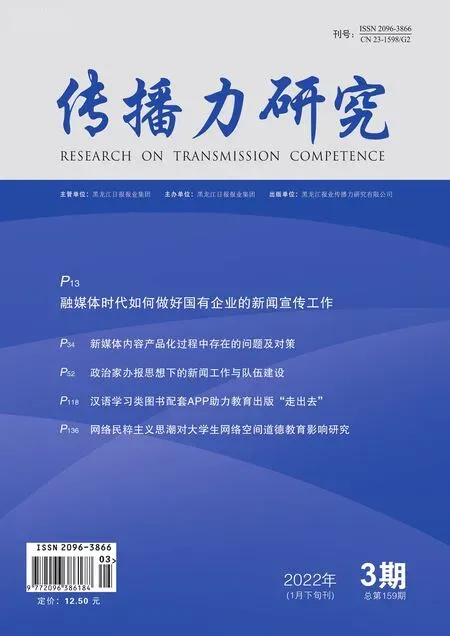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類雜志生態位拓展研究
——以《三聯生活周刊》為例
◎趙佳輝
(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一、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與傳播媒介的發展,一方面,受眾獲取信息的途徑變得更加便捷化、碎片化和多樣化,受眾的發聲渠道和方式也得以拓展,身份由受傳者隨之轉化為用戶。另一方面,新媒體的蓬勃發展對傳統媒體造成了巨大沖擊,碎片化的信息充斥著網絡環境,被各類社交媒體瓜分的注意力使其在傳統媒體上所占的時長逐漸變短,這對期刊造成了一定影響。
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是媒介生態學,尼爾·波茨曼最早提出“媒介生態”這一概念,他認為媒介生態學是“媒介作為環境的研究”;麥克盧漢認為,媒介生態的價值是讓各種媒介共生共存。在我國,研究媒介生態的學者聚焦于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的問題。崔保國將媒介比作魚類,這提醒我們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分析媒介與生存環境的關系。邵培仁提出了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整體觀、互動觀、平衡觀、循環觀和資源觀,以更宏觀的視角研究媒介生態。
生態位規律是媒介生態學中占重要地位的理論之一,樊昌志認為,媒介生態位是媒介種群從媒介生態系統中取得的供給本種群各個媒介個體使用的生存資源,包括受眾資源和廣告主資源。
根據《2019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顯示,2019全年出版期刊總印數21.9億冊,同比2018年降低4.5%;總印張121.3億印張,同比2018年降低4.3%;期刊出版業9.3萬人,同比2018年降低2.4%。新聞類雜志亦是如此,以深度報道為核心內容的新聞類雜志競爭力逐漸變弱,受眾更青睞于碎片化、便捷化的閱讀方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基于媒介所依賴技術的發展,報紙、期刊與互聯網等媒介越來越趨于融合,這不僅體現在媒介形態的融合,還體現在媒介功能、傳播手段、所有權、組織結構等要素的融合。同時,媒介融合不是多種媒介形式的簡單相加和組合,而是一種媒介再造過程,通過新媒介對傳統媒介的補充、整治、調和直至兩者融合形成一種新的復合媒介,從而實現再媒介化。①在媒介融合的推動下,傳統媒體紛紛積極尋求轉型道路,借助各類新型媒介,改變經營策略,推出適宜用戶喜好的產品。
本文選取《三聯生活周刊》作為研究案例,《三聯生活周刊》的前身為鄒韜奮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創辦的《生活周刊》,自1995年復刊以來,因其文化性與新聞性并重,深受讀者的歡迎,在新媒體沖擊下,《周刊》重視起轉型之路,孵化了多個新媒體項目,積極拓展媒介生態位。選取《三聯生活周刊》作為研究對象,一定程度上可以為其他雜志社的媒介生態位拓展提供借鑒。
以下將從《周刊》在轉變用戶策略、堅守深度報道、打造移動客戶端及拓展盈利渠道等方面進行展開,試研究《周刊》的轉型策略。
二、轉化思維方式,拓展用戶生態位
依據產業生態學的觀點,生態位寬度是對某一特定資源維度或資源軸上的生態位區域的度量,拓展到媒介生態領域,一家媒介公司為了維持或擴大自身在媒介系統中現有的生存資源,會拓寬生態位,尋求更好的發展。
在傳統的新聞生產過程中,專業的媒體從業人員生產內容,經由各級媒體,再分發到受眾手中,這一過程中以專業的媒介組織為核心。然而,隨著新媒體的發展,信息的生產者、消費者乃至信息都發生著一定的變化,這種傳統視角的觀念逐漸變得過時。
在信息生產者方面,由于傳播技術的更迭,信息的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關系變得模糊,UGC生產的大量內容進入網絡空間,加劇了信息的碎片化,使之更難獲取受眾的注意力。此外,海量的信息令信息消費者的選擇性極大地增加,進而使消費者群體也出現碎片化的趨勢,“大眾”分裂轉化為無數個社群中的“用戶”,因此,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在轉變視角,精準定位目標用戶,為細分化的用戶群體提供細分化的內容。
互聯網時代,有一種理論可以適用于當今的信息生產,長尾理論認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當商品儲存、流通、展示的場地和渠道足夠寬廣,商品生產成本急劇下降以至于個人都可以進行生產,并且商品的銷售成本急劇降低時,幾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極低的產品,只要有賣,都會有人買。這些需求和銷量不高的產品所占據的共同市場份額,可以和主流產品的市場份額相當,甚至更大。借用于此,在互聯網時代,以往那些不受重視的小眾的信息產品得到更多關注,由于數量和規模巨大,累計起來的收益甚至可以超過主流產品。
基于此,三聯生活周刊針對還未開發的“中閱讀市場”,推出了適宜互聯網受眾閱讀習慣的“中讀”APP,“中讀”的名稱源于《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李鴻谷提出的“中閱讀”概念:高于7萬字的閱讀傳統書籍、雜志是“慢閱讀”,低于3 000字的碎片化閱讀是“快閱讀”,“中閱讀”則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一種閱讀狀態。自2017年“中讀”APP面世以來,打造了以音頻為核心的知識付費體系,在堅守內容質量的同時,依托技術推出適宜互聯網生存規則的產品。“中讀”APP瞄準了年輕人在通勤過程中的閱讀需求,將以音頻呈現優質的內容,以供年輕人在地鐵、公交等場景中獲取知識。
三、堅守深度報道,拓展媒介生態位
對于新聞雜志來說,深度報道是其安身立命的內容產品。根據媒介生態學的觀點來說,深度報道占據了媒介生態系統中的深度報道生態位,由此來吸引讀者資源和廣告資源。但在新媒體的沖擊下,深度報道的生產和傳播受到了挑戰。新媒體使新聞生產時效性問題再度被放大。移動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發展促進了新聞的即時傳播,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就會有無數普通人將事件信息發布到社交媒體上,而新聞類雜志對該事件的采集與加工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而當對此事件的報道分發出來后,受眾的注意力有可能已經轉移,這時獲取他們的注意力將更加困難。
在面對受眾與廣告資源被新媒體搶占的情況下,新聞類雜志堅持做高質量原創性強的深度報道,才是應該被重視的,只有這樣才能牢牢保持自己的媒介生態位。在新媒體生態下,給原創性強的深度報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初期,《三聯生活周刊》的多篇深度報道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在公共事件中發揮了公共媒體應承擔的責任與使命。正如《周刊》副主編吳琪的所言,看到大型公共事件里具體的人,和看到個體故事背后的錯綜復雜的時代與系統,是公共媒體在網絡社交時代存在的重要意義。在疫情防控期間,面對紛繁復雜的信息,三聯生活周刊微信公眾號每天整理的4—5篇文章,為讀者提供了局部的真實,雖然未必能讓全國的讀者了解當前疫情的全景,但是可以對當下的處境可以獲得非常客觀的了解。隨著疫情逐步緩解,媒體也將這一變化傳遞給公眾,改變疫情初期人們對這一事件的認知,以構建更完整性的事實。
另外,媒體在深度報道中更應洞察人性。《周刊》將報道視角聚焦于疫情下的普通人,在文章《“圍城”方艙》中,記者駁靜走進方艙醫院,采訪了老人胡曉霜及家人被隔離的故事,其中一條胡曉霜用了半個小時學習打字發出一段文字:“陸久春(胡的丈夫),你還好嗎?你要堅強,我等你回家……”打動了屏幕后的讀者們,紛紛在文章下留言詢問陸久春的情況。疫情期間,在不斷上漲與降低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周刊》將描寫視角聚焦于他們,激發讀者的共情能力,深度報道也更加飽滿,取得了不同于其他新聞產品的效果,這是《三聯生活周刊》能鞏固其媒介生態位的重要原因。
四、深化用戶體驗,拓展內容生態位
在新媒體沖擊下,《三聯生活周刊》雜志運營團隊意識到雜志銷量的下滑和讀者資源的減少后,嘗試鋪設自己的新媒體布局。2015年,提出了“1+N”的新媒體布局,“1”是雜志的整體轉型,“N”是用1—2年的時間探索新媒體布局,尋求雜志轉型的基礎。基于此《周刊》運營團隊嘗試制作了兩款新媒體產品,即“松果生活”和“熊貓茶園”,并于2017年5月推出“中讀”APP。
“中讀”不僅僅是紙刊在互聯網的平移,而是一個不斷增量的產品。2018年初,雜志推出68元年卡,包括過去十年雜志的電子刊在內被一搶而空,但在團隊看來,這一現象只是因為過去紙質雜志的讀者出于對雜志的熱愛,化作對舊產品新形式的支持,而不是真正為產品的新內容買單。傳統媒體對新媒體產品的開發,不應是照搬原有內容,這樣雖然可以增加使用新媒體產品的用戶,但這是建立在侵蝕原本內容的舊用戶的前提下的,只有把舊內容當成一個“IP”去運營,不斷推出增量化的產品來鞏固這一IP,才能吸引更多用戶。2018年下半年,《三聯生活周刊》開始將產品IP化,制作了《宋朝美學十講》等精品音頻課程,出版了同名圖書,又與優酷合作將內容升級為付費視頻。從過去生產的眾多知識中,提煉出新的產品結構,將內容付費IP版權化,開啟了知識開發、服務與變現完整的產業鏈體系。
作為傳統媒體入局知識付費,本身就具備一定的內容優勢,自創刊以來積累的大量優質素材,經過重新拆分、重組,從而形成一個個內容產品。“中讀”創立后,確定了“打造原創精品課”的核心內容方針,精品課圍繞一個選題,會邀請十多個主持人來共同完成經一個選題,這個選題已經過內容團隊的事先策劃,會圍繞這一選題去進行一個全鏈條式的IP開發生產線,如,做音頻、做圖書、做視頻等。這一精品課開發模式,打破了以往“個人專欄式的常規課程模式”,解決了選題跟著主持人走的難題,并且針對同一選題邀請十多位主持人集思廣益,增加了付費內容的深度。團隊推出的第一個精品課《宋朝美學十講》,選題創意就是來源于《周刊》的兩期爆款內容“我們為什么愛宋朝”,在發現讀者對宋朝歷史感興趣后,內容團隊邀請10位主講人錄制700分鐘的音頻課程,對宋朝歷史進行講解,音頻課程上線后,又與出版社合作,將內容再升級產生新的圖書。同時,與優酷合作,再將產品升級為10集付費視頻產品。
五、豐富盈利方式,拓展功能生態位
媒介融合背景下,《三聯生活周刊》盈利模式也發生了改變,不僅通過傳統廣告和雜志訂閱盈利,還開拓了以下渠道獲益,產品結構更加趨于穩定。
(一)知識付費會員
在《三聯生活周刊》旗下的“中讀”APP中,推出了聽書年卡、單本電子雜志付費、課程付費、雜志電子刊年卡,以及包含精品課程和聽書功能在內的知識會員等多種付費模式。在初次注冊賬號時,還會贈送7天知識會員供新用戶體驗。在特定節日時,“中讀”APP會開展相應的促銷活動,如在2021年5月20日,開啟4周年慶+520特惠專場,以上付費服務均以五折以上的價格促銷,用低價吸引更多免費用戶付費。
(二)電商服務
除“中讀”APP外,《三聯生活周刊》在多家電商渠道開辦了線上商城。在旗下的微信公眾號上內嵌了線上書店服務,用戶可以在書店中單獨購買當期雜志或圖書,也可以以拼團的形式享受更低的價格。此外,《三聯生活周刊》還在天貓、京東等購物平臺上開設旗艦店,不僅可以訂閱新雜志和購買往期雜志,還銷售各類文創產品,旗艦店中使用預充購物金及滿減活動,吸引雜志讀者付費。
(三)線下活動
《三聯生活周刊》中的“1+N”布局中,推出了“松果生活”平臺,通過共享生活方式領域的線下活動,邀請了在美食、音樂、旅行等各個領域的高手入駐,開設沙龍、課堂、主題游學等線下活動,向眾人傳遞這種生活方式。
六、結語
《三聯生活周刊》以其內容為優勢,在轉型過程中確立了“新聞+文化+生活”的辦刊道路,從海量的內容中提取適宜IP化的資源,推動用戶為知識付費。依據總經理李鴻谷在《三聯生活周刊》轉型三周年會議上的講話,公司定位已從傳媒公司轉型為內容傳播公司,《周刊》和新媒體產品對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不僅樹立了媒體公信力,還贏得了大量讀者信任和贊賞。
周刊轉型成功的另一方面表現在營收結構上,來自新媒體的營收在逐年增長,從2017年的40%到如今的70%,這體現了《三聯》轉型路上的另一方針:打通超級平臺的渠道通路。通過搭建微博、微信公眾號及視頻號等方式,將這些新媒體賬號定位于“超級平臺的頭部賬號”,體現更豐富的廣告價值。
回首《三聯生活周刊》轉型之路,它將媒介生態位拓展至用戶、媒介、內容和功能生態位,僅用三年時間就完成了轉型周期中第一階段“內容互聯網化”的策略。雖然接下來還有內容數據化和數據的資產化等兩階段需要完成,但它在第一階段的轉型策略,可以為其他新聞類雜志轉型提供有效借鑒。
注釋:
①黨東耀.媒介再造——媒介融合的本質探析[J].新聞大學,2015(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