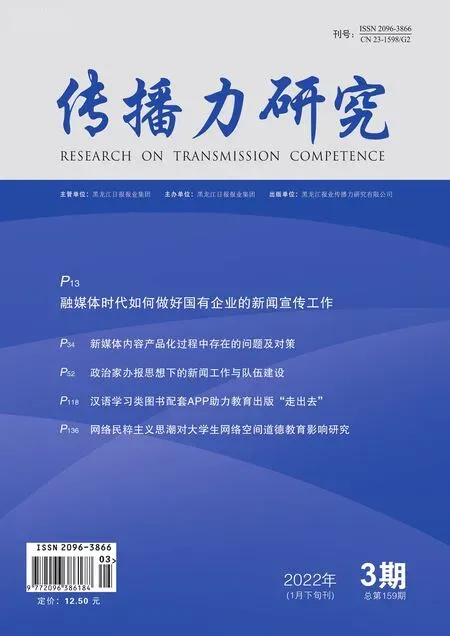經管類圖書常見編校錯誤
◎王藝博
(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經管室,北京 100710)
一、引言
圖書是知識和文化的載體,肩負著傳承人類文明的使命。編輯負責圖書的審讀和二次加工,其主要工作就是將粗加工的稿件經過自己的修改、潤色、整理,轉化為出版物,因此出版高質量圖書的責任自然就落在了編輯的身上。
隨著出版數量的增多,出版物質量良莠不齊,出現了很多編校質量不合格的圖書。2019年,國家新聞出版署組織開展了圖書“質量管理2019”專項工作。經專家審核,國家新聞出版署認定35種圖書編校質量不合格。圖書“質量管理2019”專項工作重點圍繞文藝、少兒、教材、教輔、科普類圖書進行了編校質量檢查,共組織抽查100家圖書出版單位的300種圖書,其中文藝類105種、少兒類44種、教材類58種、教輔類46種、科普類47種。經專家審核,認定35種圖書編校質量不合格,其中,文藝類11種、少兒類2種、教材類8種、教輔類3種、科普類11種,涉及29家圖書出版單位。國家新聞出版署每年3月都會組織開展有關圖書質量管理的專項工作,其目的就是為了防范編校質量不合格的圖書流向市場。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高速發展的時期,圖書出版業也迅速發展,圖書種類越來越多。人們對經濟管理知識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因此,我國的經管類圖書出版迅速興起,很多出版社紛紛涉足經管類圖書的出版。經管類圖書的興起不僅豐富了我國的圖書市場,促進了我國出版業的飛速發展,而且還帶來了先進的經濟管理理念、技術和方法,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本文從作者多年編輯工作經歷出發,從經管類圖書的編輯入手,對圖書編輯加工過程中容易出現的常見編校錯誤,進行了分類分析,并進行了舉例說明,以期對提高出版物質量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二、經管類圖書常見編校錯誤
按照《圖書編校質量差錯認定細則(修訂版)》(2005)的規定,圖書編校質量差錯分為文字、詞語、語法、標點符號、數字、量和單位、版面格式等方面。鑒于篇幅有限,筆者結合多年工作經驗,提取了圖書出版中常見的、有代表性的編校質量差錯問題進行分析。
(一)政治性差錯
政治性差錯一般指在和黨和國家意識形態保持一致、與社會主義核心體系保持一致方面的錯誤。發表違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和舉動就是犯了政治性差錯。重視政治性差錯是出版物的首要任務。一旦出現了嚴重政治性差錯,往往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因此,出版人員一定要避免政治性錯誤,這是一條紅線,不能碰。盡管經管類圖書多數不涉及社會學、政治學的領域,但是也要繃緊政治性差錯這根弦。在多年的工作經歷中,筆者碰到過不少經管類圖書出現政治性差錯的例子。
在編輯公共管理名著譯叢項目的時候,筆者發現這套書的總序中,有段文字提到了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者將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前后顛倒,寫錯了。表達準確是圖書的基本要求,將人名弄錯屬于出版硬傷,國家領導人代表著我國的形象,領導人姓名更不應該出錯,如果貿然出版,將會造成重大出版失誤。
在編輯《如何贏得一場“戰爭”》這本書時,筆者發現并處理了幾處政治錯誤。比如書中提到:“這將使日本與其部署在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中國南方、菲律賓、臺灣的部隊相互隔絕,同時也將切斷日本用于生產的原材料;另外,它將使轟炸整個日本大陸成為可能。”這句話就犯了政治性差錯。臺灣、香港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不是獨立國家,這段話將臺灣和其他國家并列,將其列入與國家齊平的地位,未將我國領土表達完整、統一,犯了重大政治錯誤。
在講到美國太平洋戰爭時,作者提供了一張當時的地圖,在地圖中,中國被分為滿洲、西藏、臺灣、新疆和中國幾個大塊。和上面的錯誤一樣,這張地圖也犯了的破壞祖國統一的政治錯誤。臺灣、香港、西藏和新疆都是隸屬于我國的省市自治區,不能和中國并列為國家。這是重大的政治性差錯,違反了政策性文件、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和團結,如果貿然出版,將釀成重大的出版事故。
在多年的編輯工作中,筆者也發現了與上述情況不同的政治性錯誤。比如,有一部書稿將臺灣、香港和別的國家并列稱為國家,臺灣和香港只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如若與其他國家并列稱為國家,勢必導致嚴重的政治錯誤;有一部書稿在致謝中提到國立中正大學字樣,這種政治性錯誤比較隱蔽,一般會被忽視。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的大學不可能是國立大學;有一部書稿提供的中國地圖中,沒有包含臺灣,這種也是容易被忽視的政治性差錯。對這種政治性差錯,編輯一定要重視起來,在工作中多加總結、認真學習,不斷增強自己的編輯素養,提高政治覺悟,以避免重大出版事故的發生。
(二)知識性差錯
知識性差錯指的是歷史和學問方面的錯誤。出版物中常見的知識性差錯主要有文史知識錯誤、自然科學知識錯誤、事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等名稱錯誤。圖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傳播知識、傳承文明,所以不能有知識性錯誤。讓讀者讀到正確的知識,是編輯的責任,防范知識性差錯是每一位編輯都要把好的關口。造成知識性差錯的原因不只是圖書內容上整體性的理論知識等方面的欠缺,而且包括由于常識的欠缺、技術上的疏忽、文字表述不當等造成的涉及知識性內容的差錯。經管類圖書屬專業圖書,有很多專有名詞和技術用語,用錯的話會造成誤解,甚至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因此更不應該犯知識性錯誤。
筆者曾經編輯過一本書,書中提到:“中方——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薄一波同志。”這段話粗看上去沒有毛病,但實際上卻犯了一個知識性錯誤。文中提到薄一波曾經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經查證,國家經濟委員會也沒有設立過主席職務,薄一波同志也只是擔任過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一職,并無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一職,因此此處應該改為中方——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同志。如果編輯平日里知識儲備不足,不了解真實情況,就不會發現這樣的知識性錯誤,如果直接出版,就會鬧出笑話。
比如,筆者2021年出版的《增長之源》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始于壘土,縱觀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濟發展……”這段文字引用的是《道德經》中的一句話。原文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文中所引的文字與原文不符,“始于壘土”應該改成“起于累土”。這種錯誤就屬于引用知識錯誤。
再如,《央地關系》這本書中寫到:“在2006年以后,招牌掛出讓的土地數據中,也包含大量的工業用地。” 招拍掛一般指我國的土地招拍掛制度。土地招拍掛制度是指我國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出讓管理制度。我國并沒有招牌掛這樣的土地制度,因此,這里的招牌掛就犯了常識性知識錯誤,應當改為:“在2006年以后,招拍掛出讓的土地數據中,也包含大量的工業用地。”。
編輯要避免知識性差錯,就需要平日里不斷學習,提高自己的知識儲備,擴展自己的知識面,使自己成為一名雜家,不了解時多查資料,這樣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編輯,能夠及時發現知識性差錯,最大可能地避免知識性、常識性、邏輯性等錯誤。
(三)語法錯誤
語法是字、詞以及詞組句子等語言要素的運用規范。只有正確運用語法,語言才能被人所理解,才能成為交際的工具。語法錯誤也是很常見的圖書錯誤,語法錯誤會產生歧義,輕則讓人不知所云,重則貽笑大方,因此,編校人員必須重視書稿中的語法錯誤。圖書中常見的語法差錯大致分為:詞性誤用、指代不明、搭配不當、句子成分殘缺等。
比如,《經濟學的異端》一書書稿中,有這么一句話:“法律機構和包括股票市場在內的金融機構的職能,就是降低貸款人的風險并便利他們為實業提供資金支持。”這句話就犯了語序不當的錯誤,是一個病句。應該改為:“法律機構和包括股票市場在內的金融機構的職能,就是降低貸款人的風險并使他們為實業提供資金支持更為便利。”
再如,同上書稿中有這樣一句話:“他實際上是將全部資源看成為某種賦予的東西。”這句話中有成分多余的錯誤,應該改為:“他實際上是將全部資源看成某種賦予的東西。”
在《央地關系》書稿中,筆者發現有如下語法錯誤。比如:“假如我們是某個地區的居民,最期待的是地方政府能夠改善教育水平,讓孩子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水平……”,這句話就有搭配不當的語法錯誤,不能說接受良好的教育水平,可以改成,讓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也可以改成,提高孩子們的教育水平。
比如,書稿中說“其中明末顧炎武提出的寓封建于郡縣方案有著非常閃耀的思想光輝。” 這句話包含搭配不當的語法錯誤,非常是副詞,閃耀是動詞,不能說非常閃耀,應該將非常閃耀改為非常奪目。
比如書稿中說“就中國這個的超大型國家而言……”這句話就有語序不當的語法錯誤。“的”不應該放在超大型前面,應該改成:“就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而言……”
(四)詞語差錯以及錯別字
詞語差錯是圖書編輯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的錯誤,詞語差錯常表現為錯字、別字、異體字、詞語運用不準確以及生造詞語等錯誤。出現這種錯誤的原因,多半是因為作者手誤、知識面不足、誤解詞義、錯把口語當書面語。經管類圖書也不例外,在編輯過程中經常會遇到詞語差錯。
比如,“筆者深恐學力未充,研究未明,愿與關心該主題的同道一起……”作者意圖表達的應該是在學習上力有不逮的意思,但是作者犯了生造詞語和亂改成語的錯誤,沒有學力未充這樣的成語,應該改成:筆者深恐在學術上力有不逮……
比如,“正象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一樣,政府也要追求他的利益。”象不能做介詞,應該將句子中的象改為像,以表達如同、比如的意思。
比如,“向上級政府慌稱公共事務的收益與成本,以取得來自上級政府的更多的轉移支付資金支持。”這句話中就犯了生造詞語的差錯,沒有慌稱這個詞,應該改成謊稱。
比如,“救災依賴涉及農業立國的國家,旱澇豐欠往往此起彼伏,為克服災害的負面影響……”,這句話就犯了生造詞語的錯誤,漢語中沒有豐欠,只有豐歉一詞,豐指的是豐收,謙指的是歉收,因此,應當將文中的豐欠改為豐歉。
比如,“這樣一來,如果證券需求的增長慢于供給的增長,除非銀行體系抵銷了這一運動,否則利息率水平將趨于上升,反之亦然。”抵銷指的是某種賬的沖抵,抵消指的是兩種事物因為相反作用力而相互消除。上文明顯表達的是消除的意思,這句話犯了錯用詞語的差錯,抵銷應該改為抵消。
(五)版面格式差錯
書稿中的版面格式錯誤比較常見,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前后不統一、不一致,經管類圖書也不例外。比如,書稿前文將將經濟學家稱為約翰·穆勒,后文卻翻譯成約翰·密爾;前文翻譯為米塞斯,后文卻變成了米瑟斯;前文將年代寫成1980年,后文卻變成了一九八〇年;前文使用的是羅馬數字,后文卻變成了英文字符;在表示數字時,前文用阿拉伯數字,后文卻變成了漢字數字格式;腳注序號有的章節是每頁從1開始,有的章節卻變成了連排;比如將另一本的作者簡介或者內容簡介放到一本書上;有的表格有表頭,有的表格沒有表頭;前后專業術語翻譯不統一,例如前面翻譯成新新古典經濟學,后文卻翻譯成新-新古典經濟學;有的數字千分位用逗號隔開,有的用空格隔開;等等。
(六)標點符號差錯
按照國家規定,1995年12月國家技術監督局發布的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是判定標點符號正誤的依據。圖書中會大量用到標點符號,標點符號又多種多樣,因此標點符號差錯也是最復雜、最常見、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經管類圖書書稿中也存在不少標點符號的錯誤。比如:
“感謝上海證券報的沈編輯……”
圖書、報紙名、期刊名等的題目在文章中出現要使用書名號,這句話中上海圖書報屬于報紙名稱,所以應當加上書名號。
“但是這兩個荒謬的數字-9和140,影響了個人的判斷。”
上文中一字線后面文字是解釋說明性文字,應當改為破折號。
“三位金融學者系統地研究了足球,板球,籃球,冰球等國際頂級賽事……”
頓號用來表示并列詞語間的停頓,停頓較長是才用逗號,因此上文中的逗號應該改為頓號。
標點符號容易用錯,錯誤的形式表現多種多樣,因此編校人員在審讀書稿的過程中要加強意識,努力防范標點符號差錯。
三、結語
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到:“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這說明編校差錯在圖書出版中是避免不了的,是正常現象。這么說當然不是為圖書差錯開脫,而是說明出版人要不斷學習,不斷提高,以應對不斷出現的新的問題和錯誤。
圖書質量關乎文明傳承,關系重大,出版人必須要高度重視圖書質量。因此,在經管類圖書的出版過程中,責任編輯和校對人員需要更加增強自身的責任意識,不斷學習,提高自身編輯素養,多了解常見的編校錯誤,加大對圖書編校系統流程的把控力度,認真負責,關注每一個具體細節,盡量保證經管類圖書編校的細節性和整體性的統一,從而盡可能地降低經管類圖書編校的差錯率,有效提高經管類圖書編校工作的質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