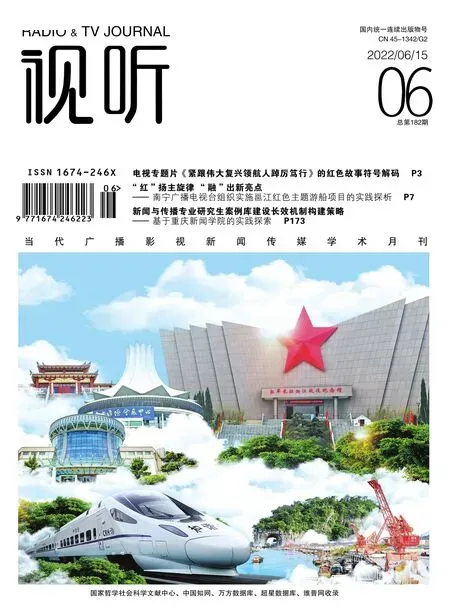從代際區隔到代際互惠:銀發綜藝節目《屋檐之夏》的雙向治愈探索
李 阮
《屋檐之夏》是由嗶哩嗶哩和中國老齡協會攜手推出的首檔忘年共居觀察紀實真人秀節目。該節目采取“真人秀+觀察室”的模式,邀請3位長居上海的獨居“寶藏老人”與多位“滬漂青年”共同體驗為期21天的代際共居。以往的銀發節目,如中央電視臺的《夕陽紅》《樂齡唱響·全國老年合唱大賽》、江蘇綜藝頻道的《緣來不晚》、東方衛視的《忘不了餐廳》都單純聚焦銀發族,呈現他們在“家”以外的社交活動與生活態度。《屋檐之夏》獨辟蹊徑,創造性地跳出聚焦同類、呈現清一色銀發世界的桎梏,著眼于代際關系,通過青老共居,嘗試搭建隔代共情的橋梁,探索全新的生活方式。
一、青老共居、代際互惠、懷舊情結、跨代際社交:豐富銀發題材
(一)青老共居:特殊場域下情感缺位的替代性滿足
替代性滿足理論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學。弗洛伊德認為,當人們對原初對象的欲望因受到阻礙而無法滿足時,就會設法尋找一個接近原初對象的替代品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滿足,從而消除緊張和焦慮的情緒。也就是說,當欲望能量在最初對象上遇到阻礙時,就會向其他對象轉移;如果再次遇阻,就再次轉移,直到尋找到一個替代對象以消除緊張、滿足欲望為止①。本能欲望尋找替代對象的過程是一個層層轉移、不斷妥協、逐步向上(升華)的過程,人在本能上總是渴望獲得最接近原初對象的替代性滿足。
包羅萬象、極具現代化氣息的奇幻魔都上海,既是全國大學畢業生就業首選城市之一,又是一座深度老齡化的城市。上海為“滬漂青年”和獨居老人帶來更多生活、教育、醫療、科技等機遇的同時,也使社交孤獨成為集體癥候。在上海這個特殊場域下,年輕人背井離鄉有“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孤寂漂泊之感,老年人由“被陪伴”狀態走向“獨居”狀態存在“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之感,二者的家庭情感均處于離場狀態。《屋檐之夏》中,89歲的朱爺爺日復一日的生活曲線(小橋流水飯店——太平洋咖啡館——居家別墅),劉雪華一語道破獨居的無奈(“其實一個人住,別的都不怕,萬一有一天你不小心摔跤了,是沒有人知道的。”),大學生小顏身上厚重的漂泊感,都是情感缺位、社交孤獨的現實注腳。
人是情感化的動物,個體對家庭情感的渴望不會因缺失而消失,往往會通過轉移獲得替代性滿足。《屋檐之夏》策劃組敏銳地捕捉到青老群體這一情感空缺,創造性地將鮮有交集的“滬漂青年”和獨居老人聚集于同一屋檐下,不僅滿足了熒屏內兩代人對家庭溫暖和親情的渴求,實現情感的替代性滿足,還為隔代人相互靠近、互相了解、良性溝通提供了經驗。此外,熒屏外具有相似經歷的個體也能通過觀看節目,在共情中釋放思念情緒、治愈孤寂心靈,找到代際相處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例如,由《屋檐之夏》引起的話題討論#你對家人最大的遺憾是什么#,讓不少網友重新審視自身與家人的關系,采取行動,減少遺憾。
(二)代際互惠:人文關懷下前后象征模式的完美融合
瑪格麗特·米德在《代溝》一書中指出,社會中存在三種文化模式:后象征模式、互象征模式、前象征模式。后象征模式是長老模式,老一代是文化的制裁者和領路人,文化傳承依靠代代相傳,傳遞的內容是持續不變的意識。互象征模式是同輩模式,指采取某種向同輩人,如向游戲伙伴、同學和一起學藝的人學習的模式,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文明。前象征模式是指由于年輕人對依然未知的將來具有前象征性的理解,年長者不得不向孩子學習他們未曾有過的經驗。在米德看來,代際間存在不可逾越的溝壑:“整個世界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年輕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們年長的人——隔著一條深溝互相望著……這樣的溝是不會彌合、不會變窄的。”②
尼爾·波茲曼將印刷媒介時代稱為“闡釋時代”,主張印刷媒介隱喻理性、嚴肅和邏輯,常以晦澀語言刊載政治、文化內容。印刷媒介時代,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導致知識壟斷,年輕人只能遵循后象征模式實現文化傳繼。而新媒體時代,電子媒介擊碎傳統的“時空偏向”,形塑網狀的權力結構。年輕人憑借著對新環境的快速適應和新媒介的熟練使用,暢享知識共享的紅利,進一步瓦解年長者壟斷知識的局面,后喻文化(前象征模式)成為現代社會的表征。然而,無論是自上而下的傳授模式,還是自下而上的反哺模式,都在無形中將老年人和青年人區隔開來,呈現出代際斷裂、代際沖突的特征。如《中國式相親》節目中,23歲的趙浩然為40歲的林嘉莉爆燈時,遭到母親強烈反對,“代際戰爭”成為節目焦點。在隔代親子真人秀《寶貝的新朋友》中,爺爺姚安濂和萌娃蟲蟲在游樂園和蛋糕房多次爆發沖突,陷入僵局,成為節目的一大看點。
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和公平理論,單方面得到后輩的支持或者單方面向后輩提供支持都會使老年人處于一種不平衡的代際關系之中,只有當代際交往處于有來有往的互惠狀態時,二者才能從中感到滿意或幸福③。因此,在銀發節目中過多呈現代際隔閡或代際斷裂,可能會誘發個體對隔代相處的恐懼和擔憂,無助于個體幸福感和價值感的提升。與瞄準代際沖突的節目不同,誕生于亞文化社區的《屋檐之夏》更強調前后象征模式融合下的代際互惠。節目對準三組各具特色的家庭,集中呈現隔代群體的互惠過程,為老青群體提供心理關懷和精神關愛的同時,也傳達了與時俱進、積極向上的生活理念,極具人文關懷。
如劉雪華家庭,拉宏桑耐心地為劉雪華講解何為B站、何為UP主,通過話題溝通增進彼此之間的關系。拉宏桑還和貝貝一起幫助劉雪華克服出門社交的恐懼。而劉雪華憑借自己的睿智和經驗,細心開導拉宏桑在陌生環境中做自己,擺脫拘謹感,耐心分析貝貝的暗戀經歷,從過來人的角度傳遞戀愛經驗。朱爺爺家庭,阿雷和Miya尊重并保護朱爺爺的童心,策劃多組“重返青春”的活動,完成老人家的心愿。朱爺爺則以自身對生活的態度引導兩位年輕人規劃好自己的未來。這種雙向互惠的敘事方式,有利于讓隔代群體在共處中發現彼此的寶貴之處,激發個體對青老共居的向往和熱情。
(三)懷舊情結:社會變遷下記憶重組與身份認同的新嘗試
社會學家Davis認為,懷舊是個體對過去的一種向往,但這種向往有可能是對故土的思念,也有可能是對過去人和事的渴望,而且這種渴望和思念并不局限于某類人身上。簡單地說,懷舊是現代人自我安慰和自我救贖的重要手段,是人們在精神層面重返“家園”的過程④。在經歷消費社會的虛無和狂歡文化的刺激后,個體尤其是年長者遭受著巨大的文化沖擊,呈現出認知失調的狀態,具有很強的“被剝奪感”與“參與式危機”,迫切需要從過去的記憶中尋求精神撫慰和文化庇佑,懷舊文化應運而生。
記憶是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也是一種歷史書寫的結果,更是人類生命的自我持存。記憶在瞬間生成,又綿延久遠,它使過去澄明于現在,又將未來置放在現實中考量。它使個體的生命片段得以連綴為一個貫穿始末的歷史過程,并因而賦予人對自我的認知和認同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一輩人有一輩人的記憶。曾經家喻戶曉的劉雪華、曾經年輕有為的朱爺爺以及誨人不倦的魏奶奶,都有屬于自己的高光時刻和一生無法忘卻的記憶。《屋檐之夏》在三組家庭的敘事過程中運用了諸多懷舊元素,追溯當事人的記憶,既彰顯了銀發綜藝的人文屬性,又塑造了老青共看的可能。如節目邀請演員劉雪華錄制節目,勾起了老青群體對《少年慈禧》《幾度夕陽紅》《春天后母心》《甄嬛傳》等經典作品和“太后”形象的回憶,搭建老青共情的意義空間,讓隔代群體在記憶追溯和重組中獲得情感共鳴與情緒增值。
朱爺爺在節目中多次提及上海的標志性建筑、承載公共記憶的物質空間——百樂門,引發了觀眾的濃厚興趣。阿雷和Miya為此精心策劃,在百樂門這個歷史性建筑里舉行“重返二十歲”的盛大舞會,幫助朱爺爺重溫青春記憶,實際上是將個人空間中朱爺爺對過往的私人回憶轉化為公共情感空間中觀眾對集體記憶的訴說與緬懷,是構建身份認同的重要手段。小顏、小精靈和小丁在教師節這一特殊時刻,為魏奶奶舉辦“教師節聯歡會”。濃厚的儀式感不僅為奶奶回望青春、追憶教師生涯提供了契機,還為老年教師群體再度挖掘內在能力和自身價值、提升自我效能感和身份認同創造了機會,是“積極老齡化”的重要實踐。
(四)跨代際社交:脫域機制下血緣關系向陌生關系的跨越
談及代際,人們通常會想到基于血緣的親子關系。血緣關系是由婚姻或生育而產生的人際關系,具有長期穩定性和深刻性,是人類最基本的關系。古有通婚化解戰爭之例,現有骨肉至親、血濃于水、骨肉相連之比喻,均體現出血緣關系在關系維系方面的強大作用。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我國代際關系類綜藝往往體現的是基于血緣的代際關系,如爺孫隔代親子生活體驗秀《寶貝的新朋友》、代際相親節目《新相親大會》、親子觀察秀《我家那小子》和《我家那閨女》等。
然而,數字技術的縱深挺進導致時空分離,吉登斯言下的“脫域”成為現代社會的表征,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⑥。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不斷變遷,家庭規模趨于小型化,傳統的三世四世不異居的居住格局已被打破。部分家庭因工作遷徙或觀念沖突,年長一輩和年幼一代未有共居的經歷,兩代人的相處方式由原始的長久性面對面交往轉向屏幕前的瞬間互動,想要靠近卻不知如何靠近,成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如《屋檐之夏》中的朱爺爺和孫女Sasa。對于這一現狀,以往拘泥于血緣關系、熟人社交的代際類綜藝可能無法為陌生的兩代人提供具有參考性的建議。
而《屋檐之夏》跳出“親子關系”的單調格局,首次讓陌生的隔代人同住一個屋檐下,客觀反映當下社會家庭結構的變遷。節目沒有設置刻意的對話、劇本和沖突,鮮明的代際差異和陌生的社交關系足以在日常交流中營造出莫名的緊張感,牽動觀眾情緒,反觀自身。如鏡頭前大膽自如的拉宏桑在陌生人面前卻敏感脆弱,不知道如何與陌生長者相處,頻頻主動出擊卻難破尷尬氣氛。在善于社交的貝貝入住后,拉宏桑更是躲在房間里崩潰大哭。她的無助與自我懷疑讓觀眾不由發出“拉宏桑簡直是另我”的感慨,引起個體對同輩社交和隔代社交的共鳴與思考。
此外,節目使用紀實性的拍攝手法,全面、真實地呈現陌生的隔代人從陌生到熟悉、從拘謹到自如的社交全過程,從中折射出三組不同的代際關系:劉雪華家庭——如女生宿舍般的舍友關系,朱爺爺家庭——和諧互助的朋友關系,魏奶奶家庭——傳統長慈孫孝的祖孫關系。這三組家庭的關系展現,對于個體反思代際隔閡、打破血緣桎梏、探討新型代際關系具有現實意義。正如臨別時朱爺爺對Miya說:“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
二、遮蔽與啟示:銀發綜藝發展之道
(一)融入農村題材,補全代際圖景
美國政治學家伯納德·科恩在《新聞媒介與外交政策》一書中提出大眾傳媒對公眾的強大影響力:“在許多場合,報刊在告訴讀者應該‘怎樣想’時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訴讀者‘想什么’方面,卻是驚人地成功。”在中國語境下,農村和城市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水乳交融,相互滲透。老齡化并非城市的獨特景觀,而是全社會共有的難題。《屋檐之夏》節目組只將鏡頭指向城市中的三位老人:演員劉雪華、上海紳士朱爺爺、一代名師魏奶奶。他們均身處一線城市,“老有所養”的物質基礎較為豐厚,思想較為開明,可能無法完全代表中國老年群體的群像。如果單純聚焦城市老年群體可能會造成媒介圖景的不完整,甚至是媒介歧視,使農村老年群體或農村代際關系被邊緣化。因此,《屋檐之春》《屋檐之秋》《屋檐之冬》應邀請更具多元化特征的老人參與節目,尤其是鄉村老人,以補全代際圖景。
(二)增加老年觀察員,豐富老年視角
代溝是指由于時代和環境條件的急劇變化、基本社會化的進程發生中斷或模式發生轉型,而導致不同代之間在社會的擁有方面以及價值觀念、行為取向的選擇方面所出現的差異、隔閡及沖突的社會現象⑦。《屋檐之夏》的常駐觀察員由齊思鈞、王瀚哲、姜廣濤、張怡筠、泡芙喵-PUFF等成員組成,他們均不屬于銀發族,與節目中的三位老人屬于不同代,可能會存在代溝現象。在節目討論環節,常駐觀察員由于相關經歷匱乏可能很難準確細致地描述或解釋老年人的心理活動,并給出相應的參考性建議。飛行觀察員中雖然也有年長者,如復旦大學梁永安教授,但節目中青年觀察員總體比例遠遠大于老年觀察員,老年視角的不足可能無法對老青共住期間老年人產生的種種行為和心理進行深度剖析。因此,未來的節目中應增加更多的老年觀察員,豐富老年視角,以增進青年人對老年人的理解,提升青老共居的可能性。
三、結語
老年人既具有日趨衰老的自然屬性,又具有歷經滄桑的社會屬性。以往,一些聚焦于家庭矛盾、城鄉沖突的大眾媒介多關注老年人的自然屬性,塑造了老年人孱弱、無知、固執、難以溝通等負面形象,導致老年人的失語與刻板固化,淪為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而今,《屋檐之夏》在關注老人身體素質自然變化的基礎上,更強調老年人歷經滄桑后的人生智慧和厚重積淀。該節目作為國內第一檔忘年共居觀察紀實真人秀節目,首次將人生小白和人生前輩聚集在同一屋檐下,捕捉二者的孤獨與困境,以青老共居、代際互惠、懷舊情結、跨代際社交等視角創新了銀發綜藝節目,打破了青老群體之間的壁壘鴻溝,破除了青老群體難以共居互惠的刻板印象,增進了不同代際間的相互了解,為國內銀發綜藝帶來了更多可能性。《屋檐之夏》的后續節目制作,應在節目取材和觀察員設置方面進一步創新,例如增加更多的鄉村視角和老年觀察視角,從而豐富銀發綜藝的傳播圖景。
注釋:
①霍連彬,米丹.替代性滿足:親密關系視角下手游《戀與制作人》的用戶研究[J].東南傳播,2018(06):112-115.
②[美]瑪格麗特·米德.代溝[M].曾胡 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20-93.
③許琪,王金水.代際互惠對中國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1):104-115+145.
④張一.從社會學角度看我國綜藝節目的“懷舊情結”[J].當代電視,2015(08):95-96.
⑤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2.
⑥秦朝森.脫域與嵌入:三重空間中的小鎮青年與短視頻互動論[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08):105-110.
⑦周怡.代溝現象的社會學研究[J].社會學研究,1994(04):6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