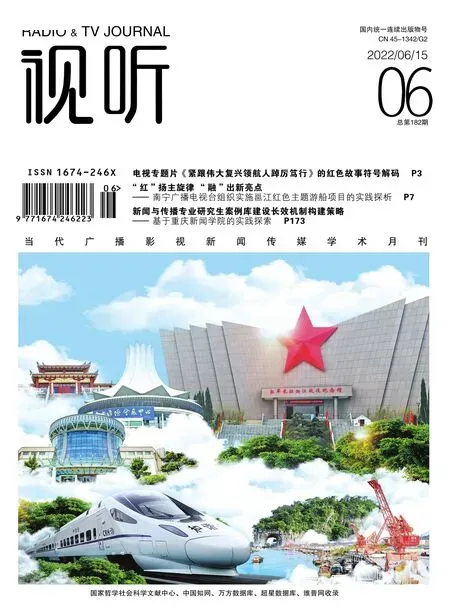符號學視域下《人世間》的敘事探究
文婭妮
對于一部文學作品來說,故事內容就是整個作品的核心要素,也是編劇最能表達情節與情感的出處,無論是對國民性格的探索,還是與時代背景融合,故事、人物的正反面以及情緒與欲望影影綽綽地暗示和透露,都需要讀者挖掘。符號學認為,社會上的一些人或事都可以看作符號的代表,以此來指明方向。符號學理論的關鍵是提供線索,促進人們從表象到本質的深挖。《人世間》根據梁曉聲的同名小說改編,以周家三代人的視角講述人世間50年的跌宕起伏,全面展示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表現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態,幫助不同年齡的受眾在劇中找到認同感和歸屬感。
一、《人世間》背后文化圖式的符號
電視劇《人世間》從字面上解釋是關于歷史與個人,生活在時代中的故事,無論重現還是再現,落腳點仍然是“劇”。《人世間》將背景放在20世紀60年代末,反映歷經幾十年的當地變化。編劇在創作中巧妙地將大環境放入家庭小環境下,加入其他視覺符號,滿足觀眾的審美期待和心理需求。由此可見,電視劇《人世間》不僅遵循類型化的成規,也具有明確的時代指向和現實表征。這種文化圖式建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與靈魂,是中國人千百年以來的生活寫照。由于時間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嬗變,劇中引發了許多人的共同回憶,在特殊的社會語境中構筑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是在一個群體里或現代社會中人們所共享、傳承以及一起建構的事或物①。像《人世間》這樣的電視劇在社會語境的結構性制約與創作者主體能動性中尋找自身的發展路徑,向著真情背后的文化圖式成功邁進。2022年1月開始熱播的《人世間》,使得不同年齡段的受眾在劇中都找到了認同感和歸屬感。世間總有磕磕絆絆,同行的還有人性的溫暖和生活的煙火氣息。在《人世間》這部劇中,有許多富有年代感的物件,如磚房、東北土炕、燒火的土灶、喝水的瓷缸子等,都生動地反映出那個年代所具有的特色。它們代表著老一輩的集體記憶,又糅合了當下人們對當時年代的理解與感受。正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世間》這樣的電視劇通過集體記憶的符號隱喻傳達出正確的社會價值導向。
二、《人世間》的敘事藝術
(一)角色符號彰顯脈脈溫情
《人世間》作為一部有深度的影片,導演借助時代洪流,以崢嶸歲月的溫情去打破世俗常規來敘述整部作品。形象的塑造與作品相互配合,成為點燃觀眾思想情緒的一劑良藥,也成為作品主題表達的重要手段,更能在吸引觀眾注意力的同時讓觀眾獲得心靈的震撼。《人世間》劇中將周家三兄妹(周秉義、周蓉、周秉昆)代表的“光字片”區居民為起筆,父親周志剛參加西南地區的“大三線”建設,周蓉追隨愛情去了貴州下鄉,家里只留下小青工周秉昆和母親。這樣的劇情設置營造了年代感,強化了代入感。劇中周秉昆的角色符號塑造得很成功,在敘述中著墨最多。他是“民間倫理本位意識”和“好人文化觀”的角色載體。對理想主義的愛情堅守,友情道義的擔當,親情守望的主心骨,是周家幾代人的角色符號。導演在劇中借著這些符號,把沉浸于中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的生活狀態以及身心所賦予的儒家文化,展現給世人看。
每個人物身上都被賦予了一種符號化象征,“名、權、利”以角色為線索,在出現之前都必須變成一個故事。零起點的他們在奮斗與努力中成就了自己,平民化的角色拉動著觀眾的認知心理。周秉義代表“權”,一生為“仁義”而活,可以說是人民心中的好公仆化身,一心向正,沒有一絲污點。周蓉代表“名”,是浪漫自由的知識分子,敢愛敢追求,在生活中磨平了棱角,角色立體鮮活。周秉昆代表了“利”,哪怕具有再優越的條件,但不被父親認可,沒有正式工作的編制也是不行的。看似發生在20世紀,卻與現實生活貼得很近,能讓受眾產生情感共鳴。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亙古不變的是“家”文化的傳承。留心觀察《人世間》中如喬春燕、鄭娟、曲書記這樣的女性形象,觀眾會發現其角度之深刻。角色中把充滿裂痕的情感關系裹藏在人性溫柔之下,讓女性的形象在劇中有了新的含義,對當下年輕人的生活起到了一定的啟示作用。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下,男子地位高,女人就應該以家庭為主。而周蓉是一位有文化、有學識的女性,在她的人生經歷中,可以看出女性地位的提升,更符合當下的社會觀念。這部劇的表現方式與以往的不同,個人視角下的所見所聞成功消解了劇中宏大敘事的刻板印象,不再渲染大背景,而是把重點放在劇中人物身上,角色聯動,更能引發受眾思考,充滿了生活化氣息。不脫離現實,讓受眾能產生自我折射,對當下人的家庭觀、婚姻觀具備現實關懷作用。在以往電視劇中,通常歷史是主體,個體為主體敘事服務。進入新時代后,為了制作更加精良的作品,拉近與觀看者的距離,劇中的敘事視點發生了轉向,個體成為敘事主體,更具貼近性。
(二)時空符號展現情感脈絡
如何讓敘事結構把劇中包含的元素有機地整合到一起,向觀眾呈現完整的視聽故事成為重中之重。《人世間》按照時空符號順序,以周家三兄妹為主,講述他們身邊各個階層人物的生活和命運,伴隨時代轉折下的夢想與堅持。看似平凡的生活,自然流露出點點滴滴的細節,都能撐起劇中情感的脈絡起伏。在每一集中都會有幾個矛盾沖突點,在認知角度下,通過環境的轉變與人物關系來激發受眾的情感。不同時空背景下的人物故事改變著受眾的心理節奏。在觀看作品時,故事發展脈絡、時空架構、情緒基調的把控、人物的動作和語言節奏形式及各種角度所揭示的人物情感和情緒,都影響著觀眾的主觀感知。即使是在線性敘事中,該劇的節奏也不拖沓,而是緊湊巧妙地弱化了時代背景,就此突出不同時空下的人物關系圖。
由趙孝思、沈亮所著的《影視劇作的敘事藝術》一書將敘事的空間分為大空間和小空間,大空間是說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小空間則是他們生活的地方,矛盾沖突發生的地方②。在電視劇《人世間》中也有著這樣的敘事空間。編劇很巧妙地把大的背景放在了小人物身上,通過他們的故事架構展開敘事。就居住環境來看,《人世間》聚焦在吉春市“光字片”這一平民社區;就時代屬性而言,導演選擇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現在的年輕人對于1969年到1988年這19年的生活是比較陌生的,該劇以平民為代表,從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體現時代的變遷。本來是大的歷史,卻定格在一群小人物身上,在小環境下用故事來敘事,以此讓觀眾感受到以周家為代表的幾個家庭在生活中情感交織的矛盾。劇情有起有伏,每個人物在生活背景的壓迫下也逐步轉化,這樣的敘事讓觀眾更能體會到真實。歷史只是劇中的背景,只有好的故事結構才撐得起它的內核,這樣的結構安排的確很精妙。
(三)文化符號一窺內容之美
文化符號是一種高度濃縮的價值觀念傳播載體,它在傳播信息方面有效便捷、易于辨認、認同度高,是文化傳承、傳播的高效工具,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象征符號。能指與所指的符號分類單一,擴展后可賦予其更多的文化象征內涵。在《人世間》中,周秉昆不顧家人阻攔及周圍人的閑言碎語,勇敢追求幸福,娶了鄭娟。正是這種單純而熾熱的情感,才寫下了那段最美的愛情宣言。《人世間》也表現了一種綠葉對根的情誼。與原著相同,堅持將工人群體的藝術形象置于作品的高光時刻,謳歌周秉義、周志剛他們這一群人的奮斗精神,他們不與命運妥協,一直隱忍與堅持。該劇以微小的事件或沖突為切入點,慢慢展開敘事,身在劇外,心隨劇行,以小見大。拒絕簡單化的劇情,在追求真實感的過程中,還原大半個世紀中國人吃穿用度的細節。物件在劇中顯得格外突出,大眾澡堂、綠皮火車、糧票、郵票等,均勾勒出一幕幕鮮活的生活畫面,也展現了東北吉林當時的風貌全景。該劇最終表達一個宏大且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體現著一部精良作品所帶給觀眾的美學意蘊和藝術價值。
法國著名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在文章《攝影影像的本體論》中提出電影現實主義理論。他認為,人類追求真實來復現內心所需,這就要求電影電視劇技術內容的完善,“電影是現實的漸進線”,與任何藝術對比都更接近生活現實③。因此,在進行藝術創作時,無論是從主題、內容還是形式方面,都應時刻注意藝術的審美作用。美學的特征顯得很突出,在形式上,注重作品整體的格調和意境,特別注重細節真實。從演員在不同時代的服飾變化、造型、臺詞、動作,到使用的道具、場景還原等,都是經過導演們的精心考量、打磨而成的。比如周秉昆穿著的被接了好幾節的紅色毛褲、接雨水的盆子、冬天房屋外檐做的長冰美術工藝,可以看出劇組在每一處細節上都很用心,力求真實,在體現深刻主題的基礎上帶給觀眾記憶的共鳴。
值得一提的是,《人世間》中的一首同名歌曲,將承載50年光陰的一家人的苦樂年華表達得非常清晰。從開始低訴到中間的婉轉悠揚,再到最后的謳歌,“草木會發芽,孩子會長大,歲月的列車不為誰停下”,辭藻間與劇中人物命運的關系緊緊相扣。不管世間有多少滄桑變化,平凡的小人物都能夠撐起屋檐下的一方煙火。歌曲渲染了當年崢嶸歲月中發生的故事。劇中用不同的音樂旋律劃分,既交代了大的時代背景,又規避了直接、生硬的表現。最難能可貴的是,電視劇呈現出真實的視覺效果,令欣賞者心曠神怡。用音樂調動觀眾的情緒,撫慰每一個靈魂,溫婉或深沉,抒發了人物在時代下的情感,以及對“家”不變的信仰。
三、《人世間》精神眷戀的隱喻寄托
家國情懷和文化倫理在《人世間》是有所體現的,時間跨度50年,體現其間的人生故事。有人在《人世間》劇中看見了歲月的傷痕,有人在劇中看見了生活的苦難,也有人在劇中看見了溫情與希望。伴隨著時代的變遷,愛情早已升華為親情,《人世間》表現了傳統文化中平凡又感人的情感主題。這樣的設計歌頌了主人公對待愛情的精神,也是一種小家情懷的表達。在《人世間》中,周秉昆用善良溫暖了鄭娟,鄭娟的付出給予了周家母親第二次生命,作品之外還有創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孝道”的堅守。周志剛只有一場三線隧道工作的場景,表現他一次次放棄回家過年的機會。在這樣的職業精神下,從生活的角度去打磨人物的高光時刻。作為一種常見的影視表現形式和文化載體,因與“非虛構”和“信息價值”緊密相關,這樣的劇作建構旨在讓觀眾在感受情感的同時能重新審視他們一生的艱苦歷程。
家國情懷是大部分中國電視劇導演都非常偏愛的主題。劇中不乏浸潤中國人身心的“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文化。在《人世間》的結局中,周秉義患了胃癌,令觀眾感到惋惜。他一生銘記父親的教導,兢兢業業,不給周家丟臉,不給國家拖后腿,拼盡最后一口力氣也要改變“光字片”,讓大家過上好日子,盡自己所能去改變現狀。將個人命運與家國命脈交織纏繞,以映照歷史的人文視角呈現出一種家國同構的史詩格局。該劇的著眼點不僅在愛國的民族大情懷上,更凸顯出中國傳統文化下的家國情懷與文化倫理的表達。從周父口中可以隱約感受到家是《人世間》這部劇的主題,在老“光字片”中也有體現,而“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五條街道則暗喻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觀。既定的軌道,復雜的人世間,周家三兄妹的人生軌跡也緊緊跟隨時代的洪流,代表著五四運動以來第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識。長兄周秉義響應黨的號召,最終成為清正廉潔的公仆,一生兢兢業業;二姐周蓉是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過于理想化;三弟周秉昆是踏實能干的工人,也是真正維護周家的人,恪守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而劇中的人物都是歷史的縮影,“小家庭、大國族”“小情感、大故事”。將普通的人物深深嵌入時代的畫卷之中,以不同的人物情節體現時代烙印,讓觀眾深刻感受到故事的轉變以及劇中隱藏的深厚文化內涵。
四、結語
有學者認為,《人世間》恰如一江浩蕩的生活流,在50年的蜿蜒曲折中寫出了國家發展和老百姓生活的磅礴變遷,其中流淌的人與人之間的無限情義深深打動并溫暖了觀眾的心,堪稱一部當代中國的影像心靈史詩。所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人世間》正是在這情、義與語之間達到了高度的藝術平衡,彰顯了主題創作中重大現實題材電視劇的新高度④。在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的觀照下,《人世間》這部電視劇具備真實的歷史故事。在歷史和現實中,書寫了當代中國百姓的生活史詩,既沒有脫離歷史的軌道,又與現實契合,并非用一些背景史來謀取噱頭,而是讓人物故事富有現實浪漫的色彩,展現出溫柔敦厚的情感。在此過程中,劇情形成了一種相互拉扯的張力,耐人尋味。《人世間》通過平實的敘事,年代生活的點滴營造,給觀眾呈現出久違的平民感,讓觀眾一下子回到那個充滿濃郁人情味兒的年代。劇中角色符號更加點明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從美學角度看,《人世間》注重作品整體的格調和意境,服飾、道具等一系列文化符號讓真情在劇中出圈;用音樂調動觀眾的情緒,溫婉或深沉,抒發了人物在特定時代下對親情、愛情的表達;在符號學視域下探究影視劇中的敘事藝術,用傳統文化中平凡感人的情感主題來體現小家的情懷,讓觀眾產生自身觀照,引發情感共振。《人世間》不僅具有教化方面的價值導向功能,而且為電視傳播發展的再生產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注釋:
①王明柯.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53-56.
②蔡騏.影像傳播中的歷史建構與消解——解析電視傳播中的“口述歷史”現象[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02):59-67+111-112.
③鴻鈞.巴贊是什么?——巴贊電影真實美學與文化人格精神讀解[J].當代電影,2008(04):33-44.
④張斌.《人世間》:人世間浩蕩的是情義無限[EB/OL].中國青年網,2022-02-1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5063479216585109&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