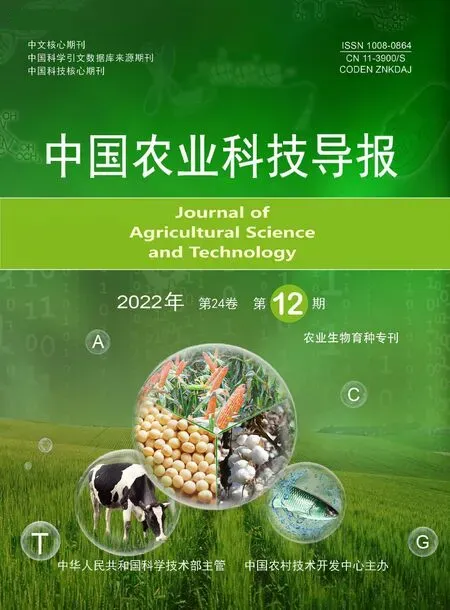農業合成生物研發與風險管理
王旭靜, 燕永亮, 王友華, 唐巧玲, 焦悅, 王志興*
(1.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北京 100081; 2.農業農村部科技發展中心,北京 100176)
合成生物技術作為21世紀的一項顛覆性技術,是通過引入模塊化概念和系統設計理論,對生物體進行設計改造或者從頭合成全新人工生物體系,是分子生物學、工程學、信息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會聚型創新技術,具有工程化、標準化、智能化特征,正在引發第三次生物科學革命和推動產業方式變革[1-3]。合成生物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有望解決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抗逆、環境資源等制約農業發展的世界性難題,為保障糧食安全、發展生物經濟注入新動能,已成為全球科技競爭戰略制高點[4]。同時,合成生物技術與其他技術一樣,是一把雙刃劍,在給人類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潛在風險,需加強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
1 農業合成生物技術的發展歷程
合成生物技術最初由Hobom[5]于1980年提出,表述為基因重組技術。2000年,庫爾(Kool)用合成生物技術來描述生物系統中非天然存在的功能性有機分子的合成[6]。同年,Mcadams等[7]在大腸桿菌中成功構建第1個基因開關,標志著合成生物技術時代的正式開啟[8]。隨后,2002年在大腸桿菌中成功構建了用于生產青蒿素的甲羥戊酸途徑;2006年成功構建了產青蒿素的酵母菌;2010年,人工合成的蕈狀支原體基因組邁出了人工合成基因創造新細胞的歷史性一步。自此,生命科學從“認識生命”走向“合成生命”的新階段[9-11]。2013年,Paddon等[12]完成酵母中青蒿素半生物合成工藝,從酵母中合成青蒿素使抗瘧疾藥物成本下降90%,被認為是合成生物技術應用的里程碑事件。自此,合成生物技術在生命健康、環境資源和農業生產等領域的創新應用發展迅速,預計到2025年市場規模將突破200億美元[4]。
從合成生物技術的概念和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合成生物技術與轉基因技術在研究內容和技術方法上是重疊的,合成生物技術使用的元件和模塊在轉基因技術中同樣使用,二者都需要用到DNA重組技術和遺傳轉化技術等。區別在于轉基因技術只是轉化少量外源基因,而合成生物技術傾向于轉化多基因甚至整個代謝通路,從系統層面實現對植物體系的從頭設計與改造。可以說合成生物技術是轉基因技術的延伸和迭代升級,比轉基因技術更具有不確定性和復雜性。
2 農業合成生物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2.1 國際農業合成生物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合成生物技術成為全球農業科技競爭戰略制高點。美國作為合成生物技術的領頭羊,多次以總統令的形式發布對合成生物技術的戰略部署,2022年9月,時任總統拜登發布“推進生物技術和生物制造創新以實現可持續、安全和有保障的美國生物經濟”的行政命令,舉全國體制推動合成生物技術的創新應用。歐盟于2014年推出《歐洲合成生物學下一步行動》,“歐洲地平線”項目計劃在2021—2027年投資1 000億歐元用于支持合成生物等前沿基礎和技術創新研究。英國2012年發布《合成生物學路線圖》,2016年實施《英國合成生物學戰略計劃》[13-14]。
合成生物技術成為市場資本追逐的新方向。據統計,僅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合成生物學市場的投資額高達46.08億美元,同比增長409%(據Synbiobeta的數據顯示,https://www.synbiobeta.com/)。巴斯夫、拜耳、陶氏化學等大型跨國化工集團斥巨資投入,金融和風險投資積極介入合成生物學領域,創立了以 Zymergen、Ginkgo Bioworks、Twist Science、Intrexon、Amyris等為代表的超過200家的初創企業(https://golden.com/query/list-ofsynthetic biology-companies-XKB)。在農業投資領域主要關注動物疫苗、生物飼料、農業用酶、非化學害蟲控制和生物農藥等方面,如美國的Pivot Bio公司采用合成生物技術開發了針對玉米作物的 Pivot Bio PROVEN 固氮產品,融資總額高達 6億美元(www.pivotbio.com);美國Indigo Agriculture公司基于作物微生物組開發出提高作物耐干旱脅迫的合成菌群微生物肥料,估值超35億美元等(www.indigoag.com)。
核心技術創新取得突破。Shendure等[15]研發出低成本、高通量的新一代DNA測序技術,保障了“海量基因組信息”的快速積累,挖掘并建立了包含4萬個代謝反應、5 000多個合成生物途徑的大數據集。基因編輯、DNA合成技術、染色體工程技術、生物信息技術等前沿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元件設計、底盤適配和元件裝配奠定了良好基礎,加速了認識和改造生命的步伐,目前已發展到真核生物基因組的合成和優化階段[16-19]。
研發出一批農業合成生物產品。研究人員開發出系列生物傳感器,包括檢測植物內源激素信號的熒光共振能量轉移生物傳感器ABACUS和ABAleon、檢測植物營養物質改變的生物傳感器cpFLIPPi以及對生物和非生物逆境做出反應的植物前哨生物傳感器等[20-22];創制出比野生型水稻葉酸含量高150倍的生物強化水稻,生長量提高40%的含有人工合成光呼吸旁路的水稻等新種質[23-24];開發出系列細胞和植物工廠,如Amyris公司在酵母菌中構建了青蒿素半生物合成工藝,產量提高10倍[12];在本氏煙草中重構天然產物的通路,成功合成長春花堿等多種天然活性物質[25-26]。
生物安全評價技術同步發展。各國在加強合成生物技術研發的同時,十分重視生物安全科技創新,在技術研發與產品應用的風險形成機理、安全評價與檢測技術及產品研制方面取得一系列進展,努力構建全方位的生物技術安全科技支撐體系。基因組、轉錄組、蛋白組、代謝組等多組學協同識別合成特征,解析風險形成的分子機理和可能產生的非預期效應[27-30]。大數據驅動生物技術產品高效精準溯源及檢測技術發展,實現對DNA的實時、無信號標記、無需標準物質的絕對定量測量[31-32]。此外,毒蛋白、過敏原數據庫逐漸系統化,研制出系列環境和食用安全評價與檢測產品、標準和規程[33-34]。
2.2 我國農業合成生物技術研發與應用
我國高度重視合成生物技術研究,積極加強合成生物技術戰略布局,習近平總書記2015和2016年2次對合成生物學發展做出重要批示。“十三五”期間,科學技術部在合成生物學領域先后啟動10項“973”計劃項目和1項“863”計劃重大項目;2018年啟動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合成生物學專項。《“十四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將合成生物技術列為引領產業變革的顛覆性技術。未來10~20年,我國將實施農業合成生物技術“三階段跨越”發展戰略,通過技術跨越(2020—2025)、產業跨越(2025—2030)和整體跨越(2030—2035),促進我國農業合成生物技術研究開發與產業化整體水平達到世界先進水平[4]。
我國合成生物學研究雖然起步稍晚,但呈現迅猛發展態勢。研究人員發掘和表征了一批產量、抗鹽堿、抗干旱、固氮泌銨、氮高效利用等元件[35-39],評估了抗逆功能器件和最小或最佳固氮裝置[40-41],發展了利用微生物成像質譜和組合生物合成技術平臺,合成了系列新型“非天然”聚酮化合物[42-43],首次實現了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44],創制了富含花青素的“紫晶米”等新種質[45]。此外,在高光效C4水稻的設計研究、人工耐銨泌銨固氮工程菌等創建方面也取得積極進展[46-49]。
3 農業合成生物的安全管理
合成生物技術是基因工程技術發展的新階段,其潛在風險與轉基因技術的風險點類似,存在誤用濫用帶來的倫理問題、生態安全風險和食用飼用安全風險。目前,國內外已建立了科學有效的轉基因生物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體系,將農業合成生物產品納入轉基因生物監管體系,能夠防控潛在風險,保障產業健康發展。
3.1 農業合成生物的潛在風險
3.1.1 倫理風險 合成生物技術突破了傳統的自然進化歷程和限制瓶頸,改變了人們對進化的認知,帶來了差異化的生物倫理思考和擔憂[50-51]。在農業領域,合成生物技術主要用于解決世界性農業難題,為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抗逆和生物質轉化等難題提供解決途徑,不會引起在醫療領域對生命不尊重等方面的倫理道德問題,但會產生誤用濫用所引起的科技倫理問題,如將毒蛋白、過敏原、抗營養因子等導入底盤生物。所以,需要加強倫理審查,提升研究者的倫理規范意識,通過體制機制建設杜絕違背科技倫理的行為,趨利避害。
3.1.2 合成特征風險 合成生物中導入多個組件,與底盤生物整合過程中可能產生染色體重組、基因重排而干擾底盤生物的基因表達和特征特性,產生一些新的功能而引起非預期效應,以及組件能否穩定遺傳等[52]。這些合成特征方面存在不確定性和復雜性,需要從組學水平精準解析合成特征,從分子水平識別生物組件對底盤生物基因表達和遺傳穩定性的影響。
3.1.3 生態風險 合成生物改變了底盤生物的代謝途徑和表型特征,其生存適應性不確定,有可能會改變其生存競爭能力;釋放到環境中,導入的生物組件可能會通過基因飄流而在不同生物間傳遞,可能會對有益生物等其他非靶標生物產生潛在影響,也可能會對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生態群落以及有害生物地位演化產生影響等[53-54]。這些不確定性和復雜性都可能會帶來一定的生態環境風險,需進行環境安全評估。
3.1.4 食用和飼用安全風險 合成生物存在插入的生物元件DNA片段和轉錄RNA的安全性,如表達蛋白是否會具有毒性、過敏性、致畸性等[55-57];除了目標產物外,代謝中間產物多樣,是否影響底盤生物的食用和飼用安全;外源基因插入而引起的底盤生物組成預期和非預期的變化,從而影響食用安全性問題等[58]。合成生物需要從營養學評價、新表達物質毒理學評價、致敏性評價等方面進行評估。
3.2 農業合成生物的安全管理
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科研機構等基于對合成生物學理念的理解,結合合成生物特性,提出了合成生物學的管理設想。2014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二次締約方大會明確了合成生物屬于《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中關于改性活生物體的范疇[57]。目前,歐盟、美國等以生物技術和遺傳修飾生物為切入點對合成生物技術產品進行監管和治理[59-60]。
美國通過聯邦立法為合成生物提供明確的制度依據,衍生出行業規范,實行從研發到市場全鏈條多頭監管。實驗室研究管理隸屬于國家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NIH 重組DNA咨詢委員會認為,在多數情況下其生物安全風險類似于重組DNA研究,當前的風險評估框架能夠用來評估合成生物的研究。為了提供關于合成核酸風險評估和管理研究的基本原則和程序框架,NIH將重組DNA分子研究指南改編用于重組或合成核酸分子的評估指南[61]。農業合成生物與轉基因作物管理框架和模式相同,由農業部、環境保護署和食品藥物管理局3個部門依據《生物技術管理協調框架》協同管理,重點評估產品的分子特征、環境安全和食用安全3方面[62]。
歐盟對新技術采取的是預防原則,認為新技術存在潛在風險,采取以過程為基礎的安全評價管理模式,總體上對轉基因產品控制十分嚴格。歐洲食品安全局是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專門機構,負責對轉基因產品全過程監控,并為歐盟委員會和各成員國相關法規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歐盟認為合成生物仍屬于重組DNA的技術范疇,已建立的轉基因生物和病原體風險評估標準、方法和風險管理體系在農業合成生物監管中仍然適用,應將其納入現有的轉基因生物監管法律體系中[51,63-64]。
我國已建立了一套科學規范并符合國情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體系,具有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健全的管理體系和強有力的技術支撐體系。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既針對產品又針對過程,依照受體、基因、遺傳操作的風險高低實行分級分階段評價管理,在任何一個階段發現任何一個對健康和環境不安全的問題,都將立即終止以確保安全。依據我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對轉基因生物的定義,農業合成生物也屬于基因工程技術的范疇,依據轉基因生物管理體系對其監管可有效防控風險。
4 結語
農業合成生物技術作為一項“會聚研究”技術,通過BT+IT的交叉融合,正在引領現代農業跨越發展,為解決農業發展的制約性問題、促進生物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但也面臨著風險和挑戰,需要加強風險評估和安全監管。我國農業合成生物技術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整體研發水平處于發展中國家領先地位,并向國際先進水平跨越,但在智能技術研發、技術集成創新、產業化應用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建議統籌布局,強化科技創新,加快推進元器件挖掘、人工智能、細胞工廠等基礎研究,提升基礎前沿與應用轉化的融合。與此同時,加強風險評估和安全監管,科學防范風險,強化農業合成生物技術風險識別與預警、風險評估與檢測、風險防控技術等安全創新研究,提高風險評估能力;加強生物安全監管,在現有轉基因生物管理框架的基礎上,基于主要國家合成生物安全管理政策邏輯分析框架,提出符合我國國情、與技術水平相協調的法律治理對策和生物安全監管機制,嚴格農業合成生物技術研發應用監管與科研倫理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