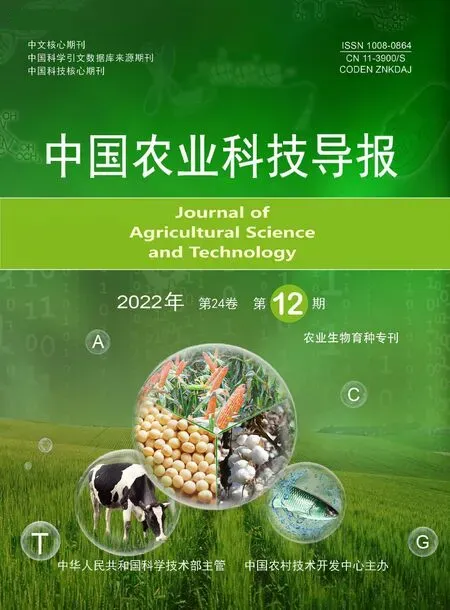生物育種產品食用安全評價研究進展
徐彤曉, 賀曉云, 黃昆侖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農業農村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食用)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3)
生物育種是利用遺傳學、細胞生物學、現代生物工程技術等方法原理,利用轉基因、基因編輯、全基因組選擇和合成生物學等技術,培育生物新品種的過程[1]。現代生物育種新技術是基于分子生物學工具進行作物分子育種的一類新技術,可以短期內使作物產生新的有利性狀,促進作物新品種的開發,如基因編輯技術、RNA干擾技術、同源轉基因技術等[2]。其中,轉基因技術是現有生物育種技術中發展最快、效率最高的針對作物單一性狀改良的技術。生物技術食品是指利用轉基因、基因編輯等生物育種新技術改變基因組構成的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產生的產品,包括動植物、微生物本身及其直接加工品[3]。
1996年,全球生物育種作物大規模商業化生產,種植面積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迅速增長[2],在解決全球糧食問題、環境保護、提高食品營養質量、制藥業、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生物技術商品化生產的不斷深入,生物育種技術的潛在風險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全球針對生物育種新技術產生的作物新品種的安全性評價尚未達成統一共識,對其安全監管的思考也不盡相同,限制了這些作物新品種的研發和商業化應用進程[4]。本文綜述了現階段國內外生物育種食用安全性問題及安全性評價方法,并總結了國內外生物育種新技術新產品的安全性和監管方面實施的管理政策和法規,以期對我國生物育種新技術作物的安全性提供借鑒。
1 生物育種食品的安全問題
生物技術同所有技術一樣是一個中性的技術,對人類文明發展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其潛在危害的一面。利用轉基因、基因編輯等生物技術可改良農作物抗蟲、抗病、抗逆境及抗除草等生物性狀[5];還可以改善農作物品質,如蛋白質和維生素含量及營養結構等[6]。目前,應用最廣泛的生物育種產品是轉基因抗除草劑作物[7],其次是轉基因抗蟲作物[8],抗病及品性改良的生物新技術作物也已得到廣泛應用,主要涉及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等作物,生物育種食品潛在的安全問題集中在毒性、過敏性及對環境影響等方面。
1.1 毒性問題
人們對生物技術產品普遍關注的是,新基因及其產物是否具有固有毒性,宿主代謝途徑的改變及固有毒性或藥理活性物質的過度表達是否會導致生物體產生新的毒性風險[9]。多年研究發現,食品中外源DNA序列本身不會通過直接毒性或者基因轉移對人類健康產生風險[9],如果新表達蛋白質沒有在消化道中完全消化,則應關注其是否具有影響健康的作用。
1.2 致敏性問題
食物過敏主要是由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in E,IgE)介導的速發過敏反應[10]。致敏性是生物技術食品的另一個潛在風險,其表達的新蛋白或在胃腸內消化后產生的殘留片段可能導致過敏風險[11]。因此,安全性評估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評估轉基因植物及其產生的新蛋白質的致敏性。
1.3 營養問題
生物技術食品的營養問題主要集中在原材料關鍵性營養成分是否發生改變。利用生物技術插入外源基因或編輯體內基因的目的是改變靶生物特定的營養成分,提高其營養價值,如低芥酸油菜等[12]。通過生物技術改變性狀后,人們普遍擔心該食品會不會因為提高某種關鍵性營養物質而降低其他關鍵營養物質含量,或提高某種毒性物質表達等問題[13]。另外,由于外源基因的來源及導入位點的不同和隨機性,有可能導致基因缺失、錯碼等突變,從而使目標產物的性狀、數量及部位與預期不符,進一步產生非預期效應[14]。
1.4 其他問題
抗生素標記基因是生物技術食品對人類健康的另外一個安全威脅[15]。存在于生物技術食品中的標記基因,經攝入后可能會通過水平基因轉移和重組轉移到人和動物體的腸道細菌或病原體中,從而使這些微生物產生抗生素抗性,進而影響人或動物抗生素治療的效果[16]。
2 食用安全性評價方法
隨著生物技術飛速發展,生物育種產品逐漸商品化,生物育種食品安全性評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生物育種食品在進入市場前要經過全面的安全性評價。到目前為止,凡是經過政府部門嚴格審批獲準上市并進行科學評價的生物技術食品都是安全的。對生物技術食品的安全性評估是一項復雜且精細的綜合性工作,目前得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聯 合 國 糧 農 組 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以及多個國家或地區認同的原則是實質等同性原則、個案分析原則和逐步完善原則等[17]。OECD于1993年提出了實質等同性原則,并得到了FAO和WHO的認同。連麗君等[18]認為,生物技術食品與現存食品在化學上的相似性并不能夠證明其對人類是安全的,應當補充毒理學及免疫學等其他方法檢測,通過更有效的評估系統提供更具有說服力的數據。歐盟認為,實質等同性僅是將新食品與相似的傳統食品比較,并不是安全的營養學評價,其對生物技術食品安全性評價是有用的,但不是唯一的[19]。發展至今,食用安全評價內容主要包括營養學評價、毒理學評價、致敏性評價以及非預期效應評估。
2.1 營養學評價
生物技術食品的安全性評價主要是基于實質等同性原則,實際上是一個比較的原則,即將生物育種食品與長期安全食用的對照物進行比較分析[20]。近幾十年來,在輻照食品、新型食品和水果蔬菜的動物安全和營養測試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方法也適用于生物技術食品以及飼料的安全性和營養性評價。
生物技術食品與原食品在關鍵性營養成分上的差異可作為安全性評價的綜合指標之一。關鍵營養成分指主要營養素和微量營養素,主要營養素包括脂肪、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等,微量營養素包括礦物質、氨基酸、脂肪酸和維生素等。Padgette等[21]對耐除草劑G2-Aroa玉米、轉AO高植酸酶玉米及其非轉基因玉米的主要營養成分(水分、灰分、脂肪、粗蛋白和纖維)含量進行了比較,發現材料間上述營養物質含量差異不顯著,總體營養水平相當,個別差異屬于自然變異,且均符合國家標準并在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參考范圍內。對抗草甘麟大豆與常規大豆關鍵性營養成分的研究,并未發現二者存在差異[21]。對轉生長素基因鯉魚與普通鯉魚肌肉中粗蛋白質、粗脂肪和氨基酸等主要營養成分,以及鈣、鎂、鋅、鐵、灰分等微量營養成分的研究表明,外源基因插入對轉基因鯉魚肌肉中氨基酸含量等主要營養成分沒有影響[22-23]。周興華[24]將具有抗蟲性和耐除草劑的轉基因玉米、土豆、大米、大豆和西紅柿等長期喂養大鼠或小鼠,并測量其體重、進食量、血生化、血常規、臟器系數、組織病理學等參數,并沒有表明暴露動物臟器或組織的病理學異常。
2.2 毒理學評價
對于利用生物技術引入植物體的新表達蛋白質的毒理學評價一般包括新表達的蛋白質與已知毒性蛋白質氨基酸序列的相似性比較、體外模擬胃液蛋白消化穩定性試驗、新表達蛋白質熱穩定性試驗、小鼠急性經口毒性試驗以及大鼠90 d喂養試驗等。
生物技術食品的毒理學研究主要通過動物試驗來完成,目前常用大鼠、小鼠、斑馬魚、小型豬和雞等動物進行試驗。轉基因食品毒性評估方法包括微核試驗、精子畸變試驗、艾姆斯試驗、急性口服毒性試驗、90 d喂養試驗等。主要測定指標與營養學評價類似,包括體質量、進食量、血常規、血生化、尿液指標、臟體比等。轉基因魚的毒理學試驗結果表明,攝食轉“全魚”基因的小鼠,其生長、血常規、血生化成分、組織病理、生殖機能以及子一代的生長和發育等都沒有顯著性影響[25]。
OECD關于單一明確定義化學品的指南試驗中所述的單劑量和重復劑量毒性試驗、生殖和發育毒性試驗以及免疫毒性試驗方法足以對單一物質進行安全性試驗。同時還有一些體外方法可能有助于轉基因植物衍生食品和飼料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評估,如通過搜索新蛋白質或其降解產物與已知毒性蛋白質的序列同源性或結構相似性;用于研究新表達蛋白的消化穩定性的模擬胃液和腸液試驗,用于模擬新蛋白在加工過程中的穩定性的熱穩定性試驗;預測外源基因產物是否導致基因突變、染色體畸變和DNA損傷和修復的體外遺傳毒性試驗等[26]。
2.3 致敏性評價
生物技術食品中新基因所表達的蛋白有可能引入新的致敏原,有些蛋白質在胃腸內消化后的片段也可能存在致敏性[27],如對巴西堅果過敏的人對轉巴西堅果基因的大豆也過敏[18]。目前,對生物育種食品致敏性評價的重點是基因來源、新引入蛋白質與已知致敏原的氨基酸序列是否具有同源性、新引入蛋白質與變態反應個體血清IgE的免疫結合反應、體外模擬胃腸液消化穩定性、動物模型。
Dunn等[28]研究評估轉基因大豆品系、近等基因品系和其他3個商業大豆品系的IgE結合蛋白的潛在差異,基于血清IgE免疫印跡,在大豆品系之間鑒定出微小的質量差異,然而,根據抑制ELISA試驗,不同大豆提取物與混合血清的反應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部分研究采用嚙齒類動物模型及體外模型進行關于轉基因食品致敏性的研究[8]。研究人員給大鼠喂養MON 810玉米,沒有誘導Cry1Ab特異性免疫反應,也未產生抗Cry1Ab抗體[29]。Cas9(CRISPR)/Cas9系統的廣泛使用使得研究人員關注Cas9和Cas9基因編碼的肽的免疫原性,在體外模擬胃液中用天然或熱變性Cas9測試消化率,發現并沒有表現出導致過敏性的免疫原性[30]。
2.4 非期望效應評價
對生物育種產品的非期望效應評價常采用轉錄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等非靶向技術。組學技術可以可視化營養或環境改變時生物體發生的所有變化,不僅可以用于評估生物育種產品本身,也可以用于受試對象的研究。例如,采用宏基因組技術探究轉基因食品對于動物腸道菌群的影響,Zhang等[31]給SD大鼠喂食非轉基因大米及不同水平表達人乳鐵蛋白(hLF)的轉基因(GM)大米Lac-3,結果表明喂養70%表達hLF的轉基因大米的SD大鼠,腸道微生物群結構略有變化,喂食不同hLF表達水平轉基因大米的SD大鼠腸道微生物群多樣性沒有顯著差異。此外,生物育種產品是否會發生基因水平轉移也是關注的焦點。趙志輝等[32]在分析轉基因抗草甘膦大豆對大鼠內源和外源基因遺傳轉化及其生理代謝的影響時,用轉基因大豆粉喂養大鼠,在大鼠的血液、組織和器官中均未發現內源和外源基因片段,喂養轉基因大豆與給予普通維持飼料的大鼠體重和血清方面無顯著性差異。
3 新技術新產品的安全性評價
3.1 重組酶制劑
酶制劑是指應用化學或物理方法,將酶進行分離提純、加工、修飾,制成的具有催化活性的生物制品[33]。1969年第一例轉基因微生物問世,1989年第一例轉基因微生物酶制劑獲得批準。如今食品行業利用轉基因微生物發酵生產獲得食品配料和食品添加劑已成為主要趨勢。通過發酵法生產的食品配料和食品添加劑,有近80%以上來自轉基因微生物。隨著合成生物技術的發展,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食品原料轉為微生物生產。對食品酶制劑的安全性評價主要采取毒理學研究,包括遺傳毒性試驗、小鼠經口急性毒性試驗和大鼠90 d經口毒性研究,此外還需要進行致敏性研究和飲食暴露評估,通過以上試驗檢測指標后,方能證明某種食品酶制劑是安全的。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于2022年10月通過毒理學、致敏性評價,批準1項轉基因黑曲霉菌株產生的食品酶β-半乳糖苷酶的安全性評估,該食品酶主要用于加工乳清。EFSA食品接觸材料、酶和加工助劑專家組(food contact materials, enzymes and processing aids,CEP)認為,盡管在預定使用條件下不能排除飲食暴露引起的致敏性風險,但這種可能性很低。因此CEP得出結論,該食品酶在預定條件下不會引起安全問題[34]。
3.2 RNA干擾
RNA干擾(RNAi)是指在進化過程中高度保守的、由雙鏈RNA誘發的、同源mRNA高效特異性降解的現象。RNAi在自然界中廣泛存在,利用內源性siRNA在真菌、昆蟲、植物和動物等生物中調節目的基因的表達非常普遍。沒有研究表明生物技術食品中存在的siRNA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研究人員廣泛審查了與食物一起攝入的dsRNA的安全性,描述了dsRNA,siRNA和miRNA對人類和動物健康的危害[35-37]。沒有證據表明攝入RNAi食品會對人體產生不良反應,此類食物口服攝取率低,并且有許多胃腸道障礙,因此不會造成危害[38]。此外,已經有食用RNA作為食物的歷史,而攝入食物本身不會產生已知的不良反應,28 d口服毒性研究進一步支持了飲食dsRNA食物不會引起腸道吸收和不良反應的這一發現[39]。與傳統轉基因作物的食用安全性評價相比,RNAi轉基因作物沒有新型外源蛋白的表達,因此,蛋白質層面上的食用安全性可以不再作為重點評價對象,但是仍需關注RNA干擾目標基因后可能對生物體帶來的非預期的影響。
3.3 基因編輯
基因編輯技術由于其對特定位點的定向編輯功能,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基因功能研究和作物育種,并開發出了作物新品種。傳統的基因編輯技術是將外源DNA片段插入受體的基因組中,改善基因功能,進而使受體表達優良的性狀,獲得人類需要的品種。隨著分子生物學的迅速發展,能夠實現對生物體基因組精確編輯的多種基因編輯技術相繼出現,能如利用核酸酶使生物體內的DNA雙鏈斷裂,以非同源末端連接或同源重組的方式對基因組DNA特定位點進行突變、缺失或者基因的插入與替換[40]。美國是最早對食品進行基因編輯的國家,于2015年批準了基因編輯的蘑菇。隨后,美國和各國科學家實現了各類食物的基因編輯,如基因編輯的水稻、魚類等。我國已利用基因組編輯技術研發了一系列的水稻、小麥和動物等新品系,2014年中國科學院遺傳發育研究所高彩霞團隊和微生物研究所邱金龍團隊合作,利用基因組編輯技術,定向突變了小麥的感病基因MLO,獲得了對白粉病具有廣譜持久抗性的小麥品種[41];2022年該團隊闡明了小麥新型mlo突變體的分子機制,表明其具有抗病性并能夠高產,而且能夠利用基因組編輯技術快速獲得具有廣譜抗白粉病的新型小麥優勢品種[42]。如今基因編輯技術已經在動植物基因功能、育種等領域廣泛應用。目前,各國對于基因編輯產品的安全性評價和管理主要采取“個案分析”的原則:①如果有新的外源DNA插入,則該產品仍將被認為是轉基因產品進行管理,②如果新品種中無外源遺傳物質且與傳統育種得到的作物相似,則可以簡化管理[43]。基于此,我國于2022年出臺了《農業用基因編輯植物安全評價指南(試行)》。
3.4 合成生物學
與轉基因食品、基因編輯食品相似的合成生物學食品也屬于高新生物技術在食品生產加工業上的應用產物。合成生物學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它將分子生物學、工程學、數學、化學、信息學等學科知識與實踐結合在一起,對生命體進行遺傳學設計和改造,從而使細胞和生物體具有特定的生物功能,使其在能源、醫學、農業、環境等領域發揮價值。合成生物學食品是將合成生物學技術應用到食品制造的各個環節中得到的可食用的物質,例如利用重組大腸桿菌發酵生產的母乳中含量最豐富的寡聚糖2’-巖藻糖基乳糖(2’-FL),目前國外已經將其應用于嬰幼兒乳粉的配方中[44]。
4 展望
由于有一些對生物育種作物負面影響的個案報道,使人們對轉基因作物的環境和食用安全性產生了極大的擔憂[45]。陳君石院士提到“對于人的消化系統來說,它不區別是不是轉基因食品,所有蛋白質進入人體都一樣進行消化吸收,至于它是什么基因,并不會影響人的基因,不必因此為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擔憂。”
美國對生物技術食品持積極支持的態度;歐盟采用“預防原則”作為管理生物技術食品的基礎[46];我國政府高度關注現代生物技術,支持和鼓勵生物育種產品的研究。由于管理更加標準化、法制化和嚴格全面的科學評價,迄今為止很少有食品和環境安全事件被科學地記錄下來。生物技術在促進農業增產增收、改善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經濟、社會效益已非常明顯。國際衛生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許多主要的國際學術機構都指出,生物技術的食物安全風險是可以有效控制的,經過科學評估和批準合規的生物育種作物與非生物育種作物一樣安全。實踐證明,生物技術育種的廣泛應用已是大勢所趨。綜上,一方面要不斷有新的生物技術應用于食品中;另一方面,我們應當及時完善生物育種產品食用安全評價方法和標準體系,為我國生物育種食品提供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