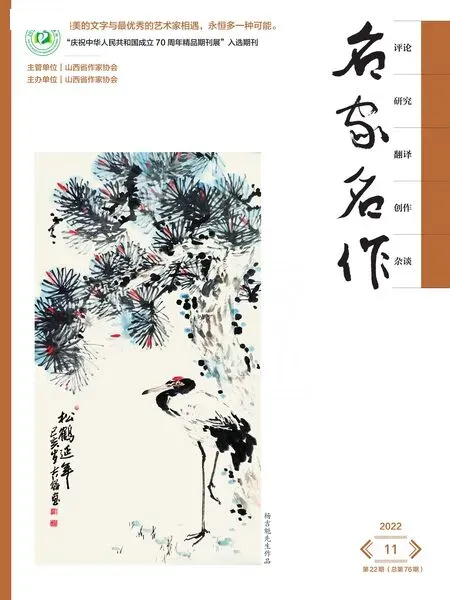賴斯翻譯批評理論關照下的《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兩種譯本對比研究
王 歌
一、《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及譯本簡介
十八世紀英國新古典主義啟蒙文學家——塞繆爾·約翰 遜 ( Samuel Johnson , 1709 -1784) 的 To the Right Honorable the Earl of Chesterfield (《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為歐洲文學史上的散文名篇。眾所周知,該信表面看仿佛是對伯爵的“感謝”,但就實質內容而言,卻是一篇充滿反諷意味的討伐權貴的檄文。
對于《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的譯本,辜正坤先生分別有文言文譯本和白話文譯本兩種。原作誕生的時期是英國古典主義文風盛行時期,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清朝乾隆年間。辜正坤選擇將古典英語翻譯成中國雅致的文言文,最大限度地考慮了這種時空對應聯系。黃繼忠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教授,也選擇把這封信用文言文進行翻譯,從內容和形式上都是很好的選擇,可見黃繼忠先生深厚的文言功底。
二、賴斯的翻譯批評理論
德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凱瑟林娜·賴斯(Katharina Reiss)的代表作《翻譯批評:潛力與制約》出版于1971年,在該書中,賴斯提出的翻譯批評理論為全面、系統、客觀地評估譯文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和模式。賴斯基于布勒對語言功能分類的基礎,將原文本分為以內容為重的文本、以形式為重的文本、以訴請為重的文本和以聲音媒介為重的文本四種文本類型,并針對不同類型的文本提出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和評價標準。
(一)賴斯翻譯批評的文本類型
賴斯是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建立了一個以文本類型為導向,同時兼顧語言內因素、語言外因素以及功能因素的翻譯批評模式。這種翻譯批評模式為翻譯批評者全面、客觀地評估譯本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和模式。根據布勒關于語言功能的理論,語言主要有三大功能,即描述功能、表達功能、訴請功能[1]。賴斯認為,和上述語言的功能相對應,文本可以劃分為以內容為重的文本、以形式為重的文本、以訴請為重的文本、以聲音為媒介的文本[2]。根據賴斯的理論,這四種不同類型的文本,針對其譯文也存在不同的翻譯評價標準。
(二)語言要素
在評價譯文時,賴斯(2004)認為首先考慮的應是原文的文本類型,其次不應忽視語言要素和非語言要素,因為二者對評價一篇譯文有一定的客觀規約作用,否則整個翻譯批評實踐過程會變成某種主觀評判,缺乏客觀依據[3]。從語言學范疇來看,語言要素主要包含文體、詞匯、語義以及語法四個方面。當從語言要素出發評價翻譯時,譯文應盡可能文體對應、詞匯準確、語義對等以及語法正確。
(三) 非語言要素
非語言要素屬于語用學范疇,對翻譯批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主要包括題材、直接情景、接受者因素、發話人因素、時間因素、地域因素以及情感內涵等[4]。非語言要素中的諸多方面對于譯本有一定的影響,且具有制約作用,作為重要因素,翻譯批評者在實踐過程中應重點考慮。賴斯提出的語言要素和非語言要素被用來評價目的語文本的充分性,這兩種要素也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
三、兩種文言文譯本的對比分析
(一)語意層面
“The notice which you have been pleased to take of my labors...and do not want it.” 作為原文的經典語句,約翰遜運用了排比與遞進的修辭方法,增強了語句的節奏感,展現出寫信人語氣的鏗鏘有力。語意層面上層層遞進、氣勢恢宏,能使讀者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辜譯為“大人而今忽有雅興垂顧拙編……再不需閣下揚譽之辭!”[5]。字詞均與源語字詞相對應而譯,用了三個排比句,且在排比句中的措辭也使語意層層推進,深刻地表達了原作者面對遲來恩惠的無動于衷和暗含的譴責之情。黃譯“閣下于拙著之錦注……不勞垂頤矣”[6]。語句較為簡練,也用了對仗工整的排比句,但是在句意上只是平行表達了成名后面對遲來恩惠的遺憾之情,沒有推進式地表達出約翰遜的心灰意冷、妻子亡故失去伴侶的經歷,對等效果上不如辜正坤譯本。
(二) 詞匯層面
“I know not well how to receive,or in what terms to acknowledge.” 辜譯:“奈何在下不慣貴人垂青,茫然不知何以領受、何辭遜謝。”與黃譯“然仆生平鮮蒙貴人恩典,是以受寵若驚,不知何以答謝”對比來看,辜將源語“how to receive”充分譯出“何以領受”,黃譯為“受寵若驚”,相比之下,辜譯將詞意表達得更充分。另外,辜正坤用了兩個“何”字更凸顯了說話人的氣勢,更能充分體現原作者寫信時的心情。
“till I am solitary,and cannot impart it”中的“solitary”,辜譯為“鴛鴦失伴”,黃譯為“孑然一身”。書信的背景是,約翰遜的妻子已于1752年逝世,他當時在寫這封信時,已喪偶3年。因此辜譯的“鴛鴦失伴”比“孑然一身”一詞更充分。譯者有義務使譯入語讀者知曉原作者當時所說的喪偶情況,讓譯入語讀者與源語讀者一樣對約翰遜心中的苦楚感同身受。
(三)語法層面
原文書信上的落款日期是“7th February,1755”,辜譯為“一千七百五十五年二月初七日”。但實際上,這樣的處理是錯誤的。當時的英國是以公歷紀年的,而辜譯的“初七”是中國農歷的表達,這樣就和原文的落款日期有所出入,很顯然屬于錯譯。而黃繼忠的“1755年2月7日”則是正確的翻譯。
第一段中的“that two Papers”,辜譯為“近日揭載二文”,黃譯為“閣下曾二度撰文”。黃將“Two papers”翻譯為“二度撰文”,即“寫了兩次”。然而,當時的切斯菲爾德伯爵共寫了兩篇文章發表在《世界報》上對此褒獎。因此對比考量,辜譯的“二文”更加準確明晰。
(四)文體層面
從文體層面來講,《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屬于書信體文本。根據書信體的寫作格式,辜正坤和黃繼忠兩位先生的譯文都符合書信的寫作特點。但在處理原文信件的日期時,黃繼忠依照原文格式將日期置于開頭,而辜正坤選擇將日期放在書信最后,這符合中國書信的特點。另外,從文體風格來講,兩個譯本所采用的文體風格都與原文本保持一致。辜正坤教授和黃繼忠先生都選擇漢語文言文來翻譯,兩種譯本都向讀者展現出了類似18世紀英語語言的古典主義文風。
四、影響兩種譯本的非語言要素
(一) 直接情景
根據賴斯關于直接情景的論述,非語言要素也許會使原作者簡化所要傳達信息的語言形式,源語讀者往往能夠用自己的語言腦補省略的情景,這便與某一段落或是某一時刻的直接語境密切相關。而譯者則需要將自己置身于原作者當時所處的情境中,才能判斷出最佳的對等詞[3]。例如,信件全文中多處將一些字母特意大寫(如Papers, Dictionary, Public, Great, Mankind 等), 在第二段運用夸張的Mankind暗示奔走于伯爵門下的文人墨客,又借用 the World 來比喻試圖收名定價于伯爵的文人寒士。以此可以知曉原作者在當時揮筆寫信時的心境,作者的語氣是譏諷的。辜正坤先生正是細細品讀了原文,將自身置于原作者的處境中深刻地感知其思想情感,才更準確地在譯文中投射出原作者的譏諷語氣。從傳達原作者嘲諷的語氣程度看,黃繼忠譯略顯遜色。
(二)時間因素
如果一個文本的語言與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密切相關,那么時間因素就會對翻譯決策產生影響。在翻譯一些古語文本時,詞匯的選擇、老式的詞法句型、特殊修辭方法的表達等都應該盡量靠近原文本中的相應用法。比如說,18世紀的文本翻譯應該與20世紀的文本翻譯有明顯區分,即使其譯者是20世紀的人[7]。正如辜正坤(2000)所言,“假如由上述中的任何一位大師來翻譯約翰遜的文章,我們自然會期望他們把這位同時代人的大作譯成頗為高雅的文言文,而絕不是白話文,這是毫無疑義的。”由此看來,辜正坤和黃繼忠先生也是考慮了時間因素,優先選擇把18世紀英國古典主義文風的書信翻譯成了同時期清朝的文言文版本,以保留古典的文風。
(三)接受者因素
接受者因素中的接受者主要指源語文本面向的讀者或聽眾。它需要嚴格與譯者心中的目標讀者或聽眾有所區分,否則會招致不同的翻譯標準。翻譯時我們將文本的接受者作為一個決定因素時,只需思考當原作者在用源語創作時意圖呈現給接受者的是什么。接受者因素往往在通俗的習語表達、引語、諺語、暗喻中影響明顯,譯者有義務使目標語讀者在自己所處的文化語境下理解文本內容[8]。例如,約翰遜在第四段引用了典故“a native of the rocks”,這在源語讀者群中是眾所周知的形象,然而對于譯出語讀者會不知所云。因此,辜正坤和黃繼忠在翻譯原文本時,都考慮到了這一影響因素,在譯文后特別加了譯注,解釋了典故的出處和含義,幫助目標語讀者理解源語含義。黃譯為“鐵石心腸之輩也”,辜譯為“草野之夫”。兩者都將源語的語意價值呈現出來,暗示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是一個毫無文化修養 、冷酷無情 、不識英才的所謂“草野之夫”。
五、結語
本文嘗試立足于賴斯的翻譯批評理論對《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的兩個文言文譯本進行對比評價。在界定原文文本類型后,分別從語言要素和非語言要素角度對兩個譯本進行對比研究,挖掘其異同。通過分析發現,盡管辜正坤與黃繼忠的文言文譯本在語法上各有瑕疵,但都屬于難得的佳作。但是對目的語讀者來說,辜正坤譯本比黃繼忠譯本略勝一籌。辜正坤譯本重視遣詞造句,典故、引語、詞匯等的翻譯較黃繼忠譯本而言更為充分對等,語言層面上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對原作的忠實。而黃繼忠譯本則較多地傾向于意譯,譯出的個別文言詞匯較為偏離源語。如源語讀者所能感受到的一樣,中國讀者讀辜正坤譯本,從字里行間能夠很容易地感知原作者的言外之意,理解原作者的自我肯定和對伯爵的批評與譴責 、藐視與諷刺,辜正坤譯本鮮明地突出了原作的主題思想。
以上筆者的分析評價難免有偏頗之處。文學翻譯實屬難事,文學翻譯批評則是難上加難。筆者在賴斯的翻譯批評理論框架下對兩種譯本進行對比分析,可見翻譯批評理論對于指導翻譯實踐、提升譯者翻譯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