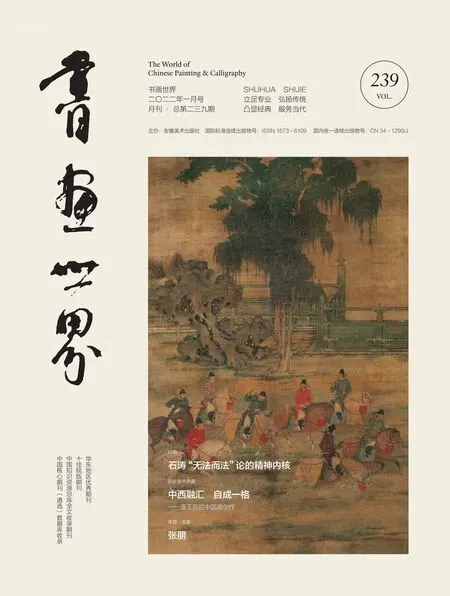淺談謝赫“六法”
徐小云
關鍵詞:《古畫品錄》;六法;梅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謝赫提出了“六法”,但他沒有對“六法”進行解釋,這就引發歷代對“六法”的內涵眾說紛紜。本文以“梅”為切入點,嘗試對“六法”的內涵進行簡要解讀。
張彥遠對謝赫“六法”有如下理解,他認為: “ 古之畫, 或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 則形似在其間矣。” 謝赫將“ 六法” 中的“ 氣韻生動” 放在首要位置,張彥遠也推崇氣韻、骨法,但是張彥遠認為“經營位置”為畫之總要。那么為何不是居于首位的“氣韻生動”?
“氣”與“韻”是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氣”與“韻”表達了中國藝術所追求的生命的律動及內在精神的統一。有一說認為應該將“氣韻生動”作為最后一法,因為它是繪畫最終所要追求的效果。筆者并不贊同這一觀點。謝赫將“氣韻生動”置于繪畫“六法”之首位,將“氣韻生動”視為繪畫藝術的本質特征。相比其他“五法”,“氣韻生動”并不是訴諸視覺形象的外在因素,而是內在的神韻、氣質。筆者比較贊同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的“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陳師曾在《文人畫之價值》中也是將“人品”放在第一位,人的品質格調決定了其創作、欣賞的水準。例如,梅是“四君子”之一,歷來就被看作高尚人品的象征,畫家往往借畫梅抒發自己的意志,而畫面帶給觀者共情力程度的高低便是判定作品是否“氣韻生動”的一個重要標準,也是創作者人品、氣質的體現。所以“氣韻生動”是衡量人品和畫品高低的本質因素。
“經營位置”,筆者理解為,藝術的表現是訴諸大眾視覺的表現形式。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最先看到的是畫的構思、構圖,即“經營位置”。筆者認為“經營位置”所要闡釋的是一種構思方法。一幅好的藝術作品的畫面該如何去經營?這涉及畫面的經營、布局、安排。而這布局安排就需要畫家周密地、深思熟慮地去反復推敲。清代鄒一桂認為:“愚謂即以六法言,亦當以經營為第一,用筆次之,傅彩又次之,傳模應不在畫內。而氣韻則畫成后得之。一舉筆即謀氣韻,從何著手。以氣韻為第一者,乃鑒賞家言,非作家法也。”清代范璣在《過云廬畫論》·《花卉論》中云:“學者不留心章法,但摹真影稿,千手雷同。”此二者皆提出了“經營位置”的重要性。以畫梅為例,筆者認為“經營位置”好比是梅樹整體的輪廓或梅的主干,而“氣韻生動”就是梅的精神、靈魂和血液。“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是梅干上的枝節、花朵和梅果,“氣韻生動”需要以這個主干,即梅樹的外形為基礎,以形傳神。雖然強調不刻意追求形似,而是著重表達梅的精神內涵,但“形”是最基本的要素。“傳移模寫”,對它的一般解釋為“臨摹、學習傳統”之義。張彥遠甚至認為此為畫家末事。還有一種解釋是:“魏晉南北朝以至唐代復制名畫(或名書)的一種技術。”更有甚者將其排除在畫外。“傳移模寫”不僅具有字面之義,而且含有“在繪畫過程中,按照物象形體,將其描繪至畫面”的內涵,即對景作畫,此種求形似之法,類似今天的現場寫生。古梅寫生,應在梅的形似基礎上融入作者的主觀情感,對所要表現的梅,首先使其符合繪畫的藝術審美需要,經過畫家的加工剪裁、藝術處理或者夸張變形等手法,將其呈現在畫面上。總之,這樣做還是要符合梅的物理、物情、物態,即正確地表現出它的內在結構和情態。
謝赫的“六法論”是一個較為完備的繪畫理論系統,它所包含的每個要素都是必不可少和相互統一的。具體體現在繪畫藝術作品中,諸要素所扮演的角色又各不相同,并互為主次關系。梅作為中國最傳統的花卉之一,是歷來文人墨客最喜歡表現的題材之一。關山月的《一笑暖千家》、齊白石的《紅梅喜鵲》,都是畫盛開的紅梅,體現出的是“幸福”“喜悅”等吉祥寓意。在這里色彩給人的視覺沖擊是主要的,色彩成了傳達物象內涵的主要形式,與之相對的就是“六法”中的“隨類賦彩”。我們畫梅不僅要表現它的外在結構,更重要的是表現它不屈不撓、不畏強暴的品格和精神,并以這種品格喻人,也就是將人的思想物化。所以古今文人畫家往往以梅象征自己高潔、孤傲的品格。如王冕的《墨梅圖》以水墨點染花朵,枝干挺勁有力,神韻秀逸。《墨梅圖》在表現技法上呈現給我們的是清雅的筆墨、勁健的骨力,以及疏淡的畫面空間感。他以骨秀神清的梅象征自己不與世俗同流、不屈服的精神品質。正如他詩中所言“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在這里畫面所體現的精神是第一位的。
謝赫的“六法”是古今品評繪畫的審美標準,是中國畫中情感表達、物象結構、筆墨、色彩等的重要品評標準。“六法”各自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相互滲透、相輔相成,“六法”不僅是對古代繪畫實踐的經驗總結,對今天繪畫理論研究和創作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應該辯證地去繼承和發展。
約稿、責編:徐琳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