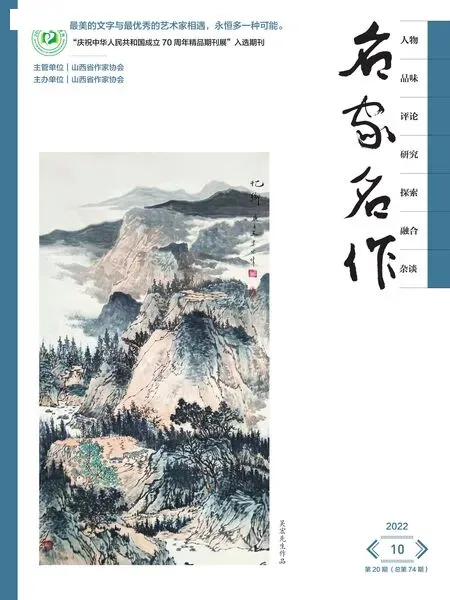“畫中又逢桃花源”
——仇英《桃花源圖卷》賞析
甘郁雯
“桃花源”一詞最早出自東晉文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文,文中所描述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lái)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fā)垂髫,并怡然自樂”的場(chǎng)景,已然成為世人心中所向往的隱居之所。正是在這樣一種對(duì)理想的追求之下,產(chǎn)生了一股桃源熱。對(duì)于這一流行的桃源文化,自然少不了對(duì)它各方面的再詮釋,不僅唐宋元時(shí)期都有相關(guān)詩(shī)文創(chuàng)作,而且李昭道、荊浩、關(guān)仝、郭熙、李唐、馬和之、趙伯駒、趙伯骕、劉松年、趙孟頫、錢選、王蒙等畫家也都有桃源圖流傳,內(nèi)容、形式不盡相同,也各有風(fēng)采。
明代以降,以“桃源”為主題元素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再次流行,一方面得益于陶淵明詩(shī)文集的廣泛流傳,在繪畫領(lǐng)域掀起一股熱潮,明四家中的幾位畫家都曾畫過(guò)該題材;另一主要原因是明代嚴(yán)苛的政治環(huán)境下,大批文人志士不愿入仕為官,由政治動(dòng)蕩所引起的避世心理引發(fā)了明人對(duì)自我覺醒和精神超越的思考與追問。
仇英是明四家中比較特殊的一位。首先在于他身份的特殊,據(jù)史料記載,仇英出身寒門,在十幾歲時(shí)迫于生計(jì)跟隨父親做了漆匠。身為工匠的仇英,與沈周、文征明以及唐寅的文人身份相比,自然是懸殊的。其次,在藝術(shù)史中,后人常把明四家分為沈周、文征明一類與唐寅、仇英一類,不過(guò)在當(dāng)時(shí),唐寅仍被認(rèn)為地位高于仇英,因?yàn)樘埔m然科考失敗,但仍屬文人之列,相較之下,即使學(xué)師周臣成為職業(yè)畫工的仇英的身份仍然與這三人有著明顯的區(qū)別與差異。再次,在于仇英繪畫風(fēng)格的不同,仇英的繪畫作品多設(shè)色,以工筆為主,山水以青綠為主,仇英的山水畫多學(xué)趙伯駒、劉松年,發(fā)展了南宋李唐、劉松年、馬遠(yuǎn)、夏圭的“院體畫”傳統(tǒng),取各家之精華,又融匯了自己的風(fēng)格,既保持工整精艷的古典傳統(tǒng),又頗有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妍而不甜的新典范。董其昌雖不推崇以工致細(xì)巧見長(zhǎng)的院體工筆畫,但對(duì)仇英本人及其作品,卻給予極高評(píng)價(jià):“蓋五百年而有仇實(shí)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非以賞譽(yù)增價(jià)也。實(shí)父作畫時(shí),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shù)亦近若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xí)。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lái)也。”
一、畫面內(nèi)容
在仇英眾多優(yōu)秀的作品中,也有這樣一幅以“桃花源”為主題的青綠山水畫。該畫以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作為素材,將武陵漁人眼中的桃花源通過(guò)畫卷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整幅畫以青綠設(shè)色為主,采取分節(jié)點(diǎn)式的構(gòu)圖方式,雖無(wú)明顯的時(shí)間分段,但通過(guò)場(chǎng)景的變換表現(xiàn)出武陵漁人的行蹤,與《桃花源記》文本一一對(duì)應(yīng),將漁人發(fā)現(xiàn)洞口、棄船探之、見桃花源、與人詢問等場(chǎng)景完美展現(xiàn)出來(lái)。畫中繪有四十多個(gè)人物,他們形態(tài)各異、表情豐富、惟妙惟肖。其中有劃船的漁夫、打柴的樵夫、扛鋤的農(nóng)夫、玩耍的男孩、閑聊的男女,每個(gè)人都在這里做著自己的事情,怡然自得,展現(xiàn)出田園生活的無(wú)限樂趣。畫中山水和人物完美結(jié)合,渾然一體,營(yíng)造出景致優(yōu)美、春意盎然的人間仙境。
欣賞仇英的《桃花源圖卷》既是一種視覺上的盛宴,也是對(duì)精神和心靈的洗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兩棵高聳的翠松,將觀者的注意力匯集于此,使觀者不自覺地將自己代入為誤入桃花源的武陵漁人,與他共享第一視角。首段,群山、云霧相互環(huán)繞,溪水兩岸的桃花正值開放,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把時(shí)間線索巧妙暗藏在緋紅的花朵之中。隨著漁人探究的深入和畫面的延展,在臨盡水源處出現(xiàn)一洞口,漁人棄船視之并走入洞穴,首段落幕。在畫卷中能夠看到在走出洞穴之后,漁人終于進(jìn)入桃花源境內(nèi),故事也迎來(lái)了第二段發(fā)展:“復(fù)行數(shù)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從漁人的視角望去,群松左下方有一個(gè)正在撐船的漁夫,可能正在捕魚。河流上端是已經(jīng)耕耘好的水田,細(xì)看,畫家將秧苗都做了粗略的表現(xiàn),阡陌之間,有一背著鋤頭的農(nóng)夫,農(nóng)夫前面有一童子,童子左手提罐,右手指向前方,似乎正對(duì)他身后扛著鋤頭的父親說(shuō)著什么。順著童子手指的方向看去,目光越過(guò)幾株不知姓名的雜樹來(lái)到山頂?shù)囊粋€(gè)涼亭上,涼亭雖小,卻五臟俱全,有座椅,有柵欄,顯然是供給忙活一天的農(nóng)人休憩的絕佳之地,飲茶或飲酒,配上絕佳的觀景位置,頗有一種陶淵明詩(shī)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適與放達(dá)。轉(zhuǎn)而,漁人的到來(lái)引起了當(dāng)?shù)鼐用竦捏@訝,打破了這里的平靜:“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lái)。具答之。便要還家,設(shè)酒殺雞作食。村中聞?dòng)写巳耍虂?lái)問訊。”由此,畫面來(lái)到第三段,漁人的突然到來(lái)讓村莊的人紛紛前來(lái)圍觀并對(duì)漁人進(jìn)行一系列的詢問,在這里,我們通過(guò)他們之間服裝與造型上的差異能夠一眼就判斷出誰(shuí)是漁人誰(shuí)是本地人,這樣看來(lái),漁人才是“悉如外人”也。這一段畫面中,著重突出了人物間的關(guān)系發(fā)展,也是畫卷的高潮之處,營(yíng)造出一種此時(shí)無(wú)聲勝有聲的動(dòng)感。背景中房屋只露出邊角一隅,坐落在群山之中,使得整個(gè)環(huán)境更具生活氣息。緊接著,視線隨著漁人變換,熱情的村民們“便要還家,設(shè)酒殺雞作食”。在他們的交談中,關(guān)于桃花源的由來(lái)也逐漸清晰:“自云先世避秦時(shí)亂,率妻子邑人來(lái)此絕境,不復(fù)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wú)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余人各復(fù)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在最后一段的畫面中,動(dòng)態(tài)各異的人物展示出了場(chǎng)面的熱鬧,他們或手提酒壇或相互扶持,準(zhǔn)備款待漁人。最后便是漁人停留數(shù)日后辭去的畫面,卷尾放大能夠看到漁人不舍地眺望著,畫中山峰、樹石的畫法皆趨于規(guī)格化,幾何形的皴法,鮮艷的青與綠和赭石互成對(duì)比,頗見仇英的功底。
二、圖像元素解讀
整幅長(zhǎng)卷的畫面內(nèi)容按照故事發(fā)展的變化進(jìn)行表現(xiàn),完美復(fù)刻出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該卷卷首有乾隆題詞:
己未歲題趙伯駒桃源圖,有云山春靄鈔鑼溪之句。越四十年,己亥題仇英桃源圖,復(fù)用鈔鑼溪字,因失記數(shù)典以詢內(nèi)廷翰臣,自于敏中以下竟無(wú)知此事者。檢之十余年,迄莫能得。每往來(lái)胸次,頃幾暇偶閱舊刻元人所編陶靖節(jié)集《桃花源記》湯漢注中,始知本于桃源經(jīng),恍如重入仙源,頓逢舊跡,亦一快事。且知學(xué)問之道無(wú)窮盡也。仇英此卷即藍(lán)本伯駒,筆意超秀,頗能神似,洵為合作,即書卷短,以識(shí)賞遇。(戊申小春御筆)
據(jù)乾隆題詞可知趙伯駒也曾創(chuàng)作該系列畫作,而仇英這版即是以趙伯駒那版為藍(lán)本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到明代,“桃花源圖”突然盛行,明四家都曾創(chuàng)作過(guò)該類畫作,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仇英完美地再創(chuàng)作了趙氏兄弟的“桃花源圖”,喚起人們對(duì)“桃源意象”的審美偏好,引起當(dāng)時(shí)畫家的紛紛效仿。仇英筆下的桃源仙境,是中國(guó)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最理想化的狀態(tài):男耕女織,雞犬相聞,顯然也是他本人心中最理想化的隱居之處。
歷來(lái)“桃花源”一詞就與道教關(guān)系密切,姚鉉《唐文粹》中收錄唐代舒元輿的《錄桃源畫記》:“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溪,溪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合而視之:大略山勢(shì)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玩,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來(lái)。”該段中寫到桃源中的溪水名為武陵之源,是三十六靈洞中的一支。三十六洞是道教中的神仙洞府,李白的《尋桃花源序》,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以及北宋張君房的《云笈七簽》都將三十六洞中的第三十五洞稱為“桃源山洞”。在后世的一些文學(xué)作品中也將桃源描繪成神仙所在之地。而仇英作為道教的忠實(shí)信仰者,在《桃花源圖卷》中將他自己對(duì)于道家仙境的理解通過(guò)桃、松、山、洞穴、云這幾類主要的圖像符號(hào)進(jìn)行展現(xiàn)。
首先是“洞穴” ,在歷代桃花源圖畫創(chuàng)作中,都有對(duì)洞口及洞穴的刻畫或描寫,在道教文化中,洞穴被看作是隱士、道家修仙、仙居以及游憩的樂園,所謂“洞天福地”即是道教文化信仰中對(duì)洞穴這一物質(zhì)地點(diǎn)的精神寄托,并且逐漸成為道教文化的一大標(biāo)志。在《桃花源圖卷》中,仇英同樣使用了洞穴這一元素,進(jìn)入桃花源的洞口位于畫卷前段,洞口不小,約與漁人等高,在群山之中,唯有這一處有洞,究竟是人為開鑿抑或是天然形成,這都是畫中未傳遞出的信息。此外,這一洞口的存在與廣袤高聳的山川形成強(qiáng)烈對(duì)比,在看似沒有生命氣息的群山里,因?yàn)檫@一個(gè)洞穴,勾起了漁人的好奇之心,最終尋得桃花源,顯然告訴觀者,此洞穴應(yīng)為人工開鑿無(wú)誤。同時(shí),該洞穴也從側(cè)面突出了群山之中桃花源的神秘感,可見洞穴這一元素即是陶淵明文中連接現(xiàn)世與桃源的物質(zhì)通道,也是仇英對(duì)道家仙境應(yīng)在何處、應(yīng)為何樣的理解。其次是畫卷中頻繁出現(xiàn)的桃樹和松樹。桃樹在道教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道教將桃花作為教花,“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花被認(rèn)為是正氣之極,可以消除邪氣,屬于仙花。在眾多與道教相關(guān)的文化或故事中,都能看到桃花或桃樹的身影。在桃花源中,大片的桃樹與桃花表明此地定是一塊福壽之地,也更是因此地遍地盛開的桃花及桃樹林而有桃花源之稱。松樹冬夏常青,凌寒不凋,是一種長(zhǎng)壽之樹,更被道教視為“仙樹”。隨處可見的松樹將村舍層層包圍,從松樹的高度與繁茂程度足以表現(xiàn)出該村莊的歷史感,乃謂不知是何世也。在仇英的另一幅名畫《桃源仙境圖》中也用了大幅版面刻畫松樹,古松與道人相互呼應(yīng),加深了畫面的沉重感。而此畫的精妙之處則在于,雖沒有對(duì)于時(shí)空的直接描述,但仇英卻巧妙地將這兩種圖像元素進(jìn)行組合共同畫入卷中作為時(shí)間和空間線索,頗具新意。
在這幅長(zhǎng)卷中,還能夠注意到仇英對(duì)云的描繪。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云具有一種內(nèi)在的神話氣息,在許多文學(xué)作品或圖像作品中,在表現(xiàn)神仙和仙居時(shí),騰云駕霧或云霧繚繞成為表達(dá)身份或地點(diǎn)的主要形式。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云從具有單純的物質(zhì)性轉(zhuǎn)變?yōu)榫哂芯裥缘墓δ芴卣鳎瑯樱趪?guó)外云也有著同樣的變化。法國(guó)藝術(shù)史家達(dá)彌施在《云的理論》一書中,詳細(xì)闡釋了云的功能是如何在藝術(shù)品中發(fā)生作用,同時(shí)又是如何隨時(shí)代發(fā)生變化。云的隨意遮擋和無(wú)形性給畫面增加了神秘感,也增加了畫面的繪畫難度。帶著達(dá)彌施“云理論”回看《桃花源圖卷》,相較于傳統(tǒng)畫作中對(duì)仙境的表現(xiàn)大多用大面積的云霧營(yíng)造神秘感和不可及之感,仇英只選擇在畫卷前半段尤其是首段加入云這一元素,云的減少,并沒有改變畫面中桃花源的神秘感,反之為桃花源這一仙境增加了些許的現(xiàn)實(shí)意味與煙火氣息。在這里,云不再只是白色無(wú)形氣體,還具有“道教仙境”的所指含義,其作用在于指示觀者,此處為仙境,至于是道教仙境還是人間仙境,則是觀者的不同解答。另外,畫卷中分散的云營(yíng)造了畫面氛圍,畫卷中分散翻騰的云霧與山體相互遮擋,山借以云而顯示高聳,云則借以山顯露出形狀,通過(guò)整體與部分的比例分配和遮擋與被遮擋部分的巧妙關(guān)系共同作用于觀者的視覺,在觀者眼中,畫面動(dòng)感加強(qiáng),好似有氣流涌動(dòng),充滿生氣,同時(shí)暗示出該地域的空間之廣與維度之深,將道教中的仙境完美展現(xiàn)在世人眼前。
三、總結(jié)評(píng)析
《桃花源圖卷》這幅長(zhǎng)卷,既是陶淵明筆下《桃花源記》文稿的完美再現(xiàn),也是仇英心中的完美世界,仇英繪畫功力深厚,將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緩緩呈現(xiàn)出來(lái)。畫中的景致以散點(diǎn)透視的方式組合排列,既有自山前而窺山后的深遠(yuǎn)疊嶂,又有自近山而望遠(yuǎn)山的平遠(yuǎn)壯闊,更有自山下而仰山巔的高遠(yuǎn)雄壯。另外,整幅畫皆采用青綠技法對(duì)山水樹石進(jìn)行勾勒,松樹、桃樹及其他雜樹用色豐富,形態(tài)各異,群山之間通過(guò)色彩純度與色相的差異營(yíng)造層次,群山掩映,偶然露出的屋頂勾勒精致,色彩鮮明,典雅精致,妍而不甜。除了對(duì)景物的高超描繪外,畫中的人物也是各有特點(diǎn),此畫中所出現(xiàn)的人物多達(dá)四十多位,但每個(gè)人的神態(tài)、動(dòng)作、服裝都不盡相同,不同場(chǎng)景的人與景共融,怡然自得,展現(xiàn)出桃源生活的無(wú)限樂趣,這不僅是畫面中的情景,更表現(xiàn)出仇英渴望身處其間的心境。畫中人物與景物的完美融合,皆展現(xiàn)出仇英不凡的繪畫功底,可謂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精品畫作。此畫不同于元代后期所流行的文人水墨畫,畫中缺少了文人畫家所喜好的筆墨變化與生動(dòng)氣韻。另外,該畫選擇了用青綠技法而不是水墨畫法,在性質(zhì)上就已有了寫實(shí)與寫意的區(qū)分,對(duì)于仇英而言,他兩種技法都是熟練的,之所以選擇用青綠畫法完成這幅作品,或許在他看來(lái),適不適合才是首要選擇。作為一幅典型的院體繪畫作品,仇英的這幅《桃花源圖卷》無(wú)疑是優(yōu)秀的,他筆下彩色的世外桃源仍然給予了觀者對(duì)于陶淵明筆下桃花源的最佳想象圖卷,同時(shí),這幅作品也是仇英本人對(duì)于師古院體工筆繪畫技法的一篇完美答卷。縱然文人畫發(fā)展為主流繪畫與審美取向,又縱使在當(dāng)時(shí)被認(rèn)為其能力不足以與明四家的其他三位并列,他依然選擇堅(jiān)守著自己心中的桃花源,也堅(jiān)守著他所學(xué)的技法,他用自己的行動(dòng)告知世人,即使不被認(rèn)可、不被理解,又何足與外人道也!仇英的這種心境、這種心胸,是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與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