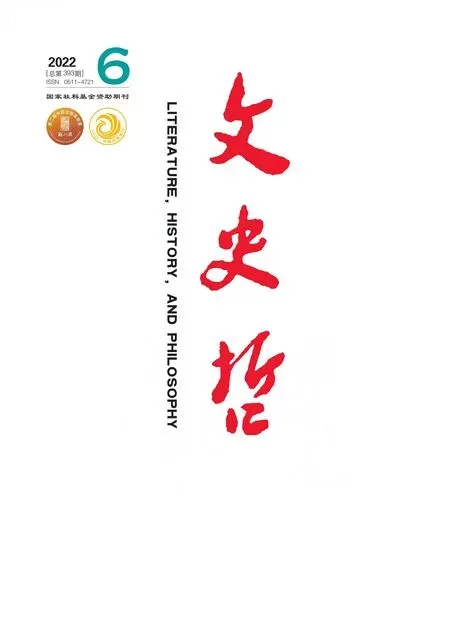王朝國家權力“構造”傳統中國社會
魯西奇
(浙大城市學院歷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310015)
在中西文語境下以及不同的學術話語中,“社會(society)”這個概念,都是指一些人基于某種共同性建立起較為密切的關聯,從而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共同性與凝聚性。它具有兩層意涵:一是指具有某種共同性的人們組合在一起,并表現出凝聚性;二是因某種關聯組合在一起的人群具有某種共同性,并且同屬于維系此種共同性的某種“制度”或“體系”。前者可稱為“具體社會”,如村落社會(共同體)、地方社會等,是因“共同”而形成的“凝聚”,強調的是成員之間的關系及其密切程度,亦即凝聚性;后者可稱為“整體社會”,如中國社會、西方社會以及身份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是從“整體”抽象出“共同”,強調的是其成員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亦即共同性。無論是“具體社會”,還是“整體社會”,使其構成社會的,都是“關系”——雖然關系的性質各不相同,緊密程度亦各有異,但其成員之間都具有共同的關系,并表現出某種凝聚性。
所謂“中國社會”,也有兩層內涵:一是“在中國的社會”(Societies in China),即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形成并發展的社會。它是一個復數,大致相當于“具體社會”,意味著中國這塊土地上存在著諸多社會,從家庭、村莊、不同尺度的地方、族群或民族,都可能形成具有凝聚性與共同性的社會。二是“中國的社會”(Chinese Society),即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形成并發展的具有某種同一性和內聚性的社會。它是一個單數,大致相當于“整體社會”,意味著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各種人群在整體上構成一個社會,其極致的表現方式應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
凝聚性與共同性是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社會形成的充分必要條件。人群要形成社會,其成員之間必須發生“關系”,建立起較為穩定的關聯;而“關系”要穩定下來,形成某種“凝聚性”,就必須具有“共同性”。在“具體社會”中,共同性是團結、凝聚的基礎,而凝聚與團結則強化、突顯了共同性;在“整體社會”中,其初不具有顯明共同性的人群,因為各種原因,被“凝聚”“團結”或“歸納”“概括”在一起,并因此而產生或被認為具備了某種共同性,這就是由凝聚或歸納“造就”了共同性。基于共同性的團結,或者由團結而形成共同性,是“社會”形成的兩種基本路徑:前者形成“具體社會”,后者形成“整體社會”。
分析“社會”的形成與構造,也就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是從人們的共同性出發,分析人們如何立基于其內在的需要,相互交往、互助、團結,并建立規則,從而形成社會。霍布斯、洛克、盧梭、滕尼斯、涂爾干、馬克斯·韋伯等,雖然各有其分析路徑與指向,但均從人們相互間的關系、交往、互助、情感、認知出發,討論社會的生成及其構造。這就是由“共同性”發展出“凝聚性”而形成“社會”的進程。二是從已經凝聚成(或假設已凝聚)的“整體社會”出發,分析其內在結構與特點,從中抽象出某種共同性,并據之界定其社會的性質或類型。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的界定,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中國學者關于“封建社會”的認知,基本上是在認定其社會“存在”的前提下,探究其社會所具有的共同性,并據之定義其社會的。這就是由“整體社會”概括或抽象其“共同性”并進而界定“社會”的理路。當然,在具體的理論闡釋與分析過程中,歷史進程中的“實然性”描述與理論分析中的“應然性”抽象是融會在一起的。
關于“中國社會”的形成與構造的分析,也主要遵循上述兩種研究理路。考察“在中國的具體社會”,主要從具體社會(如村落社會、地方社會)內部入手,分析其共同性(共同利益、共同目標、共同特征等)、凝聚性(向心力、核心與邊緣的結構以及離散傾向)的形成及其表現;探究“整體的中國社會”,則多承認或預設“中國社會”是一種具有凝聚性的歷史與現實存在,分析其要素、結構與特征,概括出整個中國社會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然后在歷史進程中追溯這些共同性的形成過程和原因,并將之作為中國社會凝聚性的基礎。實際上,這兩種研究理路有一個共同的取向,即無論“在中國的具體社會”,還是“整體的中國社會”,都主要是基于其內在需要,在內因的推動下,在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并表現出其共同性、凝聚性及其結構特征的。
歷史過程確實如此嗎?
雖然有不同的解釋,但學者們比較一致地認為,“村落共同體”(村落社會)是村莊立基于其內在需要而自發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目標與共同情感、共同遵守某種規范的、具有內聚力的社會單元,其基本單位應當是自然村。可是,在分散居住、規模較小的散村占據主導地位的南方地區,作為行政管理單元的“里”,更多地發揮了凝聚、組織村民,形成共同規范,并由此形成“地域共同體”或“村莊聯盟”的作用;即使在北方地區占據主導地位的集村里,以村落為單位形成的鄉村基層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組織,也往往與行政管理的基層單位“里”疊合在一起,才能較為穩定。換言之,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整合、規范并“形塑”了鄉村社會組織,并使各地區的鄉村社會組織在鄉里制度的規范下,表現出較為一致的結構性特征。
作為基本社會單元的家庭,具有最為明顯的共同性與凝聚性。家庭,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生成的,其構造也表現出明顯的自然特征(以血緣為中心、婚姻為紐帶)。可是,自從商鞅變法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之后,家庭(家戶)的規模、分異、結構及其功能,就與歷代王朝國家的戶籍制度密切聯系。簡言之,中國古代的“家庭”并非“自然生成的”社會單元,而是受到王朝國家戶籍制度規范、制約下的“家戶”——它既是一種生活生計單元,更是一種社會管理單元。同樣,“家族”也絕不是“家庭”自然發展或聯合的結果,家族的發展、規模、形態及其功能、作用與意義,均受到王朝國家相關制度的嚴格規范與控制。宋代以后,在南方地區,家族(宗族)得到政府的鼓勵,在社會管理領域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地域社會”論和有關地域(地方、區域)社會的研究,建立在“場域”的設想之上,強調地域內在的凝聚力,以及這種凝聚力對地域社會結構及其共性的塑造。在這種理路下,地域社會的形成主要被認為是地域內在的需求,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可是,大部分歷史學者考察的“地域”,均立基于歷史時期或現實中的行政區域,至少是受到行政區劃的影響或制約;關于地域社會形成過程的考察,基本上是以王朝國家權力的滲透、行政權力的展開以及當地人群與王朝國家權力的互動為核心線索而展開的;其結論性認識,也往往指向王朝國家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形塑”了地域社會,制約乃至決定了其基本結構、根本特征及其發展變化和方向。
進而言之,“整體的中國社會”或“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根本上是以中國統一的政治體為前提的,國家權力對于“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構造、發展都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毫無疑問,政治統一是整體性中國社會、一致性中國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基礎。離開政治上的統一,離開王朝國家權力對于幅員遼闊的廣大地域以及社會經濟與歷史文化各異的諸種人群的有效統治,討論中國經濟與文化的凝聚性與共同性,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根本上說,國家及其權力當然是從社會中產生的,是先有社會,后有國家。可是,在中國古代諸種“具體社會”與“整體社會”的形成過程特別是其“結構過程”中,王朝國家權力卻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國家權力造就的權力集團與權力關系網絡,構成了諸種“社會”的基本框架;國家權力對于社會成員的身份界定及其所屬人群的等級劃分,奠定了社會層級與族群分劃的基礎;國家權力確定并推行規范或標準的行為模式,并進而塑造社會習慣,影響制約人們的思維方式;國家權力給諸種“社會”提供文化闡釋,通過符號與儀式,將它們描述、表達出來,并賦予其屬性和地位。質言之,國家權力“形塑”了諸種“社會”的基本框架和結構,并賦予了其共同性與凝聚力。
第一,權力產生權力集團,形成權力關系網絡,構成不同層次的社會關系網絡的骨架。在血緣或地緣關系占據主導地位的鄉村基層社會,獲得王朝國家授予不同權力的鄉吏里胥、土豪鄉紳以及鄉望耆老,共同構成鄉村社會的基本權力格局,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其社會關系網絡。在鄉鎮、縣域等不同空間尺度的地域社會,王朝國家的制度規定了其社會體系的基本范疇,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確立了其社會體系的基本格局,國家權力的下傳與滲透構造了地方社會的權力集團與權力體系,并賦予了不同地域社會的統一性。“在整體的中國社會”層面上,王朝國家通過權力將各地區的地方勢力納入王朝國家的權力體系之中,通過政治控制、制度規定、經濟籠絡、教育選舉等一系列手段,將地方性的權力體系整合到王朝國家統一的權力體系中,從而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官僚社會。以權力為基礎的官僚社會,是統一的整體性中國社會的核心組成部分。
第二,權力確定個體及其家庭的身份,構造身份制社會,并形塑其層級結構。在中國古代,每一個人及其家庭都擁有王朝國家界定并賦予的、劃分為不同層級的身份,同一層級身份的人及其家庭構成社會集團或社會階層,擁有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地位,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從而形成層級式身份制社會。在身份制社會中,個人及其家庭的身份,標志著其與王朝國家體制間的親疏程度,影響乃至決定著其經濟社會地位,以及其在政治與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在身份體系中的位置越高,與王朝國家權力體制間的距離越近,就越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資源、財富與晉升的機會或可能。所以,身份制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形塑”并“規范”“強化”了傳統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影響乃至決定著社會流動。王朝國家權力賦予其臣民以身份,將其納入王朝國家主導的身份制體系中,使其在“編戶齊民”與“官僚士紳”制度下獲得共同性,并在統一的身份制體系內流動,從而強化了其凝聚力。
第三,權力區分人群,從內到外、從“我者”到“他者”、從華夏到蠻夷,劃分為不同等級,構成同心圓式的社會體系。國、野之分,華夏(漢)與蠻夷之別,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的空間差異,腹里與行省的劃分,均通過政治理念、制度規定等權力方式將地域與人群分劃開來,并界定其在王朝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屬性和作用,從而奠定了整體性中國社會的“同心圓”結構。在不同層級的地域社會中,政治中心(行政中心)往往構成其核心:治所城市不僅集中了其所在地域的精英與資源,還作為權力中心,控制、剝削整個地域,并進而形成社會中心;從城市到鄉村,從核心到邊緣,權力的觸角逐步伸展開來,將不同的地域與人群納入權力網絡中來,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不同層級的同心圓式社會結構。即便是在鄉村基層社會,權力也通過鄉里制度、宗族、祭祀組織等,自上而下地滲透,從中心到邊緣延展開來,從而強化其固有的凝聚性與共同性。由此,不同層面的“中國社會”均程度不同地表現為同心圓式結構,并與政治權力體系的同心圓式結構疊合在一起,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社會”的凝聚力與共同性。
第四,權力確立“正統的”或“標準的”行為方式,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塑造其思維方式,促進社會共同性的形成與維護,進而強化其凝聚力。漢代縣、鄉三老以及里父老皆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明代則在各里選舉“年高有德行者”任里老人(耆宿),“俾質正里中是非”,“導民善,平鄉里是非”。歷代鄉村社會中的長老,大都是由官府選任的,其教化權力主要來自王朝國家的授予或委托。王朝國家正是通過鄉村長老,行使其教化權,將國家正統的意識形態與“正確的”“標準的”行為方式傳輸給不同層面的社會及其成員,并通過各種途徑,逐步樹立起權威地位,使社會成員在潛移默化中,奉行其準則,將之內化為社會的普遍規則與個人的行為習慣,進而演化為社會共識與個體普遍的思維方式。權力主導并造就的行為規范與思維方式的統一性,是不同層面的“中國社會”之所以具有共同性和凝聚力的根源。
第五,權力通過符號與儀式等,描述并表達社會及其結構,界定社會及其屬性。符號是社會標識其自身及其成員的工具,并在社會構建、運行與維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儀式既是表現社會結構的可視化方式,也是促使社會群體不斷強化其認同感的手段。在中國古代,符號與儀式,主要是由王朝國家權力造就、控制并操弄的。在戶口登記與納賦服役的過程中,編戶齊民獲得了用漢字書寫的名或姓名,從而將其在國家與社會體系中的位置表達出來。國家權力通過宮室衙署、乘輿鹵簿、衣冠服飾、璽印綬帶以及諸種禮儀活動,展示其權力,彰顯其尊貴與威嚴,以表達其在政治與社會體系中的主導、核心位置,從而突顯官與民的分別,描繪出以權力為中心、從官至民地位遞減的社會結構。在不同層面的地域社會,各種儀式活動均旨在展現不同的權力與社會構造,而王朝國家的權力大多占據著主導地位。國家權力主導的符號與儀式,至少在形式與表達層面上造就了“中國社會”的統一,并增強了其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