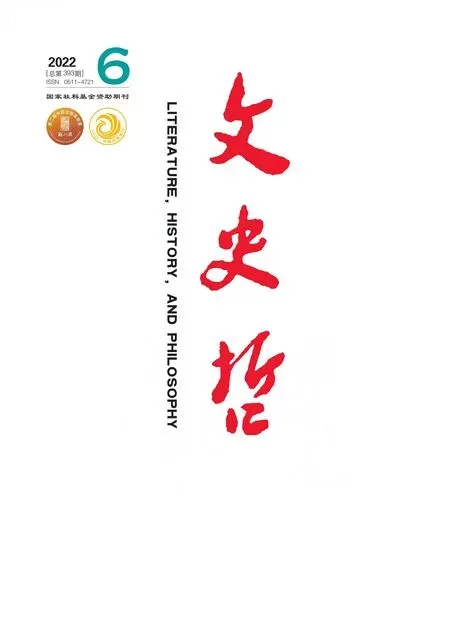中國古代“物論”探析
李賢中
一、引言:“物論”與“思想單位”
我們先來界定一下本文的研究對象“物論”。張立文教授在《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中有專章探討“物論”,他指出:“‘物’這個范疇涵蓋面廣,涵義深刻,它勾畫了自然、社會、人生的各個方面的經驗和體驗,故物便具有本體范疇的意味。”(1)張立文:《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09頁。本文所謂之“物論”是指以“物”為核心概念的相關論述,包含經驗客觀之物、內心思想之事物(2)小篆“物”從牛,凡生天地間者皆物,牛為先民日常生活所見之大物,故“物”從牛。“物”在引申義上泛指有形之萬物與無形之萬象,也即“萬事萬物”。《禮記·中庸》:“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鄭玄注:“物,萬物也,亦事也。”《孟子·盡心上》:“萬物皆備于我矣。”趙岐注:“物,事也。”參見高樹籓編纂:《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臺北:正中書局,1984年,第949頁。,它們經某主體詮釋后,以“思想單位”方式構成的理論,即為物論。“物”的論述,涉及物的產生、認知、比較、表達,物與人的關系,物之概念特性及人對物的回應、處理與達成理想等內容。
從更大的文本脈絡來看,公孫龍關注認知之結果,論及“而指非指”,含有對所知與對象物進行比較之意,而采取懷疑的不可知立場。辯者的“指不至,至不絕”雖然不涉及物之所以然,卻可通向對物的片面理解而不絕,是為樂觀預期的不可知立場。惠施的“歷物”,是一種歷覽辨之、思維對認知結果加工作用的體察,側重內在思想對認知結果的同異比較,而認可相對主觀性的認識結果,但強調需要厘清立場、說明觀點。莊子也觀察到作為表達者的人對認知結果的處理,認為物“謂”之而然,與個人意圖、立場、觀點的轉換有關,進而不滿足于主觀相對性的認知、表達結果,而企向“登假于道”的超越態度。《大學》之“物”論,則言道德修養而延伸于政治之“事”,關注如何達成儒家德治天下之理想。
簡言之,中國古代與“物”有關的論述脫離不了“人”,人的認知、思維、表達、實踐等亦都與人所了解的“物”相關,沒有完全絕對客觀的、獨立的物,只有在人的各種有限能力作用下展現的物。
再看作為本文研究方法之關鍵詞的“思想單位”。“思想單位”是筆者多年前提出的一種研究方法,作為詮釋或解析傳統文獻的工具(3)李賢中:《從“辯者廿一事”論思想的單位結構及應用》,《輔仁學志(人文藝術之部)》2001年第7期,第79-90頁。。近年來,筆者逐步建構這一理論以強化其可操作性,曾從多方面說明“思想單位”的性質、作用、層次及其內涵要件、遞演關系等(4)李賢中:《先秦邏輯史研究方法探析》,《哲學與文化》2017年第6期,第71-86頁。。其中,“思想單位”有情境構作、情境處理與情境融合三個層次,其提問方式包括:有什么、是什么、為什么、會怎樣、要怎樣等一系列問題要素。
“思想單位”是有意義的思維情境。它通過將認知境遇中客觀的事物轉換成主觀的思維情境,或將文獻中的客觀文字理解為自己的詮釋得以形成。“思想單位”指思維情境中所蘊含的“然”“思路要素”,以及“所以然”。它由思維情境衍生,但不等同于一般的思維情境。它像一段錄像,在其中的某些歷程片段為“然”;就某些歷程片段,基于相關問題思考,對前述為“然”之歷程片段加以解釋,便得到“所以然”;聯系、綜合這些“然”“思路要素”“所以然”所構成的可被理解、可被解釋、有意義的結構,就是一“思想單位”。只有可以合理解釋所見事物或所構作之事物的思維情境,才算“思想單位”(5)某些人可以理解的事物,另一些人未必能夠理解。就此而言,不同人的“思想單位”之構成未必相同。就同一個人的知識成長過程來看,在不同的知識水平階段,其“思想單位”也會有所變化。我們可用融合性或更后設的合理性標準,檢視各“思想單位”的意義飽和度。更多相關討論可參考李賢中:《先秦邏輯史研究方法探析》,《哲學與文化》2017年第6期,第78-81頁。。
從文本的理解到理論的重構,“思想單位”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呢?從“思想單位”視角看,所謂“理論”,無非就是理論建構者通過對一定范圍內諸現象的觀察,尋索出相互關系及現象變化中的理則,并且用語言文字系統地表達出來。理論的構成,包含下列幾方面(6)參見李賢中:《墨學——理論與方法》,臺北:揚智出版社,2003年,第211頁。這里調整了順序,并增加了第5項。:
1.對所觀察到的現象的描述(“思想單位”之情境構作層:有什么以及是什么)。
2.解釋現象中事物間的因果(或倫理、利害、權力、結構等)關系(“思想單位”之情境處理層:為什么)。
3.基于因果或其他關系推測現象中事態的未來發展(“思想單位”之情境處理層:會怎樣)。
4.處理或解決在現象中發現的問題(“思想單位”之情境處理層:要怎樣)。
5.處理或解決后的階段性反饋、修正與統整(“思想單位”之情境融合:有什么、是什么、為什么、會怎樣、要怎樣等的一致性與融合性)。
以下,我們從“思想單位”的不同向度,簡要解說中國古代的各種“物論”。
二、認知、比較向度的“指物論”與“歷物論”
《莊子·天下》說:“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7)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第1111頁。公孫龍《指物論》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8)王啟湘:《公孫龍子校銓》,楊家駱主編:《名家六書 墨經校銓》,臺北:世界書局,1981年,第62頁。,意思是:對象物必須透過指涉作用才能呈現,不過,被指出而呈現者不同于對象物(9)這一概括系在比較周云之、孫中原、龐樸、馮耀明相關解釋的基礎上提出的。更多相關討論可參見李賢中:《從〈公孫龍子〉的詮釋比較看經典詮釋之方法問題》,《名家哲學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62-171頁。。此與《莊子·天下》篇中辯者第十一事之“指不至,至不絕”(10)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1106頁。相互關聯。“而指非指”可視作對“指不至”的進一步解釋,強調指涉作用的認知結果并不等同于認知對象。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如下追問:如何達成這種“不等同”判定?如果有人認為某認知結果不等同于認知對象,那么,抱持這種主張的人就必須知道那對象“是”什么。可是,此人如果知道那對象“是”什么,那就不能說“而指非指”。答案需要從“至不絕”中尋找。我們可以這么來看:“指涉作用的認知結果并不等同于認知對象”這一理解中的“認知對象”也只是一種暫時的理解,它會被之后的再認識、再理解修正或補充,每一次認知結果相對于之后的認知都是“而指非指”。上述論辯連起來就是“指不至,至不絕”。可以說,正是辯者的“至不絕”的“至”,衍生出了公孫龍的“物莫非指”;辯者的“指不至”的“不至”,衍生出了公孫龍的“而指非指”。
《莊子·天下》又說:“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11)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1106、1112頁。惠施嘗試說明造成這種“指不至,至不絕”情形的緣由:人們在認知過程中一定有所比較,然而事物間的比較關系是無法窮盡的。他強調,“歷物”是人類認知過程的重要環節,也即歷覽辨之。“分辨”離不開“比較”,“比較”須以至少兩個、兩類、兩階段的事物作為相互比較的對象,這樣才有諸如下述的異同呈現:“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12)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1102頁。比較出的大同(大類)、小同(小類)還可進行“類”之間的比較。人對于某一事物的認知是透過特定觀點與標準的“比較”,經比較而有同異,基于同異而進行歸類,有所類同者在思想界中取得一位置,而可確立為一“名”。透過這些“名”而形構思想界中的內容,再進一步就可以呈現人們所見的意義世界。因為比較無法窮盡,所以“指不至”;又因為比較又可以不斷進行下去,所以“至不絕”。惠施認為解決此一問題的方法在于,將此看似對立的兩個面向統合于同一認知主體的思想界中,“物”不再是客觀之物,而是思想之物,也就是“歷物”。“歷物論”對認知結果采取相對性立場,如“南方無窮而有窮”(13)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1102頁。。對惠施的“歷物論”,可進行“思想單位”解析如下:
1.所謂的“物”有什么?思想界中可設想無限的大(“大一”)與無限的小(“小一”),還有天、地、山、澤、日、南、北、中央、今、昔等時空概念,以及各種大類(“大同”)、小類(“小同”)概念。
2.“歷物”是什么?所謂的“歷物”,都是經由人思維運作后的思想物,含有人的觀點、特定范圍、標準與比較。
3.為什么?萬物不斷變化(“物方生方死”(14)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1102頁。),人只能掌握變化中的片段,透過思維的概念化作用進行比較(“萬物畢同畢異”),并且也只能因順人的觀點與設定的范圍進行判斷(“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15)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1102頁。)。
4.“歷物”會怎樣?可以基于上述相對性作用歷覽萬物,進而論述各種事物對象(“不辭而應,不慮而對,遍為萬物說”(16)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1112頁。)。
5.怎樣歷覽萬物?要盡可能與各對象有同一的觀點,了解各種對象的不同立場與視域,將之納入主體思想系統之同異序列,亦即以泛愛的方式歷覽萬物(“泛愛萬物,天地一體”(17)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1102頁。)。
在公孫龍的“指物論”中,其“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所謂的“物”即認知的客體,而“指”則包含著作為認識主體之能力的“能指”、作為被指涉對象的“所指”,以及指涉作用的“物指”(18)李賢中:《先秦名家“名實”思想探析》,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65頁。。認識的作用是“能指”指向“所指”,進而構成“物指”,以獲得認識的結果。原本的物雖然不能被完全把握,但經由“指物”,思想中的“實”卻是可以確定的。所謂的認識結果,就是經“指”而來,在思想中確定的、為“名”所表達的“實”。公孫龍提出了終極實在不可知的認知難題,卻又在表達上要求一名一實,可謂名副其實的“唯行說”(19)《公孫龍子·名實論》曰:“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王啟湘:《公孫龍子校銓》,楊家駱主編:《名家六書 墨經校銓》,第80-81頁)鑒于公孫龍強調“唯乎彼、此之謂”,相對于莊子的“兩行說”,龐樸稱公孫龍的思想為“唯行說”。可參見龐樸:《公孫龍子研究》,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第48-49頁。,正如公孫龍《名實論》所謂:“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20)王啟湘:《公孫龍子校銓》,楊家駱主編:《名家六書 墨經校銓》,第79頁。
如前所述,惠施主張了解各種對象的不同立場、觀點與視域,以“泛愛”的全面性來處理相對性的認知結果,所謂“泛愛萬物,天地一體”,是一種對比了解各種觀點的“相對論”。面對此終極不可知的世界,公孫龍在表達上并不以實在界為基礎,而是以思想界為底線,在邏輯正名的維度上(21)從邏輯學角度看,所謂“正名”,就是要求名必須具有自身的確定性,即“彼”之名必須專指彼之實,“此”之名必須專指此之實。而這樣的名必須限于概念之名,而非允許一詞多義的語詞之名。參考周云之:《名辯學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0頁。嚴格要求在思想界、表達界中名與實的一一對應。惠施以“相對”性方式處理思想內容的做法則是以“泛愛”為基礎,力求同情地理解各種觀點,以此把握用名者的相對根據,進而確立名實的意義。我們對公孫龍的“指物論”進行“思想單位”解析如下:
1.指涉作用的發生條件包括什么?包括認知主體與認知客體——主體指涉客體而得到某種認知結果。
2.指涉作用于其上的“物”是什么?就“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而言,“物”是不能被完全把握的認知對象,而且,認知結果是根據對象而存于思想界中的實與名(概念),不同于認知客體。
3.為什么“而指非指”?“物”為有,“指”為無。認知結果為名(概念)之“無”,認知客體為可感觸之“有”(22)《公孫龍子·指物論》:“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王啟湘:《公孫龍子校銓》,楊家駱主編:《名家六書 墨經校銓》,第63頁)。
4.指涉作用下的認知結果會是怎樣的?在二元認知結構下,指涉作用本身就阻礙了真正認識的可能性。(23)《公孫龍子·指物論》:“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與為指。”(王啟湘:《公孫龍子校銓》,楊家駱主編:《名家六書 墨經校銓》,第65頁)既然認知者連“物”是什么都不能完全把握,又怎能相對于“物”來談“指”?不過,雖然人無法認識真正之“物”,但經“指”而來的“實”在思想界則是可確定者。
5.面對指涉作用的上述限制,要怎么辦?對“物”進行指涉作用后,在思想界與表達界要以名舉實,一名一實,名副其實。
綜上所述,公孫龍與惠施都是在主客二元的認知結構下,遭遇認知“原本之物”這一困難的,他們進而都從思想與表達的一致性上提出了脫困的可能性。
三、超越向度的“齊物論”
《莊子·達生》曰:“凡有貌相聲色者,皆物也。”(24)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634頁。因此,物包含著可以感知的具體事物。這些可觀察的事物,處在不斷運動變化中,正如《莊子·秋水》所云:“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25)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585頁。莊子的齊物思想必須從“道”的觀點來看。莊子認為,“道”是自滿自足、沒有分界的全體之“一”。在他看來,世間的萬物雖然有成有毀,好像各有其分界,但這并非真相,因為具體的事物只是“道”之分,道之分使我們得見一事物之成,但此事物之成,必然使彼事物有所虧損或銷毀。這正如《莊子·齊物論》所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26)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70頁。因此,從莊子“道通為一”的觀點來看,萬物有共通的根源,且彼此相互關聯。就現象而言,然與不然、可與不可之差別因人的觀點、認知之不同而產生,但成毀變化的本根則是無所差別的。
《莊子·齊物論》:“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27)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69頁。萬物是變化無常的現象,隨著人的既定立場或成心而掌握其所謂之物。“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成玄英疏曰:“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28)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61頁。此“成心”之說乃以惠施“歷物”思想中的“今日適越而昔至”為例,并批評說這是把沒有的事當成有。“所謂之物”除了在立場、觀點上有人的主觀性外,在語言表達上也有虛飾障蔽之處,“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29)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63頁。。在莊子看來,能成一家一派,或在一定范圍中自圓其說的理論就是小成,然而各種理論都有其限度,把那些有局限的學說當成普遍的真理,就遮蔽了大道。儒、墨之爭無非是以別人所非的為是,以別人所是的為非。
此外,莊子的“齊物論”也對公孫龍的“指物論”進行了批判。《齊物論》對于公孫龍“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批評如下:“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30)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66頁。這意味著:公孫龍所談論的指涉作用是主客二元的認知模式,以此來說明所認識的結果不同于所認識的對象(而指非指),不如以非指涉作用也即“吾喪我”的“道通為一”方式,來說明指涉作用在認知究竟事物上所受到的限制。正如用主客二元模式下所認知的“馬”無法通達那“究竟的馬”那樣,不如用超越二元模式的“非馬”來說明二元模式之“馬”非“究竟所是之馬”。任何指涉都以“道通為一”的整體性為根據,萬物就如“馬”一樣,是同一整體觀照下的東西(31)曾春海等:《中國哲學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5年,第137頁。。就此而言,“齊物”之基礎在于“體道”。
“道”是無所不在又是絕對不變的本根,現象來自本根也歸屬于本根。面對不斷變化的萬物,人基于他所觀察體會到的經驗對“物”加以論述,造成了各種分歧的論點與主張。此即“因是因非,因非因是”(32)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66頁。。反而言之,只有達到“道”的高度,才能觀悟眾說紛紜之“物”的分歧論點,也即“有真人而后有真知”(33)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226頁。。那么,如何才能登假于道呢?《人間世》所謂的“心齋”,《大宗師》所謂的“坐忘”“朝徹”“見獨”等,正是《莊子》書中所提出的能登假于道、達到“道通為一”境界的功夫。
對莊子的“齊物論”,我們可做“思想單位”解析如下:
1.莊子對于“物”的相關論述有哪些?有貌相聲色者、有共通的根源者、有成毀變化者,以及有天籟、地籟、人籟、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各家各派的學說與是非。
2.“物”是什么?是人之所謂(“物謂之而然”(34)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69頁。)。
3.為什么是“人之所謂”?正是因為人的觀點、認知有所不同,所以才會產生然與不然、可與不可之差別(若就成毀變化的本根而言,則唯有無所差別的“道”)。
4.各種分歧的“物論”會怎樣?“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35)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51頁。,分別彼此,不見對方,各有是非,所言未定,均是無益之言辯。這導致了對“道”的遮蔽,產生了“指物論”“歷物論”,以及儒、墨之是非等。
5.要怎樣?要經由工夫,提升自我,登假于道,以“道”的整體性、全面性齊平各種物論。
一般認知必有所待的對象,依賴相關的條件,但其所待的對象、所依賴的條件卻是無法確定的。為何無法確定呢?這是因為萬物皆在變化中,所有事物都依賴著無數的相關條件,若無整體之知、究極之知,任何局部的判定、階段性認知,皆如“至不絕”之知那樣,都是可疑的。唯有體道的真人,才能體會玄深的大道,將一般認知提升為真知。懷有這種真知的真人,能超越人事上的成敗,不在意個人得失,感官經驗的刺激也不會對他造成任何影響。他能超脫形骸地執著,不以心損道,而擁有真正的知。這種真正的知就是超越向度的“齊物論”的基礎。
四、倫理政治向度的“格物論”
《大學》關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發展性論述以“格物致知”為基礎。其中所謂的“知”,就《大學》整篇內容而言,并非萬物之知,而是修養自身并推擴于更大范圍的家、國、天下,使一切治理完善之知。《大學》主要在五個地方言“知”:1.“知止而后有定”;2.“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3.“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4.“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5.“大畏民志。此謂知本”(36)這五處文字參見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五《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第983、983、983、984、986頁。。此五處文字,有二處言“知止”,三處言“知本”。“知止”即“知止于至善”,“知本”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37)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五《禮記》,第983頁。。能知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即“知之至”,整體而言所知者即“大學之道”(38)趙澤厚:《大學研究》,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第245-246頁。。《大學》之“知”有特定之范圍與對象,指的是道德生命在自我與人群關系中發展的根本與極致,與“指物”“歷物”“齊物”之知不同。
“物”在《大學》中作何解呢?《大學》開篇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39)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五《禮記》,第983頁。關于此段中的“物有本末”,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之為始,能得為終,本始于先,末終于后,此結上文兩節之意。”(4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第5頁。王陽明《大學問》則以“新民”為“親民”,而認為“明德為本,親民為末”(41)王陽明:《王陽明全集》(肆),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第72頁。,并強調本末為同一物之本末。趙澤厚則主張:“物有本末者,應以明明德為本,以止于至善為末。”(42)趙澤厚:《大學研究》,第190頁。眾說關于何為“本”雖無異,但對“末”的看法卻各有不同。不過,不論《大學》之“末”具體為何,我們從其對前述發展性歷程的論述中,皆可見“物”之內涵。
《大學》關于這一發展歷程的論述如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43)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五《禮記》,第983頁。這一發展要經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系列過程,過程中的內容都屬于“物”之內涵。因此我們必須探究這些歷程中都包含哪些現象。
在“修身”方面(44)《大學》相關文本如下:“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五《禮記》,第986頁),相關現象描述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這些描述指向人際關系中與行為相對應、在行為發生前所抱持的態度。之所以會有先在的態度,是因為對方身份、地位、與己之關系造成了情感上的好惡,進而造成相應行為方式的先在的態度。這種態度會使人偏頗而失其正道,欲加以矯正,須導正更核心的主體,亦即“心”。
在“正心”方面(45)《大學》相關文本如下:“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五《禮記》,第986頁),相關現象描述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等。這些描述指向各種不平和的情緒。人之所以會有這些不平和的情緒,乃因受到外在人、事、物等的刺激、干擾、誘惑、影響。這些情緒會使人心不得其正。當“心”不受外力所致的情緒干擾,而能發揮主導作用時,各種感官就能回復原本之功能。然而,“心”為內在不可觀察者,因此必須從“意”申論。
在“誠意”方面(46)《大學》相關文本如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之五《禮記》,第983頁),相關現象描述有:“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的“自慊”;“為不善,見君子”而后的躲藏掩飾。“誠意”與“自欺”是恰好相反的兩種現象。之所以會有這些現象,乃是因為人可以自知內心的狀況,而且,由于“誠于中,形于外”,他人也可看出自己內心的狀況。于是乎,人要謹慎地單獨面對自己,誠意、不自欺,以成為有德者。
至于“格物”,依《說文解字》的解釋,“格”的最初含義是“木長貌”,乃指木枝干森挺之狀,故從木。其引申義有法式、格式、格律、規格、標準、品位(品格、人格、資格),以及包含動詞含義的阻止(格格不入)、窮究等等(47)高樹籓編纂:《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第716頁。。最早對“格物”二字加以解釋的是鄭玄,其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言是緣人之所好來也。”(48)轉引自趙澤厚:《大學研究》,第200頁。由此可知,鄭玄認為,“物”指的是具有善、惡價值之事物,其性質由一價值主體的內在狀態賦予,亦即主體的先在德性內涵、動機或狀態決定了認知之物的價值定位。
后來的程伊川則用“窮”“至”來解釋“格物”之“格”。這種解釋更強調主體的主動性、程度的究極性,而“物”之則兼含物、事、理三者(49)其一,以“窮理”解“格物”:“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程顥、程頤撰:《二程遺書、二程外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7頁)其二,以“窮物理”解“格物”:“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程顥、程頤撰:《二程遺書、二程外書》,第195頁)其三,以“窮事理”解“格物”:“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黎靖德編輯:《朱子語類》[上],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第305頁)。其中,物分外在事物與內在事物,不論內外皆有其理,且理與理之間有一定的聯系性,可透過類推而予以把握,且要窮盡各物之理才能致知。擴大來看,“格物”的意涵就是“窮盡事物的價值、關系和整體和諧運作之理,使自我或相關人事物處于適當的位置”(50)王前、李賢中:《“格物致知”新解》,《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129-134頁。。格物以明了道德生命的本、末,人在自我與人群關系中,發展的根本與極致,及其實踐的進程。以下,我們對《大學》的“格物論”,做“思想單位”解析:
1.《大學》關于“物”有什么相關論述?有“物有本末”“明明德”“親民”“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以及具有善、惡性質的事物,此外還有物理、事理。
2.“格物”是什么?在倫理、政治范疇中,窮盡事物的價值、關系及整體和諧運作之理,使自我或相關人事物處于適當的位置。
3.“格物”為何是“窮盡事物的價值、關系和整體和諧運作之理,使自我或相關人、事、物處于適當的位置”?因為人之內在與外在有相關性,個體的運作與群體的運作有相關性,不同大小之群體運作也有相關性,整體中的每一個體內外、個體本身、大小群體等在動態和諧運作中,都有其合理位置。
4.在運作過程中,如果不處于合理之位會如何?個人自欺,心不在焉,產生不平和的情緒,思、言、行產生偏頗而失其正道。身、心、意皆失其位,家不可教,失眾、失國,無以平天下。
5.要如何做?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明明德于天下,止于至善。
五、結 論
“物”是一個大共名,可指的對象非常多,因此,雖然各家都使用“物”這個字,但是所構造的理論卻有頗大的差異。本文在“思想單位”名義下比較了中國古代的四種“物論”,考察不同“物論”對思維框架的影響,展示其形構的世界觀、價值觀、內在合理性及實踐性之異同。
就“物”的主要意涵而言,“指物論”之“物”乃“被指涉認知之物”,在“真正之物”方面有無法跨越的限度。在此限度之內,“指物論”旨在將“實”“名”之內涵予以固定,將“名”與“實”一一對應,以求表達上的準確。“歷物論”之“物”為“被思考比較之物”,故受限于思考者的觀點與立場,突破途徑在于改變面對萬物的方式,從“歷覽辨之”的邏輯序列轉向有情之“泛愛”(51)《莊子·德充符》記敘:“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第220-221頁),建構同異秩序,進而企向天地一體,在“整體之一”的理性把握下,分解各自觀點立場的差異。“齊物論”之“物”,為被人表述稱謂之物,以及各種相應的“物論”。它們皆有所待和預設,突破這些限制的途徑在于提升主體的境界,秉持超然的態度。“格物論”之“物”為“修養政治之事”,以及“物理”“事理”與“倫理”。此論提倡在整體的相互聯系中,于不同的階段以合宜的位置、恰當的運作,推己及人,教化百姓,以德治天下。
四種“物論”關注的問題不同,因此它們的情境構作、情境處理皆不相同。“指物論”與“歷物論”關注的是認知的限度、思維的性質,以及表達的正確性等問題。“齊物論”則是對上述兩種“物論”的批判,其特征在于以“道”的整全性來齊平萬物。“格物論”則是用“理”來貫通內外,使整個價值世界具有聯系性、發展性,其特征是強調個人的修養,高揚人之能動性對整個價值世界的影響力。
就“物論”對世界觀與思想框架的影響而言,“指物論”走不出自我的主觀世界,“歷物論”則需要在態度上從邏輯性思維方式轉向知性倫理的泛愛萬物來體認天地一體。如果說“齊物論”側重從不可知論角度引申“指物論”的話,“歷物論”則具有相對論色彩。后兩種“物論”共同轉向了形而上的“道”,將萬物統括于“道”之下、“道”之內,以此把握所謂的萬物。體道之人的優越性在于可以領悟“真正之物”。然而,莊子的“真人”帶有神秘性,在表達上也只能訴諸想象,而無法清晰論述。“格物論”則并不懷疑人們能夠真正認識這個世界,而且肯定人在這世界上的努力,認為這種努力是實現價值的正當途徑。在宋明儒學的闡釋中,“格物論”的動態價值運作有一“理”貫穿其中,并且這種價值以無限高遠的至善為終極目標。
四種中國古代“物論”似乎都對此世界有一整體性想象,都涉及并處理終極性問題。辯者所謂的“至不絕”,系認知上的無窮盡眺望。“指物論”則在有限范圍內無盡追問。“歷物論”顯示了一個至大無外的無限宇宙,而指向一種經由認知主體比較后設想出來的同異序列思想世界。“齊物論”的“道”則是超越的,也是無限的,站在萬物根源的立場上觀照那些依萬物變化而產生的各種物論。“格物論”雖然有明確的階段性目標,但最后仍然是要止于“至善”。可以說,各論皆觸及終極性向度。
四種中國古代“物論”所思考、論述之對象的性質不同,以至于情境構作的對象不同,思想定位、價值定位也不同。各“物論”所掌握的因果關系或各層面的關聯性,以及世界觀也不同,但對原本之物的追究,向往登假于道的真人真知,高揚至大無外的整體性、價值上的至善等理想性、無限性追求,則是四家“物論”的共通點,顯示了異中有同的趨向。
以上述中國古代“物論”反觀今日,現代的“物論”顯然是自然科學與科技視野下的“物論”,人類的科技發展一方面促進了人類生活的便利與舒適,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環境污染與破壞,甚至威脅到人類整體的生存。目前,主要的解決方式仍然是大力發展環保科技。相形之下,本文所論及的中國古代“物論”,其中蘊含著透過古人整體性思維來建構與發展一企向人類整體幸福的世界觀,暗示我們不能僅透過科技來解決科技所造成的問題。換言之,中國古代“物論”蘊含著從非純然科技的人文、倫理及人類心靈的超越向度認識這個世界,了解人及萬物,可以突破或平衡現代“科技物論”所造成的諸多問題,進而從哲學上建構有利于未來世界發展的“新物論”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