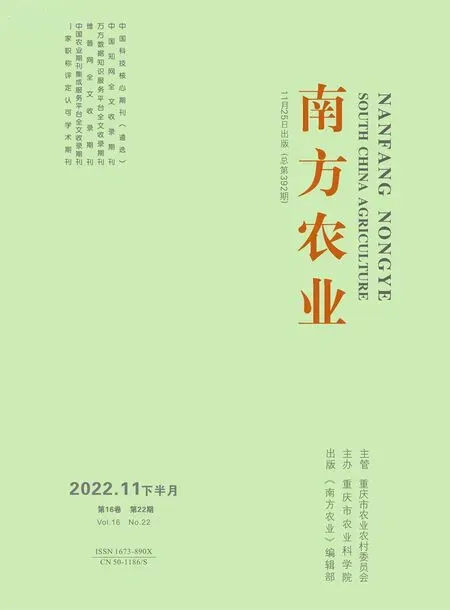漳州市龍海區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現狀及對策
郭永祥
(漳州市龍海區港尾鎮人民政府農業農村服務中心,福建漳州 363105)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也是實現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而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既可以壯大村集體經濟,增加村財政收入,為鄉村振興提供財力保障;又可以增強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激活農村活力,實現鄉村自我振興。
1 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2021 年,龍海區167 個行政村中,村集體經營性收入在5 萬元以下的村35 個,占21%;5 萬~10 萬元的村25 個,占15%;10 萬~20 萬元的村51 個,占31%;20 萬~50 萬元的村42 個,占25%;50 萬元以上的村僅14 個,占8%。由此可見,龍海區農村集體經濟雖發展成績顯著,但經營性收入占比偏低,主要是存在以下3 個方面問題。
1.1 領導干部重視不足
鎮村兩級基層干部對發展集體經濟的重視程度不夠,未能因村制宜探索多種發展集體經濟的可行途徑。部分基層干部認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發展農業生產的主體是農民,與集體經濟無關,無需發展村集體經濟;部分領導干部認為需要重視“三農”,但農村發展“等”資金,鄉村振興“靠”財政投入,基層組織運轉“要”上級資金支持,“等、靠、要”的思想認識,使基層干部特別是村兩委干部對村集體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沒有認真思考和謀劃發展村集體經濟的具體措施[1]。
1.2 產權制度改革不深入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尚處于初級階段,在許多方面還存在優化空間。從2016 年正式啟動改革,至2020 年底全面完成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工作,本次改革在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經濟收入等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但改革仍留下了許多問題,例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完成確認集體組織經濟成員身份、清產核資、明確集體資產所有權之后,如何管好用好集體資產,促進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如何保護集體所有權,防止集體所有權虛置;如何保證農村集體產權流轉的規范性、合法性,確保農村生產要素得以高效流動等。
1.3 資產管理不到位
1)村集體資源資產的承包合同未經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承包方案應當按照本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依法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承包合同之所以要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同意,是為了避免村集體資產資源在承包過程中的暗箱操作、利益輸送,確保村集體資產資源的保值增值。2)村集體資源資產的承包合同訂立存在明顯缺陷。主要表現在:①租金低、租期長甚至無期限,這類合同變相地把村集體資產資源讓給他人;②合同中沒有對合同到期后地面附著物的處置辦法做出約定,導致合同到期后村集體資產資源收回存在障礙;③合同沒有對承包方違約行為的處理辦法進行約定,如承包方對承包的土地或其他資源資產進行違規使用的,發包方有權要求承包方停止違規使用并恢復原狀,因停止違規使用所造成的損失,發包方不予賠償[2]。3)村集體資產資源的承包存在權力包、人情包現象。主要表現在部分村干部利用職權,低價承包村集體資產資源,甚至侵占集體資產資源;部分村干部把村集體資產資源以較低的價格承包給自己的關系戶。
2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必要性
2.1 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需要
為實現“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目標,除了要增加農民的工資收入、經營性收入外,還必須重點關注財產性收入。近年來,在國家各項政策的扶持下及基層政府的努力下,龍海區農村居民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但是從收入組成上來看,財產性收入占比偏低,長此以往必然會增大城鄉貧富差距。因此,在保證農民總體經濟收入穩步提升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財產性收入的比重,是促進城鄉融合、實現生活富裕的必要條件。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通過集體經濟股權分紅的方式讓農民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不僅能使農民收入結構更加合理,還能增強農民的集體意識,為加快實現鄉村振興創造有利條件。
2.2 實現鄉村振興目標的需要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工作,不斷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力度,每年投入大量的財政資金用于農業農村建設。鄉村振興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包括農村宜居環境建設、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等,需要大量的財力物力投入,僅依靠國家財政的投入是不夠的。因此,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
2.3 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的需要
國家力量的推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前提和關鍵,但增強農村自身發展的內生動力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礎,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的有效途徑[3]。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適當引入社會資本,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和農業社會化服務業,有利于促進農村產業興旺;通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可以激活農村土地、資金、人才等生產要素,吸引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促進城鄉要素市場一體化;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還可以激活農村消費市場,進一步挖掘消費潛力。
3 發展壯大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的思路
3.1 提高領導干部對農村集體經濟的思想認知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解決思想上的認識問題,才能增強工作的主動性和自覺性。為此,龍海區各級黨委、政府,尤其是鎮村兩級基層組織,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三農”問題的重要論述,增強抓好村集體經濟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要探索建立發展村集體經濟目標考核機制和激勵機制,在干部年終績效考核中增加發展集體經濟這項工作目標,以干部的績效考核和業績激勵并行,激發各級干部發展村集體經濟的積極性。
3.2 制訂發展集體經濟負面清單
積極引入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參與發展村集體經濟和鄉村振興,但在引入過程中要注意資本的兩面性,資本雖能促進農業農村產業的快速融合,但需規范與引導資本的健康發展,以防資本損害集體利益與農民利益。必須遵循維護農村集體利益和群眾利益,保障農村可持續發展和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基本原則。研究制訂符合龍海區農業農村實際發展的農村集體經濟負面清單制度,在外部資本投資準入領域、投資項目、出資比例、資本退出等方面進行制度設計,讓資本進入有明確的政策預期,從而吸引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進入農業農村,助推鄉村振興。
3.3 加強農村集體資源資產管理
村集體資產資源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都有可能造成集體資產資源的流失。因此,要發展壯大龍海區村集體經濟,就必須從加強集體資源資產管理入手。1)規范承包合同。對未經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存在明顯缺陷的承包合同,要依法依規進行處置。2)對存在權力包、人情包的承包合同,要進行查處、收回。對侵占集體資源資產的不法行為,要開展集中整治,切實維護集體和農民利益。
3.4 開創發展龍海區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新局面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應充分發掘龍海區地方資源優勢,整合盤活存量資產,大膽引入外部資本,最大限度發揮村集體資源資產效能,促進村集體、群眾雙增收,推進鄉村振興。
1)村集體可以利用未承包到戶的集體“四荒”地、集體所有的果園、養殖水面,采用招投標等方式引入資本,發展現代農業項目;也可以利用當地的自然環境、紅色資源等人文歷史資源,發展鄉村旅游。例如,精準扶貧首倡地十八洞村利用當地的礦泉水資源,引進企業投資山泉水廠,每年按“50+1”形式給村集體分紅,村集體年均分紅60 萬元。
2)村集體盤活整合現有存量資產,可以將村集體長期閑置不用的一些廠房或集體建設用地,承包給個人進行自主開發,或者是通過股份合作形式與企業共同開發,培育特色產業。例如,龍海區港尾鎮深沃村2019 年收回已到期集體低價包蝦池6.3 hm2,重新招標后年增加收入4 萬元。
3)村集體還可將集體積累資金,或政府提供的幫扶資金,選擇可靠、穩定的農業龍頭企業進行投資,成為企業股東,以獲得企業經營分紅。例如,2020 年,龍海區港尾鎮引導村財政比較薄弱的沙壇村、考后村和深沃村,整合上級幫扶資金和自身資金各50 萬元,投資龍海區自來水公司,每年可獲得股份分紅5 萬元。
4)村集體可通過自主經營或股份合作的方式,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要從當地種養業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市場需求,開展農資供應、種養信息咨詢、農機作業、代耕代種、農產品初加工、居家養老等各類生產性服務,增加集體收入[4]。
5)村集體還可以通過土地經營權流轉,把集體內部的閑置土地集中起來,以股份合作的方式,發展現代農業。例如,村集體可以將由于外出務工、勞動力不足導致的缺少管理、拋荒的閑置土地集中流轉,通過引進資本、技術等方式,面向市場發展現代化、規模化農業。
3.5 加強頂層設計,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為了促進龍海區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服務鄉村振興,應在法治環境、財政金融、要素市場體系等方面,加強頂層設計和制度建設,為農村集體發展提供支持,注入活力。
1)法治環境建設方面。要抓緊研究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方面的法律,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依法維護其合法權益,保證其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的基礎上,研究健全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抵押貸款和承包權退出等方面的具體辦法[5]。建立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農村產權保護法律制度。2)政策環境方面。要加大財政支持力度,通過財政資金帶動社會資本有效投資,促進村集體經濟發展。通過建立利益聯結機制,探索建立由政府、企業、村集體共同出資設立的村集體經濟發展基金。制定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采取合資、股份合作等方式參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
4 結語
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發展農村新型集體經濟,既可以壯大村集體經濟,增加村財政收入,為鄉村振興提供財力保障;又可以增強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激活農村發展活力,助力實現鄉村振興。相關工作人員要提高思想認識,增強發展村集體經濟的責任感和緊迫感。要堅持一手抓村集體資源資產管理,一手抓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要營造良好的法治、政策環境,制訂負面清單,鼓勵和支持集體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