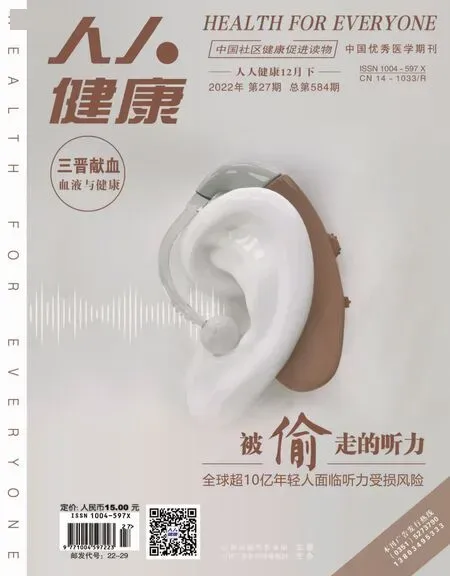葉圣陶的長壽之道
■向南

葉圣陶是我國著名的現代作家、教育家、文學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稱,他的一生對于中國的教育和文學的發展貢獻巨大。
葉圣陶出生于1894 年,少年時一路見證了清廷的內憂外患、風雨飄搖。12 歲那年,他拖著長辮子告別私塾,放下八股,一頭扎進新知識的世界,開始關心國運,思考救國之路。1912 年,從草橋中學畢業的他心懷“立國之本、首在教育”的愿望,投入了教師的職業。受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他同茅盾(沈雁冰)、鄭振鐸等人發起組織了文學研究會,寫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后來又出任商務會館編輯,主編過《小說月報》《婦女雜志》《中學生》等刊物。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等職,關注語文教學,1950 年以后的中國中小學語文教學體系,最初便是由他為主設計籌劃的。直到如今,孩子們仍能在課本里讀到他寫的兒歌《小小的船》、散文《爬山虎的腳》、童話《稻草人》……
葉圣陶一生中經歷了不少坎坷磨難,但卻始終保持著身心的健康,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依舊思維清晰,精神矍鑠。他也曾經對自己的健康表示滿意:“我的血壓總是受到大夫的贊許,高壓低壓距離適當,而且與年齡適合。透視、驗耳朵擠出的血、做心電圖,都說沒問題。”“按脈搏,總在67~74 次/分。每天早上測一回體溫,總在36℃~36.3℃。”
1988 年2 月16 日,葉圣陶在北京逝世。在人生旅途上走過了94 個春秋后,他也為后人留下了不少的養生經驗。
生活規律
許多作家寫作喜歡“開夜車”,但葉圣陶先生是堅決不熬夜的,而且生活非常規律。他每日堅持早睡早起,每晚8 點半入睡,早上5 點起床,中午1 個小時的午睡,十分注意勞逸結合、規律作息。一日三餐分別是在7 點、12 點、18 點,如此幾十年如一日,很少變化。每天堅持上午讀書寫作,下午沐浴休息。自17 歲以后他還堅持每天都寫日記,如果哪一天沒有寫就覺得這一天白過。工作之余,他也會適當安排一些娛樂項目緩解疲勞,或是聽聽廣播和音樂,或是欣賞電影和戲劇,又或是約上三兩個好友郊游小聚。
飲食有節
據葉圣陶先生自述,他從小就不甚健壯,幾十年來留下的照片,“沒有一張夠得上用‘壯’字、‘健’字形容的”。據他說是因為“飯量一向很小,吃了一碗再添是少有的事”。年過八旬之后,他每餐只能吃一兩主食,但他自己覺得再多吃就會不舒服,“何況各種菜肴同樣有營養”,所以堅持少吃為佳。
也許是江南人的原因,葉圣陶從小喝慣了綠茶,而且天天喝,80 多年沒有間斷過。有人問他身體好是不是跟喝茶有關?他半開玩笑地說:“我們這些長期喝茶的人,大概肚子里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茶銹,癌細胞長不上去,毒瘤掛不住。”
此外,葉圣陶還十分好酒,卻飲而不貪。他有自己的一套喝酒原則,一是主張少喝勤喝,慢慢喝,以微醺為最大限度,二是不喝烈性酒,多以家鄉的黃酒、紅葡萄酒為主。所以他基本上沒有喝醉的時候。
勤于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有好幾所大學聘葉圣陶當教授,可他最終選擇的是當編輯。新中國成立后即使當上了出版總署副署長和教育部副部長,他也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寫稿、看稿,把生命“碎割在給人改稿子、看稿子、編書、校字”這些事情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當編輯不如當大學教授或當官名氣大,但葉圣陶并不這么看。他認為編輯面對的不僅僅是幼稚的未成熟學童,也面向“研究科學的、文學的乃至一切學問”的專家學者,面向“經商的做工的乃至經營一切事業的”國民,這就要求“我們的編輯者都是富有經驗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種科學的學者”“時代是刻刻趨新的,學問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擴大的。要永久站在時代的前列,要探測深廣的學海”。編纂出精美的書刊,奉獻純正的“精神食糧”,成為“追蹤時代、探測學海的引導者”。
他又說:“做出版工作的人就是長壽。”做編輯工作時,只要一稿在手,一管在握,不管上班下班,無論平日節假,不計在職離退,孜孜 ,兢兢業業,一字未安,廢寢忘食,心無旁騖,世俗雜念難以侵入。每有所成,就有精神上的充實感、思想上的凈化感、事業上的成就感、生活上的脫俗感,無比愉悅,自然長壽。
平淡生活
葉圣陶久居繁華的都市,先是上海,后是北京,卻一直保持著鄉居的習慣。留的是傳統的光頭,穿的是家制的布鞋布衣,而且多是中式的。院子里稍有空地,他便種滿花木,蘇州青石弄舊居多有花樹、果樹,北京東四八條里多是仙人掌之類,他最引以為豪的是庭間一樹海棠。每至春末夏初,花事繁茂,他總要打電話請俞平伯、謝冰心等老朋友來共賞。他也有一些小愛好,從幼時起便喜歡寫篆字、刻圖章、聽昆曲,到后來又喜歡吹笛,甚至能按照工尺譜奏一曲“八陽”。他總是按著心以為然的方式,過著東方式、平民化的生活。他不向別人推薦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絕不隨俗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心胸開闊
葉圣陶喜歡廣交朋友,對任何人都能坦誠相待。在他的日記中,從未有對某個人某件事的惡言詈辭,與人交談時,他也總是做一個平易近人的傾聽者,從不爭強好勝,與人針鋒相對。若是有人去他家做客,他必然會不斷道謝并親自送客出門,至晚年不能起床時也會拱手作揖道謝。有人說:“無論何時看到他,內心總是平和的、安寧的。”朱自清更是稱贊:“他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有一次,朱自清不小心將他辛辛苦苦保存的《晨報》副張遺失了,他發現這件事時也只是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人們常說,“養生”貴在“養心”。心胸開闊,保持樂觀的心態,或許就是葉圣陶高壽無疾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