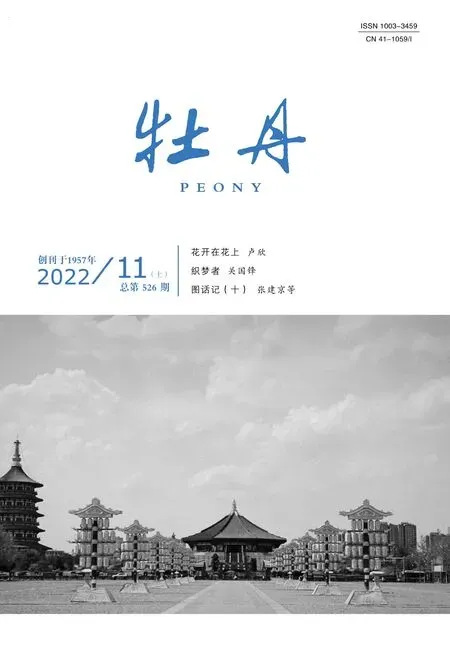鄉村教材
王國政
中年男人從胡同里緩步向村口走去,從城里專程來接他的轎車已等在那兒。站在村頭半山坡上,他后轉身,仔細地打量眼前生他養他的普通村莊。目光停頓的瞬間,他發現一條東西大街將村子分為兩半,整個村子像一本打開的大書平展在那兒,靜靜地,一聲不響。
半個月前,中年男人回到偏僻落后的村里。他感到心累、茫然,想躲開浮躁的城市和生意場,暫時靜一靜。十多天,他走進村里的莊稼地,焦黃、肥沃的土壤,腳下感到厚實和踏實。正值盛夏,蓬勃生長的禾苗染綠的田野使他眼睛放亮。他關掉手機,沒事在村子里閑逛,有時來到街坊鄰居家中,坐在土炕上,聽鄉親們拉家長里短,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遠離酒桌,一天三頓農家粗茶淡飯,他吃得有滋有味,想起了很多,也透過鄉親們滿足的笑容想到了很多。走著轉著,腳步越走越輕快,腦子越轉越清涼。離開村子返回所在的城市時,他嘴角掛著微笑,一身輕松。
地球上,城市和鄉村并存。論數量,村莊明顯占優。論單個體量,城市超過村莊。時光更迭,城市的塊頭越發見大,村莊和土地在退縮,為城市騰出地方。城市底氣十足,看不出一絲謙遜或客氣。
鄉下人羨慕城里人。他們眼里,城市是發達、富裕的代名詞。城市人身居高樓、吃穿不愁,牽狗遛彎的日子過得滋潤。鄉下人眼饞,一窩蜂往城里擠。城市人口越擠越多,多到幾乎沒有停車和落腳的地方。
城市人沒有鄉下人想象的那樣舒心。城市的逼仄和喧囂,房價攀升、求職難帶來的生存壓力,城市人困惑、糾結司空見慣。這種以焦慮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患,并非僅僅來自普通人,按照時下認同標準,坐擁一定地位和財富的成功者不在少數。
病根和解藥在哪里?
土地
不妨請出一位年長者來為土地代言。晉代大詩人陶淵明由于對官場感到厭倦,不惑之年毅然棄官歸隱田園。后來他的行動證明,他回到土地,皈依了一種純粹的自然,真實的自然。他從內心深處以自然為美,以土地為伴,因循自然,寄情土地,因自然而凈化心靈,因土地而領悟生命。當他站在山水間輕聲發出“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生命終極感悟時,可以想見,那是一種怎樣的曠達超逸、淡定從容的人生姿態。
美國人梭羅也是一位親近自然和土地的主動實踐者。他倡導樸素、清醒、自然的生活方式,一個人來到森林里,親手搭建起一座木屋,湖邊種地、垂釣、讀書,森林里漫步,想一些事情。漸漸地,他發現“大自然的純凈與恩賜真是難以形容,就像太陽和風雨,夏天和冬季,它們持續不斷地給人類送來健康和快樂!它們甚至還與人類心有靈犀,如果有人因為正當的理由而難過,那么整個自然界都會受到影響,太陽的光芒將會變得暗淡,風兒將會嘆息,云朵將會落淚,樹葉將會在盛夏時節飄零以表傷心。”兩年過后,當他離開瓦爾登湖時,感慨道:“我們的人生被許多無足輕重的事情耗費了。人真正需要的東西,基本上十個手指就能數得過來,頂多再加上十個腳趾,其他都是可以丟棄的。簡單,簡單,再簡單!”
宇宙、自然、生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道家講天人合一。對于城市人來說,身居鋼筋混凝土筑成的城堡里,腳下是厚厚的水泥地或者柏油路面,人與土地無形中氣場阻隔,難以接通地氣。城市工作生活節奏快,城市人緊張忙碌中,忽略甚至遺忘了餐桌上的糧食、菜蔬、水果來自土地和鄉村。他們習慣到公園里散步、健身,或者帶著孩子到農業觀光示范園采摘短時樂趣。在某個特定的場合,或許會隨口發出“大地啊,母親”的吟哦,而生活中真正常去鄉村走一走,親近土地,看望大地母親的城市人并不多見。是時候該向現代都市人大喊一聲了,請將腳步慢一點,再慢一點,略做停留,回頭看一眼缺衣少食依然籬下采菊,抬頭觀南山云卷云舒的陶淵明,然后與大洋彼岸那位金發碧眼的梭羅先生打個招呼,微笑示好。
土地的品格是高貴的,它沉默不語,承載、滋養著萬千動植物生命,卻從來不表白什么,索取什么,只是通過芬芳的泥土氣味與生靈對話,然后默默地承受、忍耐和付出,呈現出博大的胸襟。它以恒久的生命之軀哺育著無數鮮活生命的輪回,使地球家園始終喧嘩、熱鬧,生生不息。
這如何不令人感動,怎可以冷落和遺忘了土地。
人在塵世,與俗膩糾纏在一起,往往難以自救。鄉村的土地最具原始風貌。肥沃的土壤,利于思想的發酵,精神的成長。城市人親近土地,才能在清新的鄉村自然風中,實現心靈的覺醒,自覺掙脫俗世的誘惑,素簡清歡,還原生命本該有的樣子。
村莊
村莊大都建在山野或平原上,星羅棋布,各自相對獨立地存在著。它們與土地接茬、互融,似乎沒有惹人注目的地方,尤其那些零星散落在大山深處、山溝旮旯的村莊,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城市人餐桌上的食物,幾乎無一例外地來自這些或近或遠、或大或小的村落。
村莊的可愛之處,質樸、敦厚,它不太在意別人的目光,習慣了與土地搭伙,與自然結親。它覺得這樣安靜、平淡的日子沒有什么不好。它不擅長攀比,出風頭。
地處偏遠的村莊無法與城市近郊的村子相媲美。商業開發的腳步加快,城市近郊的土地,逐年被蠶食。村莊變成社區,平房變成樓房,農民變成居民。令這些昔日農民感到困惑的,面對兒孫天真的眼神,他們無法用語言描述村子曾經的模樣,只好來到他鄉,向后人講述村莊過去的故事。
納入城市規劃的村莊是少數,是時代的幸運兒。村民如愿獲得了數目可觀的拆遷費,住進了高樓,過上了城里人的日子。有心人發現,小區廣場上,當年喜滋滋搬進高樓的街坊鄰居常常湊在一起,懷念曾經的村子,念叨過去的好。
膠東那個偏僻的村落時常走進心頭,也偶爾回到村子。村子很普通,缺少個性和特色。因為是故鄉,每次走進村子,小住或短暫停留,生命總是被觸動,腦子更加清醒。面對依舊落后的村子,日子依舊不寬裕的鄉親,由于人微言輕,除了留下幾聲嘆息,幾多感慨,卻不能具體幫助他們做點什么,只能間或留下一星半點對村子變化并無實際用處的粗淺筆墨。
從鄉村走進城市的一族,對他們來說,村莊有著特殊的情感和吸力。一位從農村出來的官員,手中握有不少的權力,面對金錢、美食、美色誘惑,以及來自各方的壓力,始終心有定力,不為所動,以一顆平常心秉公辦事,贏得好口碑。據其本人透露,平時工作無論多忙,應酬再多,每隔一段時間他都要回鄉下老家走走,看望父母,同鄉親們見見面,拉拉呱。父母知道兒子在外面說了算,每次見面總是苦口婆心,囑咐其不要貪財,不要攀比,不能背后被別人戳脊梁骨。父母的叮囑,鄉親們艱苦的勞作、滿足的笑臉為他起到了及時醒腦和洗滌靈魂的作用。
村莊四周無邊的山野里生長著品種繁多的植物,不少可以入藥,這些中草藥材借風力、雨水配伍,清新的空氣中形成一個天然的中藥箱,置身其中,明目提神,滋補元氣。這種作用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本文開篇那位中年男人坦言,當年離開村子進城后,手腳并用,腰包鼓了,心里卻越來越空虛,也曾經到深山寺院廟宇尋求良方,效果甚微。回到都市后,面對燈紅酒綠,人情世故,重新陷入虛假、表象的成就和快樂中,焦慮、不快隨之而來。那次回村小住后不久,他連同工廠一起搬回村里。
農人
偌大的中國,農民占據人口多數,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依靠勤勞的雙手,耕耘著土地,期待著風調雨順,衣食無憂。農人一日三餐食用當季當地糧食、菜蔬,夜里睡在土炕上,白天黑夜與土地為鄰,土生土長。他們習慣了春生、夏長、秋收,生命融入四季輪回,年復一年過著與世無爭的平淡日子。土地是農人的命根子,他們對土地有感情,了解土地脾性,早出晚歸,“汗滴禾下土”,開荒造田,不舍得荒廢一寸土地。他們世世代代與土地相廝守,從土地那兒獲取新鮮的食物、歡愉的心境和健康的體魄,生命從而獲得了真正的大自由、大自在。農人的好心態生長在田野里。
北方的農人向往冬天,這是一年中相對清閑的時節。寒風里,三五成群上了年紀的老人站在向陽的墻根或草垛前,抄著手,嘴里的旱煙吐著東家長、西家短。他們最大的愿望,忙碌了春夏秋,冬季里曬曬太陽,炕頭上吃上熱乎乎的飯菜,喝上一壺燒酒解解乏,然后打著呼嚕好好睡一覺。
這些鄉村老人身上有一種天然的超越功利世俗的精神魅力,他們活得真實、善良,人格質樸、純潔,內心干凈、透亮。他們不懂得什么是人生哲學,卻幾乎人人都是生活的哲人,物質欲望低,生活追求極簡和節約,知足常樂,過著屬于自己的平淡日子。他們或許不認識幾個字,壓根就不知道老子、莊子,蘇格拉底和梭羅,不會以學問、財富、地位論高低,卻不自覺地走進了生命的至真、至善、至簡的境地。那些處在城市文化高地中的學者,或者擁有較高身份和財富的人,常常習慣在典籍中苦讀、沉思,或者打坐參悟,修煉來思考去,卻未必達到這些普通農人一樣的寡欲、淡然的生命境界。
城市人被高樓遮擋住仰望星空遠望田野的視角,忽視了土地和村莊的存在。城市噪音大,令人心急火燎。科技的進步,工具的改進帶來效率的提升,節省的大量時間卻無蹤無影,城市人的腳步反而變得更加匆忙,而且越發匆忙,焦急上火,心無定所。作為鄉下進城中的一員,這里善意地進一言,那些試圖通過到風景名勝旅游或蒲團焚香安頓靈魂的城市人,不妨多到鄉村,尤其那些偏遠落后的鄉村走一走。如果時間允許,最好小住數日,靜下心,過幾天清心寡欲的安靜日子,將原本撒在寺院里的香火錢,賜給村里那些生活困難的老人、孩童。被接濟幫扶的貧困老人、孩子或許不善于表達,只會用目光注視著你,然后躬身點頭表達真誠的感激。這個時候,你就是那些受助老人孩子心中的佛,當你與他們揮手告別時,與三叩六拜后離開寺廟時的心境是截然不同的。你會發現,那些歲月中安靜地打發日子的農人,身上散發出的表里如一,不急不躁,樸素和滿足,像一本教科書,促人真實無欺地面對人生,過好眼下的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是靈魂的道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