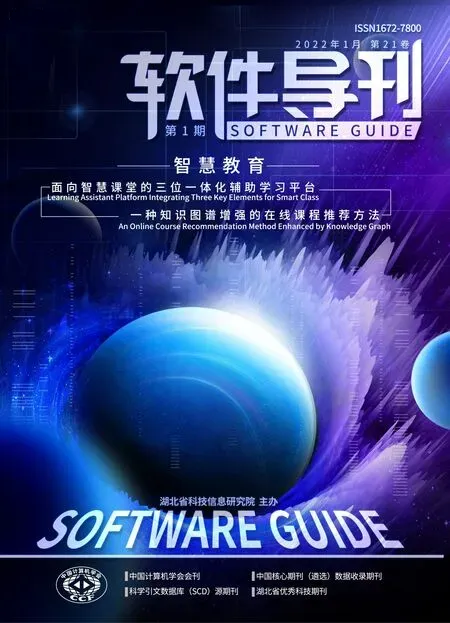增強現實技術能提升學習效果嗎?
——基于46 項國際研究的元分析
張夢潔,劉 峰
(南京郵電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0 引言
增強現實技術(Augmented Reality,AR)是在虛擬現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興技術,其允許用戶看到真實世界以及融合于真實世界之中的虛擬對象,進而拓展了用戶與現實互動的體驗[1]。作為一種新興的教育技術手段,增強現實技術在教育教學中的應用也越來越深入,引發了教育界持久的探索與爭鳴。2019 年2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等聯合發布《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實施方案(2018-2022 年)》,指出要加速建設和開發國家虛擬仿真實驗教學項目以推動我國教育信息化變革。隨著更多學校將AR 引入課堂教學,AR 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影響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關心的熱點問題[2]。目前針對AR 技術能否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的研究呈現兩類截然不同的結論:一是AR 技術對提升學習效果具有顯著正向影響[3-5],二是AR 技術對學生學習效果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6-7]。
研究結論的不統一,致使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思考3 個現實問題:一是在教學中使用AR 技術到底能不能產生更好的學習效果?二是哪些變量影響AR 對學生學習效果的調節效應?三是在教育教學中如何正確嵌入AR 技術才能有效發揮其潛在的能供性?
圍繞上述3 個現實問題,本研究擬采取元分析方法,對近10 年來國際上有關AR 對學生學習效果影響的實證文獻進行綜合分析。通過計算平均效應值,系統評估AR 對學習效果的實際影響,并擴大樣本篩選范圍,引入學習環境、學段、學科領域等調節變量以深入分析AR 應用于教學的潛在條件,同時給出改善AR 在教育中應用效果的建議,為AR 賦能教育信息化發展提供參考借鑒。
1 相關文獻綜述
1.1 增強現實技術
增強現實技術的概念最早是由Caudell 等[8]于1992 年提出的,即指通過頭戴式顯示器擴展用戶視野的技術。Azuma[1]于1997 年對此定義進行了拓展與豐富,認為增強現實技術通過將計算機生成的虛擬對象融合于現實世界中,從而使用戶看到補充現實。Milgram 等[9]則進一步定義了真實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的連接關系,對真實和虛擬元素的組合方式進行分類。如圖1 所示,環境范圍是從完全真實的環境到完全虛擬的環境,基于此,增強現實是更接近于真實環境的一端,即增強現實“增強”了用戶的現實體驗[9]。增強現實相較于虛擬現實具有3 個關鍵技術要素:融合真實世界與虛擬對象、對位匹配虛擬與現實場景信息、實現人機交互。綜上所述,增強現實技術允許用戶看到真實世界以及融合于真實世界之中的虛擬對象,“增強”了用戶與現實互動的體驗。

Fig.1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al and virtual environment圖1 真實環境與虛擬環境連接關系
1.2 增強現實技術對學習效果影響研究現狀
1.2.1 AR 技術對提升學習效果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國際上部分實證研究顯示,AR 技術的使用能夠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這一研究結論成為學術界的主流結論。比如Huang 等[10]使用增強現實技術進行消防教育,并通過對比實驗發現,AR 技術在改變學生對于消防的態度、促進認知學習以及體驗式學習方面更有效;Ekrem 等[11]在小學語文課堂上利用AR 進行詞匯教學,發現在初級語言課堂上使用AR 技術能顯著提高學習者的理解能力,并使詞匯學習更加有效;Chang 等[12]將AR 學習模式應用于自然科學教學,結果發現,基于AR 的學習指導模式不僅有利于提升學生的項目績效,而且增強了其學習動機和群體自我效能感。以上研究均與AR 能提升學習效果的研究結論相契合,支持了AR 技術賦能教育的觀點。
除以上準實驗研究外,已有的元分析研究也支持了AR技術能顯著提升學習效果的結論。例如Tekedere 等[13]對15 項定量研究進行元分析,以探究AR 技術在教育中應用的有效性。該研究結果表明,AR 技術的應用對學生的學習能產生積極作用,且合并后的平均效應值為0.67;類似地,Yilmaz 等[6]也評估了AR 應用于教學環境中的有效性,通過對12 項研究的整合分析,發現AR 對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的效應值為0.36;Garzón[14]對27 項實證研究進行文獻綜述與元分析,以確定AR 應用于教育中的地位、趨勢、機會和挑戰,計算出AR 在學習效果方面的合并效應值為0.64,表明AR 可較好地提升學習效果。
1.2.2 AR 技術對提升學習效果沒有顯著作用
另有部分實證研究則表明,AR 技術應用于課堂教學對學習效果并無顯著促進作用。Cai 等[15]以24 名初中生為研究對象,使用AR 技術教授凸透鏡成像實驗,結果發現,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測試分數不存在顯著差異;Michael 等[16]評估了AR 系統對大學生物理實驗課程的有效性,研究發現AR 系統對學生的學業成績影響并不明顯,同時相比于傳統課堂,AR 系統會導致更高的認知負荷;Chang 等[17]利用AR Flora 系統輔助學生的植物學習,研究結果顯示,基于AR Flora 的學習與傳統視頻支持下的學習對學生考試成績并無顯著影響。
綜上所述,由于實驗設計、實驗對象、教學內容、AR 應用場景等方面差異,AR 能否提升學習效果這一問題尚未達成明確、統一的結論,一方面有學者認為AR 技術對提升學習效果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另一方面有學者則指出AR 技術對提升學習效果并無顯著影響。目前,大部分研究聚焦于AR 技術應用于某一特定領域的有效性,如消防知識教學、語文詞匯學習、物理凸透鏡成像實驗教學、植物教學等,缺乏從整體上衡量AR 的綜合效果,并不能系統評估出AR的教育價值。盡管也有一些學者進行了元分析研究[13-14],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已有元分析研究樣本數量較少,使得研究結果容易受到發表偏倚的影響;其次,因樣本數量的限制,這些元分析研究未能深入評估調節變量對AR在教學中應用的潛在影響。
鑒于此,本研究采取元分析方法,將相互獨立的研究結果進行整合與量化分析,力圖從整體上評估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同時擴充樣本數量以深入分析學段、學科、學習環境等調節變量對AR 在教學中應用的潛在影響,從而獲得更客觀、科學和廣泛的研究結論。本研究主要對以下問題進行深度剖析和探討:
(1)從整體上看,AR 技術是否能提升學習效果?
(2)在不同學習環境下,使用AR 教學對學習效果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3)針對不同學段的學習者,使用AR 教學對其學習效果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4)針對不同學科領域,使用AR 教學對學習效果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5)在不同教學方法的干預下,使用AR 教學對學習效果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2 研究方法與過程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元分析(Meta-analysis)是指對同一主題、相互獨立的一系列實驗或準實驗研究結果進行綜合統計分析,按照一定操作程序抽取所需研究信息,并通過加權處理計算出整合后的合并效應值,從而獲得更加客觀、科學和廣泛的研究結果。
同時,本研究嚴格按照PRISMA 指南進行,并遵循英國心理學家Glass 等[18]提出的元分析操作程序。這一過程要求研究人員:①收集相關研究;②對特征值進行編碼;③計算單個研究的效應值;④分析調節變量對效應值的影響。
2.2 研究過程
2.2.1 文獻檢索
為獲得高質量的研究,本文主要以WOS、Google Scholar 兩大國際權威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增強現實技術的檢索詞為“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AR”,學習效果的檢索詞為“Learning Achievements”“Learning Outcomes”“Learning Gains”“Learning Performance”“Learning effectiveness”,組合檢索詞為“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LearningOutcomes”“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Learning Achievements”等。
檢索區間為2011 年1 月-2020 年12 月,文獻類別選擇article,共檢索到1 356篇外文文獻。將獲得的初始文獻導入Excel,剔除重復文獻349篇,初步篩選后得到1 007篇文獻。
2.2.2 文獻篩選
為保證研究過程的嚴謹性與科學性,本研究制定以下遴選標準:①屬于發表于2011-2020 年之間的英文文獻;②研究主題為增強現實技術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影響,文章中需要體現反映學習效果的指標;③研究方法必須是實驗或準實驗研究;④實驗干預為使用或不使用增強現實技術進行教學,必須包含實驗組和對照組;⑤研究結果需提供足夠多的數據以求得平均效應值,如樣本量、平均值及標準差。
嚴格按照以上篩選標準對檢索到的1 356 篇文獻進行審查,最終得到符合本研究要求的46 篇文獻作為元分析樣本,具體篩選流程如圖2 所示。

Fig.2 PRISMA flow for studies selection process圖2 文獻篩選PRISMA 流程
2.2.3 文獻編碼
為便于研究與分析,對最終納入的46 篇文獻進行特征值編碼。根據研究目的,所包含的編碼元素如下:作者、發表年份、實驗組人數、對照組人數、學習環境、學段、學科、教學方法及實驗結果。依據研究結論,本文將實驗結果劃分為正向影響與無顯著差異。具體編碼體系如表1 所示。

Table 1 Studies coding system表1 文獻編碼體系
為確保編碼的嚴謹性與科學性,本研究由兩位教育技術專業的研究生進行雙重編碼。編碼人員針對有異議的地方進行協商討論、反復校對,以保證編碼信息抽取的準確性。文獻編碼結果如表2 所示。學習環境中,“L”代表校內實驗室,“C”代表課堂,“O”代表校外場館;教學方法中,“T”代表任務驅動法,“S”代表講授法,“E”代表測試/評估法,“D”代表探究發現法。

Table 2 Studies coding situation表2 文獻編碼情況

Tarng and Lu Turan 等Aebersold 等Medina 等2018 2018 2018 2019 28 40 35 18 28 45 34 18小學大學大學高中天文學地理醫學數學CCLC Yang 等Yip 等Weng 等Sahin Alfadil 2019 2019 2020 2020 2020 26 19 34 50 32 24 19 34 50 32小學大學初中初中初中科學縫紉生物科學英語CCCLC ETTSSTTTE正向影響正向影響正向影響正向影響正向影響正向影響無顯著差異正向影響正向影響作者 年份實驗組人數對照組人數學段 學科 學習環境教學方法 實驗結果
2.2.4 數據分析
為綜合衡量AR 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影響,本研究采用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CMA)3.0 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與深度剖析。具體操作過程包括發表偏倚檢驗、異質性分析、合并效應值計算與調節效應檢驗等。本研究選擇Borenstein 等[19]提出的兩種元分析統計模型計算合并效應值大小,即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用標準化均差SMD 評估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程度,其中效應值(Effect Size,ES)是反映實驗效果或變量之間關聯程度的統計量。根據Cohen 提出的效應標準衡量效果,ES <0.2 表明效果較小,0.2<ES<0.8 表明具有中等效果,ES>0.8 表明效果較為顯著[20]。
3 元分析結果與討論
3.1 發表偏倚檢驗
雖然元分析是對相關領域的研究進行較為準確地系統性綜合,但也會受到一些因素干擾,如出版偏誤、樣本偏倚、文獻遺漏等。因此,需要元分析研究者對所納入的文獻進行發表偏倚檢驗,以確保樣本具有統計學意義。發表偏倚是指在同類研究中,有統計學意義的研究結果比無統計學意義的研究結果更容易被接受與發表的一種現象,且一般研究樣本普遍受到發表偏倚的影響[19]。漏斗圖法(Funnel plot)是當前學界普遍用于檢驗發表偏倚的可視化方法,又稱為倒漏斗圖法。鑒于此,本研究采用倒漏斗圖(funnel plot)法檢驗元分析樣本的發表偏倚情況,46 個元分析樣本發表偏倚檢驗漏斗圖如圖3 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本研究包含的46 個元分析樣本以基本對稱的方式分布在中線ES=0.63 的兩側,且研究樣本的效應值多集中在倒漏斗的中上方,位于底部的研究較少,說明本研究不存在發表偏倚情況,納入研究的樣本較為可靠。
3.2 AR 對學習效果的整體影響
本研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s)兩種元分析統計模型評估AR 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整體影響,結果如表3 所示。通過兩種效應模型計算出的效應值均大于0,意味著AR 教學對學習效果起著積極正向影響。分析結果顯示,異質性檢驗中Q 值為424.05、P<0.05、I2=89.36%(I2>75%),表明樣本間異質性較大,故本研究選取隨機效應模型以評估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46 個元分析樣本的合并效應值為0.63,根據Cohen 提出的效應值衡量標準:ES <0.2 表明效果較小,0.2 <ES <0.8 表明具有中等效果,ES>0.8 表明效果較為顯著。因此,從整體上看,AR 對學生的學習效果具有中等程度的影響,這也與Garzón[14]等學者的研究結論相契合。

Fig.3 Funnel plot of publication bias test圖3 發表偏倚檢驗漏斗圖

Table 3 The overall impact of AR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表3 AR 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整體影響
3.3 調節效應檢驗
3.3.1 針對不同學習環境,應用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差異
為進一步探討AR 的應用效果是否受到學習環境這一調節變量的影響,本研究根據實驗場所對元分析樣本資料進行匯總與分析(編碼信息見表2),結果見表4。由表4 可知,組間效應Chi2=6.55,P=0.038(P<0.05),表明3 種不同學習環境對AR 的應用效果存在調節作用:校內實驗室的調節效應最為明顯(效應值為0.80),課堂學習環境次之(效應值為0.61),校外場所的調節效應最弱(效應值為0.48)。

Table 4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learning environment表4 學習環境調節效應檢驗
3.3.2 針對不同學段的學習者,應用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差異
AR 應用于不同學段教學,對學生學習效果影響的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組間效應Chi2=8.71,P=0.042(P<0.05),表明AR 教學在不同學段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影響存在差異:在高職(效應值為1.02)和高中階段(效應值為1.01),AR 技術對學習效果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大學階段(效應值為0.67),AR 技術對學習效果的影響為中等水平;而在學前階段(效應值為0.39),AR 技術對學習效果的影響最弱,處于中等偏下水平。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school stage表5 學段調節效應檢驗
3.3.3 針對不同學科領域,應用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差異
目前AR 在學科教學中的應用較為廣泛和深入,為探究AR 對不同學科學習效果的影響差異,本研究對元分析樣本按學科類別進行特征值編碼(編碼信息見表2),并合并相似學科,最終劃分為物理、科學、醫學、數學、天文學、生物、英語和其它8 類。由表6 可知,物理、科學、醫學、數學的效應值均大于0.5,且雙尾檢驗(P<0.05)顯著,說明AR對這4 個學科的學習效果具有積極影響。組間效應Chi2=8.19,P=0.316(P>0.05),不具備統計學意義,表明AR 對不同學科學習效果的影響不存在顯著差異。

Table 6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the subject表6 學科調節效應檢驗
3.3.4 針對不同教學方法,應用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差異
為檢驗AR 在不同教學方法干預下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差異,本研究對元分析樣本按教學方法進行編碼(編碼信息見表2),并將教學方法劃分為講授法、測試/評估法、探究發現法、任務驅動法4 類。檢驗結果見表7,組間效應Chi2=11.97,P=0.018(P<0.05),說明采用這4 類教學方法時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存在差異:探究發現法(效應值為1.13)對學習效果的調節效應最強,測試/評估法(效應值為0.59)和任務驅動法(效應值為0.62)次之,講授法(效應值為0.40)的調節效應最弱。

Table 7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teaching method表7 教學方法調節效應檢驗
4 研究結論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對2011-2020 年發表的有關增強現實技術對學習效果影響的實證文獻進行梳理與量化分析,系統審查了增強現實技術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實際影響,并深入評估了相關影響在學習環境、學段、學科等調節變量上的差異。基于元分析結果,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4.1 AR 技術對提升學習效果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通過對46 個元分析樣本信息的編碼、整合與剖析,計算出合并效應值為0.63,說明AR 技術能夠提升學習效果,進一步驗證了AR 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的有效性。究其原因在于,相比于傳統教學,基于AR 的教學能夠將抽象的學習內容以更加直觀、可視化的方式呈現,并為學習者提供了豐富的學習情境,創造了廣闊的自主探索空間,增強了感官學習體驗。這些都有助于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與建構,并激發學生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習效果[21]。
4.2 學習環境、學段、學科、教學方法具有調節效應
在元分析研究中,相較于合并效應值,研究者往往更關注變量對研究主題所起到的調節作用[22]。本研究發現AR 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影響存在邊界條件,受到學習環境、學段、學科及教學方法等調節變量的共同影響。
(1)從學習環境來看,AR 在校內實驗室的應用效果最佳。究其原因在于,與課堂學習環境相比,校內實驗室具備更完善的技術設施,并擁有豐富的活動資源,能夠為學生提供更多合作交流、參與式學習的機會,因此能最大限度地發揮AR 的技術能供性。由此可見,AR 技術并不適用于所有學習環境,因而教師在教學實踐中不能盲目使用AR技術,應根據課程特征科學、合理地進行教學設計。
(2)從學段來看,AR 對高中和高職階段的學習效果影響最為顯著,大學階段次之,對學前和小學階段的影響最弱。這是因為AR 教學能將復雜、抽象的學習內容可視化、具體化、情境化,為學習者營造一種有趣、興奮和刺激的學習氛圍。而高中生面臨較為繁重的課業壓力,長期高壓的學習氛圍使其對學習產生厭倦情緒。使用具有強交互性的AR 技術能將學習與娛樂融為一體,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效降低認知負荷。另外與學前和小學階段的學生相比,高中生具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和技術素養,對新事物的學習與接受能力較強,能快速熟悉AR 操作系統,進而充分發揮AR 技術的應用價值。
(3)從學科來看,AR 對物理、科學、醫學和數學學科的學習效果影響最顯著,而對英語、語文等文科的影響效果較弱。主要原因在于理工科領域的理論知識一般與實踐相關聯,需要進行大量實驗。AR 技術為此類課程創設了無限的探索空間,并為學生提供無限的實驗機會,打破了采用傳統學習方式的時空壁壘。
(4)從教學方法來看,采用探究發現法時,AR 對學習效果的影響最顯著,而講授法影響最弱。主要原因在于探究發現法是一種積極的教學方法,學生不是通過記憶枯燥的概念和材料進行學習,而是在“做中學”。AR 技術賦予了探究發現法無限的生命力,為該教學方法的實施提供了硬件支撐,使得學生能夠在虛實融合的空間里進行探索,從而激發學生的主體能動性,積極進行知識建構。
5 研究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AR 技術在教育教學中的應用提出如下建議:
5.1 基于不同學習環境設計與開發適切性AR 應用
鑒于AR 技術在校內實驗室環境下的應用效果最佳,而在課堂和校外環境的應用效果較差,說明在課堂和校外學習環境中嵌入AR 技術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課堂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但AR 技術在課堂教學中的有效性并未得到充分展現。因此,研究人員需探究AR 在課堂應用效果不佳的深層原因,相關技術人員應根據教師與學生需求設計開發適用于課堂的最佳增強現實設備,以加速推進AR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23]。
6.2 結合學科特征遴選科學、合理的教學方法
基于本研究的發現,AR 技術與探究發現法的結合對學習效果的影響最顯著。探究發現法允許學生自己探索主題、建立知識聯結,因而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得到的啟發是教師在使用AR 技術時,除關注技術本身的優勢外,還應傾注更多心力選擇新穎的教學方法,而不是僅僅將傳統課堂的學習內容生搬硬套轉移到AR 系統上。因此,鼓勵教師結合學科特征與教學目標選擇科學、合理的教學方法,并借助AR 的技術優勢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5.3 研發面向不同學段的AR 教學資源與學習支持系統
鑒于AR 技術對高中和高職階段學習效果的影響最顯著,而對學前和小學階段的影響較弱,意味著教師和技術開發人員需充分考慮不同學段學生的認知發展特點,研發具有靈活性、個性化的AR 教學資源與學習支持系統。此外,在對46 項元分析樣本進行梳理、分析時發現,針對大學生和研究生群體的AR 課程資源及AR 系統較少[24],因此建議加強AR 在高等教育領域應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