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瀉病患兒合并驚厥的臨床特征及高危因素分析
王 琳,王 菡,劉小紅
(1.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陜西 西安 710061;2.西安市長安區醫院兒科,陜西 西安 710100)
驚厥是嬰幼兒期常見的臨床癥狀,兒童期的許多疾病會合并驚厥發生,但是患兒家屬普遍對驚厥發生的認識不足,易形成緊張情緒,從而造成驚厥相關疾病診療流程不規范,如過分干預、過度檢查等情況。腹瀉病是兒童常見病,是兒童患病和死亡的第二主要原因,我國每年有8.36億人次患腹瀉病,其中5歲以下兒童占3億人次,腹瀉病年發病率約為0.7次/人,5歲以下兒童的年發病率平均為1.9次/人[1]。既往對腹瀉合并驚厥的臨床研究多數僅限于病例報告,系統性的流行病學研究較少[2]。本研究以腹瀉合并驚厥住院兒童為研究對象,回顧分析嬰幼兒腹瀉合并驚厥的流行病學特征,采用病例對照研究分析疾病發生的危險因素,為臨床提供早期干預的理論依據。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選取2008年3月至2018年2月因急性腹瀉病于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住院的582例患兒為研究對象,其中以腹瀉合并驚厥的患兒為研究組(n=277),無驚厥發生的腹瀉患兒為對照組(n=305)。納入標準:①大便性質有改變,呈稀便、水樣便、黏膿便或膿血便;②大便次數較平日增多,≥3次/日。排除標準:①年齡≥14歲或≤28天;②非急性腹瀉病,病程>2周;③合并其他全身性疾病或免疫性疾病,如中樞神經系統感染、肺炎、遺傳代謝疾病等。該研究通過了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患兒及家屬均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收集符合納入標準患兒的臨床資料,主要包括①一般人口學資料:性別、年齡、居住地、居住方式;②出生史:孕次、產次、胎齡、出生體重、喂養方式、分娩方式、異常出生史等;③臨床癥狀:驚厥史、發病季節、腹瀉次數及持續時間、嘔吐次數及持續時間、脫水、發熱情況;④輔助檢查:尿酮、糞檢、輪狀病毒、心電圖、胸片、CT、磁共振成像(MRI)等。
1.3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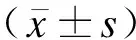
2結果
2.1兩組的一般資料
兩組患兒性別、年齡、居住方式的分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居住地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兩組的出生情況
兩組首胎、初產、胎齡、出生體重、分娩方式的分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喂養方式和異常出生史的分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1 兩組一般資料的比較[n(%)]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n(%)]
2.3兩組的臨床癥狀
兩組發病季節、腹瀉次數、嘔吐次數、嘔吐持續時間、脫水的分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既往驚厥史、腹瀉時間、發熱的分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2 兩組出生情況的比較[n(%)]Table 2 Comparison of birth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n(%)]

表3 兩組臨床癥狀分布的比較[n(%)]Table 3 Comparison of clinical symptoms between the two groups[n(%)]
2.4兩組輔助檢查情況
研究組CT異常患兒中,腦積水4例,蛛網膜囊腫4例,蛛網膜下腔增寬3例,其他病例為腦部不同部位點片狀密度增高影;因患兒配合度和既往MRI普及程度低等原因,完善MRI的患兒數量較少,在完成MRI檢查的異常患兒中,局灶性皮質損傷3例、腦積水1例、腦裂增寬1例、顳頂葉硬膜下積液1例、蛛網膜下囊腫1例。
兩組的尿酮(+)檢出率及胸片、CT、MRI異常的檢出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糞檢、輪狀病毒(+)、心電圖異常的檢出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2.5患兒腹瀉合并驚厥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經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女性患兒發生腹瀉合并驚厥明顯高于男性(P=0.01);1~<3歲患兒發生腹瀉合并驚厥是0~<1歲的6.20倍(P<0.01),≥6歲患兒是0~<1歲的0.23倍(P=0.02);嘔吐持續時間1天的患兒發生腹瀉合并驚厥是<1天的1.86倍(P=0.03),≥3天的患兒是<1天的0.23倍(P=0.02);腹瀉合并驚厥的發生與脫水程度呈反比,重度脫水患兒是未脫水的0.04倍(P=0.01);CT和MRI異常的患兒發生腹瀉合并驚厥的風險分別是CT和MRI正常的6.47和5.72倍(P<0.01,P=0.04),見表5。

表4 兩組研究對象輔助檢查的比較結果[n(%)]Table 4 Comparison of auxiliary examin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n(%)]

表5 患兒腹瀉合并驚厥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hildren with diarrhea complicated with convulsion
3討論
腹瀉是由多種病因引起的綜合征,為兒科常見病,多以嬰幼兒發病,可導致患兒脫水、電解質紊亂。小兒驚厥是大腦皮質神經元異常放電,出現局部或全身肌肉不隨意的強直性收縮,少數患兒會發展成癲癇,頻繁、長時間的驚厥發作會對患兒神經系統造成損害,影響小兒生長發育。小兒腹瀉引起的驚厥是兒科中常見的神經系統急癥。有學者認為患兒腹瀉合并驚厥的原因主要與患兒感染、高熱、年齡幼小及遺傳因素等有關,其中年齡是最主要的因素,患兒年齡較小,對外界的抵御能力較差,暴露后容易受到感染,從而導致身體出現炎癥,引起發熱,部分患兒可導致驚厥的發生[3]。
3.1腹瀉合并驚厥患兒的年齡和性別分布差異分析
本研究顯示,研究組1~<3歲患兒占80.14%,明顯高于對照組的39.67%;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也顯示,1~<3歲患兒發生腹瀉合并驚厥是0~<1歲的6.20倍,≥6歲患兒是0~<1歲的0.23倍。既往研究顯示,年齡越小神經系統發育越不成熟,神經髓鞘化越差,在多種因素影響下發生驚厥閾值越低;患兒年齡越小免疫功能越不成熟,易患感染,感染后體溫多有升高,所以小年齡兒童是驚厥發生的高危因素[4]。1~<3歲患兒的戶外活動量、機體暴露于病原環境的概率明顯高于0~<1歲患兒,因此該年齡段成為疾病高發時期。同時,相較其他年齡段兒童,1~<3歲兒童的飲食結構處于過渡關鍵期。低年齡患兒消化系統發育不成熟,消化酶活性低,加上生長發育快,需要營養物質多,消化道負擔重,容易出現消化功能紊亂,因此1~<3歲年齡段成為腹瀉合并驚厥發生的高危時期。此外,本研究顯示,女性患兒發生腹瀉合并驚厥明顯高于男性。既往研究顯示,雄激素可以影響機體大腦的學習及記憶能力,保護大腦免于外界的傷害,還可以通過調節機體相關蛋白水平進行大腦損傷后的修復[5]。雄激素可以通過上調Bcl-2蛋白、下調Bax蛋白的表達,減少抗氧化劑的消耗和抑制氧自由基的生成,從而減輕缺氧缺血后神經細胞的損傷。因此考慮男性腹瀉患兒體內激素水平與女性患兒不同,從而影響驚厥的發生。
3.2發熱與腹瀉合并驚厥的相關性
近年來,嬰幼兒腹瀉合并驚厥癥狀在臨床上比較常見,而且發病原因比較復雜,引起廣泛關注。有研究認為患兒腹瀉合并驚厥與發熱有關[6]。因小兒機體防御能力差,免疫功能不完善,易發感染性疾病,如腸道內感染導致腹瀉、腸道外感染病原體導致腹瀉或由于發熱和毒素作用出現消化功能紊亂導致腹瀉等,該類疾病又多會出現體溫升高;一方面由于小兒中樞神經系統發育不完善,皮層分化不全,神經髓鞘化未完成,興奮性及抑制性神經遞質的動態平衡不穩定,神經沖動容易泛化,造成驚厥閾值低,發生頻率高[7];另一方面由于體溫調節中樞機能發生改變,使神經系統也發生變化,表現為發熱時體溫升高引起神經元異常放電,導致驚厥發生[8]。但本研究顯示,發熱在研究組與對照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研究組患兒在體溫無明顯變化的情況下會發生驚厥,可見發熱與腹瀉合并驚厥無直接關系,不作為腹瀉合并驚厥發生的危險因素。
3.3腹瀉合并驚厥發生的機制
本研究顯示,嘔吐持續時間1天的患兒發生腹瀉合并驚厥是<1天的1.86倍,≥3天的患兒是<1天的0.23倍;腹瀉合并驚厥的發生與脫水程度呈反比,重度脫水患兒是未脫水的0.04倍,中度脫水患兒是未脫水的0.13倍,輕度脫水患兒是未脫水的0.34倍。結合研究對象臨床表現及糞便常規檢查分析,大部分患兒屬于病毒性腸炎,限于我院檢驗項目開展情況,本次研究共納入447例進行輪狀病毒檢測,陽性病例為242例,陽性檢查率為54.14%;其中研究組輪狀病毒陽性檢出率為45.49%,對照組檢出率為38.0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本研究顯示,研究組與對照組發病季節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秋、冬季節的發病率較高,與輪狀病毒在該季節高發的流行特征基本一致。因此考慮腹瀉合并驚厥的發生與輪狀病毒感染有一定的關聯性。既往國內有關腹瀉合并驚厥的研究多以輕度胃腸炎伴良性驚厥(benign infantile convulsions with mild gastroenteritis,BICE)患兒為主要研究對象。BICE的病因及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有學者根據BICE發病時間與輪狀病毒腸炎的發病季節較為一致,并在部分BICE患兒腦脊液、血液、咽拭子和糞便檢測到人類輪狀病毒(human rotavirus,HRV)基因組和抗HRVIgG抗體,推測該病毒引起的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n,CNS)感染是導致驚厥發作的主要原因[9]。關于BICE的研究表明,輪狀病毒可以釋放腸毒素NSP4誘導鈣穩態,從而破壞或者直接侵襲中樞神經系統,導致疾病的發生。同時,該輪狀病毒也可通過腦脊液直接造成神經毒性和神經遞質失調。腹瀉不伴脫水的患兒因大便次數少,隨大便排出的病毒數量也少。本研究中包含BICE患兒,因此認為,腹瀉不伴脫水的患兒體內病毒數量相較于腹瀉脫水的患兒多,存留在機體內的病原體更易導致驚厥發生[10]。有研究顯示,驚厥主要發生在胃腸炎的前3天,大多集中在24小時內,其提示病原體未經胃腸道排泄時更易導致驚厥的發生,病原體隨著嘔吐物及腸道分泌物排出后,驚厥的發生也隨之減少[11]。另有研究認為嬰幼兒患病毒性腸炎時,其驚厥閾值降低導致了反應性驚厥發生[12]。但該機制目前只是理論假設,未見科研實驗證實。臨床經驗顯示,腸道病毒感染易引起神經系統相關疾病發生,如病毒性腦炎的病原體大多為腸道病毒[13]。這些均提示腸道病毒在腸-腦相關通路中存在特殊的作用方式;另外,部分腹瀉患兒易出現代謝性酸中毒,酸中毒既可通過影響細胞內外電解質水平加重其紊亂程度,也可直接干擾神經元細胞功能,均導致出現驚厥[14]。
本研究顯示,CT和MRI異常的患兒發生腹瀉合并驚厥的風險分別是CT和MRI正常的6.47和5.72倍,提示存在腦結構異常的患兒在胃腸炎誘因下,更易造成神經系統病變,從而發生驚厥。因此,這一人群應作為提前防護的重點對象,同時做好其家屬的宣教工作。但在對照組患兒中,頭顱影像學檢查完成度較研究組明顯減少,導致數據存在一定的偏移。
綜上所述,女性患兒、年齡(1~<3歲)、嘔吐持續時間(1天)、脫水程度(輕度)、CT和MRI異常均為患兒腹瀉合并驚厥發生的危險因素。今后可進一步探索女性低年齡患兒(1~<3歲)體內代謝產物與其他患兒的差異,明確病因機制。目前由于臨床治療中缺乏對該病的認識,尤其在基層醫院,易造成誤診、漏診及治療方案混亂等現象。明確這一類疾病的臨床特點及相關因素,對臨床的治療決策有很大的影響,有助于早期明確診斷、合理治療,可減少不必要的檢查,避免過度治療。另外還可對腹瀉合并驚厥患兒進行遠期隨訪,分析疾病預后,進一步提高對該疾病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