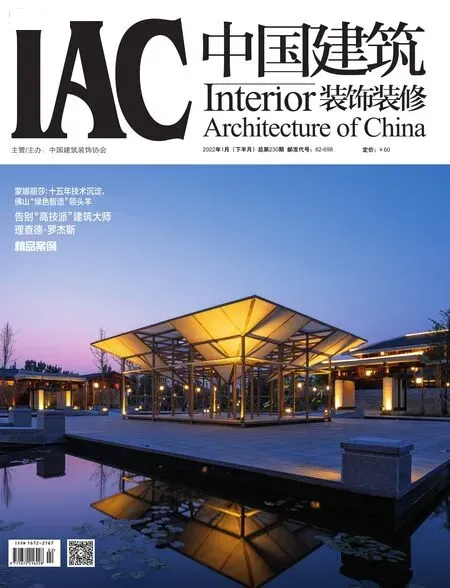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空間變革與發(fā)展
張玨菱 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環(huán)境設(shè)計系碩士在讀
田 原 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環(huán)境設(shè)計系副教授
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作為城市文化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文化表征的核心。在城市化進(jìn)程快速推進(jìn)的背景下,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與擱置的文化發(fā)展并不匹配,因此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不得不提上日程。要想在越發(fā)低迷的閱讀熱情和迷眼的現(xiàn)代化娛樂池中吸引大量民眾回歸城市文化的搖籃,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不得不面臨轉(zhuǎn)型。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民眾評判閱讀空間的首要標(biāo)準(zhǔn)是信息資源獲取的便捷度和資源的豐富度。近20 年來,民眾對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關(guān)注點從文化資源的儲備和獲取向空間環(huán)境的質(zhì)量轉(zhuǎn)移。眾多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建設(shè)也開始關(guān)注空間的功能性、特色性以及人文關(guān)懷等,同時也植入科技元素,開啟智能化新空間體驗。在此背景下,本文試圖從多角度對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空間變革進(jìn)行探討,并對空間發(fā)展進(jìn)行研究,助力于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發(fā)展。
1 城市公共閱讀空間
1.1 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
私人空間一般是指非公共生活場所,隱私作為私人空間的基本屬性,通常被理解為一項個體利益,僅限于私人生活。一旦個體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涉及公共事務(wù),那么就無私可隱,無隱私權(quán)可言。私人空間幫助社會中的個體實現(xiàn)生命的延續(xù),更具有生物學(xué)意義。公共空間最早由古希臘的廣場集會演變而來,有準(zhǔn)入資格的上層人士來討論城邦大事,這樣一群人聚在一起進(jìn)行集體性的討論就形成了公共話語權(quán)。到如今發(fā)展為更為廣泛、介入更深以及多元化的公共場所,人們在其中自由表達(dá),分享空間與信息。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公共媒體等更加廣泛的公共空間相繼出現(xiàn)。
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二元對立是自然而然的但也并不是絕對的。人只要在社會中生產(chǎn)生活,就需要與他人分享空間和資源,并建立和維系各種親密關(guān)系或遙遠(yuǎn)的聯(lián)系。
1.2 城市公共閱讀空間
公共空間是民眾聚焦公共事務(wù)、討論公共話題以及抒發(fā)個人觀點的公共優(yōu)質(zhì)平臺,在公共交往中產(chǎn)生的公共意見以及群眾發(fā)聲力量有助于民主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公共空間在古羅馬時期就存在,并隨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更新并有了更精細(xì)化的分類。隨著社會的進(jìn)步和城市文明的興起,不經(jīng)意間城市公共閱讀空間悄然登場。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作為公共空間中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它是以書籍為媒介、以閱讀為方式開展的公共交流和自由交往的活動中心。當(dāng)具備公共開放的閱讀空間和合理的公共閱讀機(jī)制,就會觸發(fā)市民集聚、閱讀和公共交往等行為。因為人是屬于社會性的群體,人本身的價值和天賦能力只有在公共空間里才能體現(xiàn)。當(dāng)有了空間載體與媒介,人自然而然便會聚集形成言語互動、信息交叉以及思想碰撞,最終形成新思想的產(chǎn)生與傳播。這種文化性質(zhì)的公共交流推動城市文明程度的進(jìn)步,這種文化屬性也正是公共文化空間的本質(zhì)屬性。
1.3 我國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興起與發(fā)展
隨著員工雇傭成本的提高和數(shù)字網(wǎng)絡(luò)的便捷化對實體書店的沖擊,單一模式下實體書店對讀者的吸引力下降。在入不敷出的困境下,我國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紛紛謀求轉(zhuǎn)型。在全民閱讀政策支持及內(nèi)因驅(qū)動的作用下,有些書店通過轉(zhuǎn)型創(chuàng)新來打破困境。它們將突破點定位在線下實體空間的整體營造上,運(yùn)用多業(yè)態(tài)融合的方式,加入飲品小食、特色文創(chuàng)以及文具用品來帶動消費,從而增加收入。同時豐富空間功能,在滿足閱讀及信息資料的獲取等基本功能之外,開辟特色文化體驗空間、藝術(shù)品展陳空間、公共活動空間、影視放映空間以及活動報告廳等復(fù)合功能的公共文化場所,以此來吸引不同興趣愛好的人群。不僅如此,空間整體氛圍的營造也逐漸細(xì)致化。別具一格的空間設(shè)計及配套的軟裝,疊加人性化服務(wù),進(jìn)一步滿足身體在空間的舒適需求。此后,各地類似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不斷出現(xiàn),并逐漸豐富和完善,成為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被稱呼為城市書房、書吧、書咖和驛站,或者城市智慧空間、創(chuàng)客空間以及知識空間等,雖然對其稱呼各異,但整體都屬于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范疇。
2 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空間變革
2.1 空間公共性的變革
在古代,書房是重要用房,私人性強(qiáng)。發(fā)展到現(xiàn)代,閱讀空間已不再嚴(yán)格的私人化,成為具有共享性質(zhì)的群體式閱讀。進(jìn)入如今消費為主導(dǎo)的時代后,圖書作為一種信息消費,真正融入了大眾生活。閱讀空間也從私人逐漸走進(jìn)公共場所,公共性成為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基本屬性。
如今“書店+”模式成為潮流,異業(yè)混搭和組合消費成為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基本業(yè)態(tài)模式,如書店畫廊、書店咖啡店、書店茶室以及書店貓咖等,如圖1 所示。當(dāng)人們習(xí)慣這種空間交往,便會產(chǎn)生空間性的集聚。在群體交往的過程中,不同類型、氛圍、主題的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對不同個體吸引程度不同。當(dāng)相同氣質(zhì)與趣味的群體進(jìn)行空間聚集,該空間便具有了一定的“私人意味”,而這種“泛私人性”受到趣味和價值觀的影響。因為每一個類型或族群都有相似的氣質(zhì)和趣味,而這種趣味共同體是通過生活細(xì)節(jié)和文化品味性相遇,猶如一個細(xì)節(jié)甚至一個暗示在向其同類招手。同一類型的集聚,就猶如自身鏡像的再現(xiàn)[1]。

圖1 北京西西弗書店咖啡館
喜好閱讀的受眾會選擇安靜舒適的閱讀空間;有交流意愿的群體會傾向帶有咖啡小食和公共交往平臺的閱讀空間;外來旅游人士或者閑逛消遣的人群會選擇具有地方特色或設(shè)計個性的閱讀空間。這種“泛私人性”的空間產(chǎn)生的空間氛圍場域同時也作用于空間中的個體。當(dāng)選擇在一個安靜舒適的閱讀空間中時,周圍的人會自然地形成一種共同的默契,達(dá)成心有靈犀的安靜閱讀的約定;當(dāng)身處小眾特色閱讀空間中時,共同的喜好會讓人與人之間產(chǎn)生不自覺的相互認(rèn)同。空間與個體相互影響作用,從而達(dá)成一個公共開放又帶有自主選擇性的泛私人化公共文化場所。
2.2 空間尺度的變革
人是萬事萬物的尺度。在不同尺度的空間和不同的場景下,人對于自我定位的認(rèn)知和對空間的感受不同[2]。當(dāng)獨自一人站在空無一人的廣場,沒有明顯的邊界和對于身體活動強(qiáng)制性的約束,就會感受到空間的開敞與自由,同時人也能在自由的空間內(nèi)更加清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感。獨自在房間里畫畫或?qū)懽鳎赃呌腥司蜁X得受到打擾,盡管空間里只有兩個人。但位于熱鬧的集市不會感到局促,個人能很好融入其中。因此,對空間的感受會受到所處環(huán)境正在發(fā)生的情景的影響。
在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中,也不斷地在開發(fā)設(shè)計各種尺度的空間來盛放不同人的身體與情感。通常在入口處會以中島式或者開放的空間來放置一些熱銷刊物或者精美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來吸引讀者,或者結(jié)合咖啡廳、花藝以及畫廊的形式來聚集人群。閱讀區(qū)空間形式更為多元,大閱讀區(qū)空間開敞,適合多人閱讀交流討論,氛圍自由輕松。獨立閱讀區(qū)一般位置相對靠近角落,設(shè)置獨立座位,有的會用隔斷對空間進(jìn)行一定的包裹。較為封閉的環(huán)境相對比較拘束,但在需要閱讀或思考的場合,私密的環(huán)境能幫助專注思想,帶來更加穩(wěn)定安全的感受。還有專門的卡座,一般會配備渲染氣氛的燈光,適合點杯咖啡看看雜志消磨時光。中庭有的還會有大臺階式閱讀區(qū),適合一些閑逛中發(fā)現(xiàn)不錯書籍時席地而坐的短暫停留者。窗邊的座位視野較好,有的會搭配精致的景觀,適合獨身一人的讀者消遣,避免了與人面對面的尷尬。現(xiàn)如今,成功的城市閱讀空間除了設(shè)置精致的閱讀空間,還會設(shè)置兒童區(qū)、報告廳、影音室和其他創(chuàng)意空間,不同空間內(nèi)有不同的活動內(nèi)容。在整個閱讀空間中,從“閱讀”這單一的活動行為中衍生出多樣的社交行為。由此,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不僅僅是販賣書籍和提供學(xué)習(xí)閱讀平臺的場所,并且逐漸發(fā)展為以“書”為文化符號牽引的社交活動的聚集地。
2.3 空間地方化的變革
19 世紀(jì),巴黎街頭出現(xiàn)的“街頭漫步者”沉迷于街頭新興景觀的誘惑和震撼,始終在城市中任意閑逛,并任由其他人對其投以好奇的目光,但在互看中彼此并沒有互動。巴黎的“街頭漫步者”揭示了隱藏在人與現(xiàn)代都市空間互動中的不安。一方面,他們被新的城市景觀所吸引,試圖探索各種未知的新鮮事物。另一方面,舊的空間和行為習(xí)慣的突然消失,導(dǎo)致他們想要尋找失去的場所感[3]。
2013 年,首家鐘書閣,上海松江泰晤士點開業(yè)。2018 年后,鐘書閣進(jìn)一步拓展書店版圖,堅持連鎖不復(fù)制的理念,根植不同城市。書店設(shè)計以文化和歷史為切入點,并不斷延伸書店功能邊界,增加餐飲和文創(chuàng)等業(yè)態(tài),進(jìn)一步深化鐘書閣作為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文化地標(biāo)作用。揚(yáng)州鐘書閣融合了揚(yáng)州古城元素,營造水與橋的仙境;成都鐘書閣結(jié)合竹林與梯田的概念,構(gòu)造圍城造型;無錫鐘書閣構(gòu)建文人園林,營造簡樸、清寧的境界;重慶鐘書閣以階梯打造錯落有致的山城風(fēng)光,重現(xiàn)3D 魔幻之城,如圖2 所示;長春鐘書閣展示了長春老工業(yè)基地的工業(yè)文明、紅色記憶以及人文筋骨;貴陽鐘書閣融合了少數(shù)民族風(fēng)情和喀斯特溶洞的自然地貌景觀;都江堰鐘書閣藝術(shù)化處理都江堰水壩,展現(xiàn)都江堰的山水景象。重設(shè)計為鐘書閣吸引了眾多的關(guān)注,但設(shè)計的核心是文化的運(yùn)用和輸出,地域文化是其支撐力量和核心要素,使優(yōu)秀的城市公共閱讀空間成為城市的文化地標(biāo)和人文景點。

圖2 重慶鐘書閣
2.4 空間邀約形式的變革
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古代,當(dāng)時的主流思想仍認(rèn)為文學(xué)藝術(shù)是屬于精英階層的事,文化知識獲取是少數(shù)人才能享受到的特權(quán)。不僅如此,在兩河流域、古埃及以及古羅馬都盛行圖書館與神廟伴生的模式。在空間上,神廟往往建立在高聳的山頂,雄偉的圓柱撐起威嚴(yán)的建筑,使其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即視感。因此,古代城市的閱讀空間對受眾者的邀約方式是單方面、低力度且有選擇性的,其公共性也只是對具有特權(quán)階層而言的公共,主要還是作為知識存儲機(jī)構(gòu)的形式而存在。
到了近現(xiàn)代,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成了時代的普世價值觀,平等分享的理念也融入到了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發(fā)展中。20 世紀(jì)初至21 世紀(jì)初,我國的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從萌芽階段快速發(fā)展形成現(xiàn)如今文化空間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閱讀不再是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而是傳播知識的基礎(chǔ)設(shè)施。與此同時,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建立并不是單向的對讀者邀約,在建立之前會考慮到當(dāng)?shù)刈x者即受眾的需求。例如,重慶南岸區(qū)一系列城市公共閱讀空間,資武道院分館(書店+武館)、小館分館(書店+設(shè)計工作室)、凍綠房分館(書店+茶室)以及南山書院分館(書店+賞琴品茗)等,結(jié)合了市民日常文化生活需求,同時增加了更多豐富的功能空間,使空間不僅僅只是閱讀,更多地滿足了社交功能及跨文化的交流。總而言之,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以及空間的變革,現(xiàn)代的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對受眾者的邀約方式也在不斷變化。兩者之間是雙箭頭指向、多元化且平等的關(guān)系,是時代發(fā)展中科技、政治、經(jīng)濟(jì)以及文化多重因素的推動下,以人為中心的雙向選擇的結(jié)果。
3 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空間改造發(fā)展策略
3.1 實體與虛體空間雙向助力
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發(fā)展到今天,已經(jīng)從以“書”為主體進(jìn)行銷售及周邊活動的標(biāo)準(zhǔn)化實體書店向業(yè)態(tài)融合的文化生活體驗空間轉(zhuǎn)型。進(jìn)一步來看,在智能化、大數(shù)據(jù)和人工智能科技逐漸滲透進(jìn)文化產(chǎn)業(yè)的趨勢下,充分發(fā)揮實體空間與虛體空間的潛在實力是賦能城市公共閱讀空間未來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智能科技和智能化設(shè)備的應(yīng)用給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智能化發(fā)展注入新的活力。大數(shù)據(jù)和云計算的云端科技,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傳輸進(jìn)入到PC、移動終端等智能設(shè)備,使得知識獲取更為簡單。同時,線下的實體空間也同樣植入各類科技設(shè)備。例如,自動結(jié)算、圖書智能檢索系統(tǒng)能便捷化員工操作,VR 技術(shù)的運(yùn)用讓空間更多元,公眾號的推廣及相關(guān)圖書App的使用能實時動態(tài)跟隨。新興技術(shù)使傳統(tǒng)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得到全面升級和重構(gòu),為讀者創(chuàng)造了豐富和多元化的閱讀場景,同時帶來智能化體驗。
在虛擬空間成為當(dāng)今社會交往行為主流陣地的情況下,實體空間的存在很有必要,受到科學(xué)技術(shù)的浪潮沖擊應(yīng)該尋求自身的發(fā)展出路,大力去創(chuàng)新發(fā)展。盡管在虛擬空間人能無視時間、地點以及空間的障礙進(jìn)行一系列活動,但情感的距離也因此拉開。人作為社會性群體,身體存在于物理性的實體空間內(nèi)并在其中產(chǎn)生生產(chǎn)實踐活動是人最直觀地接觸基礎(chǔ)生存空間,只有身體被妥善安放,精神世界才能被安撫。
作為實體空間的線下空間是提供讀書活動、文化傳播以及離線社會活動的公共場所,線上空間則是信息發(fā)布和共享、跨越時間和地域的在線虛擬社區(qū)。雙線發(fā)展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加強(qiáng)各類功能空間建設(shè),共同助力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現(xiàn)代化和多元化發(fā)展。
3.2 空間的公共性應(yīng)加強(qiáng)
現(xiàn)代都市空間秩序緊緊圍繞著各種區(qū)域,與專門的分工相關(guān),根據(jù)階層、種族以及年齡等進(jìn)行歸類,而外表和穿著不再作為社會身份地位的固定標(biāo)準(zhǔn)。但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公共性超越了傳統(tǒng)層級觀念,打通了個人、階級以及家庭等諸多社會階層和組織方式。并在文化消費的平臺上,基于生活和文化價值的一體化,開始重構(gòu)新的社會分層方式。目前,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從數(shù)量上及城市空間分布上都需大大增加,同時均衡分布,來滿足人均城市公共閱讀空間需要的實體可達(dá)性,從而實現(xiàn)不同階層、種族以及年齡的人群參與的可能。使其不僅在一線城市密布,而且在更多的城市落地開花,從而形成百花齊放的文化格局。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文化消費行為應(yīng)該被看作是一種非物質(zhì)的實踐活動。從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作為個體空間的小視角來說,公共空間的“公共性”,除了包括城市居民自由言論表達(dá)的維度,還應(yīng)該包括呼吁市民利益的角度。也就是說,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不僅僅是閱讀和獲取知識的場所,更應(yīng)該是舉辦文化活動、公眾文化訴求表達(dá)以及群體公共交往的平臺,是所屬城市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
3.3 空間在地化表達(dá)應(yīng)更清晰
現(xiàn)代人流動性較高,沒有時間在一個地方扎根,對地方的體驗和欣賞比較膚淺。如果一個人擁有藝術(shù)家的眼睛,那么他很快就可以評價一個環(huán)境的視覺效果。但是,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去學(xué)習(xí)關(guān)于一個地方的“感覺”。這種“感覺”是人的五感對空間的獨特感受,是與地方文化的共鳴,更是對該空間生產(chǎn)活動經(jīng)驗產(chǎn)生的親切感。因此,要讓城市公共閱讀空間在地化,需要營造空間氛圍、植入地方文化符號、構(gòu)建場所精神。
身體感官能直接地感受到空間氛圍。從色彩搭配、裝飾元素、家具選材、音樂風(fēng)格、小食飲品以及香氛味道等內(nèi)部設(shè)計與裝修都要符合整體設(shè)計定位,從而營造整體性的空間氛圍。此時身體感官包括視覺、嗅覺、聽覺、味覺以及觸覺都會受到外界的人為刺激。采用不同的氛圍設(shè)計會給人帶來不同的感受。當(dāng)感受好就會在內(nèi)心認(rèn)為這是可常來常往的地方。
除了營造空間氛圍形成身體的感受性,還應(yīng)植入地方文化符號元素,產(chǎn)生精神上的呼應(yīng)。在城市發(fā)展的過程中,沉淀的優(yōu)秀歷史文化與歷史記憶流淌在城市人的血液中。城市公共閱讀空間根植于城市中,屬于城市的一部分,在建設(shè)中理應(yīng)考慮將城市地域特色融入其中。在選址上可承托于具有歷史文化的區(qū)域或建筑,陳列用書可置入城市相關(guān)的歷史人文類書籍,同時加入符合當(dāng)?shù)匚幕奈膭?chuàng)產(chǎn)品和相關(guān)周邊。在室內(nèi)設(shè)計及空間布置上提取城市文化符號運(yùn)用其中。
當(dāng)人在城市公共閱讀空間進(jìn)行知識獲取、信息溝通、交流互動以及休閑創(chuàng)造等各項活動,會不斷發(fā)生文化交叉并產(chǎn)生群體氣質(zhì)。當(dāng)這種氣質(zhì)不斷積累,場所精神便隨之產(chǎn)生。城市公共閱讀空間要構(gòu)建良好的場所精神,需要引導(dǎo)整個空間文化氣場的方向質(zhì)量。在文化交流的大方向要積極、正面;在空間內(nèi)選擇的書籍、各類產(chǎn)品要品類好、質(zhì)量佳;在與其他業(yè)態(tài)融合共建的情況下,要確保該業(yè)態(tài)符合共建要求,室內(nèi)設(shè)計及空間格局有利于文化傳播與交流。好的城市公共閱讀空間與空間內(nèi)的受眾雙向影響,好的空間帶給人舒適積極的感受,不斷積累后產(chǎn)生場所精神,又為空間賦予地方文化場域磁場,從而吸引更多的人,無論本地還是別的城市居民都能感受屬于當(dāng)?shù)氐奈幕厣?/p>
4 結(jié)語
在過去的城市化進(jìn)程中,城市風(fēng)貌得以提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但城市的個性化趨向統(tǒng)一,同質(zhì)化現(xiàn)象十分嚴(yán)重。城市文化的多樣性正是潛伏在豐富多元的居住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中。隨著城市化的深入,精細(xì)化更新成為常態(tài)。當(dāng)解決并提升人的居住和工作場所的質(zhì)量這些剛性需求后,關(guān)于人的柔性需求就會上升。而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作為新型的文化空間,是城市微空間的形式之一,蘊(yùn)含著經(jīng)濟(jì)和文化價值。同時作為安置身體與精神的文化場所,具有人情味和煙火氣,進(jìn)一步形成情緒和能量的生活和工作場所。城市閱讀空間的不斷發(fā)展變革,比如多業(yè)態(tài)的融合,更關(guān)注空間尺度的舒適度,助推美化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文化內(nèi)涵以及重視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人文價等,使得其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圖書館,在滿足閱讀、資料查找的基本功能下,更多的是以“書”為媒介的空間下的平等交流與自我安置的城市公共空間。城市公共閱讀空間不僅成為城市人們新的交流溝通驛站,而且成為在城市中情感流浪的新落腳點,更是安放自己身體與情感的收容所。對于發(fā)展城市公共閱讀空間這種新型的文化空間,是現(xiàn)階段城市發(fā)展所需求的柔性發(fā)展的有效措施,也是在城市發(fā)展中著力保護(hù)人們的歷史記憶與情感觸點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