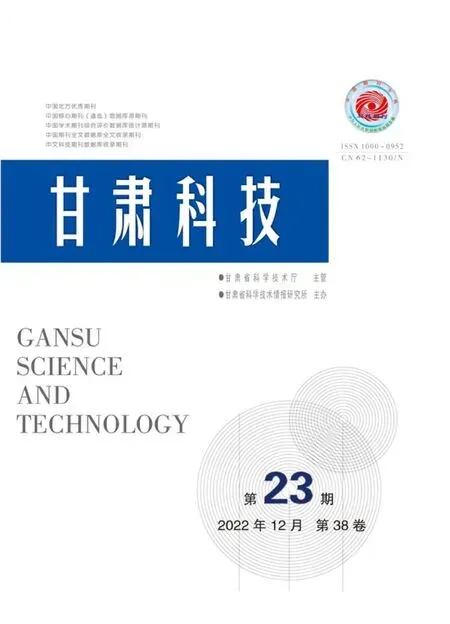消腫止痛合劑在骨傷科疾病中作用機制研究進展*
馬歲錄,何志軍,劉 濤,何元旭,王海剛,何 波,李 巖,陳 文
(1.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2.甘肅省中醫院足踝骨科,甘肅 蘭州 730050)
消腫止痛合劑是李盛華教授在臨床工作中,根據多年經驗所研制的一種具有活血化瘀、消腫止痛的藥物,已在臨床應用多年[1]。該合劑主要是由當歸、川芎、桃仁、紅花、赤芍、生地黃、三七、木香、青皮、澤蘭、甘草等藥物結合現代工藝加工而成[2]。在臨床應用中,對于關節炎、骨折、韌帶或者軟組織損傷、皮瓣移植、關節置換等都有很好的療效。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發現消腫止痛合劑治療骨傷科疾病的作用機制可能與調控VEGF-Dll4/Notch信號通路、AMPK/mTOR信號通路、PI3K/Akt信號通路以及抑制炎癥因子有關。
1 通過VEGF-Dll4/Notch信號通路治療血管損傷
創傷后組織器官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血管損傷,從而造成局部組織血液循環不佳,引起局部缺氧,很大程度上影響創傷后傷口的愈合。因此,促進損傷組織周圍血管的恢復,對于治療外周血管損傷類顯得尤為重要。
血管的生成有賴于尖細胞(頂端細胞)和莖細胞(柄細胞)參與,而這兩種細胞都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的調控[3]。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是由VEGR基因控制的,是當今公認的促進血管再生的細胞生長因子,也是刺激促血管生成途徑的始動因子。Notch信號通路是由Notch基因所調控的一種可以調節真核生物胚胎發育,細胞分化以及組織發生的高度原始的信號通路,對控制人體胚胎發育,組織生長以及維持體內平衡起到重要作用[4]。目前研究發現:Notch信號通路主要由4種Notch受體以及5種Notch配體以及相應信號傳遞過程中的一些下游分子構成,其中Notch受體主要包括Notch1、Notch2、Notch3、Notch4;Notch配體主要包括Jagged1、Jagged2、Dll1、Dll3、Dll4等[5]。
Notch1、Notch4受體以及Dll1和Dll4配體在新生的血管內皮細胞都可以表達。但是有研究表明:Notch信號通路中的配體Dll4在血管內皮上的尖細胞高度表達,在其他細胞中幾乎不表達,故而認為Dll4在血管內皮細胞生成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其在血管的生成以及穩態的維持中起到關鍵作用[6]。Notch1、Notch4受體在血管內皮細胞中都可以表達,共同參與維持血管的形成以及血管的穩定。因此,諸多學者認為:VEGF-Dll4/Notch信號通路在新生血管生成過程以及穩態血管維持中均重要的作用。
VEGF-Dll4/Notch信號通路在血管形成的過程中有諸多作用機制。已有研究證明,機體在缺氧狀態下,會釋放出大量的VEGF,激活Notch信號通路,上調Notch受體以及Dll4配體血管內皮細胞上的表達,從而加快新生血管的建立[7]。其次,VEGF的在體內的釋放也受到Dll4/Notch的負反饋調節,當機體中Dll4/Notch信號過度表達之后,會反饋性的下調VEGFR-2的釋放,上調VEGFR-1的釋放,從而防止血管的過度增生[8]。此外,VEGF-Dll4/Notch信號通路在血管形成中對于血管生成的諸多因子有一定的調控作用。
諸多臨床研究觀察到消腫止痛合劑對于外傷后機體的損傷、術后皮瓣的愈合均有很好的治療效果。趙萍[9]通過動物實驗研究發現:消腫止痛合劑不僅可以提高VEGF在損傷機體中的表達,加快骨折部位新生血管的形成,還可以作為一種自分泌因子,調節骨折后骨細胞和軟骨細胞的分化,從而促進骨折的愈合,但是該研究并沒有很好地表述消腫止痛合劑通過VEGF促進機體修復的潛在的作用機制。在此基礎上,何志軍等[10]、姚興章等[11]通過動物實驗發現:消腫止痛合劑可以上調VEGFA、Notch和Dll4 mRNA的表達,激活VEGF-Dll4/Notch信號通路,從而加快大鼠損傷皮瓣部位新生血管的形成,減輕大鼠血管內皮細胞的損傷,以避免局部組織的缺氧壞死,促進皮瓣的修復,說明消腫止痛合劑可以改善大鼠皮瓣血管內皮細胞的功能,其作用機制可能與激活VEGF-Dll4/Notch信號通路有關。
2 通過AMPK/MTOR、PI3K/Akt信號通路治療KOA
骨性關節炎(OA)是一種以關節軟骨損害為主的最常見的關節疾病,一般主要表現為關節的疼痛,僵硬以及活動受限,由于關節軟骨的損害一般不可逆,故而在治療上主要以緩解癥狀、延緩病情發展等為主。膝關節是人體下肢主要的負重關節,所以膝關節骨性關節炎(KOA)在臨床上較為多見,因此,預防膝關節骨性關節的進展對于患者功能的恢復尤為重要。有研究表明:通過調節AMPK/MTOR信號通路以及PI3K/Akt信號通路來提高機體的自噬能力,抑制細胞的凋亡過程,對骨與關節軟骨的有一定的保護作用[12-13]。
單磷酸腺苷蛋白激酶(AMPK)是一種異源三聚體蛋白,是細胞能量代謝過程中的“調節器”以及“中繼站”,其可以通過相關通路調節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Akt)以及下游的相關因子(如ULK1,Beclin1、LC3等)的磷酸化,來調控細胞的能量代謝、自噬以及凋亡的過程,以維持細胞的穩態。MTOR是細胞發生自噬的關鍵蛋白,其可以通過調節自噬過程中下游分子的磷酸化,如:ULK1、Beclin1、AKT等分子來抑制細胞的自噬,加快細胞的凋亡。PI3K作為一種膜蛋白,起著接受、傳遞信號的作用,可以通過調節AKT以及下游分子調控細胞的凋亡以及自噬。AKT的激活可以調控細胞過程中炎癥反應、氧化應激反應和細胞的凋亡[14]。
自噬是主要依賴溶酶體參與的,可以清除、降解體內受損或衰老細胞,以維持細胞穩態的一種廣泛存在于真核細胞中的降解途徑。細胞凋亡是指由相關基因控制的細胞自主有序的死亡,一般處于動態平衡之中,當機體處于應激狀態,凋亡過程就會加快,進一步加重機體的損傷。近幾年的研究表明,自噬存在于多種組織器官中,對于維持人體健康狀態以及抑制疾病的進展至關重要。細胞的自噬與凋亡是一個涉及到多種信號通路的過程,研究證實:細胞的自噬能力與其凋亡能力呈負相關。自噬的啟動主要依賴于ULK1-Atg13-FIP200激酶復合物形成并激活,當機體處于一種應激狀態,如缺氧、損傷等,會導致細胞內的AMP/ATP比值升高,激活AMPK,活化的AMPK可以抑制MTOR的磷酸化,使其活性受到抑制,間接激活ULK1;并且,活化的AMPK可以使ULK1上的一些位點激活,直接激活ULK1,最終使得ULK1-Atg13-FIP200復合物形成并激活,啟動自噬[15]。在自噬的小體膜形成階段以及招募下游分子階段,Beclin1-Atg14L-VPS34激酶復合體的形成與激活十分重要,該復合體的形成過程受到AMPK、ULK1、AKT的調節,AMPK/ULK1可以通過磷酸化Beclin1來促進該復合體的形成,而PI3K、AKT的作用則正好相反[16]。
諸多臨床研究證明消腫止痛合劑在骨關節炎、關節置換、軟骨損傷等方面有很好的臨床效果。在此基礎上,李金鵬等[17]、敬勝偉等[18]通過動物實驗研究發現:消腫止痛合劑可以顯著上調實驗動物軟骨內的AMPK、Beclin1、LC3的表達,下調MTOR、AKT、PI3K以及MMPs的表達,從而提高實驗動物應激狀態下軟骨細胞的自噬能力,減少軟骨細胞的凋亡,促進關節軟骨的修復,延緩KOA的進展。
3 通過抑制NOS、MMP9治療ASCI
急性脊髓損傷(Acute Spinal Cord Injury,ASCI)是一種具有高致殘率的嚴重的損傷。在治療上主要以早期減輕脊髓神經元繼發性損傷為主,研究表明,ASCI的患者早期體內會出現大量的一氧化氮(NO),從而加重脊髓的損傷,并且,在炎癥因子的刺激下,細胞會啟動凋亡程序,進一步加重脊髓的損傷[19]。因此,如何減輕ASCI后體內NO、炎癥因子的水平,以及防止細胞凋亡對于治療該疾病有重要意義。
NO在生理狀態下,可以防止血管痙攣,防止血小板聚集、黏附,調節機體血流量,對組織是一種保護的作用,這取決于一氧化氮合成酶(NOS)是處于一個相對于穩定的水平。當發生ASCI時,由于應激反應,體內的NOS的表達會顯著升高,產生大量NO調節局部血流,防止血栓形成,但是過量的NO可激活鳥苷酸環化酶,從而升高cGMP,造成脊髓的水腫。此外,過量的NO還可以通過與超氧陰離子自由基(O2-)結合,形成過氧化硝基陰離子(OONO-)和羥自由基(OH-),造成脂質過氧化,并且破壞細胞膜結構[20]。這些更加重了ASCI患者的病情。
抑制細胞凋亡可以防止ASCI的進一步加重。Caspase-3與caspase-9是啟動細胞凋亡的關鍵因子,caspase-9作為細胞凋亡的起始因子之一,可以最先將受損細胞中的死亡信號轉化為水解蛋白,并且激活細胞凋亡的執行因子Caspase-3等,從而啟動細胞凋亡程序。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是MMP家族中較為重要的一種,可降解內皮基底膜,使血腦屏障開放,有研究表明MMP-9參與細胞凋亡以及炎癥反應的過程[21]。
鄧強等[22]通過體外動物實驗研究發現:消腫止痛合劑可以顯著下調ASCI模型大鼠體內的NOS的水平,減輕NO引起的受損脊髓細胞的水腫以及局部炎癥因子的浸潤,并且消腫止痛合劑可以抑制脊髓受損部位Caspase-9、MMPs的表達,從而調控細胞凋亡,對脊髓神經元發揮一定的保護作用。
4 對TNF、IL-6等炎癥因子的影響
在創傷早期,由于應激反應,機體內的腫瘤壞死因子(TNF-α)、白介素-6(IL-6)、白介素-1(IL-1)等促炎因子都會顯著升高。在這些炎癥因子的作用下,體內的炎癥反應和免疫反應會被誘發,加快清除受損細胞,提高細胞凋亡的過程,不利于創傷后的恢復。
TNF是病理狀態下最早出現的炎癥介質,主要是由巨噬細胞和單核細胞產生,其可以激活中性粒細胞及其淋巴細胞等產生其他炎癥介質,如IL-1β、IL-6,從而產生“瀑布”效應,加快炎癥反應的進程[23]。IL-6、IL-1β是由多種炎癥細胞在應激狀態下產生的炎癥因子。IL-6不僅可以激活炎癥細胞、加快炎癥細胞的聚集與黏附,進而參與炎癥反應,還可以促進受損細胞的凋亡,有研究表明:IL-6升高可以提高創傷或者術后疼痛感以及其他并發癥出現的概率[24]。IL-1β是IL-1細胞因子家族中具有促炎效果的細胞因子,其除了可以促進炎癥反應,還可以破壞受損細胞線粒體功能,導致細胞因能量代謝紊亂而死亡,從而加快凋亡的進程[25]。因此,在創傷后如何減輕體內的炎癥因子的水平,在治療過程中尤為重要。
李玉吉等[26]通過臨床研究發現:消腫止痛合劑可以顯著降低骨折后軟組織損傷患者血清中的TNF-α、IL-6水平,減少壞死的發生率,促進組織的修復。在此基礎上,李金鵬、鄧強等通過動物試驗研究發現:消腫止痛合劑可以顯著降低ASCI以及OA試驗動物血清中的TNF-α、IL-6、IL-1水平,減少炎癥細胞的黏附以及炎癥反應的發生,從而大大提高損傷細胞的生存率。
5 小結
機體在挫傷、骨折以及開放性損傷等情況下,均會引起氣血損傷,血液溢于脈外,形成“離經之血”,從而導致受損部位腫脹、疼痛、出血,嚴重者引起局部壞死。消腫止痛合劑具有活血化瘀、行氣止痛之效,方中桃仁、紅花、川芎可活血化瘀;赤芍、生地、當歸可養血養陰活血,使得活血而不傷血;木香、青皮可行氣以活血,并有止痛之效;三七可化瘀止血、活血定痛,使得活血而不留淤;甘草可緩急止痛,亦可調和諸藥;諸藥合用,共奏活血化瘀、消腫止痛之效。已有研究證明:紅花、川芎、赤芍等藥物可以降低病理狀態下機體的炎癥反應,減少細胞凋亡,增強血管的穩定性,促進血管的生成。近年來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對于創傷后出現的血管損傷、軟組織壞死、缺血再灌注等并發癥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主要通過諸多信號通路探求其發病機制以及干預治療。與此同時,中醫藥在臨床上治療骨科疾病的療效日益突出,消腫止痛合劑作為一種院內制劑,在臨床已使用多年,臨床效果顯著,可以很好地改善患者的病理狀態。
綜上所述,消腫止痛合劑通過作用于不同信號通路緩解炎癥反應、減少細胞凋亡、提高自噬水平、促進新生血管的形成以及穩定,從而產生治療效果,但消腫止痛合劑是否具有更廣泛的治療作用及臨床應用價值,需要借助網絡藥理學進一步對該藥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