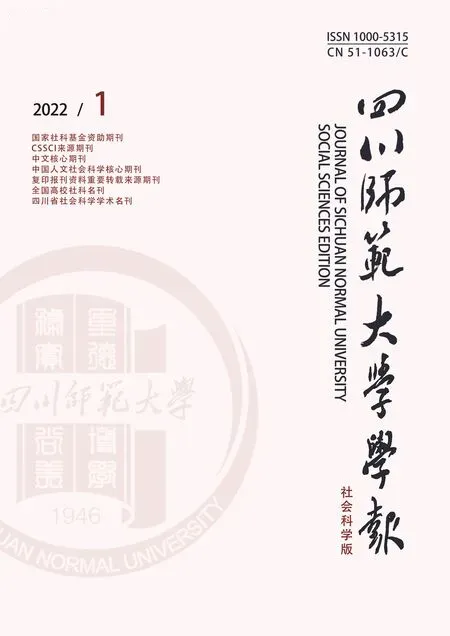多元主體視角下生態補償減貧路徑比較與行動方案選擇
宋碧青 龍開勝
生態補償的本質是尋找生態系統服務生產、消費和價值實現過程中相關方利益不均衡、交易成本過高的領域,通過制度安排使受益方付費、受損方得到補償,并激勵(或避免)相關方實施有(不)利于全局、整體和長期利益的行為(1)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編著《生態補償的國際比較:模式與機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生態補償政策多與特定的土地利用服務有關,其實施區域多為生態脆弱區且多與貧困地區在地理上有著高度的重疊性(2)吳樂、朱凱寧、靳樂山等《環境服務付費減貧的國際經驗及借鑒》,《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9年第11期,第34-41頁。。脆弱的生態環境會加劇地區貧困,農戶貧困又會增加對自然資源的攫取,加速脆弱的生態環境惡化,容易陷入惡性循環(3)Shixiong Cao et al., “Win-win Path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32, no.1 (August 2020): 430-438.。生態補償政策的設計初衷是為保護生態環境,近年來逐漸成為應用于減貧的政策工具,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環境治理問題往往與貧困問題交織,越來越多的研究聚焦于生態補償對緩解農戶貧困的作用機制及影響效應。
已有研究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生態補償對農戶減貧的影響,如不同的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減貧的效果(4)李軍龍等《激勵相容理論視角下生態公益林補償對農戶的增收效應——以福建三明為例》,《自然資源學報》2020年第12期,第2942-2955頁;吳樂、靳樂山《貧困地區不同方式生態補償減貧效果研究——以云南省兩貧困縣為例》,《農村經濟》2019年第10期,第70-77頁。,生態補償對不同收入水平農戶的影響(5)朱烈夫等《生態補償有利于精準扶貧嗎?——以三峽生態屏障建設區為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第42-48頁;馬橙、高建中《森林生態補償、收入影響與政策滿意度——基于陜西省公益林區農戶調查數據》,《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0年第11期,第58-64頁。,以及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辨析生態補償對農戶可持續生計的作用(6)趙雪雁等《生態補償對農戶生計的影響——以甘南黃河水源補給區為例》,《地理研究》2013年第3期,第531-542頁;袁梁等《生態補償、生計資本對居民可持續生計影響研究——以陜西省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為例》,《經濟地理》2017年第10期,第188-196頁;Genowefa Blundo-Canto et al.,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Livelihood Impact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ES) Schemes: A Systematic Review,” Ecological Economics149, (March 2018): 160-183.。制度環境是構建生態補償機制的先決性條件(7)曾慶敏、陳利根、龍開勝《我國耕地生態補償實施的制度環境評價》,《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114頁。,項目的補償對象一般為土地承包者,這意味著土地所有權制度和分配形式對于項目的扶貧效果而言十分重要,以致于同一塊土地的不同權利主體(比如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經營者)在參與生態補償時也存在利益沖突(8)Stefano Pagiola, Guidelines for “Pro-poo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7).。生態補償政策對依賴土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不同類型農戶收入均有影響,包括土地承包者、土地經營者以及農業雇工。多元主體生計水平的提升是項目效果持久性的有效保障,但以往研究通常只關注生態補償的參與農戶即土地承包者,少有研究考慮其他土地權利主體,論述生態補償對不同類型農戶減貧的作用路徑。
生態補償作為中央扶貧工作有力的政策工具,為脫貧攻堅目標的實現貢獻了重要力量。本文從多元主體視角出發,首先系統回顧國內外生態補償政策減貧的實踐經驗,闡明生態補償對不同類型農戶減貧的一般作用路徑及其差異,在此基礎上提出針對不同主體特征的生態補償行動方案,以期優化生態補償政策設計機制,從而為我國后脫貧攻堅時代生態補償減貧戰略的推進提供相關對策建議。
一 多元主體視角下生態補償的減貧路徑:基于文獻成果的歸納
生態補償多與特定的土地利用服務有關。由于補償項目的實施使依賴土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相關主體生計受到影響,可能會進一步引發農戶生計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擴大等其他社會問題。本文圍繞參與生態補償的土地承包者以及生計受影響的未參與項目貧困農戶(包括土地經營者和農業雇工),總結生態補償對不同主體收入的一般影響路徑。
(一)土地承包者與生態補償減貧
一般而言,生態補償的作用對象是土地承包者。對于可自愿參與的項目,土地承包者能否順利參與,首先取決于地塊位置是否位于項目劃定區域,其次是農戶是否有意愿和參與的能力(9)Stefano Pagiola, Agustin Arcenas, Gunars Platais, “Can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Help Reduce Pover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s and the Evidence to Date from Latin America,” World development33, no.2 (February 2005): 237-253; 王立安等《西部生態補償與緩解貧困關系的研究框架》,《經濟地理》2009年第9期,第1552-1557頁。;而對于強制實施的項目,只要土地承包者的地塊范圍符合要求則必須參與。生態補償通過多種補償方式彌補土地承包者損失,具體包括現金、實物、崗位、技術和教育等。
生態補償對土地承包者給予的現金或實物補償將直接影響其凈收益水平,當獲得的補償金額大于農戶參與項目的機會成本即凈收益為正時,無論農戶參與項目時是否自愿,生態補償都能提高其收入水平。但當項目的補償金額設置不合理時,農戶將面臨較高的機會成本,這會導致農戶的收入水平降低(10)李國平、石涵予《退耕還林生態補償標準、農戶行為選擇及損益》,《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年第5期,第152-161頁;Sven Wunde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he Poor: Concepts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3, no.3 (June 2008): 279-297.。現金或實物補償往往期限較短,對農戶只存在短期的作用效果,為保證項目效果持久性,需要提升農戶發展的內生動力,達致減貧增收的長效機制。生態補償對土地承包者收入的間接影響則表現為通過崗位、技術、教育等補償方式使農戶的生計資本得到積累,進而轉化為農戶的生計能力,最終助力農戶增收。
農戶的生計能力包括農戶的市場參與度和抗逆力。首先是農戶的市場參與度。生態補償中的教育、培訓計劃能夠提高農戶的技能水平和就業競爭力。崗位補償為貧困農戶提供就業機會,并對生態管護人員進行專業技術培訓和指導。如青海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保護中為農牧民設置生態管護公益崗位(11)趙翔等《社區為主體的保護:對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管護公益崗位的思考》,《生物多樣性》2018年第2期,第210-216頁。,四川省實施的諾華川西南林業碳匯項目對林農進行苗木繁育、補植、管護等方面技術培訓(12)張譯、楊帆、曾維忠《網絡治理視域下森林碳匯扶貧模式創新——以“諾華川西南林業碳匯、社區和生物多樣性項目”為例》,《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2019年第12期,第148-154頁。,洞庭湖區濕地生態補償為農戶提供環保、生產管理方面的技能培訓(13)楊新榮《濕地生態補償及其運行機制研究——以洞庭湖區為例》,《農業技術經濟》2014年第2期,第103-113頁。。其次是農戶的抗逆力。抗逆力是指農戶應用自身資本去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貧困地區生態環境脆弱以及農戶抵御風險能力不足使得農戶呈現出脆弱性特征(14)楊龍、汪三貴《貧困地區農戶脆弱性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年第10期,第150-156頁。,而生態補償提升了農戶的社會資本,增強村民間的合作和社會聯系(15)Rina Maria P. Rosales, Developing Pro-poor Marke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 Philippines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3), 58-59.,有助于集體行動的達成(16)Lindsey Roland Nieratka, David Barton Bray, Pallab Mozumder,“Can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trengthen Social Capital, Encourage Distributional Equity, and Reduce Poverty?”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13, no.4 (January 2016): 345-355.,從而分散農戶個體面臨的風險沖擊,增強了農戶的抗逆力,緩解農戶脆弱性。此外,相較于農業收入而言,生態補償款收入是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能夠對抗農戶因自然災害、價格波動而造成的農業收入損失。
(二)土地經營者與生態補償減貧
不同的生態補償項目對土地利用安排存在差異,如耕地保護生態補償允許農戶繼續耕種土地,而退耕還林、自然保護區生態補償等則限制對土地的使用。土地利用安排的差異將影響土地經營者租賃農地的能力,即改變其與土地承包者間的租賃關系。如果生態補償的實施區域已有土地租賃合同安排,那么生態補償介入可能會影響這種安排(17)Stefano Pagiola, Guidelines for “Pro-poo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7).。在限制土地使用的項目實施前,土地經營者能夠從土地承包者租入農地并按合同約定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項目實施后要求停止耕種則土地承包者將會終止租賃合同,土地經營者無法繼續租入土地,失去一部分農業收入來源致使其生計水平受損。
在部分允許繼續利用土地從事農業生產的項目中,土地經營者能夠繼續向土地承包者租入土地,土地承包者在獲得生態補償收益的同時獲取租金收入。由于實際耕作者是環境服務的直接提供者,對于提供了優質環境服務的土地經營者,理應得到相應補償,以激勵其持續采用生態友好的土地經營方式,但在現實中這部分農戶的權益往往被忽視。以我國耕地保護生態補償為例,政策實踐中涉及土地所有者、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經營者三類土地權利主體,而實際的受償權利人為土地所有者與土地承包者(18)趙亞莉、龍開勝《農地“三權”分置下耕地生態補償的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119-127頁。,對于采用環境友好型耕作方式的土地經營者未給予合理補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耕地使用過程中粗放利用、質量退化問題頻發。雖然近年實施的部分耕地保護生態補償在補償款分配中考慮到不同土地權利主體的利益,如蘇州市休耕補貼補償對象為土地經營者,南京市耕地地力保護補貼分配給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經營者,但大部分補償項目仍未考慮到多元主體間的利益格局。此外,對于采用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的土地經營者,其生產出的農產品蘊含更多的生態價值,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能獲得較一般農產品更高的價格,這一溢價也是作為對其采用生態經營方式的激勵補償。但在市場交易中,采用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的土地經營者是否獲得合理報酬具有不確定性。
(三)農業雇工與生態補償減貧
生態補償對區域勞動力的需求程度產生影響,表現為影響農業雇工的就業崗位安排。部分生態補償項目對勞動力需求降低,減少了項目實施區域為農業雇工提供的就業崗位。如森林生態補償要求農戶停止耕作,通過造林恢復生態環境,而同樣面積的林地所需勞動力投入遠低于耕地所需勞動投入(19)胡霞《退耕還林還草政策實施后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對寧夏南部山區的實證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5年第5期,第63-70頁。,勞動力農業供給時間縮短,原先被雇傭的農業勞動力變為閑置勞動力。而貧困地區農戶往往缺少其他正規部門的就業機會,多依賴于農業收入,因此導致農戶收入水平降低。如我國退耕還林工程要求停止在容易發生水土流失的土地耕種,廣西珠江流域森林碳匯項目為避免碳泄露,限制項目實施地及周邊區域農戶的林下種植、林下放牧、采伐薪柴等活動(20)陳沖影《森林碳匯與農戶生計——以全球第一個森林碳匯項目為例》,《世界林業研究》2010第5期,第15-19頁。。這些生產限制性措施會導致原先存在農業雇傭關系的農戶失去部分收入來源。部分生態補償項目對勞動力需求增加,為農業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加了農戶的經營性收入。如山東省云蒙湖水源地生態補償在保護區設置了生態保潔和垃圾運輸崗位,帶動當地群眾就業(21)耿翔燕、葛顏祥、王愛敏《水源地生態補償綜合效益評價研究——以山東省云蒙湖為例》,《農業經濟問題》2017年第4期,第93-101頁。。一項針對中國大熊貓自然保護區的研究表明,在保護區內開展生態旅游為農戶提供了部分就業崗位,幫助農戶獲得了更多收益(22)Yi Li, Peichen Gong, Jiesheng K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est Use Transition, and Farmers’ Income Differentiation: The Impacts of Giant Panda Reserves in China,”Ecological Economics180, (February 2021): 6-11.。
由此可見,當補償項目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時,農業雇工的工資性收入增加,生計水平提升,有助于緩解其貧困;而當補償項目支持對象為非勞動密集型的土地利用實踐時,其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減少,原先的農業雇工失去了部分收入來源,面臨生計轉型的局面。但由于技能水平不佳、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農業雇工較難在非農部門找到長期、正規的崗位,因而生態補償導致這部分農戶生計水平下降。
二 生態補償減貧路徑比較:不同主體路徑的差異
生態補償對環境服務的出售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收入產生影響,由于各主體在環境服務中扮演的角色各異,其減貧路徑存在異質性。本文圍繞生態補償項目地塊上不同類型農戶的權利及義務特征、補償形式及影響機制,總結生態補償對不同主體減貧路徑的差異,結果見表1。

表1 生態補償減貧路徑比較
(一)各主體享有的權利及承擔的義務存在差異
擁有土地產權是參與生態補償的前提條件,也是生態補償款項分配的基本依據。生態補償實施的項目地塊上不同主體享有不同的土地權利,其所需履行的義務也不相同。對于土地承包者而言,作為生態補償的參與者,擁有項目地塊的土地承包權,承擔項目合同規定的環境服務義務,是生態補償的受償對象。如我國實施的退耕還林以及耕地保護生態補償,地方政府在政策實踐中一般將生態補償款項支付給土地承包者,并要求其提供合同中規定的環境服務。土地經營者擁有項目地塊的土地經營權,其向土地承包者租入土地從事農業生產,不存在法理意義上的環境保護責任。但對于提供了優質環境服務的土地經營者,符合生態補償的運作規則,應當對其進行補償。農業雇工不享有項目地塊的土地權利,也無需承擔提供環境服務義務,不納入生態補償款項的支付對象,其僅通過出售勞動力換取工資報酬。
(二)生態補償對各主體的補償形式存在差異
針對不同主體提供的環境服務特點,設定差異化的生態補償形式。一般而言,要求土地承包者提供的環境服務公共性較強,多需借助政府轉移支付對其進行補償。政府轉移支付的具體形式包括縱向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以及橫向的地方政府間轉移支付,實踐方式包括發放現金、給予實物、設置崗位、技術培訓和教育投入等。土地經營者通過采用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一方面能夠生產出生態農產品,另一方面,由于生態價值外溢產生的環境外部效應,因而對土地經營者的補償,可通過政府轉移支付方式或借助市場交易機制實現。已有地方政府在耕地保護補償資金中設置一定的比例額度對土地經營者進行轉移支付,或通過市場交易使土地經營者生產出的生態農產品獲得生態溢價而獲得補償。農業雇工則是基于市場定價對其勞動投入支付相應報酬,如通過開展生態旅游為農業雇工提供服務業崗位并支付工資報酬。
(三)生態補償對各主體減貧的影響機制存在差異
生態補償對不同主體的減貧路徑存在異質性。具體而言,土地承包者是生態補償各類補償措施的直接作用對象,補償項目通過給予現金或實物補償直接影響土地承包者的凈收益水平,若參與項目后凈收益為正值,則有助于土地承包者增收減貧。此外,借助一系列配套的補償方式,包括崗位、技術、教育等提高農戶增收的生計能力,間接助力其減貧。生態補償對土地利用安排的差異影響土地經營者租賃農地能力,而土地租賃合同的維系或終止決定其農業收入水平。對提供了優質環境服務的土地經營者的補償能激勵其持續采納生態友好的土地經營方式,同時也可增加其收益。生態補償具體的運作安排影響項目實施區域為農業雇工提供的就業崗位安排,進而作用于其收入水平。當補償項目支持對象為勞動密集型的土地利用實踐時,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加農業雇工收入。部分項目為農業雇工提供技能培訓,增強其勝任崗位能力,有助于其獲得更穩定的工資報酬。
三 后脫貧時代不同主體生態補償的可選擇行動方案
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解決,后脫貧攻堅時代的主要任務是鞏固拓展扶貧成果以及治理相對貧困(23)曾福生《后扶貧時代相對貧困治理的長效機制構建》,《求索》2021年第1期,第116-121頁。。生態補償也需契合現實情勢,向構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長效機制轉變。基于前文的實踐經驗分析,在今后的生態補償政策制定中,不僅要關注項目參與者的福利水平變化,也要兼顧相關利益主體的生計水平,確保農戶協同發展,最大程度取得項目的生態、社會及經濟效益。為此,本文以提升土地承包者收入水平,維護土地經營者權益以及保障農業雇工福利水平為具體目標,提出契合不同主體特征的生態補償行動方案。
(一)土地承包者增收行動方案
由生態補償對土地承包者減貧的影響路徑可知,部分項目使參與者的凈收益水平降低,產生負面效果,為此通過優化實施策略使項目參與者實現利益最大化。
其一,增強生態補償項目瞄準性。有研究指出,部分補償項目的益貧性不顯著,較富裕農戶反而獲得了更多的項目福利(24)Nitta Atomu et al., “Direct Payments to Japanese Farmers: Do they Reduce Rice Income Inequality? Lessons for Other Asi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42, no.5 (September-October 2020): 968-981;吳樂、孔德帥、靳樂山等《生態補償對不同收入農戶扶貧效果研究》,《農業技術經濟》2018年第5期,第134-144頁。。在后脫貧時代,生態補償應與精準扶貧工作相結合,重點瞄準相對貧困人群,優先向易返貧群體傾斜。為此,需調整農戶的參與門檻,放寬對農戶土地面積、資金投入、技術能力的限制并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使政策起到較好的幫扶效果,但參與項目的農戶必須具備能夠提供所要求的環境服務的能力。
其二,優化補償標準制定規則。科學合理的補償標準是彌補農戶機會成本、調動農戶參與積極性的前置條件,在補償標準制定中需充分尊重農戶意愿。不同區域的自然資源稟賦、社會經濟條件存在差異,參與農戶的機會成本、家庭狀況也各不相同,要對不同地域、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戶制定差異化補償方案,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動態調整補償標準。
其三,開展多樣化補償形式。拓展當前政府主導的財政資金轉移支付的單一形式,如為有勞動能力的相對貧困農戶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加強教育、技術培訓等扶智措施,如農機服務推廣、專業技能培訓等;不斷引入市場機制,立足當地自然資源稟賦,發展特色農業產業。通過多種措施構建農戶生計能力培育和發展的有利環境,增強其生存韌性,實現生態補償鞏固脫貧成果的長效機制。
(二)土地經營者權益維護行動方案
生態補償通過影響土地經營者租賃農地能力及土地經營方式進而作用于其收入水平,本文為維護土地經營者權益,提出以下改進策略。
對于土地經營者可繼續租賃農地從事農業生產的情形,考慮對提供了優質環境服務的土地經營者給予一定補償。如政府可以在補償方案中設定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經營者間補償款分配的比例,以環境服務供給質量作為定價依據,構建環境服務質量評價體系,依據不同環境服務質量等級設定對土地經營者的補償數額,以此提高土地經營者的收入水平并增強其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此外,也有學者提出土地經營者由于不承擔法定的生態保護責任,不宜參與生態補償資金分配,土地經營權人直接生產農產品,通過產品價格獲得補償是優先方式(25)趙亞莉、龍開勝《農地“三權”分置下耕地生態補償的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119-127頁。。由此,為激勵土地經營者提供更優的環境服務,需建立物質化生態產品質量認證制度,體現優質生態農產品與普通農產品的價值差異,幫助土地經營者獲得更高收益。
針對土地租賃合同終止的情形,土地經營者可耕種的土地面積減少,減少了其農業生產活動,部分農戶變為閑置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面臨生計轉型的局面。為此,生態補償應擴大技術培訓、產業扶持的覆蓋面,將因項目實施而生計受損的這部分農戶納入政策范圍,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優化農戶勞動力配置以獲得更多收入。
(三)農業雇工福利保障行動方案
農業雇工僅按照雇傭合同約定提供體力勞動,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環境服務提供者,不屬于生態補償資金的分配對象。生態補償影響農業雇工的就業安排,對于補償項目支持對象為非勞動密集型的土地利用實踐,項目實施后產生閑置勞動力,部分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二三產業,但多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收入低且不穩定(26)繆麗娟、何斌、崔雪鋒等《中國退耕還林工程是否有助于勞動力結構調整》,《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年第3期,第426-430頁。。針對這部分農戶,生態補償在設計時要考慮實施區域的勞動力就業結構調整問題,使這部分因項目實施而產生的閑置勞動力得到有效配置。
具體而言,一是促進閑置勞動力“離土”即本地非農就業。以政府為主導,積極吸納引進社會資本,依托生態保護建設項目,落地生態產業發展,如生態旅游、生態農業等,為閑置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二是促進閑置勞動力“離鄉”。對于自身素質較優的閑置勞動力,政府需發揮中介橋梁作用,與勞動力需求度較高地區建立合作關系,積極引導閑置勞動力流向經濟發達地區收益更高的非農產業。
對于補償項目為勞動密集型的土地利用實踐,已有研究指出當前崗位類生態補償提供的就業崗位質量不高,且減弱了參與者拓寬就業渠道的主動性(27)杜洪燕、武晉《生態補償項目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影響——基于農村地區自我發展能力的視角》,《人口與經濟》2017年第6期,第116-124頁。。為此,政府可聯合高校或科研單位,下沉基層為農業雇工提供農業技能培訓,一方面有效提升農戶的技能水平,另一方面也促使其提供更優質的環境服務。
(四)保障措施
生態補償項目的平穩、有效運行離不開相關保障措施發揮的輔助性作用,主要應圍繞完善生態補償監測機制、建立退出機制以及完善補償立法展開。
第一,完善監測機制。需定期監測評估農戶收入情況和環境服務提供水平。當前需重點關注易返貧人群,包括不穩定的脫貧人口以及邊緣易致貧人口,將上述群體納入監測范圍,通過建立易返貧人口數據平臺,定期走訪摸排,及時了解農戶動態并施以幫扶措施。對農戶提供的環境服務質量的監測則可通過在村莊設置管護人員崗位,定期對森林保護、土地耕作等環節進行監管。
第二,構建退出機制。依托監測平臺獲得的信息,動態調整項目參與者,使有限的補償資金達到最優配置。具體而言,若農戶有效提供了環境服務并已脫貧,則將其退出;若農戶提供了環境服務但屬于易返貧人群,則考慮轉變補償方式、優化幫扶形式;若農戶未按規定提供環境服務但屬于易返貧人群,則加強對其環境服務質量的監督;若農戶未有效提供環境服務但已脫貧,則主動終止項目合同。
第三,完善生態補償立法。生態補償為我國的減貧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后脫貧攻堅時代仍將繼續發揮價值,為此,需健全生態補償立法體系,有效補足當前生態補償立法零散、標準各異、監管不嚴等短板,形成一套規范的法理約束。一是出臺正式的生態補償政策,明確各類生態補償的補償標準、范圍、程序等內容,界定各利益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將各類生態補償制度納入統一、完整的制度運行框架中;二是制定生態補償市場化運作規則,包括市場化準入、具體流程、收益分配等細則,確保生態補償市場化機制的規范運行。
四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多元主體視角,在系統梳理國內外生態補償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探討了生態補償對土地承包者、土地經營者以及農業雇工減貧的影響路徑及其差異,并針對不同農戶特征提出后脫貧時代生態補償行動方案。結果表明,不同類型農戶的土地權利及義務特征、適用的補償形式以及減貧作用機制存在差異。土地承包者擁有項目地塊的土地承包權,需承擔提供環境服務義務,其減貧機制在于生態補償影響土地承包者的凈收益水平與生計能力;土地經營者擁有項目地塊的土地經營權,不承擔提供環境服務義務,其減貧機制在于生態補償影響土地經營者租賃農地能力和干預其土地經營方式;農業雇工無參與項目地塊的土地權利,不承擔提供環境服務義務,其減貧機制在于生態補償影響農業雇工的就業崗位安排以及通過提供技能培訓提高其勝任崗位能力。
本文依據路徑分析提出針對不同主體的生態補償行動方案:為促進土地承包者增收要增強項目瞄準性、優化補償標準制定規則以及開展多樣化補償形式;為維護土地經營者權益,可在補償方案中設定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經營者間補償款的分配比例或構建生態農產品市場化機制,并對土地經營者提供技術培訓、產業扶持;為保障農業雇工福利水平,可依托生態保護建設項目,落地生態產業,通過政府引導其非農轉移就業,為農業雇工提供農業技能培訓。此外,還需完善生態補償監測、退出機制,推動生態補償立法以保障項目有效運行。
誠然,不同的生態補償項目在設計機制、實施方式上存在差異,這表明對項目的減貧效果和實施策略還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今后的生態補償機制設計中,應當重視所有的權益主體而非單一利益主體,既要考慮提供環境服務的直接權利主體,也要兼顧因項目實施而受影響的相關主體,充分考慮多主體的利益格局變化,增強政策扶貧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