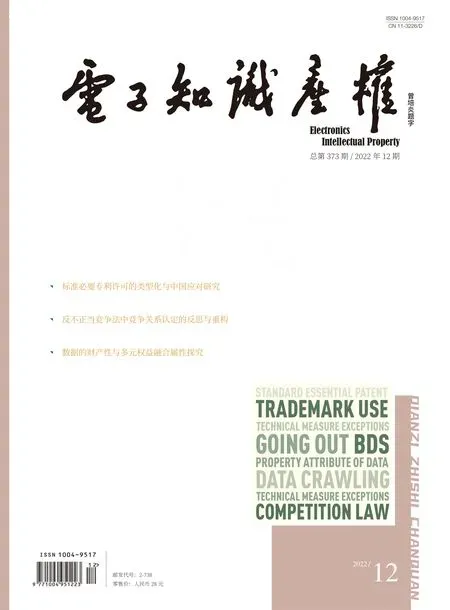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體系化分析
文 / 劉云開
一、引言
互聯網、電視網、電信網“三網融合”技術的革新與普及為廣播電視行業開辟了新的市場空間,同時引發了一系列新型法律問題,深刻影響《著作權法》中“傳播權”體系內容的變動。廣播組織權利制度是隨“三網融合”技術發展而變動最大的著作權制度之一。2021年6 月1 日,我國修訂后的《著作權法》正式實施,1. 參見中國人大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1/272b72cdb759458d94c9b875350b1ab5.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7 月31 日。意味著我國著作權法進入一個新的“解釋論時代”。2020年《著作權法》對我國廣播組織權利制度做出諸多調整,其中最大的調整莫過于在權利內容上為廣播組織增設“信息網絡傳播權”。該權利使廣播組織對其播出的廣播電視節目的控制從“非交互式”領域擴展到“交互式”領域,極大擴張了廣播組織權利范圍。對此反對觀點認為:(1)該權利既是對廣播組織權“以信號為基礎的方法”的背離,也將嚴重侵蝕公有領域;2. 參見王遷:《對<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的四點意見》,載《知識產權》2020年第9 期,第42-46頁。(2)由于作品、表演和錄音錄像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制度十分完善,因此該權利存在的意義不大,其適用范圍僅限于廣播組織享有非專有使用權的內容和公有領域內容;3. 陳紹玲:《論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適用空間》,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 期,第65-74 頁。(3)廣播組織在播放他人制作的廣播、電視的過程中沒有貢獻新的內容,對廣播、電視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并不合理,該權利范圍應僅限于針對廣播組織自己制作并播出的廣播、電視。4. 袁鋒:《新技術環境下廣播組織權的問題與完善——兼評最新<著作權法>第47 條》,載《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 期,第109-119 頁。上述反對觀點展現出一定的“規則懷疑論”傾向,且第(2)種觀點與第(3)種觀點所提供的最終方案截然對立。由此表明,圍繞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而產生的理論爭議并未隨《著作權法》的修訂完成而消失,相反卻會對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條款的適用產生障礙。法律屬闡釋性概念,5. 【美】德沃金:《法律帝國》,李常青譯,許宗英校,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 頁。立足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條款,運用解釋論方法回應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客體爭議、范疇界定和體系銜接問題,以確保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的準確適用,既是一種可行選擇,更是一種迫切要求。
二、因何設權: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正當基礎
(一)本土需求:廣播電視節目數字化進程加快
隨著數字與傳媒技術的融合與革新,電視行業已經進入融合發展的快車道。我國廣播機構已不再滿足于使用傳統的模擬傳輸技術向公眾提供廣播電視節目,而是抓住“數字賦能”的機遇,借助電視網、電信網、互聯網等多種通道,以電視或網絡直播、轉播、點播等多種方式傳播其廣播電視節目,從而提升傳播效率和節目收視率,便捷觀眾選擇需求,助力廣播電視產業發展。報告顯示,2021年全國廣播電視行業總收入首次突破1 萬億元,其中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業務實際創收收入9673.11 億元,分別同比增長24.68%和25.43%;智能終端用戶和有線電視雙向數字用戶逐漸增長,全國交互式網絡電視(IPTV)用戶超過3 億元,互聯網電視(OTT)用戶數超過10 億元。6. 參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2021年全國廣播電視行業統計公報》,http://www.nrta.gov.cn/art/2022/4/25/art_113_60195.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6 月20 日。但與此同時,隨著廣播電視節目“數字化分發”進程的不斷加速,廣播電視機構與傳統的網絡平臺在數字空間形成競爭關系,其共同的目標是網絡受眾及其注意力。由于公眾對廣播電視節目的獲取更加便捷,加之網絡平臺缺乏嚴密的監管措施,導致部分用戶通過電視、網絡非法錄制和傳播廣播電視節目的行為日益嚴重,廣播機構失去節目控制權的風險越來越大。7. 參見《廣播部門目前的市場和技術趨勢:導言和內容提要》,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及相關權常設委員會SCCR/30/5文件,2015年6 月17 日發布。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不法侵權人的行為嚴重分流了廣播電視節目的受眾注意力,而廣播組織者的維權成本則不斷提高。8. 參見劉云開:《廣播組織權客體之再辨析——兼評我國新<著作權法>第47 條》,載《電子知識產權》2020年第11期,第13 頁。
然而在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前,廣播組織權的權利范圍僅限于禁止未經其許可而對廣播電視節目進行轉播、錄制和復制三類情形,不延及網絡領域,9.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10)第四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有權禁止未經其許可的下列行為:(一)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轉播;(二)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錄制在音像載體上以及復制音像載體。”侵權人將廣播節目通過互聯網傳送到用戶終端的行為十分多見,例如一些網站未經授權向公眾提供體育賽事的網絡直播和點播回看服務,其中既涉及廣播電視節目的網絡轉播,也涉及信息網絡傳播。顯而易見的是,此種行為必將給廣播機構的合法利益帶來嚴重損害,廣播機構的相應投資可能付諸東流。如果著作權法缺乏相應規范,廣播機構和司法機關面對此種非法行為也顯得無能為力。在“浙江省嘉興華數公司與中國電信嘉興分公司侵犯廣播組織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被告通過互聯網轉播了涉案廣播電視節目,但尚不能依據原《著作權法》的規定將該行為認定為“轉播”,加之廣播組織也不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因此無法規制被控侵權行為。10. 參見浙江生嘉興市南湖區人民法院(2011)嘉南知初字第24 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浙嘉知終字第7 號民事判決書。更重要的是,當前多數廣播電視盜錄盜播行為都發生在網絡空間,如果不將廣播組織權利范圍擴展到網絡領域,廣播組織將不能獨立于著作權人而單獨起訴侵權行為人,但廣播機構的損失并不因此而降低。11. See Shyamkrishna Balganesh, The Social Costs of Property Rights in Broadcast (and Cable) Signals,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22: 1303, p. 1319 (2007).因而,將廣播組織權的權利范圍延伸至網絡領域,為廣播組織賦予網絡轉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對于維護廣播電視機構的投資和合法利益具有現實性和必要性。
(二)國際動向:SCCR 擬擴張廣播組織權利內容
為廣播組織賦予信息網絡傳播權既是我國維護廣播電視機構合法利益、規范行業競爭秩序的實際需求,也與國際立法趨勢保持一致。擴張廣播組織權利內容,強化廣播組織權利國際保護,這是《羅馬公約》制定以來持續存在的一項國際知識產權議題。近年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與鄰接權委員會(SCCR)致力于制定一份具有現代意義的《保護廣播組織條約》,國際社會代表在廣播組織權利保護問題上也表現出權利擴張的主張。
在1948年《伯爾尼公約》布魯塞爾修訂會議上,締約方圍繞“是否應當將版權擴展到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和廣播機構”這一議題展開討論。隨后國際社會于1961年單獨締結了《羅馬公約》以保護上述主體利益。根據該條約第十三條,廣播機構有權授權或禁止他人轉播、錄制、復制以及向公眾傳播其廣播節目。12. Se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formers,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adopted at Rome on October 26, 1961.但《羅馬公約》的實施范圍極為有限:第一,它只對廣播節目的“同步廣播”提供保護,而不包括“延遲廣播”這類核心業務;第二,它只規制傳統的無線轉播行為,而不規制包括有線電纜和數字廣播在內的傳播方式。當然這與條約制定時有線廣播尚處于起步階段有關,締約方未能預知廣播技術發展之迅猛。第三,該條約的適用范圍十分有限,只有加入《伯爾尼公約》或《世界版權公約》的簽署方才能成為該公約的成員單位。1974年的《布魯塞爾公約》是第二個保護廣播組織權利的國際條約,但因為該公約旨在保護原始衛星信號的傳輸,而非廣播信號的再次傳輸,導致其適用范圍依然十分有限。在后來的TRIPS 協定締結過程中,盡管有線電視技術在當時已十分普及,但其僅僅納入了《羅馬公約》的實質性條款,而未將有線廣播寫入TRIPS 協定。其原因在于,各締約方主要圍繞網絡和數字技術給版權法帶來的挑戰展開討論,而忽略了廣播電視技術的發展現實。13. See Mantani Sharma, TRIP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the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Stalemate or Deliberate Ignorance?, Richmon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Vol. 24: 5, p. 19 (2018).同時TRIPS 協定被設想為“最低標準”條約,并沒有更新現有國際知識產權條約的想法。14. See Laurence R. Helfer, Adjudicating Copyright Claims Under the TRIPS Agreement: The Case for a European Human Rights Analogy,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9: 357, p. 360 (1998).因此廣播組織錯失了擴張權利內容的機遇。
1997年,WIPO 舉辦“世界廣播、新通信技術和知識產權研討會”(即“馬尼拉研討會”),此次會議所達成的共識是,現有廣播組織國際保護制度需要順應廣播技術的發展,有效遏制廣播盜版行為。15. See WIPO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 Related Righ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WIPO Doc. SCCR/1/3, Sep. 7(1998), p. 4.1998年,WIPO 成立SCCR 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更新廣播組織國際保護制度。然而從1998年至今,SCCR 已連續主持召開四十二屆會議討論制定具有現代意義的《保護廣播組織條約》,旨在應對新技術環境下的廣播組織權利國際保護問題,但由于各國分歧過大,至今尚未就條約的實質性內容達成共識。《保護廣播組織條約》由此成為知識產權保護史上爭議最大、難度最大、制定時間最長的條約。16. 胡開忠:《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權利內容立法的反思與重構——以“修正的信號說”為基礎》,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2 期,第39 頁。但在這一過程中,具有推動意義的事件是WIPO 在2006年大會上決定SCCR 應力求商定并最后確定“以信號為基礎”的保護目標、具體范圍和對象。17. See The WIPO Treaty on the protection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Informal Paper. Prepar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SCCR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f the SCCR at its 16th Session (March 2008), p. 2.當然在條約磋商過程中,一些代表提出了“基于權利的進路”或“基于內容的進路”。該觀點認為,《保護廣播組織條約》應是對《羅馬公約》的更新,以彌補通信技術發展所產生的保護差距。新的條約應當沿襲《羅馬公約》,對已經存在的權利進行更新。然而反對者認為,許多國家并沒有加入《羅馬公約》,也沒有為廣播組織提供版權法意義上的保護,“基于權利的進路”將導致許多國家版權法中為廣播組織機構新增“知識產權層”(layer of IP rights),由此可能會損害消費者利益,鎖定公共領域的內容,并扼殺技術創新。18. See The WIPO Treaty On The Protection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Informal Paper. Prepar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SCCR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f the SCCR at its 16th Session (March 2008), p. 7.也有一些代表認為,應當以“防止信號盜竊”為目標導向,采取“基于信號的進路”,賦予廣播機構對“載有內容的信號”所享有的權利,“有限而具體地關注保護信號免遭故意盜用或盜竊”。19.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WIPO Broadcast Treaty Provided by Certa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 and Performers' Representatives (Sept. 5, 2006), at http:// www.eff.org/IP/WIPO/broadcasting_treaty/wipo-statement-20060905.pdf (Last visited on August 24, 2022).
在網絡廣播領域,SCCR 最初沒有計劃將“網絡廣播”納入條約討論范圍,決定暫時留給以后單獨討論。但在SCCR 后來召開的會議上,許多國家的代表認為,未經授權通過信息網絡傳播廣播信號的行為十分嚴重,新的《保護廣播組織條約》需要增加信息網絡傳播權,以保護其國內廣播機構的投資利益。SCCR 對此提出了三種替代解決方案,簽署方可以:(1)簡單地批準與廣播有關的條約和有線廣播;(2)批準條約并通知WIPO 總干事其選擇包括對網絡轉播的保護;或(3)批準條約并通知總干事其選擇包括對網絡轉播和信息網絡傳播的保護。20. Matthew D. Asbell, Progress on the WIPO Broadcasting and Webcasting Treaty,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4: 349, p. 353 (2006).在2022年5 月9 日—13 日舉行的SCCR第四十二屆會議上,SCCR 發布了最新的《經修訂的產權組織廣播組織條約案文草案》(以下簡稱《案文草案》),該《案文草案》相比于2019年的《經修訂的關于定義、保護對象、所授權利以及其他問題的合并案文》(以下簡稱《合并文案》),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將“廣播”的定義范圍擴展到了“計算機網絡”領域。該《案文草案》第二條規定,“廣播”是指以有線或無線手段傳輸節目信號供公眾接收。在關于該定義的解釋中,《案文草案》指出,“‘廣播’中不僅包括無線傳輸,還包括‘有線’傳輸。該定義由此涵蓋所有傳輸,包括通過電纜、衛星、計算機網絡和任何其他手段。因此,‘廣播’的概念在本條約中是完全技術中立的。”該建議認為,不應將“網絡傳輸”排除在“廣播”定義之外,而應當明確網絡傳輸屬于廣播行為。如果各成員方希望將網絡傳輸排除在條約適用范圍之外,可以通過條款保留的形式予以執行。21. See Revised Draft Text for The WIPO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Treaty, prepared by the SCCR Acting Chair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CCR Vice-Chair and facilitators. SCCR/42/3, May 9-13(2022). p. 10.筆者認為,新《案文草案》將“網絡廣播”納入“廣播”的范圍,更具有現實意義。第一,網絡作為傳輸廣播電視節目的重要通道,在許多國家已經相當普及,成為廣播機構的重要投資場域。如果在新的《保護廣播組織條約》中排除網絡廣播,將極大限縮條約的適用范圍和制定意義,更甚者可能再步《羅馬公約》的后塵;第二,不少國家的著作權法已經賦予廣播組織網絡轉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在條約締結過程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代表肯定條約納入網絡廣播的意義。
(三)域外經驗: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實踐
為了實施《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公約》(WCT)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兩項條約,強化數字網絡環境下著作權和鄰接權的保護,歐盟于2001年通過了《信息社會中著作權和版權指令》(以下簡稱“《指令》”)。與目前保護廣播組織的國際條約以及此前歐盟制定的廣播組織權保護規定相比,該《指令》對廣播組織提供的保護更加嚴格。首先,《指令》保護的對象不限于無線廣播,同時將有線廣播、衛星廣播也納入保護范圍。《指令》第二條規定,廣播組織就其通過無線、有線或衛星傳輸的廣播的制品,享有授權或禁止他人復制的專有權。22. 參見《信息社會中的著作權與鄰接權指令》第二條第5 款。其次,《指令》同時為廣播組織規定了“提供權”,即信息網絡傳播權,由此廣播組織對其廣播的固定享有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擇的地點和時間可獲得的專有權。23. 參見《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第三條第2 款(d)項。歐盟這一《指令》,及時把握住廣播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趨勢,擴張了廣播組織權的權利范圍,實現數字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權利保護力度的強化。除歐盟成員國外,瑞士等一些歐洲國家和日本等一些亞洲國家都為廣播組織賦予信息網絡傳播權,為數字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提供了高標準的權利保護。如《瑞士著作權和鄰接權法》第三十七條第五款規定廣播組織有權通過任一媒介向公眾提供其廣播電視,使公眾可以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接收。《日本著作權法》對“無線廣播組織”和“有線廣播組織”均賦予了信息網絡傳播權,其第九十九條之二規定:“廣播組織專有接收廣播或者接收廣播后進行有線廣播,將廣播內容進行信息網絡傳播的權利”;第一百條之4 規定:“有線廣播組織專有接收有線廣播并將其進行信息網絡傳播的權利”。
當然,域外規定對我國立法而言僅具有參考意義,是否為廣播組織賦予信息網絡傳播權,應以本土需求為遵循。曾有觀點認為,雖有部分發達國家賦予廣播組織以信息網絡傳播權,但更多發展中國家出于保護自身文化產業的需要,并未將廣播組織權延伸至網絡領域,我國不應超越發展階段規定這一權利。24. 參見許福忠:《廣播組織權中的轉播權不應延伸至互聯網領域》,載《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2 期,第44 頁。但是將發展階段作為我國著作權保護的標準,顯得過于絕對。在沒有國際強制義務的前提下,我國是否應當為廣播組織賦予信息網絡傳播權,更應當關注我國廣播電視產業發展需求與著作權法公有領域的保護。報告顯示,我國廣播電視覆蓋人口數居世界第一,廣播影視制播能力顯著增強,目前廣播影視規模已躍居世界前列。25. 參見《國家統計局發布報告:我國廣播影視規模已居世界前列》,載《中國廣播》2019年第8 期,第41 頁。賦予廣播組織以信息網絡傳播權,強化廣播組織權利保護,營造良好的廣播電視產業生態,符合我國廣播電視行業發展實際情況。
三、以何設權: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客體依據
客體是界定權利的依據,是理解廣播組織權不能回避的問題。廣播組織權客體是廣播組織權利制度中的核心問題,也是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過程中最富爭議的問題之一。近年來,學界關于廣播組織權客體的討論激烈,集中表現為“節目說”和“信號說”之爭。26. “節目說”認為廣播組織權的客體是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參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98 頁;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 頁。“信號說”則認為廣播組織權的客體是廣播電臺電視臺發射的“載有節目的信號”,參見王遷:《廣播組織權的客體——兼析“以信號為基礎的方法”》,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1 期,第 100-122 頁;胡開忠:《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權利內容立法的反思與重構——以“修正的信號說”為基礎》,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2 期,第39-50 頁。遺憾的是,學理界和立法界對這一問題仍未達成共識。我國著作權法在此次修訂中也未對“節目說”和“信號說”做出明確選擇,使這一問題更加撲朔迷離。解釋和適用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必須正確分析廣播組織權客體。
(一)反向推理:網絡傳播權對于界定廣播組織權客體之意義
反向推理是填補規范漏洞的方法之一,適用于立法者有意或者依法律目的將法律后果僅僅適用于事實構成要件的情形,它是一種具有規范目的的評價活動。27. 舒國瀅、王夏昊、雷磊:《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 頁。從解釋論視角看,在不明確廣播組織權客體是A 還是B,由A 無法推導出規范效果C 但由B 可以推導出規范效果C 時,那么根據已經存在的C,可以對廣播組織權客體屬于A 還是B 進行反推。當前,廣播組織權客體“節目說”“信號說”之爭,與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之間呈現出“內包蘊含關系”。28. “內包蘊含關系”是指特定法律規范所規定的事實構成要件是其所規定的法律后果的必要條件,該事實構成要件已在法律規定中對所有可能產生法律后果的情形都被窮盡列舉出來。換言之,有法律后果G 一定有事實構成要件F;而沒有事實構成要件F,就沒有法律后果G。參見舒國瀅、王夏昊、雷磊:《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410 頁。
權利客體是連接不同主體之間的媒介,29. 方新軍:《權利客體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 頁。對權利客體的界定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一些學者基于“權利邊界決定客體類型”的錯誤認知,提出廣播組織應受保護的利益類型決定了其客體類型:一是“轉播權”用于維護廣播組織的瞬時利益,因此其客體為轉瞬即逝的“廣播電視信號”;二是錄制權、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用于維護廣播組織的延時利益,其客體則是具備延時性的“廣播節目內容”。由此該觀點認為廣播組織權的客體既包括“節目”又包括“信號”。30. 陳紹玲:《論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適用空間》,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 期,第70 頁。事實上,這種廣播組織權“雙重客體論”的論證邏輯值得反思。首先,從體系化視角考察,廣播組織的轉播權、錄制和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是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三類并列的權利,既屬同一條款中的平行權利,其權利主體、權利客體必然具有一致性,否則將違反法律的體系化原則。其次,在法律邏輯上,“權利邊界決定客體類型”不符合事實基礎,因為權利的客體是權利設立的基礎,31. 參見方新軍:《權利客體的概念及層次》,載《法學研究》2010年第2 期,第36 頁。客體的作用是界定權利。32. 參見梅夏英:《民法權利客體制度的體系價值及當代反思》,載《法學家》2016年第6 期,第29 頁。因此權利客體是權利內容生成的依據,如果不明確法律保護的客體,就無法明確法律關系中不同主體的行為邊界。質言之,廣播組織者應當享有哪些權利,取決于著作權法對廣播組織權客體的定位,因此更符合邏輯的研究思路是“權利客體決定權利內容和權利范圍”。盡管2020年《著作權法》在處理廣播組織權客體時試圖擱置爭議,但權利客體具有唯一性,立法者在決定賦予廣播組織以信息網絡傳播權時,事實上就已明確了廣播組織權的客體,只是沒有在法律條文中釋明。
法律解釋是法律適用范圍之內的一種情形,是對既有客觀法律不明確之處的澄清。33. 陳輝:《論功能主義法律解釋論的構建》,載《現代法學》2020年第6 期,第61 頁。由于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論基礎是權利客體,因此根據著作權法中廣播組織權利內容推導廣播組織權利客體,則屬于法律推理功能的重要展現。相對于廣播組織所享有的有線或無線轉播權、復制權和錄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對于推導廣播組織權客體而言更具有說服力:首先,“復制權”和“錄制權”是《羅馬公約》為廣播組織設定的權利,而我國學者關于廣播組織權客體的爭論在《羅馬公約》體系下已經存在;其次,轉播權是“節目說”和“信號說”都主張的權利,因此盡管2020年《著作權法》將廣播組織轉播權擴展到網絡轉播領域,但該權利本身無助于解決廣播組織權客體爭議;最后,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是此次修法中爭議最大的權利,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論證基礎各不相同。以信息網絡傳播權為基點進行“由權利到客體”的反向推導,對于解決2020年《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中廣播組織權客體不明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二)客體排除:“信號說”與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相矛盾
在我國學理上,“信號說”源于SCCR 為制定《保護廣播組織條約》而確立的“基于信號的進路”,也稱為“以信號為基礎的方法”。2019年,SCCR 編擬的《合并文案》將廣播組織的保護對象確立為“廣播組織播送的,或代表廣播組織播送的,作為廣播的載有節目的信號”,34. See Revised Consolidated Text on Definitions, Object of Protection, Rights to be Granted and Other Issues, SCCR/39/7, page 6.但不延及其中所載的節目。所謂“載有節目的信號”,是指通過電子手段生成、最初播送以及采用任何后續技術格式的載有節目的載體。35. See Revised Consolidated Text on Definitions, Object of Protection, Rights to be Granted and Other Issues, SCCR/39/7, page 5.2022年SCCR 擬議的最新《案文草案》將“節目信號”界定為“原始傳輸形式和任何后續技術格式的載有節目的電子生成載波”。我國理論界所持的“信號說”即來源于此,認為廣播組織權的客體是SCCR 文件中的“載有節目的信號”。
然而,就“信號說”與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關系而言,二者屬于“互斥關系”。換言之,與“信號說”相對應的結論是反對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原因在于“信號”是能傳播節目的電子載波,36. 參見《發送衛星傳輸節目信號布魯塞爾公約》第一條。“載有節目的信號”在物理性質上是流動的,信號本身無法被固定、上傳、點播和下載。37. 參見王遷:《對<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的四點意見》,載《知識產權》2020年第9 期,第42-46 頁。而信息網絡傳播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交互式傳播”,也即公眾能夠將廣播電視節目固定下來,上傳到網絡服務器中,供網絡用戶依其時間和地點自行點播和下載。故而根據信號傳輸的技術特征,“信號說”理論與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本質內容相沖突,若認為廣播組織權客體為“信號”,則無法得出廣播組織應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結論。但也有代表認為,“廣播電視信號”可以固定,但事實上能夠“固定”的是信號中儲存的信息,信號本身則僅具有瞬時性特征。既然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為廣播組織規定了信息網絡傳播權,那么無論從立法論還是解釋論看,都應認為我國廣播組織權的客體不是信號。
從國際立法來看,SCCR 選擇“基于信號的進路”并不等同于“廣播組織權客體是信號”。在《保護廣播組織條約》制定之初,各國存在認知分歧,提出了“基于內容的進路”和“基于信號的進路”兩種方案。38. See Lisa Mak, "Signaling" New Barriers: Implications of the WIPO Broadcasting Treaty for Public Use of Information, Hastings Commun.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30: 533, p. 540 (2008).SCCR 最終選擇了后者,一方面力圖有針對性地遏制信號盜竊行為,另一方面希望通過聚焦重點問題,為條約的順利制定積累更多共識。無論選擇何種模式,對廣播組織權利保護來說均只具有方法論意義,而不具有確定權利客體的功能。換言之,“基于內容的進路”和“基于信號的進路”都是強化廣播組織權利保護的路徑,無論選擇何種路徑都能夠實現既定目標,至于SCCR 最終選擇后者的原因,是考慮到不同國家對廣播組織的保護模式存在差異,為了盡可能地縮小差異、凝聚共識、減少分歧而做出的選擇,而不是在將信號作為廣播組織權客體的基礎上選擇的方案。
除此之外,“信號”作為廣播組織權的客體還面臨著解釋困境。信號是信息或數據的物質載體。傳統的廣播電視信號在法律上稱為無線電頻譜,而無線電頻譜資源在法律屬性上為物權客體,屬于國家所有。39.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百五十二條確定了無線電頻譜資源的物權屬性,其所有權歸屬于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線電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無線電頻譜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國家對無線電頻譜資源實行統一規劃、合理開發、有償使用的原則。”我國民法學者認為,無線電頻譜資源,也稱為頻率資源,一般指9KHz-3000GHz 頻率范圍內發射無線電波的無線電頻率的總稱,它是一種自然界存在的電磁波,是一種物質。參見孫憲忠:《中國物權法:原理釋義和立法解讀》,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 頁;參見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20 頁。SCCR 特別強調《保護廣播組織條約》保護的是“載有節目的信號”,表明并非所有的信號都受廣播組織權保護,只有承載廣播電視數據、圖像或聲音的電磁波,才是廣播組織權的保護對象。但在文義上,其案文落腳點終究是“電磁波”而非電磁波中的節目信息。如果由此認為廣播組織權客體是作為物質形態的信號,將直接與知識產權客體的非物質特性相違背。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國家承認“物質材料”可以成為知識產權的客體。美國之所以通過保護“信號”的方法為廣播組織提供法律保護,其原因在于美國并不承認廣播組織屬于版權法主體。美國學者在《保護廣播組織條約》制定過程中就極力反對,認為美國加入《保護廣播組織條約》將對美國版權制度產生重大轉變:首先,它將促使在其版權法中加入一個新的權利主體,從而破壞美國版權法的現有結構;40. See Letter from Patrick Leahy, Chairman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and Arlen Specter, Ranking Republican Member, to Hon. Marybeth Peters, Register of Copyrights, and Hon. Jon Dudas, Director of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ar. 1, 2007), at http://www.keionline.org/misc-docs/broadcast-treaty.pdf (Last visited on August 28, 2022).其次,美國學者認為此舉將違反美國版權法中的“獨創性”要求,因為廣播機構只是傳播他人創作的作品,并不由此產生具有獨創性的新作品;最后,賦予廣播組織以若干年保護期限,也將嚴重阻礙公眾對信息的獲取。41. See Lisa Mak, "Signaling" New Barriers: Implications of the WIPO Broadcasting Treaty for Public Use of Information, Hastings Commun.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30: 533, p. 543-544 (2008).為解決上述擔憂,后來美國成功說服SCCR 大會將條約的范圍縮小到保護廣播公司信號免遭盜竊所必需的條款。42. See Marlee Miller, The Broadcast Trea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ignal Piracy in North America, Business Law Brief (Am. U.), Vol. 4: 33, p. 36 (2007).由此可知,美國從最初反對制定《保護廣播組織條約》到主張“基于信號的進路”,都是由美國版權法律結構和版權立法傳統所決定的。與此相同的是,歐盟代表主張為廣播組織納入網絡轉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也有其本土立法實踐為支撐:一是認可廣播組織的版權法主體地位,二是認可強化廣播組織權利保護的必要。然而相比之下,我國學者主張以“信號”為基礎設計廣播組織權制度,弱化廣播組織權利內容,既不符合我國立法實際,也不符合本土產業發展需求。
(三)客體確認: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以“節目說”為基礎
“信號說”作為廣播組織權客體難以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得以證立。根據網絡傳播技術特性,能夠在信息網絡空間進行傳播的,只能是某種非物質化的信息,而非信息的載體。43. 劉文杰:《互聯網時代廣播組織權制度的完善》,載《環球法律評論》2017年第3 期,第15 頁。廣播組織能夠據以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基礎是“非物質化的信息”,這與知識產權“客體非物質性”這一本質特性相契合。44. 參見吳漢東:《無形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3 頁。根據體系解釋,作為廣播組織權客體的“特定信息”與著作權人創作的作品、音像制品制作者制作的音像制品具有非同質性,否則將沖擊廣播組織作為獨立的鄰接權主體的地位。SCCR 所主張的“載有節目的信號”明確了信號中的信息——廣播電視節目,即由廣播或電纜傳播播送者向公眾提供的聲音,圖像序列或音像序列。45. 【西】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與鄰接權》,聯合國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1 頁。在我國,“節目說”遭到部分學者的反對,是因為“廣播電視節目”的屬性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曲解:
曲解一:認為“廣播電視節目”是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而非鄰接權客體。46. 參見胡開忠:《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權利內容立法的反思與重構——以“修正的信號說”為基礎》,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2 期,第41 頁。有學者在解釋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時認為,在作品、表演和錄音錄像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制度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存在的意義不大,對于未經許可交互式傳播廣播電視節目的行為,廣播組織者完全可以依據其與著作權人、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簽訂的合同,享有對作品、表演和錄音錄像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以此規制侵權行為。47. 參見陳紹玲:《論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適用空間》,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 期,第70 頁。這實際上不僅造成了“廣播電視節目”和“作品”“音像制品”之間的混同,而且混淆了不同主體所付出的不同勞動,從而將廣播組織通過廣播行為向公眾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等同于未經加工的作品、音像制品等節目素材。這種理解對廣播電視節目的屬性產生誤讀,將廣播組織的勞動過程“簡單化”“機械化”和“僵硬化”,否定了廣播組織的勞動投入和投資價值。從廣播電視節目和節目素材的關系來看,廣播電臺、電視臺首先對被授權播出的作品、制品或者其他節目材料享有“播放權”,該權利來源于著作權人、音像制品制作者或者表演者等主體的授權許可;但是,廣播組織在廣播過程中,不僅需要對作品、制品或者其他節目材料進行編排,而且需要通過信號加工和傳輸,實現“節目素材——信息流——視聽畫面”的轉換。公眾最后通過廣播電視等媒介接收到的節目(包括聲音與畫面),包含了廣播電臺、電視臺的勞動和技術投入,才屬于廣播組織的勞動成果。因此,廣播電臺、電視臺對其播放出來的、公眾到接收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壟斷利益,而不是對被授權播出的作品、制品或者其他節目材料享有壟斷利益。實際上,廣播電視“節目”并不等同于“節目內容”,節目內容是指被傳播的作品/制品,而“節目”是廣播組織對已有作品/制品的傳播而產生的新的內容。48. 參見馮曉青、郝明英:《<著作權法>中廣播組織的多元主體地位及權利構造——兼評<著作權法>第47 條》,載《學海》2022年第2 期,第187 頁。將廣播電視節目視為作品的錯誤在于:廣播電視節目是廣播組織對作品等節目、音像制品等素材加工處理的結果,是向公眾傳遞出的節目聲音和畫面的組合,不具有獨創性,不能將其視為作品。而廣播組織對其自己制作的《動物世界》《星光大道》等作為“作品”的節目,在向公眾播放之前已經存在著作權,廣播組織對這些“節目”是否享有鄰接權,取決于廣播組織是否將“節目”中的聲音和畫面傳遞給公眾。
曲解二:認為廣播組織僅基于播放行為而獲得鄰接權保護的正當性不足。該觀點認為廣播組織只是作品、音像制品的機械搬運者,其對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除了添加“臺標”之外,再無添加任何新內容,而廣播組織對節目的播放所形成載有節目的信號,才是其獲得廣播組織權的依據。49. 參見王遷:《對<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的四點意見》,載《知識產權》2020年第9 期,第42-46頁。這一觀點同樣無視廣播行為的技術屬性,否認廣播組織的勞動價值和經濟投入。事實上,對廣播組織而言,信號作為節目信息的傳輸載體只具有工具意義,只有信號中的信息才是投資對象。簡言之,信號中立,信息有價。廣播組織只是信號的利用者,但“利用信號”只是廣播活動中的一個環節,尚不能稱為對節目傳播作出的貢獻,廣播組織只有運用信號將打包完成的節目信息傳遞到觀眾面前,才完成了整個投資過程。在“北京冬奧會體育賽事節目盜播行為保全”案件中,法院認定被申請人因“向公眾提供冬奧會賽事節目的在線直播”而構成著作權侵權和不正當競爭,其理由并非“盜竊節目信號”。50. 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2)滬0115 行保1 號裁定書。同時在我國,干擾或屏蔽正常廣播信號的行為,屬行政違法行為而非知識產權侵權行為。
曲解三:認為廣播組織完全能夠以“非畫面保護途徑”獲得權利保護。如有學者認為,廣播組織能夠以作品著作權人的身份主張自制節目的著作權保護,以錄制者的身份對不構成作品或元素主張鄰接權保護,以被授權人的身份對被授權節目主張合同權利。51. 袁鋒:《新技術環境下廣播組織權的問題與完善——兼評最新<著作權法>第47 條》,載《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 期,第109-119 頁。此種觀點本質上也屬于對廣播組織權的正當性認識不足。廣播組織者當然能夠基于作者身份主張自制節目的著作權保護,但此時廣播組織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者,其權利來源于“創作作品”;而廣播組織基于“傳播作品”行為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鄰接權,與基于創作行為獲得著作權保護并不矛盾,兩種行為和兩種成果在法律上并不難區分。事實上,一個主體在社會關系中通常都充當著多重角色,法律不應對其社會角色設置限制。而以錄制者、合同當事人主張權利之說,同屬此類誤解。因此,只要承認廣播組織在廣播電視節目制作和播出中做出了貢獻,就這個貢獻而言應獲得多少權利,取決于立法者的考量,立法者賦予其信息網絡傳播權并不會引發法律邏輯困境。52. 參見張偉君:《論鄰接權與著作權的關系——兼談<著作權法>第47 條(廣播組織權)的解釋論問題》,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1年第3 期,第91 頁。
從技術上說,“節目”是廣播組織活動的綜合體,因而更接近受保護的客體。53. 【法】克洛德·科隆貝:《世界各國著作權和鄰接權的基本原則:比較法研究》,高凌翰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 頁。在“三網融合”背景下,公眾可以利用網絡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通過電視點播、回放觀看電視節目,為了防止他人未經許可復制或錄制廣播電視節目后通過信息網絡傳播的方式進行傳播,為廣播組織設定信息網絡傳播權就顯得十分必要。因此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源,來自于廣播電臺、電視臺通過一系列技術手段而最終向公眾播放出來的廣播電視節目,包括節目聲音和節目畫面,這與著作權人對其作品、音像制作者對其制作的音像制品所享有的權利存在本質不同。按照這種“由權利到客體”的反向推導,可以論證廣播組織權的客體是“廣播電視節目”。
四、如何設權: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范構造
以2020年《著作權法》第十七條為立足點,從解釋論視角分析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規定,有助于明確該權利的規范構造:一方面,基于該權利明確廣播組織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的專有權邊界;另一方面,圍繞當前學界對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產生的“許可權”或“禁止權”性質爭議,明確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許可模式。
(一)專有范疇:控制廣播電視節目的交互式傳播
1.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旨在規制廣播電視節目“后續播放”
廣播組織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為專有權利,廣播組織可以依據該權利禁止他人未經許可地使用。表現在行為范疇上,廣播組織可以禁止他人對廣播電視節目實施“交互式傳播”。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為廣播組織賦予的“播放權”,既涵蓋實時播放,包括有線和無線轉播權,也涵蓋后續播放,包括錄制和復制后的播放以及通過信息網絡進行的“交互式傳播”。在《著作權法》修訂之前,信息網絡傳播權是著作權人對其作品所享有的一項法定權利,該權利來源于WCT 第八條54.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公約》(WCT)第八條規定:“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作者應享有專有權,以授權將其作品以有線和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包括將其作品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可以獲得這些作品。”中的“向公眾提供作品的權利”。WCT 第八條為著作權人規定了兩項權利,包括“廣播權”(即該條款前半句“授權將其作品以有線和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和“向公眾提供作品的權利”,二者共同構成了理論意義上的“向公眾傳播權”。其中“向公眾提供作品的權利”的內涵是“使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可以獲得這些作品”。55. 參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公約》(WCT)第八條后半段之規定。這是我國《著作權法》中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直接來源。此處的“信息網絡”為廣義上的網絡,包括以計算機、電視機等各類電子設備為終端的計算機互聯網、廣播電視網、固定通信網、移動通信網,以及向公眾開放的局域網絡,56.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12年11 月26 日通過,2020年12 月23 日修正)第二條之規定。這與WCT 第八條對未來技術發展保持開放性的做法相一致。57. 參見劉銀良:《信息網絡傳播權及其與廣播權的界限》,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6 期,第101 頁。信息網絡空間具有開放性、公共性、非同步性和交互性的特點,58. 參見【美】理查德·斯皮內洛:《鐵籠,還是烏托邦——網絡空間的法律道德》,李倫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4 頁。其中開放性和公共性構成了“向公眾傳播”的基礎,非同步性和交互性是“信息網絡傳播權”區分于“廣播權”的重要特征。在2020年《著作權法》中,廣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界限明顯,二者的區分標準就是“交互式傳播”與“非交互式傳播”之分。
2.廣播組織基于權利專有性控制廣播電視節目的“交互式傳播”
廣播組織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與著作權人的網絡傳播權除客體不同外,二者所規制的行為相同。在“三網融合”背景下,觀眾對廣播電視節目的收看擁有更多自主權,人們不僅可以通過電視廣播定時收看節目,也可以通過互聯網點播、回看廣播電視節目,一定程度上看,廣播組織在對其播放的節目降低了主導力量;59. See Current Market and Technology Trends in the Broadcasting Sector, SCCR/30/5, page 6.此外,如果公眾將非法錄制或復制下來的廣播電視節目通過信息網絡進行傳播,不僅將給著作權人和廣播組織帶來慘重的經濟損失,無法維護廣播組織機構的投資利益,而且還將導致廣播電視節目內容質量日益低下的惡性循環,無益于增進社會公共福利。此即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設立的現實依據。進一步而言,廣播組織權的目的在于通過法律手段確保廣播組織因播送廣播節目所付出的技術性、組織性和經濟性投資得到回報,因此在具體權利設置上,如果將“有線和無線轉播行為”納入廣播組織權利體系,從而使廣播組織能夠控制對廣播電視節目的網絡實時轉播,那么就沒有理由將通過信息網絡手段傳播廣播電視節目的行為排除在廣播組織的權利控制范圍之外,因為“交互式”傳播使廣播電視節目在網絡空間中保留的時間更長、傳播范圍更廣、受眾更多,他人針對廣播電視節目非法實施的“交互式”傳播行為給廣播組織造成的損失比“非交互式”傳播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更大。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為廣播組織增設信息網絡傳播權,意味著廣播組織者對廣播電視節目的點播、回放等非交互式傳播行為享有控制權,那么公眾通過電視點播、回放觀看的方式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收看廣播電視節目的行為,落入到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涵攝范疇。廣播組織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與“網絡轉播權”共同承擔著規制網絡環境下以“交互式傳播”和“非交互式傳播”方式播放廣播電視節目的功能。2020年《著作權法》為廣播組織增設的這兩項權利,對于遏制“三網融合”發展趨勢下的廣播電視節目盜播行為、維護廣播組織機構勞動成果和投資利益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前述關于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適用范圍的“否定論”“懷疑論”“限縮論”等觀點,將架空《著作權法》的現有規定,有違“有效解釋原則”。60. 參見張偉君:《論鄰接權與著作權的關系——兼談<著作權法>第47 條(廣播組織權)的解釋論問題》,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1年第3 期,第95 頁。
(二)許可模式:對節目交互式傳播的“有限許可”
1.“有權禁止”不排除廣播組織對其廣播電視節目享有許可權
《羅馬公約》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廣播組織應當有權授權或禁止轉播其廣播節目”,這實際上賦予各締約國可以采用“許可權”或者“禁止權”的模式規定廣播組織權。對于廣播組織權的權利性質,國際知識產權法專家存在不同的解釋。有學者認為廣播組織權的權利性質為“專有權”,包括轉播、錄制以及在收費場所公開傳送廣播的權利;61. 【法】克洛德·科隆貝:《世界各國著作權和鄰接權的基本原則:比較法研究》,高凌翰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 頁。而也有學者認為,授予廣播組織(準許復制或向公眾傳播其節目)的權利,并不意味著這些機構或第三者可免去作者、表演者和制作者的授權,除非實施強制許可制。62. 【西】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與鄰接權》,聯合國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4 頁。盡管我國沒有加入《羅馬公約》,但根據TRIPS 協定的規定,我國需要承擔《羅馬公約》所規定的實體義務,而我國《著作權法》關于廣播組織權的規定也主要來源于這一公約。2020年《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采取“廣播電臺、電視臺有權禁止未經其許可的下列行為”的表述,通過行為列舉的方式為廣播組織規定轉播權、錄制和復制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據此,有學者認為廣播組織權屬于“消極的禁止權”,63. 參見王昆倫:《從我國廣電實踐重新審視廣播組織權制度》,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7年第7 期,第21 頁;閆書芳:《賦予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合理嗎》,http://www.cipnews.com.cn/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125499,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7 月31 日。只能消極地禁止他人以非法手段實施上述行為,但不具有主動許可他人轉播、錄制、復制或者通過信息網絡傳播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的屬性;64. 參見秦儉:《互聯網環境下廣播組織權與著作權的利益沖突與平衡——以“網絡轉播權”的利益分配為例》,載《電子知識產權》2019年第5 期,第26-36 頁。或認為除非有相反的明確約定或授權,對包含他人作品或錄音錄像制品的廣播、電視,廣播組織不得復制發行、重播或許可他人播放其已經錄制的包含他人作品或錄音錄像制品的廣播、電視。65. 參見管育鷹:《我國著作權法中廣播組織權內容的綜合解讀》,載《知識產權》2021年第9 期,第3-16 頁。但上述觀點值得商榷。回歸我國《著作權法》中的廣播組織權條款,對“禁止未經其許可的行為”進行邏輯分析,可以得出兩個結論:(1)經廣播組織許可,他人可以實施某種行為,即廣播組織有權許可他人實施某種行為;(2)未經廣播組織許可實施某種行為,廣播組織有權要求該行為人停止侵權。據此,從廣播組織與廣播電視節目被許可人之間的關系來看,廣播組織有權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許可給他人傳播。然而,《著作權法》為何不以“專有權”的形式為廣播組織賦權?這是由廣播組織權的生成機理所決定的,同時該機理也影響著著作權人和廣播組織、其他鄰接權主體、廣播電視節目被許可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2.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有限許可”屬性的機理及體現
《著作權法》為他人傳播廣播電視節目設定了義務,即禁止未經廣播組織許可的轉播、錄制、復制和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從權利義務的對應關系看,與他人所負有的義務相對應的,屬于傳播組織權利所及范疇。這意味著廣播組織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轉播權、錄制和復制權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廣播組織自身可以根據《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三款第三項的規定自主實施與上述權利相對應的傳播行為。而從許可權的角度看,廣播組織所享有的許可權屬于“有限許可”。廣播組織所編排和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中包括各類作品信息、不構成作品的音像制品信息以及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其他材料信息。作品、音像制品的“再現”由著作權人、音像制品制作者所壟斷,由于著作權法的規定或者在先合同約定,廣播組織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屬于對前述作品或者音像制品的合法再現。但是,他人未經許可對廣播組織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進行轉播或者通過信息網絡傳播,既是對作為廣播組織權客體的廣播電視節目的非法再現,也是對廣播電視節目中的作品、音像制品以及相關表演活動的非法再現。這意味著,在廣播電視節目之上當然地存在著一層屬于著作權人、其他鄰接權主體的權利,他人對廣播電視節目的傳播和利用,既影響廣播組織的利益,同時影響相關著作權人、其他鄰接權主體的“底層權利”。但《著作權法》同時保護廣播組織和著作權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并不意味著重復保護,也不會產生權利邊界不明的問題。由于二者的權利來源不同,即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來源于作品創作行為,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來源于作品傳播或者作品加工行為,二者的勞動屬性及勞動結果差異明顯,由此所形成的兩種權利在邊界上十分清晰。只不過一些廣播電視節目中包含著作品,他人對廣播電視節目的利用自然包含著對該作品的利用,此時需要獲得著作權人和廣播組織的雙重許可。這表明廣播組織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許可權”,只是這種許可屬于“有限許可”,具體情形包括:
情形一:若廣播組織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中沒有包含他人創作的作品或制作的音像制品,或該節目素材完全來自于公有領域,那么廣播組織可以直接將該廣播電視節目許可給他人使用;
情形二:若廣播組織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中包含他人創作的作品或制作的音像制品,那么被許可人在同時獲得相關著作權人、其他鄰接權主體、廣播組織的許可時,可以轉播、錄制、復制或者通過信息網絡傳播廣播電視節目;
情形三:如果廣播組織事先與著作權人、音像制品制作者以及表演者等主體約定,獲得以“轉授權”方式許可他人以信息網絡傳播的方式利用廣播電視節目中包含的作品或制品的權利,那么被許可人可以直接依據其與廣播組織之間的約定傳播該廣播電視節目;
情形四:如果著作權人、音像制品制作者以及表演者等主體拒絕廣播組織以“轉授權”方式許可他人使用其作品或制品,那么廣播組織此時對其播放的包含他人作品或音像制品的廣播電視節目僅享有“禁止權”。
上述情形表明,廣播組織權利內容一定程度上受廣播組織與作者或其他鄰接權主體之間的協議內容影響。廣播組織首先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禁止權”,在所有情形下都有權禁止他人非法利用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其次,如果廣播組織基于其與作者或其他鄰接權主體之間的合同關系,對“底層權利”享有“轉授權”的權利,那么廣播機構則能夠授權他人以有線或無線方式播放其廣播電視節目,此時并不存在影響、限制或侵害“底層權利”的風險。我國一些學者對廣播組織權利內容進行綜合解讀時就持此種觀點。66. 例如有學者認為:“廣播組織對不包含他人作品或錄音錄像制品的由其自己制作和播放的廣播、電視,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使用,也可許可他人以《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各種方式使用;對包含他人作品或錄音錄像制品的廣播、電視,廣播組織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以《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各種方式使用,但除非有相反的明確約定或授權,廣播組織不得復制發行、重播或許可他人播放其已經錄制的包含他人作品或錄音錄像制品的廣播、電視;對未經許可使用包含他人作品或錄音錄像制品的廣播、電視的行為,著作權人、錄制者和廣播組織均可請求禁止。”參見管育鷹:《我國著作權法中廣播組織權內容的綜合解讀》,載《知識產權》2021年第9 期,第3-16頁。從體系上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不得影響、限制或者侵害”條款就是對廣播組織權“有限許可”屬性的闡釋。廣播機構對其廣播電視節目享有的權利,自然適用于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
五、權利協調: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與相關制度的銜接平衡
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具有“權利限制”屬性,主要表現為該權利的行使對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產生限制。更進一步來說,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對“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對著作權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產生限制。此外,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引入還面臨著“侵蝕公有領域”的質疑,可能產生著作權法實施的制度性風險。對此有必要在相關制度之間尋求協調或化解之策。
(一)法定許可:擴展“廣播組織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范圍
1.該權利對“廣播組織播放作品法定許可”的影響機理
“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是與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密切相關的一項制度。根據著作權法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應當按照規定支付報酬。67. 參見我國《著作權法》(2020)第四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這里的作品是指除視聽作品之外的其他作品,視聽作品被排除適用該制度。68. 參見我國《著作權法》(2020)第四十八條之規定。由于《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前,廣播組織僅享有無線轉播權,廣播組織播放作品的行為屬于廣播行為,因此該制度也被學者稱為“廣播權法定許可制度”。69. 參見劉銀良:《我國廣播權法定許可的國際法基礎暨修法路徑》,載《清華法學》2019年第2 期,第163-180 頁。從文義上分析,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是對著作權人廣播權的限制,這與2020年《著作權法》實施之前廣播組織所享有的“無線轉播權”相對應。
廣播權法定許可制度具有正當性。第一,法經濟學認為,法定許可制度的優勢在于降低權利流轉帶來的交易成本。70. 參見熊琦:《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溯源與移植反思》,載《法學》2015年第5 期,第72 頁。對廣播組織而言,其為制作廣播電視節目需要使用數量較大的作品,但由于廣播電視節目時效性強,制作周期短,廣播組織通常無法及時獲得著作權人許可,而只有依靠廣播權法定許可方能解決所涉作品的著作權問題。71. 王昆倫:《廣播電視網絡同步播放中的版權問題研究》,載《中國廣播》2014年第9 期,第38-40 頁。第二,從著作權法所期實現的法律目標來看,廣播權法定許可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打破權力壟斷、保障公眾信息獲取權,也有助于著作權人獲得合理報酬。72. 胡開忠:《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問題研究——兼論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改》,載《知識產權》2013年第3 期,第3 頁。第三,從國際公約視角考察,《伯爾尼公約》第十一之二條第三款規定了與廣播權限制相關的臨時錄制事宜,可視為廣播權法定許可的國際法基礎。73. 劉銀良:《我國廣播權法定許可的國際法基礎暨修法路徑》,載《清華法學》2019年第2 期,第166 頁。第四,WCT 第八條在規定“向公眾傳播權”時,也在第十條規定了相應的“限制與例外”,即在不影響作品正常利用,也不無理損害作者合法利益的情況下,締約方可在立法中對作者權利規定限制或例外。74. See WIPO Copyright Treaty (adopted in Geneva on December 20, 1996), Article 10,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此即廣播權法定許可制度的基本依據。
然而與修訂前的《著作權法》相比,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為廣播組織增設網絡轉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廣播組織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的控制不再局限于“非交互式傳播”,并因此享有更多法定利益。那么,“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范圍是否因為2020年《著作權法》的通過而從廣播權領域擴張至包括廣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在內的“向公眾傳播權”領域呢?有國外學者認為,對廣播權的限制應僅限于初始無線廣播行為,75. See Mihaly Ficsor, The Law of Copyright and The Internet: The 1996 WIPO Treaties,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ras. C8.05-C8.07.不適用于初始有線廣播和網絡直播行為,更不能適用于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但也有觀點認為,廣播組織基于法律規定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自動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由于廣播電視節目中包含著作品,且廣播組織在播放廣播電視節目時無需事先獲得著作權人對其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授權許可,因此廣播組織在事實上享有對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定許可。由此可見,作為一項新權利,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必然對著作權法中的相關制度產生影響。如何理解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與“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之間的關系,還需要回到《著作權法》相關條文之中。
2.該權利擴張了“廣播組織播放作品法定許可”的適用范圍
從解釋論視角分析,“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范圍是否延伸至“信息網絡傳播權”領域,首先應當正確理解“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中的“播放”一詞的含義。在許多國家的《著作權法》中,“播放”被界定為借助無線電波對聲音或合成音像的傳送;76. 【西】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與鄰接權》,聯合國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1 頁。《羅馬公約》第三條f 款規定,“廣播的播放”是指供公眾接收的、通過無線電波對聲音或音像的傳播。77. 參見《羅馬公約》第三條第f 款之規定。當然這種理解具有歷史性,因為隨著“三網融合”技術的發展,廣播電視節目的播放已經不再局限于“無線電波”。不過“對聲音或音像的傳播”作為這一概念的核心要素并沒有發生變化。“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中的“播放”可以理解為“對聲音或音像的傳播”。
廣播組織通過廣播手段向公眾傳播廣播電視節目的行為當然屬于“播放”,而通過信息網絡傳播廣播電視節目是否屬于“播放”的涵攝范疇卻需要解釋。從WCT 第八條以及我國《著作權法》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定看,其核心要素在于“向公眾提供作品”,從而使公眾能夠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收看或下載。盡管“提供行為”和“播放行為”都具有“傳播”含義,但“提供廣播電視節目”在文義上并不直接等同于“播放”。廣播組織主動以數字形式將廣播電視節目保存或者上傳至網絡服務器中,其間并沒有產生“主動播放”這一事實行為。然而,廣播組織傳播廣播電視節目的主要形式卻是播放,其向公眾提供廣播電視節目并不是目的,只有播放廣播電視節目才能吸引受眾、收回成本并從中獲益。就此而言,提供行為是播放行為的手段,播放其廣播電視節目才是提供作品的最終目的,因此“播放行為”能夠被“提供行為”所吸收,信息網絡傳播處于“播放”一詞的涵攝范疇。質言之,信息網絡傳播旨在規制廣播電視節目的“后續播放”問題,以信息網絡方式傳播廣播電視節目時不可能規避播放行為,受眾每通過網絡點播、電視回放等途徑收看廣播電視節目,都包含著一次播放行為。立法者在賦予廣播組織以信息網絡傳播權時,必然預想到廣播電視節目的后續播放問題。由于廣播組織基于法律規定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從而在事實上享有對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定許可。因此,“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的“播放”應當做擴張解釋,其既包括廣播行為,也包括信息網絡傳播行為。
上述結論可通過目的解釋予以檢視。有學者認為以非自愿許可名義進行的轉播之所以應當是“同時進行而且不加修改”的轉播,其原因是那種“錄后廣播”與《伯爾尼公約》中提及的“公開傳播”相差甚遠。78. 【西】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與鄰接權》,聯合國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89 頁。但這種理解具有歷史性,非自愿許可之所以僅適用于“同步轉播”,主要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而在傳媒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這一制度要求應當有所變革。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的目標在于減少交易成本。“有線和無線轉播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都是2020年《著作權法》中的廣播組織權,其中“有線和無線轉播權”與廣播行為相對應,“信息網絡傳播權”與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相對應。既然廣播作品需要“范圍廣泛、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的作品,那么通過信息傳播廣播電視節目自然也需要以“范圍廣泛、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的作品”為基礎。如果“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不能延伸至信息網絡傳播權,那么廣播組織將一邊適用廣播權法定許可制度播放作品,另一邊還要與著作權人另行談判廣播電視節目的后續播放問題,這非但沒有降低廣播組織與著作權人之間的談判和交易成本,甚至還將導致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被架空。
從國際立法來看,將“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延伸至信息網絡傳播權領域也不存在障礙。WCT 第八條在規定“向公眾傳播權”的同時,也根據《伯爾尼公約》第九條第二款所確定限制和例外的“三步檢驗法”,在其第十條規定了限制和例外條款,并將它擴大適用于所有的權利。79. WIPO. Summary of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 (1996), at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ip/wct/summary_wct.html,(Last visited on August 30, 2022).在《WCT 條約議定聲明》中,各締約國認為該“限制與例外”應繼續適用并適當地延伸到數字環境中。80. 完整聲明為“不言而喻,第十條的規定允許締約各方將其國內法中依《伯爾尼公約》被認為可接受的限制與例外繼續適用并適當地延伸到數字環境中。同樣,這些規定應被理解為允許締約方制定對數字網絡環境適宜的新的例外與限制。”See Agreed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adopted by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December 20, 1996), Agreed statement concerning Article 10.因此,將“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延伸至信息網絡傳播權領域與國際條約的規定并不沖突。
3.該權利的“權利限制”屬性與《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不沖突
“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是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法律制度,其對著作權人而言是一項權利限制制度。由于廣播組織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因此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范圍得到擴張,其不僅是對著作權人廣播權的限制,同時也是對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限制。然而,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為廣播組織增設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同時,還在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增設了一項規定:“電臺、電視臺行使前款規定的權利,不得影響、限制或者侵害他人行使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81.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20)第四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那么廣播組織因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而對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造成的限制,是否與《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相矛盾?
從體系解釋視角分析,“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屬于由法律直接規定的著作權權利限制制度,它與《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并不矛盾。首先,從《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與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的關系看,二者均由法律直接規定且處于平行關系,前者屬于“著作權權利限制”條款,為例外性條款,后者屬于“禁止限制著作權”條款,為原則性條款。根據“原則之中允許存在例外”的理念,例外應優先于原則適用。這意味著,《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所規定的行為,不受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的約束,此時第四十七條第二款應當解釋為“電臺、電視臺行使前款規定的權利,不得影響、限制或者侵害他人行使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其次,《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屬于緊急立法的產物,如果認為廣播組織因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而對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造成的限制與《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相矛盾,那么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就屬于對四十六條第二款的限制,這意味著在《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之前已經存在的“廣播權法定許可制度”將不復存在,這不僅動搖了我國著作權法的制度框架,也與國際公約的規定相違背。再次,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是對廣播組織“行使權利”的限制,而根據四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廣播組織權的屬性為“有限許可”權。“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適用于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并不意味著廣播組織享有以“轉授權”方式將廣播電視節目中所包含的作品、音像制品許可他人通過信息網絡進行傳播。在廣播組織與被許可人的關系上,廣播組織在授權他人以信息網絡方式傳播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時,仍然屬于“有限許可”,此時被許可人還應取得著作權人、音像制品制作者以及表演者等主體的授權。因此《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主要是針對廣播組織在許可他人傳播廣播電視節目所做出的規定,而非對其自行播放廣播電視節目所做出的限制。《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可視為對四十七條第一款“禁止未經許可”表述所作出的補充和說明,旨在進一步說明廣播組織權的“有限許可”屬性。最后,從權利基礎和權利范圍來看,廣播電臺電視臺對“節目的播放”所享有的權利,與著作權、其他相關權人對作品、音像制品、表演活動享有的權利本身就是不同的,82. 劉云開:《廣播組織權客體之再辨析——兼評我國新<著作權法>第47 條》,載《電子知識產權》2020年第11 期,第27 頁。《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實際上屬于多余條款。即使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具有“權利限制”屬性,其與《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也并不沖突。
4.應適當提高廣播組織播放作品的付酬標準以平衡不同主體利益
目前,我國未就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已發表作品的法定許可制度制定相應的付酬標準,而是在2009年11 月僅就播放錄音制品的法定許可問題出臺了《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錄音制品支付報酬暫行辦法》。8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錄音制品支付報酬暫行辦法》,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9-11/16/content_5919.htm,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8 月1 日。在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已發表作品適用法定許可制度如何付費問題上,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第三十條對此做出規定,確立了“以約定報酬優先,以法定付酬標準為補充”的付酬方案。84. 我國2020年《著作權法》第三十條規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標準可以由當事人約定,也可以按照國家著作權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付酬標準支付報酬。當事人約定不明確的,按照國家著作權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付酬標準支付報酬。”由于缺失具體付酬標準,因此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已發表作品主要以合同約定形式付酬。然而,由于廣播組織與著作權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作者獲酬權可能難以保障。85. 彭桂兵、朱雯婕:《論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的存與廢——基于立法價值的視角》,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5 期,第88 頁。對此國務院相關部門應當制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已發表作品的付酬標準》,或者在正在修訂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中提供具體操作方案,明確付酬標準和救濟措施,從而降低著作權人因權利限制而產生的利益損失。與此同時,“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作品法定許可制度”擴張適用至信息網絡傳播權,除限制了著作權人的廣播權之外,還對著作權人信息網絡傳播權造成限制,由此打破了著作權人和廣播組織之間原有的利益平衡關系:2020年《著作權法》修訂前,廣播組織通過“無線轉播方式”播放廣播電視節目的基礎是廣播權的法定許可,廣播組織只需按照廣播作品的付酬標準向著作權人支付作品使用費;而2020年《著作權法》修訂后,廣播組織還能夠通過信息網絡傳播的方式播放廣播電視節目,相應地,廣播組織應當按照通過信息網絡傳播方式播放作品的付酬標準向著作權人支付作品使用費。也即,廣播組織應當在原有支付作品使用費標準的基礎上,增加作品使用報酬,以補償著作權人因信息網絡傳播權受到限制而產生的損失。盡管許多情況下,廣播組織播放作品時按照使用作品的數量向著作權人支付使用費,在合同中以籠統的方式約定作品使用行為,但這種付酬標準多是以廣播組織不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為前提的。但當廣播組織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時,廣播組織將從這種權利擴張過程中獲得更多利益,其利益基礎包含著著作權人因創作作品而付出的勞動。在此情形下,廣播組織應適當支付給著作權人更多作品使用費,以此實現雙方利益平衡。
(二)公有領域: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侵蝕公有領域觀”及回應
2020年《著作權法》為廣播組織增設信息網絡傳播權面臨的另一質疑是此舉可能損害著作權法中的公有領域。公有領域是不受知識產權法保護的領域,處于該領域的智慧成果可以為社會公眾自由利用。86. 胡開忠:《知識產權法中公有領域的保護》,載《法學》2008年第8 期,第64 頁。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超過保護期限的作品因進入公有領域而可以被公眾自由利用。在《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過程中就有學者擔憂,廣播組織享有信息網絡傳播權將使廣播組織對他人制作的節目,甚至是公有領域的作品在播出后獲得保護期長達五十年的專有權利,從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87. 王遷:《對<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的四點意見》,載《知識產權》2020年第9 期,第44-45 頁。美國學者最初反對美國加入《保護廣播組織條約》談判的原因之一,也是認為賦予廣播機構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以時間期限將對版權公共領域造成限制。他們認為,這將允許廣播機構通過簡單播放行為對公有領域的材料獲得額外權利,使公有領域的材料變為私人專有權利,這違反版權制度“促進文化事業發展”的終極目標。88. See Matthew D. Asbell, Comment and Recent Development: Progress on the WIPO Broadcasting and Webcasting Treaty,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4: 349, p. 361 (2006).
上述擔憂的實質是認為賦予廣播組織對廣播電視節目以專有權,將降低公眾從公有領域中獲取作品的機會。通常而言,作品、音像制品進入公有領域后,可以為公眾自由獲得和使用,從而實現知識傳播與知識共享的立法目標。89. 參見李建華、梁九業:《我國<著作權法>中公有領域的立法構造》,載《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 期,第40 頁。但是截至2021年底,廣播電臺、電視臺、廣播電視臺等播出機構2542家,90. 參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2021年全國廣播電視行業統計公報》,http://www.nrta.gov.cn/art/2022/4/25/art_113_60195.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6 月20 日。如果認為每一個廣播機構在首次播放作品,甚至每一次播放作品后,都對其播放的包含該作品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五十年的權利期限,那么公眾利用該作品的空間就被大大壓縮。尤其是當該作品進入公有領域,著作權人無法對該作品享有財產權利,廣播組織卻能夠通過播放該作品而實現對包括該作品的廣播電視節目的控制,可能會引起著作權人的不滿,因此上述擔憂不無道理。
對此,有學者提出協調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與公有領域保護沖突的路徑,認為由于鄰接權依附于著作權,根據鄰接權權利范圍不得大于著作權權利范圍的原則,當一個作品進入公有領域后,廣播組織亦不得對該作品以及包含該作品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任何壟斷利益,由此能夠最大程度地保護公有領域,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這種觀點盡管能夠最大程度地維護公有領域,但是“鄰接權權利范圍不得大于著作權權利范圍”這一前提難以經得起推敲。鄰接權盡管與作品傳播密切相關,但其亦具有相對獨立性,著作權法基礎理論中并沒有“鄰接權權利范圍不得大于著作權權利范圍”的要求。對超過保護期限的作品而言,表演者能夠通過對該作品的表演而享有表演權、音像制品制作者也能夠通過錄制活動享有音像制品制作者權,相應地,廣播組織通過播放該作品從而對包含該作品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廣播組織權并無理論障礙,因此鄰接權與著作權的權利范圍不存在孰大孰小的區別。由于在大前提上存在錯誤,因此這一路徑不具有可行性。
事實上以筆者之見,為廣播組織賦予信息網絡傳播權并不足以侵蝕著作權公有領域。首先,無論從產業需求還是立法實踐看,應當承認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價值。廣播組織在播放廣播電視節目的過程中做出了相應貢獻,廣播電視節目中也承載著廣播組織的投資利益,根據傳統的勞動財產權理論,應當賦予廣播組織一定期限以維護其廣播投資。“三網融合”背景下,廣播組織者的投資向網絡領域延伸,導致廣播投資的增長。借助網絡技術,廣播電視節目的保存更加便捷、保存時間更長,廣播組織的預期利益更多,賦予廣播組織以信息網絡傳播權是產業和立法的雙重選擇,不宜否定。其次,我國通過“首次播放”對廣播組織權的保護期限予以限制,有助于維護著作權法中的公有領域。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三款規定:“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權利的保護期為五十年,截止于該廣播、電視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12 月31 日。”這說明在廣播組織權的保護期限上,立法者強調將“廣播、電視”的“首次播放”作為廣播組織權保護期限的起算點。“首次播出”作為對廣播組織權的時間限制,能夠最大程度地預留公有領域空間,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再次,“侵蝕公有領域”的觀點仍將“節目”與“節目內容”混為一談。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從與廣播機構相同的來源自由獲取和使用屬于共有領域的作品或材料。91. See 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 Negotiations on Broadcast Treaty Raise Concerns (Sept. 8, 2006), at http:// www.cdt.org/publications/policyposts/2006/16 (Last visited on August 24, 2022).如果認為賦予廣播組織以信息網絡傳播權將限制公有領域,那么相應的,包括廣播組織轉播權、出版者權、表演者權、音像制品制作者權的各類鄰接權也將同樣面臨著侵蝕公有領域的問題。92. 參見張偉君:《論鄰接權與著作權的關系——兼談<著作權法>第47 條(廣播組織權)的解釋論問題》,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1年第3 期,第91 頁。最后,即使面臨“作品僅由廣播機構保存,公眾難以獲取”這一極端情形時,也不應對廣播機構予以苛責,這是由于我國《著作權法》中缺乏“作品獲取權制度”所導致的。在我國著作權法制度下,“保護版權技術措施”與“維護公眾作品獲取權”之間也呈現出此種緊張關系,其解決之道在于,立法者可以要求廣播機構或技術措施實施者在特殊情形下向公眾提供相應作品。
六、結語
2020年《著作權法》賦予廣播組織以信息網絡傳播權符合“三網融合”技術發展的趨勢以及廣播電視產業發展的現實。本文基于《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梳理了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背景、客體依據、規范構造及其對著作權法中其他制度產生的影響與協調路徑。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所涉爭議,是因廣播電視節目滲入了廣播組織、著作權人、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等眾多主體的勞動而致,但這并不影響廣播組織鄰接權主體的獨立性,也不影響《著作權法》為廣播組織賦予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正當性。可以預測,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會面臨較多適用困境,因而“限縮適用論”“有限適用論”等觀點將不攻自破。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適用,更重要的問題是厘清廣播電視節目中所含“權利層”。通過廣播組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正確適用,將充分實現尊重廣播組織的勞動價值、有效維護數字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技術投資的制度目標,同時平衡廣播組織與著作權人、音像制品制作者、表演者乃至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關系,促進我國廣播電視產業和版權產業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