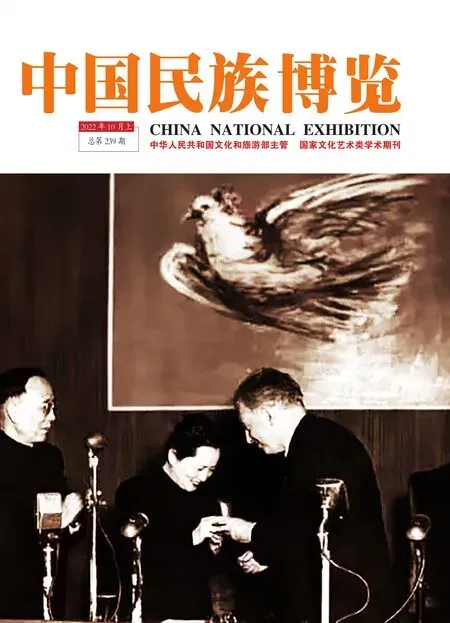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法哲學思想考述
趙啟博
(貴州財經大學,貴州 貴陽 550004)
引言
歷經五千年的風雨洗禮,中國的法制史其實不僅包含著時間的長遠,而且囊括了廣闊的范圍。無論是內容的博大還是法律文明的推進,都能夠充分地展現中華民族成長歷史上不斷變化,不斷擴展和不斷充實的法制內容。擁有著非常開闊的包容性,既體現漢族禮法合一的核心也包含了少數民族所特有的習俗法則。在這些基礎之上共同形成獨具一格的中華法治哲學思想。
在漫漫波瀾浩蕩的中國法史發展長河中,少數民族群眾建立的民主王朝和自治政權對構建中華民族法系的繁榮發展和成熟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如以鮮卑民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其所制定的《北魏律》可謂是集大成者,其既繼承了漢律,也糅雜了南朝各律,可謂我國法制史上的里程碑。北魏之后的東魏、西魏也頒布了《麟趾格》和《大統式》。這一時期,還有北齊王朝也制定出了譽滿后世的《北齊律》。除此之外,女真金王朝制度的《泰和律義》、契丹遼王朝制度的首部法典《咸雍重修條制》等等,都表明少數民族法制史是中華法系不可或缺的組成元素。
因此,研究和探索古代少數民族法哲學思想,不僅可以完善和考察我國古代法律文明的發展變化歷程,也有利于深入挖掘“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法制體系特征。對于當今我國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化建設的道路有著重要的參考和學習意義,也能夠使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社會結構更加緊密團結。①
一、我國少數民族在古代法制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沿革
(一)先秦時期
從法制歷史的角度來看,中華民族法制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至先秦戰國時期,在這一時期中華民族就已經開始不斷地對自己周邊其他少數民族的法制文明進行深入學習和同化融合,特別是在以中原為地區的部分漢族(或稱為華夏族)為主體,融入和同化了周邊華夏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大部分部落后,“中華民族大統一”這一思想才逐漸形成,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在秦大統一滅亡之后,我國才會不斷的在戰亂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亂局中走向統一和強盛。史料記載:“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②,提示我國最早的法制出現在長江流域三苗部族。杜預注釋《左傳》時指出:“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是三苗也。”貧富分化引發對被貧窮人口的剝削,進而產生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矛盾,為了鎮壓被剝削者,刑罰即隨著出現。時間推進來到夏商周時期的時候,這一刑罰制度就演變轉化成為奴隸五刑——墨、劓、刖、宮、辟,并沿用至漢初。
(二)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
從周王朝走向沒落的春秋戰亂時期一直發展至秦漢年代,此時生活在北方的牧民,也就是匈奴民族。他在向封建社會邁進的同時,實現了社會生活制度的進步,而且基于自己生存的基礎和環境建立起了統一的軍事政權。此時也出現了關于少數民族刑罰的最初萌芽和形態,“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中國古代法律第二次與少數民族進行大規模融合是在西晉末年的“五胡”時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北朝,以鮮卑族為統治者的習慣法開始流傳。《魏書·刑法志》其中就鮮明地記載了在魏國時期按相關“禮俗”形成的約定和犯罪之人受到懲罰。并且后來成功占據中原后,為了加強相關政令和統治的推行。又大刀闊斧地對自身法制加以改革,對漢族法制及法文化進行借鑒、歸納、吸收,與此同時又保留了游牧民族特有的務實上進效率之風,在諸多漢族律法學者的傾力相助之下,實現了轉變法律建設的快速進程。并且頒布了享譽后世的《太和律》。該律典繼承了漢、魏、晉時代發展過程中經歷的相關儒家法律思想和文化的精髓所在,同時也糅雜了少數民族自身的法制思想,是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全方面大融合,可以說北魏深深地影響了中華法系后世的進程。
(三)隋唐時期
我國之于立法思想和傳統習俗,在唐朝時期就能夠看到統治者對于多民族習俗和約定俗成法律的尊重態度。在《唐律疏議》中相關的記載能夠充分體現,他是這樣記載,對于蕃夷之國的人,犯了同樣罪,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相關習俗和法治規定進行處理,如果他們的相關習俗無法處理,則按照當時社會流行的法制進行處理。
這一律文首次開創了,在一個大一統王朝中對不同民族在某些情況下,可適用本民族法律制度的思想,從這里能夠充分顯現唐朝在當時盛世發展的時代,所擁有的的廣大包容性,對于各民族政策和觀念的寬容,也充分肯定了少數民族自身的法制。唐太宗曾言:“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四夷可使如一家。”③在這種寬松和包容的氛圍下,唐朝在當時疆域之內,在民族區域設立的州縣數量頂峰時期高達八百多個,這些民族區域內設立的州縣,各民族可以依據自身民族的相關習俗和法制開展相關社會事務的處理和解決。
(四)宋元時期
宋朝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朝代,其面對許多少數民族的崛起,制定了許多與少數民族有關的法律如《番官法》《番兵法》《番丁法》《茶馬法》等。另外,在這一時期,西夏、金國、遼國全部建立,其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原地區相對先進和完善的法制條令,根據自身發展和民族狀況,西夏、金國、遼國都頒布了各自本土的條律,其中都能看出融入宋律的痕跡。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西夏的《天盛律令》是一部經典之作,其不僅能夠代表當時西夏的法制,甚至還可以代表當時中華法系的法制,對于歷史上中國法制文化的建設成就而言,西夏法制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并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元朝是一個以蒙古族為主體的王朝,元朝在繼承唐宋律的基礎上,吸收了金律遼律西夏律,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一代法制。在相關法律的編纂上,融合前人法制成就,結合蒙古習慣,借鑒唐宋律法精髓,形成了元朝律法,并且,元朝統治期間重視漢法應用,這也促進了漢族法文化和少數民族法文化的進一步融合。
(五)明清時期
吸收元朝的典章與監察法規,明清時期的法制思想得以發展。其中清朝是以女真部落為主建立的政權,其通過參考漢族的法制思想,并立足本民族原有的法制思想,建立了清朝新的法制思想和體系。清朝開國皇帝皇太極就曾經說過,自己創立這一國家,怎么能夠摒棄民族的制度,而順從他們的制度呢。④但是另一方面,清朝也積極地吸收了漢文化中的先進思想,其中對于清朝和漢族文化有著一定判別的思想和制度,清朝就此也提出了兼揉式的對策和更改,在清朝發展的這一時間之內,先后修訂了多部《大清律例》,其中不僅僅保護了滿族的貴族權益,同時其他的相關條例也在最大程度內保留了唐宋明時期相關封建法典的哲學思想,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發展下最后一部囊括了前人法律智慧和精髓的封建法典。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清朝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治理中法治建設的出臺十分重視,有多部針對民族發展治理的法令制定,包括西藏、苗疆、回疆地區的章程條例等等,這些例律都體現了清朝在民族立法方面的獨特成果,對于國家穩定發展的維護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我國少數民族對古代法制文明形成的影響
溯本求源,從中華法制文明的起源來看,三苗是最早設立法制的民族,也為我國后續法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到南北朝時期,法律逐漸由習慣法演變為成文法,統治者對法制的重視也可見一斑,《九朝律考》記載:“孝文用夏變俗,其于律令,至躬自下筆,凡有疑義,親臨決之,后世稱焉。”⑤并提出“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法為治要”的重要思想。《北齊律》曰:“蓋唐律與齊律,篇目雖有分合,而沿其十二篇之舊;刑名雖有增損,而沿其五等之舊;十惡名稱,雖有歧出,而沿其重罪十條之舊”⑥,上述律令的制定出臺,明顯對后世的法制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并且,伴隨“德主刑輔,立法并用”的儒家思想日漸發展,少數民族法制思想逐漸與漢法相融合。《唐律疏議》便是通過對各家法哲學思想進行融合借鑒的成果,其圍繞相容互補的法制建設原則,將禮法結合的特質完美展現,并影響后世律令的制定與形成,如:元朝“祖述變通”的治國思想,清朝在對待民族問題立法上“因俗制宜”的指導思想等。
中華民族擁有廣闊的包容胸懷,有諸多民族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盡管各民族由于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文化、經濟發展的水平也各有差別,但是其對于構建整個中華法系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法制歷史是各民族的文化共同凝結形成的,是各族法哲學思想的充分展現,是各民族法制思想在交流和碰撞中產生的文明成果。
三、我國少數民族法制史對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意義
五千年的中華歷史充分證明了中華法系是由古代各民族法制理念共同孕育出的結晶,雖然在大多數歷史時期都是以漢族為主體,但是誰也無法否認沒有各族不落窠臼的法律智慧,沒有各族開拓進取的法制思想,就沒有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中華法系。
從厚重的歷史走來,中國始終保存著自己的“根”和“魂”,從“五刑”到現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體系,中國法制思想是在經年累月的實踐中發展形成的,其中包容了各民族所需、所想、所求。未來,在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道路上,少數民族的訴求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因此,對我國少數民族法哲學思想史的研究,在當下更凸顯出重要的理論價值。
注釋:
①福澤渝吉.文明論概略[M].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②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
③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56.
④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20.
⑤⑥程樹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