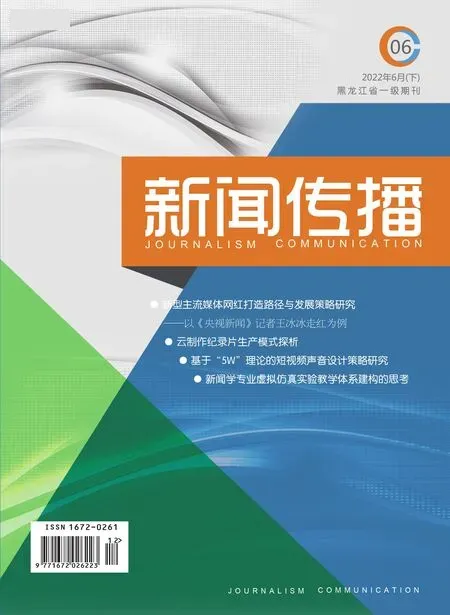30年代《譯文》的創辦與特色
喬 艷
(長安大學人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64)
在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翻譯一直是重要的“源頭活水”,也構成了民國時期各類書報雜志的重要內容。以期刊而言,民國時期的文藝期刊幾乎都是創、譯并重,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的276 種刊物中,刊載文學譯作的有200余種,占比超過80%。但純粹以翻譯文學為對象,全部刊載譯文的期刊卻并不多見,直到上世紀30年代《譯文》出現。《譯文》創刊于1934年,由魯迅、茅盾等人發起,歷時3年,先后出版29期。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專門的文學翻譯類期刊,它的體例、風格極大影響了后期的同類期刊,建國后出版的《譯文》雜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續了30年代《譯文》的風格。
一、《譯文》的創辦背景
(一)“雜志年”的時代背景
1934年《譯文》創刊號提到要“在這‘雜志年’里加添一點熱鬧”,[1]“雜志年”的名稱源于上世紀30年代國內期刊的蓬勃發展,“據《人文》月刊統計:一九三二年收到全國雜志為八七七冊,一九三三年為一二七四冊,一九三四年為二零八六冊”。[2]“雜志年”的出現有多重原因:一方面,相對書籍而言,期刊內容豐富,信息傳遞及時,定價低廉,適合大部分讀者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各類文學社團要傳達自己的主張,開辟文學陣地,也紛紛創辦雜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政府對書籍嚴格審查,大量包含進步思想的書籍被查禁,為了應對文化圍剿,文藝工作者不得不采取對策,包括化名寫文章、出版新刊物等。實際上,雜志面對的審查壓力也很大,在《譯文》創辦的過程中,從人員設置到稿件編輯都可以看出審查的痕跡。刊物最初由魯迅等人發起,魯迅是前3期的實際編者,但為了應對審查,刊物對外的編輯人一直是黃源。由于同樣的原因,魯迅在《譯文》的多篇稿件都采用筆名發表,僅創刊號就用了許遐、鄧當世、茹純等三個名字。
(二)翻譯的不景氣
《譯文》創辦還與文學翻譯的困境有關,從清末到20世紀30年代,外國文學翻譯已經發展了半個世紀之久,其間雖然不乏名家名譯,然而缺乏翻譯規范,翻譯質量低下的問題始終存在,且愈演愈烈。《譯文》創辦時面對的情況是,“一些投機者不負責任的胡譯、亂譯、瞎譯、趕譯,讀者上了幾回當,翻譯馬上便被輕視,被拋棄了。”[3]因為不好賣,一些雜志打出“不收譯稿”的牌子,好壞翻譯被一視同仁,很多譯者也被迫擱筆。作為《譯文》主要發起者的魯迅正是在翻譯“倒運”的情況下,提出創辦刊發翻譯的專門類刊物,以譯品精、質量高、印刷好來提高翻譯身價,鼓勵優秀翻譯,改變國內翻譯界的風氣,后來的事實證明,《譯文》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三)讀者對外來文學的熱情
魯迅看重翻譯,除了將其視為“他山之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讀者的需求。雖然翻譯中的低劣之作影響了讀者的閱讀熱情,但仍有大量讀者對國外作家作品抱著強烈的興趣。在《譯文》創辦前,同為生活書店發行的《文學》雜志剛剛出版了兩期外國文學專號,分別是1933年2卷3期的“翻譯專號”和5期的“弱小民族文學專號”,引起人們對于翻譯的重新探討,并且在讀者中大受歡迎。這也使茅盾受到鼓舞,并與魯迅商討,決心創辦一個以翻譯為對象的純文藝雜志。《譯文》出刊半個月,《申報·自由談》副刊就有一篇題為《歡迎〈譯文〉月刊》的文章,其中表現出讀者對于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及翻譯的渴望,作者形容看到《譯文》創刊號,就像缺乏母乳的嬰兒得著了奶媽似的,因此希望“這家新店子按時開門,并且擴充營業(出版叢書)”。[4]
二、《譯文》的編輯特色
(一)圖文并重
在文字之外多加圖畫,是《譯文》在視覺上的重要特點。當時文藝期刊普遍采用插圖,而《譯文》大量使用圖畫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對于文字轉換,復制的圖畫更能保留原味,也更能傳達外國作家作品的本來面貌。相比其他期刊,《譯文》的插圖數量多,每期少則6 幅,多則10余幅,多與外國作家作品相關,如2卷2期刊載法國作家左拉的作品和評論,該期插圖中有5 幅與左拉有關,包括“左拉最后之像”“左拉與其家族”等。少數與期刊內容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國外藝術家所作的風景畫、木刻等,用編者的話說,算是送給讀者的一點“小意思”。穿插在雜志各處的圖畫增加了閱讀趣味,也使《譯文》對外國文學的譯介更加生動和豐富。
(二)多出特輯、專號,尤其關注俄蘇和弱小民族文學
相比單篇文章,特輯、專號的譯介相對系統和全面,能夠更立體地展示作家、思潮,甚至某國文學的面貌。《譯文》29 期中包含了10 個特輯、專號,除新2 卷3 期哀悼魯迅先生特輯外,其余全部是外國文學專號,包括高爾基、普希金、羅曼·羅蘭、狄更斯等。專號多以作家紀念日為契機,如新2卷6期“普式庚逝世百年紀念號”,新1卷2 期“羅曼·羅蘭七十誕辰紀念”等。專號內容表現出對俄蘇文學的重視,10 個特輯、專號中,俄蘇作家占據了6 個(杜勃羅留波夫1,普希金2,高爾基3),期刊發表的全部133篇文章,大約來自20個國家,其中俄蘇作家作品47 篇,約占35%。同時,《譯文》關注弱小民族文學,包括希臘、匈牙利、葡萄牙、克羅地亞、波蘭等國,還曾在新3卷2期開辟“西班牙專號”。對俄蘇和弱小民族文學的關注既體現了編輯魯迅一貫的文學傾向,也與上世紀30年代國內局勢(抗戰)有關,同樣受到影響的是對日本文學的譯介,雖然魯迅精通日語,《譯文》也有多篇文章從日文轉譯,但該刊從未譯介日本文學。
(三)以“后記”介紹作家作品
“后記”是魯迅的創新,自第1 期延續到雜志終刊。一般由譯者撰寫,包括若干篇小文章,每篇一二百字,介紹作家作品,說明文章來源。作為一種短評,“后記”常在寥寥數語中點出對象的特質,尤其對一些在國內不知名的作家作品而言,《譯文》的介紹尤為重要。此外,“后記”也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翻譯亂象,樹立了翻譯規范。以轉譯為例,通過第三國語言轉譯而來的文字有二次變異的嫌疑,因此常為人詬病,但早期翻譯受人力和資源限制,轉譯難以避免,《譯文》創刊號的9篇文章中至少3篇由第三國語言轉譯。針對這些作品,“后記”中都詳細介紹了轉譯來源,如果戈里短篇小說《鼻子》由日文轉譯,并參考德譯本,匈牙利作家柯龍曼·密克薩斯小說《皇帝的衣服》由英文轉譯,希臘作家G·特羅什內斯的《教父》由英文轉譯等。同時,也介紹了原譯者的信息等,以便于有能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考原文,因此,既達到了廣泛介紹的目的,也較好地彌補了轉譯的缺陷。早期翻譯存在很多問題,如隨意刪改原文,不注明譯文出處,不標出原作者,著譯不分等。通過“后記”的設置,《譯文》為改善翻譯面貌做出了探索。
三、《譯文》的價值與影響
《譯文》出版時面對的環境并不好,一方面,是國民黨當局的文化圍剿;另一方面,出版界對翻譯缺乏信心,生活書店在當時較有遠見和冒險精神,但對《譯文》的前途也并不看好,最初約定只試出3期,書店不支付稿費和編輯費用,如銷量不錯再行補算。而《譯文》創刊號在一月之內就再版了4次,在讀者中取得了成功。1935年《譯文》意外停刊,編輯黃源本打算赴日,有報紙專門刊出一則消息,“《譯文》編者黃源赴日后,讀者對于《譯文》雜志之是否繼續,十分懷念”,[5]從一個側面也可見雜志在讀者心中的地位。
《譯文》的成功也為文學翻譯帶來了新的希望。茅盾回憶,“《文學》《譯文》掀起的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熱潮已影響到整個文壇,已經有人在稱呼即將到來的一九三五年為‘翻譯年’了”。[6]在《譯文》之后,國內先后出現了《世界文學》(1934-1935)《西洋文學》(1940-1941)《文學譯報》(1942-1943)等多個專門刊載翻譯文學的期刊,它們的風格、體例都受到了《譯文》的影響。創刊于1942年的《文學譯報》在發刊詞中總結國內期刊,高度評價了《譯文》的價值,“《譯文》對于翻譯水準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時也給一些從事翻譯的學徒,指示了選擇材料的原則,開辟了他們的視野。”[7]作為專門的文學翻譯類刊物,《譯文》出版時間最早,期數最多,影響最大。它通過有計劃、有目的地譯介國外優秀文學作品,在當時起到了開辟文化陣地、對抗文化圍剿的作用,從長遠來看,對中國翻譯文學的發展也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