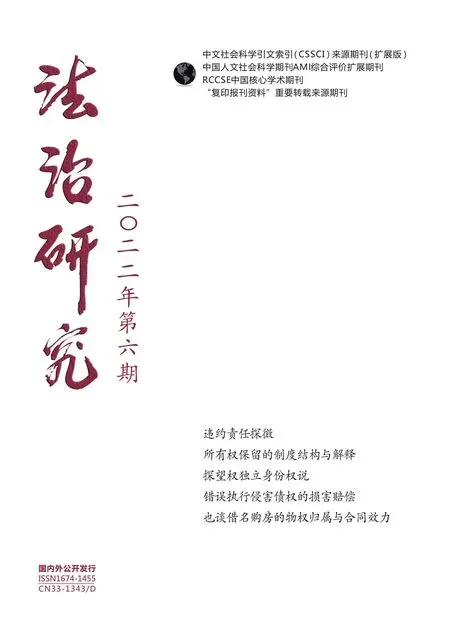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適用規則再檢討*
馮 源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單方舉債適用規則的確立與完善,歷經艱辛,牽動社會敏感神經。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簡稱“司法解釋二”)第24 條規定是單方舉債適用規則確立的標志,同時因為其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為原則,夫妻個人債務為例外的處理方式”,①參見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19 條第3 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在學術上和法律實踐中均引起較大爭議。基于約定財產制較少、缺乏書面要件,非舉債配偶一方對舉債方與第三人之間的經濟往來不知情等諸多原因,非舉債方欲利用但書中的例外情形來推翻夫妻共同債務的推定無比艱難,②參見王雷:《〈婚姻法〉中的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范》,載《法律適用》2017 年第3 期。實證研究也能夠充分反映這一條適用的現實狀況。③參見陳法:《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之檢討與重構》,載《法商研究》2017 年第1 期。2016 年以來,“法工委收到公民提出的近千件針對這一規定的審查建議”。④《重磅:人大法工委正在審查并推動解決“婚姻法24 條”》,載“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http://www.nwccw.gov.cn/2017-12/26/content_190528.htm,2022 年1 月24 日訪問。經過多年討論與爭鳴,最高人民法院先是出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增加兩款列舉式的除外情形⑤在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的基礎上增加兩款,分別作為該條第2 款和第3 款:“夫妻一方與第三人串通,虛構債務,第三人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從事賭博、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中所負債務,第三人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對第三人的權利進行限制。繼而又頒布并于2018 年1 月18 日起執行《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法釋〔2018〕2 號”),明文確立了“家事代理權”,是否構成共同債務取決于是否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負債。《民法典》的有關規定與司法解釋的最新舉措體現出明顯的承繼關系,爭議未必偃旗息鼓,而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卻越加復雜。本文從《民法典》中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適用規則出發,分析其與相關聯規范的關系,反思其能否窮盡共同債務認定的各種情形,做到有效平衡夫、妻、債權人三方利益。
一、夫妻共同債務抑或個人債務的判定標準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適用規則是婚姻家庭領域內一個較為復雜的命題,對其完善步履維艱,因為立法需滿足多種價值訴求與平衡多方關系。在價值訴求上,既追求民事主體之間平等、公平,又需要向弱勢群體的保護傾斜。同時,維持夫、妻、債權人三方利益平衡難度頗大,立法既需要考慮面向債權人的是夫妻共同體,夫妻可能會聯合欺詐債權人;也需考慮夫妻關系的可變性,夫妻一方可能會與債權人惡意串通,損害另一方的利益。當然,問題的解決方式還受制于一國夫妻財產制,共同制或分別制決定了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舉債究竟應該被推定為共同債務為原則,或是個人債務為原則。
(一)共同財產制:債務類型的判定基礎
共同財產制對夫妻財產關系有較為明顯的捆綁作用。“夫妻一體主義”價值觀導向消極財產共擔的形式,但共同財產制本身對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夫妻財產關系變化缺乏必要回應,推定為共同債務的基調并未錯誤,但其代價則似犧牲公平。
當事人通常不否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生之債一般為共同債務,但也質疑特殊情形下認定為共同債務的不合理性。例如,不知情、沒同意、動機自利、虛構債務、借款用于非法目的等等。爭議內容的復雜性,決定了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適用規則本身的多重標準,需徘徊于不同夫妻財產制所對應基本原理之間,大部分認定為共同債務,部分負債則由舉債方個人負責。這對立法是個挑戰,循著立法的軌跡,可見相關立法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使命: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國的夫妻財產制徘徊于不同立法思潮⑥受教會法夫妻“一體主義”思潮影響而形成日耳曼法習慣法的財產制逐步發展為共同財產制,影響法國等國家;受羅馬法夫妻“別體主義”思潮影響而形成的分別財產制,對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瑞、日、韓產生重要影響。參見陸靜:《大陸法系夫妻財產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40-42 頁。之中。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參照德國、瑞士等多國立法例首次設立夫妻財產制,“以提高妻之地位”⑦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親屬法》,順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版,第13 頁。。新中國成立之后,卻更多受到前蘇聯影響,由于前蘇聯已在《法國民法典》影響之下建立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1934 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第13 條規定“男女同居時所負的公共債務,則歸男子負責清償”,這是由于新文化運動下婚俗改革、解放婦女的立法結果,因為“女子剛從封建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她們的身體許多受了很大的損害尚未恢復,她們的經濟尚未能完全獨立,所以關于離婚問題,應偏于保護女子,而把因離婚而引起的義務和責任,多交給男子擔負。”⑧王歌雅:《紅色蘇區婚姻立法的習俗基礎與制度內涵》,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05 年第2 期。1950 年《婚姻法》規定男子承擔補充連帶責任⑨《婚姻法》(1950)第24 條:“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擔的債務,以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償還;如無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或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不足清償時,由男方清償。”便是延續了1934 年的立法傳統,共同償還意為連帶,并由男方承擔補充責任。此后,在個人財產自主權意識不斷增強,財產的形式更加豐富多元的社會變遷背景下,共同債務的承擔越來越注重平衡夫妻雙方的利益。1980 年《婚姻法》開始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以共同財產償還。”若“以”這樣的表達方式尚屬猶豫,2001 年《婚姻法》中“應當”的表達確定無疑地重申共同償還為原則,但不排斥當事人與法院的變通。⑩《婚姻法》(2001)第41 條:“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
(二)認定不同債務類型的基本原理
既然共同制決定了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生債務的一般基調,那么,哪些因素能夠區分出共同債務與個人債務的不同類型?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的探討,集中于對三類要素的整合:時間要素指向形式,即結婚與否是否對債務承擔方式造成特殊影響;身份關系的維持指向共同生活的實質,即共同生活通常導致個人、共同債務難以區分;單方舉債則指向夫妻各方在婚姻關系中的相互名義,是彼此獨立,還是代理甚至代表。整合之中涉及平衡與取舍,若立法存在糾結立場或規定漏洞,司法實踐必然對債務性質左右搖擺。
以結婚與否判定債務屬性。此時,起關鍵作用的是結婚的法定要式,婚前與婚后被切割為不同階段。若以共同財產制為基礎,意味著由婚前到婚后較可能導致消極財產(債務)共同承擔的結果。以結婚為要式進行時間切割是一種形式切割,共同財產的演變則與合伙制的婚姻歷史文化相關,有學者解讀為婚姻制度起源的社會經濟基礎,?參見蔣月:《婚姻家庭法前沿導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4 頁。“婚姻建立了性別不同的任務有別,其后果是使兩性之間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依賴;為了生計,必須合伙”?[法]安德烈·比爾基埃等:《家庭史:遙遠的世界、古老的世界(卷一)》,袁樹仁等譯,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101 頁。。建立于合伙基礎上的共同財產制在后世社會變遷中或被承繼或被反轉,大陸法系部分國家在共同制的基礎上建立夫妻法定財產制度或具備共同制的部分要素,而英美法國家不存在財產共有的概念,分別財產的傾向更為濃厚,即獨立人格下的獨立財產,這樣的反轉意味著另一種選擇。?參見[美]凱特·斯丹德利:《家庭法》,屈廣清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65 頁。即使婚姻關系締結不使原本的個人債務轉變為共同債務,至少婚后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符合家庭成員的期待。因結婚取得了共同生活的名義,可以作為共同債務的起算點。
以舉債用途判定債務屬性。作為法律認可的親屬身份行為,結婚以婚姻登記為要式,而家庭以共同生活為主要目的。舉債用途不拘泥于登記時間,更多關注家庭生活的經濟本質,負債是否為了共同生活。以婚姻為前提的家庭是個人集體生活的起點,故家庭以身份關系為紐帶,而行經濟生活的本質。?例如學者潘允康認為家庭是婚姻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生活的組織形式。參見潘允康:《社會變遷中的家庭》,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 頁。在美國著名的萊西案中,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指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夫妻雙方實為伙伴關系的本質,而婚姻財產的分配需要代表雙方在合伙事業中的共同利益性。?See Lacey V.Lacey,45 Wis.2d 378,173 N.W.2d 142(1970).在隨后的赫爾姆斯利案中,法官進一步指出婚姻伴侶是平等的貢獻者。?See Helmsley V.Helmsley,639 So.2d 909(Miss.1994).基于伙伴關系而對財產的公平分割法,例如《統一結婚離婚法》第307 條之一規定,允許對不論是何種時候以何種方式以夫妻一方或雙方共同名義獲得的財產進行分配,“舉債用途”是重要的考慮因素。故而,婚姻的任何一個階段都可能因為共同生活而負債:其一,結婚取得了共同生活的法律名義,結婚期間的負債一般認為是共同債務,或者認為是不可辨駁的共同債務,或者認為是推定的共同債務(可以推翻)。其二,在婚前為共同生活而負債并非毫無可能,越臨近結婚,越有可能為結婚預備而負債。因缺少法律名義,婚前負債一般不被認定為共同債務,除非當事人承擔更加積極主動的證明責任,證明為了將來共同生活而負債。其三,婚姻終止后為共同生活而負債,因婚姻關系已然結束,債權債務應該了結清楚。既缺乏婚姻關系的現有名義,也不存在獲得名義的將來可能性,一般不存在共同債務的認定余地,除非是為了子女而負債,離婚并不令父母子女的身份消除。
以代理(代表)理論判定債務屬性。代表理論是代理理論的更進一步,更有復古情懷。由于代表人與被代表人的緊密關系,代表人的行為視為本人的行為。在外部關系上,在任何場合中,原則上都是相互之間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某一方進入不負法律責任的避風港幾乎沒有可能,在格局上第三人利益的保護絕對優先,法律關系的雙方為家庭共同體與第三人。代表論的觀點非常危險,不應該是我國立法能接受的觀點,夫妻雙方為對方全權負責,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婚姻將成為生命無法承受之重;與非法人組織的合伙類比,后者僅指向經濟職能且有范圍,而家庭職能的全面性則使得債權債務的發生具有不可預知性,夫妻之間只能處處小心提防、謹慎行事,否則就是對婚姻的期待太過理想主義。與代表理論相比,代理理論相對折中,最大優點在于指明了夫妻一方行為的界限,例如,超越日常家事代理范圍的應該單方負責。如果說原《婚姻法》第17 條?《婚姻法》(2001)第17 條: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對家事代理權仍屬于“猶抱琵琶半遮面”,法釋〔2018〕2 號已然為其正名。值得注意家事代理權與夫妻財產制的關系,共同財產制存在推定的家事代理權,此時需要反向立法限定家事代理的范圍;分別財產制需要調和個人自治與共同生活之間的關系,此時需要正向立法另行授予代理名義。
二、三方平衡格局的立法維持與困境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的適用規則與夫妻財產制關聯性強,而法定夫妻財產制受一國傳統文化意識、民眾生活習慣和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制約較大。?參見夏吟蘭、薛寧蘭:《婚姻家庭編立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9 頁。基于我國同居共財的婚姻家庭習慣,家庭成員之間交往密切。在傳統家庭分工下,男方承擔較多經濟責任,為家庭提供了穩定的經濟來源。共同財產制的建立既符合婚姻的倫理機能,也符合利益共享的社會現實。基于共同財產制的制約,本規則往往圍繞是否構成“共同債務”進行認定。同時,析出不符合共同債務的情形,增加共同債務認定的準確率。維持丈夫、妻子、第三人三方利益平衡如此困難,毋寧說相關條款更致力于減少可能出現的糾紛。?參見馮源:《夫妻債務清償規則的價值內涵與立法改進》,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 年第5 期。
(一)一般規則的解釋傾向
原“司法解釋二”第23 條與第24 條的銜接,能夠勾勒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負債的一般性質認定,此時宜用時間切割方法來進行解釋:婚前單方負債,推定為個人債務,例外為共同債務;婚后單方負債推定為共同債務,例外為個人債務。婚姻所形成的共同體,在于親屬身份的創造,個人財產的相接,“婚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關系為目的,從而婚姻生活一般為精神的生活共同(互相親愛、精神的結合)、性的生活共同(肉的結合)及經濟的生活共同(家計共有)。”?史尚寬:《親屬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98 頁。《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3 條的規定可以看作是這種立法精神的部分延續,即“婚前單方負債,推定為個人債務,例外為共同債務”,這種例外說明時間切割的形式標準的運用并非絕對,而僅僅是通過結婚所創造的表面證據,可以利用“共同生活”的實質標準推翻,成立共同債務。《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1 條和第33 條形成呼應,在沒有特殊約定的情況下,排斥了個人債務因婚姻的締結轉化為共同債務的可能性,這種溯源法使得夫妻不同的債務類型顯得涇渭分明。之所以是部分延續,主要因為新法意圖對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飽受詬病的問題進行“破局”:婚前負債主要是個人債務,且夫妻之間走向結合、精誠協力,較少涉及共同負債,發生糾紛一方承擔責任的情形較多,第三方的存在感很弱;破局集中于對婚后債務承擔規則的修正,雖然婚后負債主要是共同債務,但當夫妻關系走向破裂、相互對抗之時,這種不加區分的共同債務導致非舉債配偶方負擔不公,與真實的情況南轅北轍,第三方難免會“漁翁得利”。
對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婚后推定為共同債務的立法傾向如何進行破局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第24 條的規定存在根本性錯誤,與當時上位法《婚姻法》第41 條之間產生了目的推定制與合意推定制的矛盾。21參見但淑華:《對〈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推定夫妻共同債務規則之反思》,載《婦女研究論叢》2016 年第6 期。完全顛覆第24 條的規定并非破局的關鍵,因為原《婚姻法》第41 條相當于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一般規則,第24 條不存在根本性錯誤,而在于“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技術導致個案顯失公平。原《婚姻法》第41 條嚴格區分共同債務與個人債務,“共同債務共同償還,個人債務個人償還”,而共同債務的形成基礎即共同生活,“身份的結合絕非關系人有不同之目的而互相對立,乃超越個人,包括個人,而有共同目的之本質的結合。”22戴炎輝、戴東雄:《中國親屬法》(第二版),三民書局1987 年版,第2 頁。這樣的一般規則在《民法典》時代也得到了延續,即為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無論婚前還是婚后都是共同債務。故而原24 條本質上屬于原41 條的延伸,由于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的財產基礎,婚后單方舉債一般認為是因共同生活而舉債;原24 條并非單獨創設了合意推定制,似乎單方舉債就意味著將不知情的配偶另一方拖入負債的深淵;合意推定制和目的推定有很強的關聯性,既然已經締結以共同生活為基礎的婚姻,則可推定通常存在舉債合意。換言之,原24 條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結婚已授予夫妻之間代理名義。即便如此,原24 條立法失之絕對。《民法典》規則調整的關鍵并不在于另起爐灶,而考慮個案衡平、減少推定的絕對性是破局的關鍵。畢竟,在一般規則上總體有利于第三人,主要是由于我國法定夫妻財產制所帶來的共同債務推定造成的。不受限制的代理權有時屬于單方一廂情愿,實質上另一方利益受損,若受損方屬于弱勢一方,將逆反婚姻家庭法保護弱者的價值取向而造成社會情緒反彈,屬于立法必須控制的風險。再則,這樣的立法結構也未充分注意到社會變遷下的個人財產與共同財產之間此消彼長的關系:部分學者對個人人格淹沒于團體人格的夫妻共同財產制表達不滿,認為應該縮小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增加個人特有產的范圍;也有學者認為共同財產制一刀切式的立法方式,僅能顧及夫妻關系的一般狀態,無法考慮到夫妻關系的特殊狀態。23參見蔣月:《20 世紀婚姻家庭法:從傳統到現代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413 頁。
(二)具體規則的解釋傾向
既然一般規則不存在根本性謬誤,則應從具體規則上控制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存在的法律風險,讓原24 條以另外的方式獲得新生。首先,可采取的方法就是對代理進行甄別。最高法院“補充規定”的公布起到了這樣的效果,“補充規定”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4 條中得到延續,可以結合舉債用途與夫妻代理理論綜合分析。“補充規定”增加了推翻夫妻共同債務推定的理由,其可以被歸納為兩大類型:其一,喪失共同財產制基礎,即構成對“共同生活”的根本性違反,這屬于最強推翻、當然推翻,隱含著自己事務自己負責的價值取向。當然推翻見之于原24 條的兩項除外規定,現在散見于《民法典》第1065 條第3 款、第1060 條,與夫妻約定財產制相關或作為在此基礎上的延伸條款:如果夫妻之間實行約定財產制,且第三人知情的,屬于個人債務;如果夫妻一方與第三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的,個人清償。前者將內部約定的知情面擴大到第三人,突破了合同的相對性,約定財產制條款發揮對外效力;而后者屬于夫妻一方的意思自治,表達了獨自承擔債務的意愿。《民法典》允許雙方約定消極財產承擔方式,所以當這樣的約定被另一方知曉時,對其發生法律效力。當然,圍繞債務承擔發生糾紛時,不能期待第三人自證不利,所以舉證責任往往落到被迫卷入債務旋渦的夫妻另一方。故而,最強推翻條款的立法思路即便正確,現實生活中卻用到很少,成為一定意義上的“僵尸條款”,從事實上而不是法律上令第三人得到更多好處。《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4 條(即“補充規定”)通過甄別代理,新增了推翻共同債務推定的情形:其一,夫妻一方顯然不具備舉債合意,即通謀虛構債務的情形下不保護第三人利益;其二,夫妻一方惡意,即不合法債務禁止第三人主張權利,相對前者“舉重以明輕”。值得注意,通謀虛構債務本屬無效意思表示,而非法債務本就不受法律保護,這樣的代理方式本該無效,那第34 條屬于畫蛇添足嗎?并非如此!“補充規定”出現之前的原24 條是怎樣光景,法院樂于適用一刀切的推定方式,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規定而決不會犯錯誤,非舉債方完成最強推翻又如此艱難,結果是推翻不了。很難期待,法院去尋找民法的一般條款去幫助非舉債方另辟蹊徑。24參見《民法典》第153 條:“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第154 條:“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補充規定”作為風險控制條款,防止司法實踐中“違反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僅憑借條、借據等債權憑證就認定存在債務的簡單做法”2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網:《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及夫妻債務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6982.html,2021 年1 月15 日訪問。;故主要貢獻在于通過明文規定的方式,發揮法院在此類案件中適當的能動性,審查夫妻債務是否真實發生。
僅憑從外延上甄別代理、改善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范的困局,仍不充分;列舉式的除外情形與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總有隔閡,這樣的立法難免掛一漏萬,因此“補充規定”出臺之后,仍然投訴不斷,對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的修修補補顯然無法應對日益增加的夫妻債務糾紛。故而,進一步瓦解原24 條的規定就成為不得已為之的選擇,甄別代理并不否認當然代理,但再次破局就要從代理本身入手,才能釜底抽薪式地解決原24 條的困局。于是,法釋〔2018〕2 號率先明示“家事代理權”的內涵,單方舉債即使有無限種可能性,也能以家庭日常事務作為分水嶺判斷是否構成共同債務,家庭日常事務和共同生活的實質相關性,令法釋〔2018〕2 號從共同債務的內涵出發,對癥下藥。家事代理權屬于借鑒式的立法成果,在諸多國家的立法中均有體現,例如德、法、日、意等國,英美國家也存在類似家事代理的制度。26參見馬憶南:《日常家事代理權研究》,載《法學家》2000 年第4 期。雖然各國立法對于家事代理所指向的范圍規定不同,但通常認為是“夫妻雙方及其共同子女日常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事項”27江瀅:《日常家事代理權的構成要件及立法探討》,載《法學雜志》2011 年第7 期。,基于濫用家事代理權產生的債務,由個人負責。
三、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與家事代理權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適用規則日臻完善,也就有了現在《民法典》相關規范的基本格局:《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1 條為個人債務和共同債務畫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第33 條以時間這一形式標準對兩者進行切割,婚前成立共同債務需要與實質標準“共同生活”相連接。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以新的面貌出現在《民法典》中,真正的將《民法典》第1062 條“夫妻對共同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落實于細微規范。原24 條一刀切的推定為共同債務的規定方式已經被家事代理權改造,被《民法典》第1064 條代替,這是“內部限制”;法釋〔2018〕2 號作為對原24 條的“補充規定”,出現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4 條,這是“外部限制”。兩者并行不悖。
(一)《民法典》中夫妻共同債務條款的適用協調
《民法典》第1064 條與《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4 條在適用上一般沒有沖突,應先考慮外部限制,再考慮內部限制。較多推定為共同債務是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的風險,而較多推定為“家庭日常事務”是《民法典》第1064 條可能面臨的風險,因其沒有說明何為家庭日常事務。從《民法典》第1064 條第1 款分析,其立法是基于夫妻的代理關系及其限制。一方面,夫妻一方以雙方名義舉債,應認定為共同債務。根據第《民法典》第1064 條第1 款,雙方名義的獲得,可以是“共同簽字”,或者“事后追認”,故單方簽字成立狹義的無權代理。有了家事代理權的限制,使得糾紛解決法律效果完全不同,之前即使不為了家庭日常事務但若不符合列舉的例外,仍然屬于共同債務。未嚴格按照簽字、同意或追認要求的“共簽”,應當盡可能利用意思表示解釋規則探知夫妻的真實意思表示。28參見葉濤:《民法典時代夫妻債務“共債共簽規則”中的合意認定》,載《法治研究》2020 年第5 期。偽造簽名,如果非舉債方能夠證明確屬于偽造,則和單方舉債并無二致,若不屬于家庭事務,成立狹義的無權代理,應當由舉債方自己負責。即便如此,家事代理權仍然無法走出迷霧的森林。何為家庭日常事務,立法語焉不詳,在法官不愿意使用自由裁量權之時,存在徑行推定為家庭日常事務的可能性。
《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4 條的列舉情形不在家事代理的范圍,體現為違反“共同生活”宗旨的情形,但列舉事項不完整,立法效果恐被打折扣。本立法作為風險控制條款針對事實上不滿足共同生活標準的情形。值得思考的是,除了通謀虛構債務和非法債務之外,是否還存在與共同生活宗旨相抵觸的其他情形?有學者主張,單方舉債應當適用雙重推定規則,推定舉債方配偶實施了欺詐行為,29參見胡苷用:《夫妻共同債務的界定及其推定規則》,載《重慶社會科學》2010 年第2 期。因此當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時,舉債方也同時需要證明自己不存在欺詐行為。這無異于自證不利的“有罪推定”,雖然并不合理,但至少表明在單方負債的情況下,有相當一部分情形屬于為自己而負債,與共同生活完全無關,因此更有效的方法在于進一步豐富推翻夫妻共同債務的列舉情形,應考慮將不符合“共同生活”的情形均排除在共同債務的范圍之外;另一方面,這樣的規定也和夫妻之間當然存在的家事代理權形成呼應,明顯不符合共同生活條件的事項應逐漸排除出代理的范圍。還存在一種更加特殊的情形,此時夫妻一方或雙方存在破壞共同生活的事實,應該結合《民法典》第1077 條、1079 條第3 款來進行體系解釋,若夫妻雙方處于冷靜期、某一方存在破壞共同生活的過錯或者雙方之間達到分居的法定期間,即使沒有離婚,這樣事實也應該認定構成對共同債務推定的推翻。在冷靜期,很多夫妻已經在做離婚預備,雙方的婚姻關系危機四伏,共同生活瓦解的風險大。符合《民法典》第1079 條第3 款的法定列舉情形,構成夫妻感情破裂,可以作為離婚理由提出,此時自然與共同生活實質要件不相符合。
(二)單方舉債規則的補充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的適用規則業已建立,即使仍有缺陷,也很難以動搖基本夫妻財產制的方式獲得修正,例如增設非常法定財產制這樣的方式。據此特殊情形下30夫妻關系出現法定事由時,如分居,或一方濫用日常事務代理權侵害另一方財產權,根據法律規定當然適用分別財產制,或經夫妻一方申請,由法院裁定宣告適用分別財產制。參見官玉琴:《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法理基礎及離婚婦女財產權益保護》,載《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6 年第6 期。,原屬于共同債務范圍的負債被認定為個人債務,“有利于保護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及維護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31陳葦:《中國婚姻家庭立法研究》,群眾出版社2000 年版,第205 頁。。例如《瑞士民法典》規定,夫妻非常法定財產制可基于重要事由依申請而設立(第185 條),或者夫妻一方破產時當然設立(第188 條)。32參見戴永盛譯:《瑞士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69 頁。雖然《民法典》第1066 條已經提供了婚內分割夫妻共同財產的可能性,但并未從根本上破解共有為基礎的夫妻財產制,而在有債權人參與的情況下亦無法平衡三方關系。學者研究非常法定財產制的適用情形主要包括,夫妻一方存在明顯不當的財產處分行為或者夫妻處于分居的事實狀態,33一方拒絕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一方對他方合理且必要的財產處分行為拒絕同意;一方管理財產或處分財產行為存在明顯不當;一方個人財產不足以清償其個人債務;夫妻雙方因感情不合而分居達到一定期間的(6 個月或1 年)。參見薛寧蘭、許莉:《我國夫妻財產制立法若干問題探討》,載《法學論壇》2011 年第2 期。也有學者認為應該加入過錯。34參見梁慧星:《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親屬編)》,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89-90 頁。既然特殊情形涉及一方過錯(難以繼續生活的主觀情形)或者分居達到法定情形(事實上沒有共同生活的客觀狀態)。受此啟發,過錯可納入對婚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不符合共同生活目的理解范疇,從而擴充《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4 條的具體情形;同時,針對家事代理權進行立法的細化。
以“共同生活”為根本認定的要件,以分類歸責為具體方法,將規范體系所針對的具體情形進行解釋。何為“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指向家庭的實質要素,從根本上體現為居所、家庭成員、物質資料等形式要素35參見[德]邁克爾·米特羅爾、雷音哈德·西德爾:《歐洲家庭史》,周尚意、趙世玲、趙世瑜譯,華夏出版社1987 年版,第7 頁。之間的連接關系,古德較早認為包括物質及社會活動,36參見[美]威廉·J·古德:《家庭》,魏章玲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 頁。我國學者對此有人口生產、經濟、感情、社會關系多層面理解。37參見馬有才:《婚姻家庭十年概述》,載《社會學研究》1989 年第4 期。以“共同生活”作為基本出發點,考慮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被推定為共同債務的可推翻情形:其一,以意思自治的方式變更。由非舉債方證明推定的共同債務已被變更為意定的個人債務,以意定的方式排斥債務與共同生活的相關性,符合民法私法自治的精神,此時結合《民法典》第1060 條與第1065 條第3 款進行綜合認定。其二,通過惡意負債破壞舉債行為與“共同生活”的連接性,即《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4 條所列舉的兩種除外情形。無論是通謀虛構債務還是非法債務,通常理解為個人行為,自己負債較為妥當,與夫妻家事、共同生活本屬無關。其三,不具共同生活合意的其它特殊情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夫妻雙方約定由個人負擔的債務,但以逃避債務為目的的除外;一方未經對方同意,擅自資助與其沒有撫養義務的親朋所負的債務;一方未經對方同意,獨自籌資從事經營活動,其收入確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除了以上規定之外,應補充設置不符合共同生活的其他情形。一方面,補充不具備共同生活基礎(或共同生活基礎受到較大威脅)時所負債務的除外情形,例如包括夫妻分居一年之后形成的債務,夫妻處于冷靜期以個人名義負擔的債務;另一方面,應補充設置夫妻一方惡意破壞共同生活作為除外情形,可結合《民法典》第1079 條的過錯進行理解,補充違反夫妻忠實義務所欠債務、因對受到家庭暴力成員進行醫治所欠債務均屬于個人債務,不由另一方承擔。
細化家事代理權相關條款,進一步調整夫、妻、債權人三方承擔風險的結構。部分學者認為既往立法中“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暗示了夫妻家事代理權38參見薛寧蘭、金玉珍:《親屬與繼承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4 頁。,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說法較不明確,“不應局限在共有財產的有償轉讓、無償贈與、抵押或出租上,還應擴大解釋為夫妻對共有財產享有平等的管理權、使用權和處分權。”39孫若軍:《論夫妻共同債務“時間”推定規則》,載《法學家》2017 年第1 期。既往立法是以身份的方式推定夫妻之間相互代理,而《民法典》試圖將家事代理限制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疇之內,卻又止步于此。何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目前實踐中的裁判尺度比較混亂,大部分裁判者普遍采取了金額標準、用途標準或二者結合的客觀標準。40參見王軼、包丁裕睿:《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與清償規則實證研究》,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 年第1 期。有學者認為可采取“交易必要性”作為客觀標準,41參見繆宇:《走出夫妻共同債務的誤區 以〈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 24 條為分析對象》,載《中外法學》2018 年第 1 期。立法應從交易目的、交易服務對象、與家庭實際經濟狀況的相關度等方面42參見李洪祥:《〈民法典〉夫妻共同債務構成法理基礎論》,載《政法論叢》2021 年第1 期。予以明確細化,可細化說明家事代理的范圍。如《法國民法典》第220 條“夫妻每一方均有權單獨訂立旨在維持家庭日常生活與教育子女的合同。夫妻一方因此締結的任何債務均對另一方產生連帶約束力”43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68-69 頁。。也可將某些處分排除出家事代理的范圍,如排除人身專屬性較強行為、風險較大行為與大宗的財產處分行為。44參見胡紀平:《論夫妻家事代理權》,載《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6 期。有學者認為應將家事限定于價值微末的“家庭日常生活”范疇,不包括金錢借貸(以及類似信用交易)。45參見賀劍:《夫妻財產法的精神——民法典夫妻共同債務和財產規則釋論》,載《法學》2020 年第7 期。
四、結語
《民法典》中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單方舉債適用規則代表了一個階段的立法成果。在立法的發展過程中,原“司法解釋二”第24 條經歷了不斷更新、逐漸被代替的過程,立足于婚后所得共同制而推定個人名義舉債為共同債務,雖然基本原理無誤,但過于絕對。故而,圍繞著婚后夫妻共同債務的界定,相關立法和司法解釋逐漸被修正。第一步,從“補充規定”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34 條,甄別代理和非代理行為,除了原立法認定意定個人債務不屬于共同債務之外,虛構債務和非法債務也無法成立有效的夫妻代理。第二步,從法釋〔2018〕2 號到《民法典》第1064 條,將夫妻單方代理限定于日常家事,超越此范圍的單方舉債若成立共同債務,舉證責任由債權人承擔,由其證明屬于“家事”,即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超出部分不能輕易采用表見代理的理論而擴張共債范圍。由此可見,在我國夫妻財產制下,家事是成立共同債務的核心部分,可以當然代理;但代理是手段而非目的,也需要符合客觀要件。即便如此,《民法典》現行相關規則存在家事定義不清晰、手段情形列舉不完全的問題。從解釋論的角度,將周邊法條引入解釋的范疇進行體系解釋,結合家事應該具備的本質特征進一步完善,既能避免重復立法,又能克服法律條文之間的矛盾,有效平衡債權人、夫、妻三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