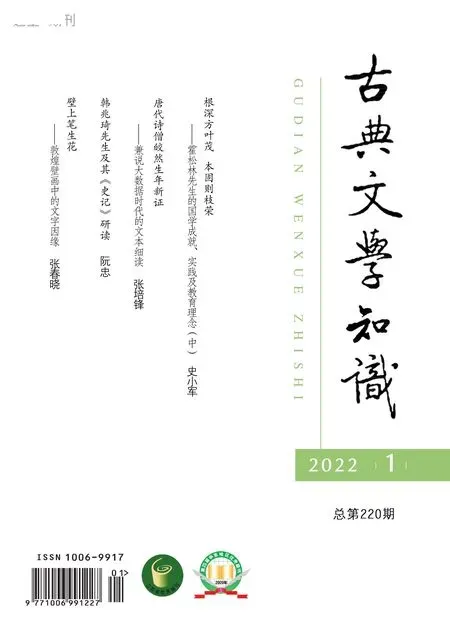大寒天與樂天相伴
陳才智
大寒深處春水生,千山萬徑閱枯榮。按照中國傳統節令,二十四節氣里壓軸的是大寒,過了大寒,意味著又過了一年。古人講,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但是,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大寒的意義之一,就是善始善終。《授時通考·天時》引《三禮義宗》說:“大寒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謂之大……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大寒的物候有三個,一是雞始乳,二是征鳥厲疾,三是水澤腹堅。就是說,母雞提前感知到春氣,開始孵蛋了;鷹隼之類遠飛之鳥正處于捕食能力極強的狀態,盤旋于空中到處尋找食物,以補充能量抵御嚴寒;在一年的最后五天,寒至極點,水中的冰一直凍到水中央,最厚最結實。而物極必反,堅冰深處春水生,凍到極點,也意味著開始走向消融了。過了大寒,就是立春,氣溫回暖,新的一年也即將開始。
在大寒這個節令,不妨與樂天相伴,看一看這位廣大教化主如何與大寒相處,怎樣樂于應命順天。白居易,字樂天。《禮記·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這是白居易名的來歷。《周易·系辭上》云:“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這是白居易字的來歷。從字面上看,“樂天”就是樂于順應天命,“居易”則是安土之意,而二者是密切相關的,因為《禮記·哀公問》云:“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從反方面解釋了安土與樂天的關聯。漢代經學大師鄭玄注曰:“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蘇軾《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說“努力莫怨天,我爾皆天民”,怨天尤人,怨恨命運,不反思己過,就會責怪別人,非君子之道也。明代王廷相《慎言·作圣篇》云:“隨所處而安,曰‘安士’;隨所事而安,曰‘樂天’。”再來看《孟子·梁惠王下》:“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與鄭玄同時代的經學家趙岐注云:“圣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也。”將樂行天道這層意思再引申一步,“樂天”還可以理解為安于處境而無憂慮,也就是陶潛《自祭文》所謂:“勤靡余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以上這些典籍均可幫助我們理解“樂天”一詞的內涵。
作為唐代最有生活情調的大詩人,白樂天可謂人如其字,對節令物候非常留意和關注。如果調查一下白居易筆下的節令物候描寫,就會發現,他的詩歌基本上涵蓋了二十四節氣,這當然與他的詩作留存數量是唐代之冠有關,但他留心身邊日常,勤于創作,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這里想和大家分享兩首他筆下與大寒相關的詩作。先來看《村居苦寒》: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被,坐臥有余溫。幸免饑凍苦,又無壟畝勤。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據《白居易年譜》,這首詩作于元和八年(813)十二月,地點是在下邽,也就是今天的陜西渭南市北下邽鎮東南。當時白居易因母親逝世,回家居喪,退居于下邽渭村老家。退居期間,白居易身體多病,生活也十分困窘,多虧得到元稹等友人的大力接濟,雪中送炭,才幸免饑凍苦。
這是一首諷諭詩。在當時文壇上,白居易最早出名就是憑借著諷諭詩。什么是諷諭詩呢?白居易自己的界定和理解是:“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比興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至于諷諭詩,意激而言質。”可見,所謂諷諭詩,內容的規定性是旨意可觀,稍存寄興,與諷為流,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比興;其創作意圖是要成兼濟之志;其藝術特征是意激而言質。按照這個理解,我們來對照著閱讀這首《村居苦寒》。
在白居易題材廣泛的諷諭詩中,這一首《村居苦寒》敘寫流暢,不事藻繪,而格外真切感人,具有紀實的史詩性質,在當時確實屬于“意激”,意見很激烈,思想很前衛,其中包含著熱烈的心腸,偉大的抱負,閃熠著推己及人的人道主義光輝。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正處于唐代中期,當時雖然相對安穩,但內有藩鎮割據,外有吐蕃入侵,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已經大為減少,可是還要供養大量軍隊,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侶、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在這種情形下,農民負擔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來自普通世家的白居易對此深有體驗,詩中所寫“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同他在另一首《夏旱詩》中所寫的“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一樣,正是他親眼所見的現實生活的實錄。
開篇“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據宋人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三:“樂天詩有記年月日者,于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爞爞。’有以見憲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競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為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霈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仆按東漢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說,正所以記異也。”可見白居易詩歌具有很強的寫實性。
《村居苦寒》這首詩的結構十分簡單,完全可以分成兩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寫農民,后一部分主要寫自己,二者同樣的是處于北風如劍、大雪紛飛的寒冬,可是冷暖對比十分明顯。農民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而自己在這樣的大寒天卻是深掩房門,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蓋,既無挨餓受凍之苦,又無下田勞動之勤。詩人把自己的生活與農民的痛苦作了對比之后,深感慚愧和內疚,以致發出“自問是何人”的慨嘆,自剖自責,這不能不說難能可貴。“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二句,可謂畫龍點睛之筆,凸現出詩人對農民饑寒交迫的深切同情。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上評論道:“詩境平易,正以數見不鮮。”正因為眼中屢次所見,所以敘寫流暢,情真意實,體現出白詩獨特的平易通俗的藝術風格。
白居易不但諷諭詩平易通俗,其他類型的詩也具有同樣的特色。比如同樣是在大寒之節撰寫的《問劉十九》: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壚。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這是一首知名度極高的邀請朋友喝酒的詩,作于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時年46歲,已經從中央朝廷的高官,被貶為地位卑微的江州司馬。劉十九大概是作者在江州時的朋友,“十九”,是指排行,名字不詳。很多選本認為是彭城人劉軻,據朱金城考證,非也。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另有《劉十九同宿(時淮寇初破)》詩:“唯共嵩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明。”可知劉十九為嵩陽(今屬河南洛陽)人。淮西吳元濟誅于元和十二年(817)十一月,此詩作于淮寇初破之時。元和十三年(818)春,白居易在江州又有《雨中赴劉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劉已先去因以四韻寄之》《薔薇正開春酒初熟因招劉十九張大崔二十四同飲》,其中的“劉十九”,應該都是指白居易在江州時的這位友人——嵩陽劉處士。
在詩體上,這是一首五言絕句。作為篇幅和字數最少的一種詩體,如何以少納多,值得考量。此詩堪稱典范。全詩簡練含蓄,輕松灑脫,信手拈來,即成妙作,而其間脈絡十分清晰。從層次上看,首句先出酒,二句再示溫酒之具,三句又說寒天飲酒最好,末句問對方能否來共飲,而且又點破詩題中的“問”字。從關系上看,首末句相呼應,二三句相承遞。詩句之間,意脈相通,一氣貫之。詩作寫盡人情之美,從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側面落筆,以如敘家常的語氣,樸素親切的語言,富于生活氣息的情趣,不加雕琢地寫出朋友間懇誠親密的關系。至今讀來,仍有余溫。
對這首詩的意境和情調,后代的批評家在欽羨之余,可謂好評如潮。比如,明代黃周星《唐詩快》評論說:“豈非天下第一快活人。”清代孫洙《唐詩三百首》評價:“信手拈來,都成妙諦。詩家三昧,如是如是。”(呂薇芬校點本)鄒弢《精選評注五朝詩學津梁》:“氣盛言直,所謂白詩婦孺都解也。”王文濡《唐詩評注讀本》卷三曰:“用土語不見俗,乃是點鐵成金手段。”(中國書店影印本)俞陛云《詩境淺說》曰:“尋常之事,人人意中所有,而筆不能達者,得生花江管寫之,便成絕唱。此等詩是也。即以字面論,當天寒欲雪之時,家釀新熟,爐火生溫,招素心人清談小飲,此境正復佳絕。”(《詩境淺說》續編)
梁啟超批點《白香山詩集》認為,白居易《招東鄰》:“小榼二升酒,新簟六尺床。能來夜話否?池畔欲秋凉。”與此詩“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是“同一意境”。讀《招東鄰》《問劉十九》二詩,可知白居易之好客,有酒則呼友同飲。今存長沙窯瓷器有兩首題詩:“二月春豐酒,紅泥小火爐。今朝天色好,能飲一杯無?”“八月新風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色好,能飲一杯無?”(田申、劉鑫《全唐詩補:長沙窯唐詩遺存》,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版)可以明顯地看出擬仿改寫白居易原詩的痕跡,這正是此詩流行一時的最佳案例。原跡字體的俗寫,乃至訛誤,充分透露出白詩在走入世俗民間時產生的變形軌跡,這一點頗有《詩三百》重章疊韻的遺韻。
“愿保喬松質,青青過大寒。”(耿湋《晚登虔州即事寄李侍御》)在自己遠貶江州之際,46歲的詩人白居易能夠苦中作樂,寒中送暖,期盼一份最最平凡的友情,這與他42歲時,在村里的農民苦寒之際,愿意站出去,寫下來,同情并呼喊,其實是心同此理、情同此懷的,皆歲寒然后知喬松之后凋也。被視為充滿“寒氣”的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里面曾說:“天氣愈寒了,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嗎?我們是有的。”也和白居易《村居苦寒》一樣,是對比著自己來寫的,這不僅是面向已逝友人的亡靈,也是面向所有需要溫暖的天下蒼生。魯迅慣于在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但寒的極點后面就是春天,所以他也曾說:寒凝大地發春華。時當歲末,令在大寒,愿我們運轉春華至,歲來嫩蕊青。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