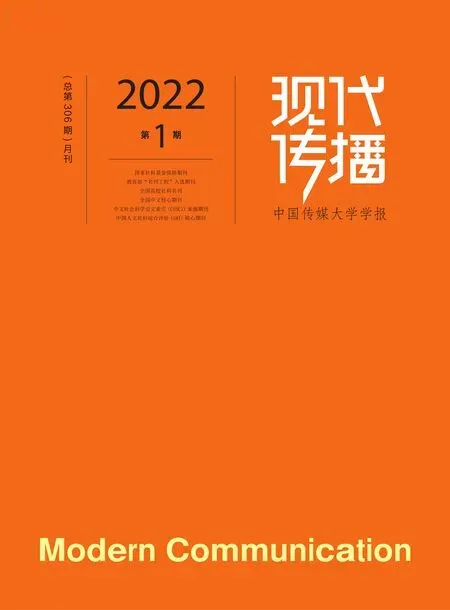傳播十要素論*
韓立新 楊新明
一、問題的提出
美國當地時間2019年11月17日上午,在結束美國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第105屆年會相關議程后,筆者和兩位同仁踏上歸程。在巴爾的摩華盛頓國際機場(三字代碼:BWI,以下簡稱巴爾的摩機場)候機的過程中,機場檢票的有趣做法引起了筆者的注意——機場方將乘客依序分成不同的小組,乘客在檢票過程中,不必排隊候檢,只需坐在座位上靜候,直到廣播和顯示屏播出自己所在的組號,然后以組為單位登機。這樣就為乘客節省出一些時間,并建立了比較清晰的秩序。從登機過程來看,乘客因為對秩序和時間有了更好的把握而表現得很安然自在。巴爾的摩機場的檢票、登機是一種社會傳播現象,反映著傳播統一于實踐,并構成實踐過程一部分的屬性,正因為如此,傳播才從實踐的內部,而不是外部,建構著實踐秩序,筆者稱這種現象為“巴爾的摩建構”。
通過對“巴爾的摩建構”這一現象的觀察,我們意識到傳播研究以信息傳送為邏輯起點的缺陷。“5W”模式確立的是“傳者—受者”分析框架,沿著這一路徑來分析,巴爾的摩建構現象中的傳播要素①為Who(檢票員)、Says What(檢票和登機指令)、In Which Channel(機場廣播)、To Whom(乘客)、With What Effect(有序登機)五個要素。②這五個要素雖然簡潔清晰,但從這個要素出發,再去觀看巴爾的摩建構,我們發現看不到原本的面貌了,使這個傳播行為、過程得以進行的環境、制度資源等都看不見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為解決這一問題、洞觀巴爾的摩建構的傳播結構提供了基于實踐邏輯的思想方法和理論工具。作為唯物史觀核心思想的實踐觀“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③。實踐作為人類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性活動,由生產實踐和交往實踐兩個方面構成,其中,交往實踐是指“多極主體間通過改造或變革相互聯系的客體的中介而結成網絡關系的物質活動。”④將交往的性質理解為實踐,是一個重要的判斷,對傳播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長期以來,傳播學研究將傳播理解為單純的認識活動,理解為信息采制與交換的活動,這樣就掩蓋了傳播主體與實踐主體的統一性,掩蓋了實踐中的客體與傳播主體的關聯性。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揭示,傳播是交往實踐中的認識活動,是交往實踐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表現。這樣,傳播的性質就是交往實踐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表現,就不是單純的認識活動,就不能脫離實踐活動而存在,而是實踐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是主體改變客體的一部分,因而傳播不是實踐之外的認識活動,而是發生在實踐活動之中的主觀能動性的表現。實踐、交往、傳播是有內在聯系的一組概念。
將傳播寓于實踐范疇,主要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傳播是促使客體狀態發生合目的性變化的實踐的一部分。認識“是主體反映客體的活動,所得到的結果是認識,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是獲得真理,它并不使客體形態發生變化,因而是一種觀念性活動,而實踐的結果,則是客體形態發生合目的性的變化,創造出人所需要的現實對象物”⑤。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視閾中的傳播是實踐的范疇,是促使客體狀態發生合目的性變化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表現,是創造出主體所需要的現實對象物的行為,傳播主體不是“純粹的認識者”,其邏輯起點不是傳遞給受者對客體的認識(或者說傳遞認識只是表面行為),而是實踐,是改造和影響客體的實踐。繁榮200余年的大眾傳媒所創造的記者這一角色,試圖描述為“純粹的認識者”,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所以可稱大眾傳媒的傳播活動為“形式上的認識活動”。
二是將傳播活動理解為實踐范疇而非純粹的認識活動,揭示了傳播主體的社會歷史性,或者說傳播主體是實踐主體的一種屬性,是實踐主體在改造客體的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將傳播活動理解為認識活動,其邏輯過程是:一個外在的客體作為認識對象,引發主體(傳者)的認識活動,形成認識及其產物(文本),然后傳遞于受者。如果將傳播活動理解為實踐活動,其邏輯過程是:主體為改變和影響客體,對客體進行認識,并將認識的結果與另一主體(受者)進行交流和互動,傳播活動是實踐主體之間的一種交往實踐,蘊涵于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之中。在此意義上,傳播是實踐的組成部分,表現在實踐主體改造客體的過程中,表現為實踐主體之間、主客體之間的互動方式。
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來觀察巴爾的摩機場的傳播活動,發現實踐主體(機場管理方、乘客),為改變出行狀況這一客體,解決出行這一社會任務,主體之間借助符合行動要求的媒介進行交往,派生出傳播主體這一角色,傳播統一于出行實踐過程中。基于此,筆者觀察到,巴爾的摩機場的傳播活動不僅包含上述的五個要素(其中,Who被視作實踐主體1,To Whom被視作實踐主體2),還有事體Matter(乘客與航空公司達成的乘坐交通事宜)、制度資源Resources(機場及登機的管理規范,管理方可以借此將乘客分組)、建構性行為Constructive Behavior(機場方借助資源將乘客分組的行為)、傳播場景Communication Scene(雙方所在的場合)、知識Knowledge(傳播活動所需要的知識)這樣五個要素。因此,巴爾的摩建構中包含的傳播要素是“5W+MRCCK”十個要素。
二、巴爾的摩建構的要素、模式與特征
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視閾下認識巴爾的摩建構的要素及其構成的模式與特征,可以發現傳播要素發生在實踐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中,是實踐要素相互作用的產物。
(一)巴爾的摩建構的要素
1.傳者與受者
傳者與受者是一對社會關系范疇的概念,馬克思認為社會關系不是理論反思的產物,而是人的生存活動和需要的產物,并且規定著人的本質,因此,他主張把社會關系當做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⑥。為了使客體發生合目的性的變化,主體需要在實踐過程中進行信息傳播,所謂的傳者和受者就是不同主體在進行信息傳播時的屬性的指稱。傳者與受者在實踐中形成了實踐關系,這種實踐關系規定了傳播關系的性質。近來學者們把傳統媒體時期的“受眾”或“用戶”視作“行動者”(actor)⑦的新認識,實質就是對主體的這種實踐關系的發現與闡發。
2.事體
在實踐關系的意義上,事體是人類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表現,構成實踐關系及其意義的隱喻空間,這意味著主體與另一主體就改造客體這一目的達成了某種協議,不同主體通過協議確立傳播關系,對自己在行動中因資源配置等原因構成的權利關系和行動秩序表示遵從。同時,事體是實踐主體行動的邊界,離開了特定的事體,主體與主體、主體與客體就不構成特定的關系范疇,行動結構也就面臨解體。
3.知識
巴爾的摩建構是實踐主體的對象性活動,這就決定了傳播活動所需要的知識是“現實的知識”,而不是自我意識的純粹性知識,馬克思深刻洞見到“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⑧所以,“對現實的知識本身就是改變現實的第一步……正確地認識現實,是為了改造現實。”⑨傳播所需要的知識表面上看是媒介使用和日常性知識,傳者根據顯示屏和廣播等載體的特性以及受者的知識結構設計信息呈現方式方面的知識等等,但實質上,傳播所需要的知識來自于實踐的規定性。在巴爾的摩構建中,是旅客出行這一實踐規定著知識的需要。
4.制度資源與建構性行為
制度資源和建構性行為是密切相關的兩個要素。制度資源是指不同主體為改造客體而制定的必須共同遵循的交往規則,建構性行為是指主體利用制度資源對另一主體進行結構化的行為。在實踐結構中,制度資源來源于傳播活動之外,建構性行為位于信息傳播之前和之中,它們為信息傳播建構合理的傳播秩序,從而順利地完成社會任務。其中,制度資源的傾向性配置賦予了一方主體開展建構行為的權利,如果說事體意味著主體的實踐關系和傳播關系的確立,那么制度資源進一步規定了這兩種關系得以運行的基本機制和形式。通過制度資源的配置,主體能夠輕易認識到自身在實踐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并且有效區分權利的歸屬和行動的邊界。因此,被賦予優勢資源的實踐主體在傳播過程中往往表現為更加自覺的狀態——主體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制度資源,且主動利用這種資源和媒介進行信息的整合與傳播,而另一主體則更多地表現為參與傳播、適應行動秩序以及反饋。隨著新媒介技術系統的介入,實踐主體被置于實踐過程的兩端,主體只需要關注自身在特定位置所進行的特定行動,實踐的中間過程由技術系統規劃與設定,過去主體不得不關注整個實踐過程的狀況及其帶來的消耗和緊張情緒,被媒介化的建構性行為消解,從而更便利地建構著新的實踐秩序。
5.傳播場景
傳播場景指的是傳播活動發生的場景,它規定了傳播活動的范圍。在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看來,傳播場景不僅是特定時空中的物質場所或區域,更是一種信息流動的模式,包含了物質場所和媒介場所,“地點和媒介同為人們構筑了交往模式和社會信息傳播模式”⑩。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視閾下的傳播場景寓于實踐場景之中,由基礎設施等實體條件和社會關系等無形條件構成,二者共同建構了信息傳播和行動相統一的場域。梅羅維茨將視點聚焦于傳播環境,強調信息傳播的場景因素,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將視點置于實踐過程,而信息傳播就統一于實踐過程中,傳播場景自然包含于實踐場景中。巴爾的摩建構的傳播場景融合了人與人、人與物協同行動的一切條件和傳播材料。
(二)巴爾的摩建構的模式
巴爾的摩建構反映了傳播與實踐的統一性。實踐就是主體為了實現自身改造客體的目的進行的對象化活動,其過程可以簡述為“目的—中介系統—客體”。實踐發生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在主體認識并作用于客體過程中,創造新的社會歷史條件,從事新的實踐。其中,中介系統是主體為實現其目的的一切手段的集合體,傳播只是中介系統的一部分,是實踐主體作用于客體的一種方式。在巴爾的摩建構中,為了改變空間的阻隔,實現通行的目的,多方實踐主體(交通管理方、運營方、乘客等)為此達成通行和服務于通行的協議(機票是標志之一),并在資源配置基礎上確立了交往關系(乘客是這一關系的一種身份化的表征);基礎設施(機場的設施)、社會系統等有形與無形條件構建了實踐得以開展的環境,規定了行動與傳播的范圍。實踐主體1即機場管理人員(傳者)利用被賦予的以及自身創造的傳播資源將實踐主體2即乘客(受者)結構化,再針對其特征選擇符合行動要求的媒介傳遞具體的行動指令。當知識進入這一過程,知識與實踐主體的知識經驗統一起來并反映在行動過程中,進而使行動與媒介相融合。如此一來,信息傳播統一于實踐主體改變客體的行動過程中,傳播屬于中介系統的一部分,在建構傳播秩序的同時提高了行動效率。由于實踐活動的內部特征,實踐主體1(傳者)結構穩定,而實踐主體2(受者)結構相對松散,以此達到客體發生合目的性變化的目標,另外,實踐主體在客體狀態變化的同時,自身也隨著客體和現實條件的變化而變化。至此,十要素建構了傳播統一于實踐的半開放式傳播模式(如圖1所示)。
(三)巴爾的摩建構的特征
巴爾的摩建構的傳播模式總體上呈現出客體發生合目的性變化、受者結構化、傳播統一于實踐這樣三大特征:
1.客體發生合目的性變化
主客體是一對關系范疇的概念,“存在物之為客體是以主體的存在為前提的;沒有認識者和改造者的存在,不對主體而言,是談不到客體,也就無所謂客體的。”因此,主體認識活動和改造活動的對象才被稱作客體。對于實踐過程而言,客體發生合目的性變化的意思是說,實踐主體從事的社會任務的面貌在主體的能動性作用下向符合主體目的之方向變化。傳播現象既發生在不同主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也發生在客體合目的性變化的過程中,并受主客體關系的規定,其邏輯過程是主體—客體—認識—主體—客體,即主體為改變和影響客體,對客體進行認識,并將認識的結果與另一主體(受者)進行交流和互動,進而改變客體。因此,巴爾的摩建構并沒有停留在主體認識客體的階段,而是憑借媒介手段和其他主體的特性來構建分殊化的信息傳播方式,使得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傳遞給另一主體,引發主體的協同行動,進而改造客體的存在狀態。
2.受者結構化
受者結構化指的是作為傳者的實踐主體依據受者和傳播場景的特質,利用制度資源將其秩序化的過程,旨在增加受者接收指令信息并依此行動的便捷性和可控性,傳者與受者、受者與受者之間形成了穩定的結構關系,以提高實踐行動的效率。新媒介技術應用提供了一個新的有序化方式,傳者對受者的結構化有時表現為對數據信息的結構化,傳者通過對數據信息進行特定目的和方式的整合,再通過媒介向特定的受者傳遞相關信息,影響和引導受者行動。數據信息的管理與傳遞,印證了“控制論之父”維納(Norbert Wiener)有關“作為消息的有機體”的論斷:“物質運輸與消息運輸之間的區別在任何理論意義上絕不是固定不變和不可過渡的”。現代信息技術是通過在實踐中的應用來影響和改變傳播的,透過屏幕后面實踐主體及其對客體合目的性變化的過程,或者說,把網絡傳播放到特定的實踐中去,才能看清楚這一點。
3.傳播統一于實踐
信息傳播是主體改造客體的中介系統的一部分,不論傳播樣態如何嬗變,實踐始終是傳播的本質屬性,實踐目的之完成是信息傳播的旨歸。由于新媒介技術的應用,線下行動轉化為線上傳播,使得實踐在許多情形下脫離實體場景,“就好像‘超文本’掙脫了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樣,數字化的生活將越來越不需要仰賴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在更廣的社會范圍內,新媒介技術不僅使得社會實踐的部分環節轉化為信息傳播,而且使得信息傳播成為實踐主體的行動環境,“智能媒體將不僅僅是媒體,而是與社會融為一體,由此改變人類的生活傳播方式。”在此意義上,信息傳播與實踐主體的行動高度統一的傳播現象正是新媒介環境區別于傳統媒介環境的典型特征。但這并沒有改變信息傳播作為實踐中介系統的實質,只不過有更多的實踐主體在其中從事著新媒介技術工作罷了。
三、十要素論:新媒介技術應用的驗證
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視閾來考察傳播活動,意味著研究視野從信息傳播范疇擴展為實踐行動的范疇。從我們今天能夠觀察到的媒介實踐來看,巴爾的摩建構廣布于組織管理的實踐活動中,例如軍事戰爭中,步兵、騎兵、弓駑兵等兵種各列其位,指揮官通過戰鼓向不同兵種傳遞具體的行動指令等。隨著新媒介技術滲透到日常生產、生活領域,新媒介技術進一步增強了實踐活動中媒介中介的作用,各種實踐行動的面貌得到重塑,巴爾的摩建構的十個要素及其性質被突顯出來。考察新媒介技術在公共服務、日常生活、工業生產領域的實踐應用,可進一步驗證信息傳播統一于實踐活動的屬性。
(一)醫療服務
在醫院信息化建設初期,“許多大型三級甲等醫院急診科普遍存在病人流量大、隨機性強、多次等候等特點,醫護人員和患者需要在醫院內頻繁移動和處理大量信息”。醫護人員和患者都在醫療實踐中經受著緊張、無序,時常出現非技術性矛盾的問題。基于移動醫療技術的預檢分診系統,為醫方解決就診無序的狀況提供了技術支撐。“信息化的急診分診系統,可在收集病人客觀信息資料、進行更加合理的分級分區、決定就診的優先次序、保證綠色通道暢通無阻、提高危重病人搶救成功率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分診系統參與的醫療流程可簡述為:確定患者病情與級別——分配到相應科室——候診區等待——廣播媒介提示患者信息——進入診室就診。作為實踐主體的醫院方憑借媒介技術向患者傳遞行動的指令,進而構建合理化的就診秩序。這一傳播過程的要素包括事體(醫患達成的就診事宜)、傳播資源(醫療管理規則)、傳者(或者說實踐主體1:醫院方)、建構性行為(醫院方憑借媒介技術與醫療規則引導患者行動)、受者(或者說實踐主體2:患者)、媒介(顯示屏與廣播)、內容(就診指令)、知識(常識性知識與媒介使用知識)、效果(就診過程有序、高效)、傳播場景(醫院)。可見,就診過程包含著巴爾的摩建構及其十個要素。政務服務和銀行服務等公共服務的實踐過程與醫療類似,導視系統等新媒介的應用,建構了新的行動秩序,使辦事效率得到提升。
(二)移動出行
移動支付、移動出行、網絡購物、網絡直播等新媒介應用業已成為日常生活領域的新媒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面貌。其中,移動出行所引發的傳播要素的流動與融合尤為典型。有學者總結了移動出行平臺的系統結構(如圖2所示),認為基于技術匹配的新型出行方式保證了時間、總里程和參與人員數量的最優化,對傳統出租車行業形成挑戰。

圖2 移動出行平臺的系統結構
這一系統結構反映了出行的實踐主體(移動出行平臺、乘客、出租車)通過媒介技術進行交往實踐的過程:移動出行平臺將用戶的出行需求、位置信息和服務提供者的車輛信息、位置信息匯聚到平臺數據庫,根據用戶對車輛及車主的偏好、位置等條件信息進行最優匹配,再將匹配好的信息分別發送至二者的移動端,二者通過傳播在現實中結合,整個過程變得精確、高效、合理。技術匹配代替了用戶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隨機尋找。其要素包括,事體(平臺、司機和乘客就出行達成的協議)、制度資源(政策規制)、傳者(出行平臺)、建構性行為(根據用戶需求匹配相應的服務提供者)、受者(出租車司機和乘客)、媒介(移動平臺)、內容(用戶的需求和位置信息)、知識(媒介使用和地理等相關知識)、效果(提高出行效率)、傳播場景(線上平臺和線下場景)。新媒介技術拓展了巴爾的摩建構的范圍,創造了新方式。
(三)智能生產
為了解決生產資源浪費、生產效率低下的問題,有的工廠所有者在機器和工人之間介入采用功能傳感器和數據采集點等智感技術,使得機器和生產資料等信息及時反饋給工人,工人依據媒介平臺顯示的數據信息調整生產,使得工業互聯網中的“人、機、物”各種實體高度協同,形成無縫融合的最終形態。這一過程的實現,是通過其事體(生產要素之間的協議)、傳者(智感平臺)、制度資源(生產制度)、受者(機器和工人)、媒介(媒介平臺)、建構性行為(智感技術將生產要素合理化調配)、內容(生產性信息)、知識(數字技術知識)、效果(提高生產效率)、傳播場景(車間和媒介場景)協同完成的。
2020年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產業互聯網發展指數China Industrial Internet Index(CII)2019—2020》顯示,產業互聯網在我國金融、制造、文娛、零售、教育、醫療、物流七大關鍵行業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企業完成業務收入12061億元,同比增長21.4%;全行業利潤保持較快增長。2019年,相關行業實現營業利潤1024億元,同比增長16.9%,而研發投資的增速高于收入增速,2019年相關行業的研發費用535億元,同比增長23.1%。可見,進一步加強產業互聯網在國民經濟中的滲透程度及其技術應用的創新發展,將成為我國數字經濟建設的重要抓手之一。目前階段,基于產業互聯網應用的生產特征主要表現為以產業互聯網平臺為中心,發揮產業互聯網連接、協同的技術屬性,連接供需兩端或多端,經過產業互聯網平臺的精準匹配,將特定的供需信息類別化,傳送至與之相符合的用戶和服務提供者,最大限度上優化生產資源的匹配和生產流程。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看,產業互聯網平臺與供需雙方都是為改變既有資源分配狀況的實踐主體,在傳播環節中,產業互聯網平臺成為數據信息的采集者、傳播者,而供需雙方成為接受訂單信息或產品信息的受者,過去完全依賴市場行動的產業形態由于產業互聯網的應用,凸顯了媒介和傳播因素的作用,反映著實踐媒介化,或者說實踐中的媒介因素顯性化的新趨勢,實踐的中介性進一步增強。
四、結論及其意義
(一)傳播要素研究的實踐轉向
美國學者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提出傳播過程的“5W”要素;美國學者R·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在其基礎上增加了傳播目的與傳播情景,提出“7W”要素;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學者麥奎爾等人(Denis Mc0uail)總結前人研究,認為最普遍意義上的傳播由八要素構成:發送者、傳遞渠道、信息、接受者、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系、效果、傳播發生的場合以及信息涉及的一系列事件。經典傳播要素研究把進行信息傳送的傳者看作邏輯起點,把傳播行為看作一個獨立于實踐之外的過程,并在這一研究傳統中逐漸擴展、深化,搭建著傳播理論框架。這與研究對象的選擇和生動的大眾傳播實踐相關,現代意義上的大眾媒體的勃興和繁榮引人關注,成為一個時代的研究熱點,研究者觀察的是大眾媒體和大眾傳播,對其呈現的看似獨立的傳播系統及其職業形態,進行著分析和概括,很容易產生暈輪效應,忽略傳播與交往、實踐的內在關系,作出傳播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過程的判斷。
上世紀八十年代,張隆棟、鄭北渭、徐培汀、陳韻昭等學者把西方大眾傳播學中的傳播要素理論介紹到國內,傳播要素與傳播模式成為影響我國傳播研究的一組重要的概念工具。與此同時,傳播研究者發現了既有傳播要素理論脫離實踐的問題,并且開始轉向實踐尋求答案,他們通過具體的實踐活動來洞察其中的傳播機制,試圖更合理地解釋社會傳播現象。截至2020年3月3日,筆者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中鍵入主題詞“傳播要素”,得到相關文獻428篇,除了20世紀80、90年代的3篇介紹性文章和2篇書評外,其余文獻均是在傳播學本土化過程中運用既有傳播要素理論觀照傳播現象的成果。這些文獻主要分為四種情況,一是以“5W”要素理論或信息論為指導,為研究對象提供一個現成的闡釋性框架(215篇);二是基于信息傳播的邏輯來剖析新的傳播現象,發現新的傳播要素(7篇),例如教育傳播的四要素和六要素;三是對既有傳播要素在新媒介環境中的新形態的考察(51篇),發現了新媒介引發傳播要素乃至整個傳播生態嬗變的現象,認識到傳播要素理論脫離實踐的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四是針對新傳播現象嘗試建構新的傳播模式(75篇),其中,在25篇期刊文章中,只有7篇屬于新聞傳播學科,其余多分布在情報科學、教育學等領域,跨學科考察更清晰地觀察到傳播要素理論脫離實踐所引發的問題。此外,在428篇有關傳播要素的研究文獻中,79篇文獻將傳播要素理論應用到網絡輿情、品牌形象、視覺傳播等領域,賦予其實踐的內涵,例如資本、權力、技術等生產層面的因素被視作傳播要素。筆者在2021年3月15日重新鍵入主題詞“傳播要素”,得到新增論文49篇,依然符合以上規律,故不贅述。
總之,研究者發現既有傳播要素理論在解釋當前的一些社會傳播現象時力有不逮,并且研究者開始將傳播要素置于具體的對象性活動的結構中進行考察,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視閾對傳播研究的重要意義。
(二)傳播作為生產實踐的中介
隨著新媒介技術在社會生產、生活領域的應用,“許多行動及其過程轉化為可傳播的數字,行動變得可以通過媒介傳播”,生產實踐過程顯示出更強的媒介化特征,傳播成為生產實踐的中介,傳播學研究也隨著新媒介技術的應用擴展至生產實踐領域。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視閾,可以讓觀察者更清晰地看到生產實踐的傳播特性,以及它在傳播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
大眾媒體作為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其本質是實踐主體進行對象性活動的中介,實踐主體通過大眾傳播來從事制度性的社會實踐。由于大眾媒體的傳播是職業化的形態,依憑的是社會制度等資源,因此大眾媒體在一定程度上是個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中心,它作為實踐結構一部分的屬性更多地表現在組織和國家意義上。新興媒體與此不同,新媒介技術在資本驅動下以技術應用的形式逐漸向全社會范圍內滲透,作為生產實踐的中介物,它在更廣的范圍上給予了生產主體與其他主體直接交往的渠道。基于新媒介技術的連接與數據化運行邏輯的生產實踐加強了生產要素與社會要素的分化、流動與融合,促進了生產格局的重組和社會面貌的重塑。經由新媒介技術的傳播活動勾連著生產實踐的全部過程,它不僅使生產實踐的行動與過程媒介化,而且引發生產實踐領域新的分工。如果從經典傳播要素研究的范式觀察,看到的是傳播活動以內容生產或信息傳遞的形式從實踐結構的外部作用于生產實踐,因而傳播與生產實踐彼此割裂,這一認識與當前媒介應用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視閾來審視,可以觀察到,多元的生產主體通過傳播活動從事著生產實踐,傳播作為生產實踐的中介這一角色被揭示出來。一方面,新媒介技術以及座駕于其上的傳播活動引發了生產實踐的進一步分工;另一方面,生產實踐的目的與邏輯又規定著主體間傳播的樣貌。在這個意義上,傳播活動作為生產實踐的中介具有了生產性特征,即傳播活動的展開寓于生產實踐之中。
總之,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出發觀察傳播活動,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一是傳播是促使客體狀態發生合目的性變化的實踐,不論作為交往實踐的環節或是生產實踐的中介,傳播需要被理解為實踐主體的對象性活動,而非停留在表面的主體之間的信息傳播;二是揭示了傳播主體是實踐主體的一種屬性,是實踐主體在改造客體的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傳播活動發生在實踐的結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傳播是實踐的組成部分,表現在實踐主體改造客體的過程中,表現為實踐主體之間、主客體之間的一種互動方式。由此來看,傳播要素研究有必要從“5W”的框架中超越出來,在社會交往與生產實踐中給予新的考察。
注釋:
① 這里的“傳播要素”是指“傳播過程的基本組成部分”或者“傳播得以進行所必不可少的構成因素”。前一定義參見陶涵主編:《新聞學傳播學新名詞詞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頁;后一定義參見邱沛篁、吳信訓、向純武等主編:《新聞傳播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頁。
② 美國學者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提出了上述傳播過程的五個要素,被后世學者奉為經典的“5W”模式。參見Lasswell H.D.TheStructureandFunctionofCommunicationinSociety.InLymanBryson.(Ed.).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New York: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1948.p.37.
③⑥⑧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03、526頁。
④ 任平:《走向交往實踐的唯物主義》,《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第54頁。
⑤ 楊權利、趙潤琦:《馬克思主義哲學專題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頁。
⑦ 顧潔:《媒介研究的實踐范式:框架、路徑與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6期,第15頁。
⑨ 馮波:《早期阿爾都塞的斯賓諾莎主義——以意識形態批判為中心》,《哲學研究》,2018年第11期,第32頁。
⑩ [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