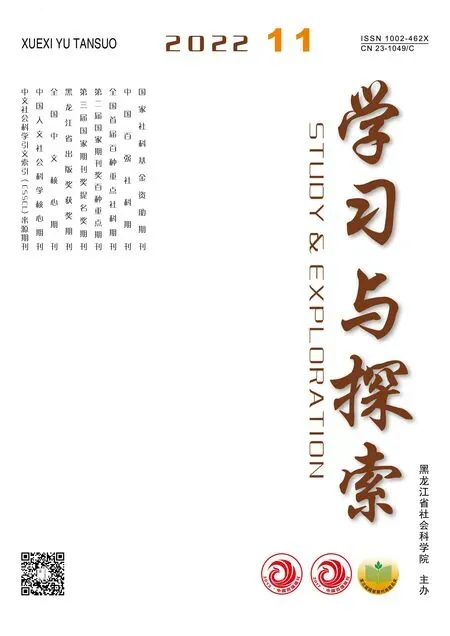蘇聯文藝翻譯與東北解放區文藝運動
韓文淑,葉靜妍
(吉林大學 文學院,長春 130012)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左翼文藝界開始了對蘇聯文藝有意識、有組織的譯介,而蘇聯的文藝觀念與文學作品也借助大規模的翻譯,逐漸影響中國文學的面貌,并產生了中國的“革命文學”與“普羅文學”。到了東北解放時期,在“以蘇為師”的潮流中,東北解放區無論是蘇聯文藝的翻譯,還是蘇聯文藝的影響,都到達了新的層面與新的階段。
一
延安時期,對蘇聯的認識和認同更多來自政治的親緣力與信念的感召力,東北毗鄰蘇聯,東北特別是北滿地區長久以來居住著不少蘇聯僑民。而蘇聯紅軍在東北光復后駐扎東北將近一年,與來到東北的老解放區的干部及知識分子密切相處。這使中國共產黨的文藝工作者,在原有的信仰相通與思想契合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情感、心理與思想上的認同。
今天,我們更多是從延安文藝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影響的角度,來解釋和理解東北解放區文藝的展開與發展。延安文藝對東北解放區文藝的指南性自不待言,但是這種完全立足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演進的解釋中仍有遮蔽,其中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和淡化了蘇聯的外來影響。這與195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當代文化史和思想史在歷史化的闡釋中,不斷削弱蘇聯影響的表述方式有直接關系。而這種方式在1980年代文學創作主潮向歐美尋求資源后被進一步強化了。
回到東北解放時期的歷史語境與文學現場,我們會發現,在東北解放區文藝運動中,無論是文藝的領導層,還是文藝的實踐層,在重視和吸納蘇聯文藝上都有著高度共識。1945年,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蘇聯所創造的新文藝,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藝的范例。”東北解放初期,不少知識分子都認定,蘇聯在文藝理論與文藝創作上取得的建樹,是當時東北解放區文學難以望其項背的。李輝英在《發揮文藝的戰斗力量》中也認為,蘇聯文學遙不可及,正所謂“看看人家看看自己,我們愈加感到慚愧”[1]。
東北解放區作家對蘇聯文藝的輸入和借鑒有著相當的主動性。可以說,蘇聯文學的傳播和接受,是東北解放區文藝運動發生的題中之義。或者說在某個層面上,對蘇聯文藝的翻譯運動與文學經驗的轉化運動,本身就是東北解放區文藝運動的結構性部分。
在出版領域,在中共中央東北局和蘇聯方面的推動和資助下,東北書店、大眾書店、光華書店、友誼書店和遼東建國書店等為代表的“紅色出版機構”有組織的開展蘇聯文學的翻譯與出版工作。據《中國現代文學總目錄》統計,東北解放區發行的蘇聯文學譯介單行本有87本之多,其中小說就有 53本,其規模可見一斑。
在報刊領域。當時在東北哈爾濱、長春、沈陽和大連等大城市設立的中蘇友好協會都有專門會刊,《中蘇研究》《蘇聯之友》《蘇聯介紹》《中蘇知識》等會刊都以“介紹蘇聯,增進友誼”為宗旨,展開蘇聯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其中很大一部是文藝領域的。《東北文藝》《東北文化》《東北日報》《文藝戰線》《文藝月報》《知識》等綜合性報刊,也設置專門的文藝欄目推介蘇聯文藝,且分工明確,各有側重。像《中蘇研究》刊發的大多是文藝類的譯作,《東北文藝》則大多是蘇聯文學理論的介紹。
在東北文藝運動中,知識分子重視甚至崇拜蘇聯文藝和蘇聯作家。例如,1948年8月東北光復3周年之際,周立波、草明、陳學昭等十幾位作家共同發表《八·一五致蘇聯作家的信》,對蘇聯和蘇聯作家致以誠摯的敬意,對蘇聯文學的經驗寄予厚望。即使像關沫南這樣來自“偽滿”的作家,也表現出了認識和學習蘇聯文藝的熱情。為紀念俄國十月革命29周年,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撰寫了《紀念十月,要學習蘇聯文化》,還翻譯了《保衛祖國戰爭中的蘇聯作家》《蘇聯文學概觀》等作品。
在解放區文學的發展的線索上,相對于延安文藝,特別是以趙樹理和孫犁為代表的政治鄉土創作,東北解放區在戰爭題材、土改題材和工業題材上都有明顯的開拓。像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草明的《原動力》和劉白羽的《政治委員》等都是典型代表。這些作品既繼承了延安文藝的政治觀念與形式策略,又有了類似“十七年”文學的那種更為宏闊的民族國家敘事的氣度與追求,表征了解放區文學到了東北解放時期在文學形態與美學格局上的重要推進。東北解放區文學能夠置于新的時代起點,取得新的歷史緯度,蘇聯文藝的影響不可小覷。
草明曾經在《火車頭》中描寫了在農村工作中信手拈來的干部劉國梁,在領導現代化的大型聯合企業時的力所不逮。而同樣,東北解放區經歷了大規模的軍事戰爭、大范圍的土地改革,以及接管和領導城市與工業的新的歷史任務。東北文藝需要面臨和表現的現實政治、經濟變革之間的內在聯系,已經較延安時期發生了顯著變化,顯然超出了延安時期所理解的“工農兵”文藝的美學規范和發展程度。正因為如此,當時的文藝批評家把“東北解放時期和東北解放區的文藝的任務”稱之為“新時期和新任務”。可以說,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社會歷史處于新的起跑線,需要文藝對這個新的社會歷史現場以深刻而有力的回應。具體來說,當時的文藝界就是以繼承、延續并超越延安文藝作為文藝建構的目標的。而客觀來講,除了民間戲曲的創作和運動,當時東北解放區的文藝生產,已經不能在已有的西北解放區的延安文學的“工農兵”經驗中尋求到更多的現成樣板。其時官方又要求作家緊密配合當時的斗爭形式和政治任務,以高效的創作表現正在展開的巨大歷史變革和豐富的現實生活。而蘇聯社會主義文藝在衛國戰爭文學和社會主義建設文學方面都積累了大量現成經驗。其實踐中探索到的無產階級文化與文學領導權,對文學如何組織、作家如何培育、評論如何展開,特別是文學創作寫什么,怎么寫,哪些主題、情節和形象是被鼓勵的,哪些主題、情節和形象是不被接納的,甚至是文學的形式、語言和風格,都有完整的認識與明確的規定。“以蘇聯為師”幾乎成為不走彎路并多快好省的開展文藝運動與文學寫作的必然選擇。
在“工農兵”文學的“涉兵題材”上,延安文學確有實踐,但更多是表現勞動奉獻和軍民魚水之情的,像孫犁《荷花淀》雖然表現了戰爭,但充滿生活氣息與鄉土韻味,戰爭的宏大場面和英雄主義格調在其中幾乎沒有顯示。這與延安時期文學的政治鄉土取向和戰爭格局是有著直接關系的。而東北解放時期,延安文學狹小的美學規范已經無法與大規模的軍事斗爭和恢弘的歷史變革相匹配了。弘揚斗爭精神,表現戰爭倫理,書寫英雄人物,成為新時代文藝的新需要和新要求。
二
1948年東北文代會召開前,東北局的機關報《東北日報》開始連載東北解放區文學的成果性作品。除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外,還有劉白羽的《政治委員》《無敵三勇士》、西虹的《零下四十度》、華山的《踏破遼河三千雪》等。從題材上就不難看到,當時認為代表了解放區文藝階段性成就的,并不是我們今天普遍認定的土改題材與工業題材,而恰恰是被今天或多或少忽視的戰爭題材。東北文代會明確地提倡作家要大力地創造戰爭文學。“文藝工作會后,大家響應林總的號召,創造戰爭的文學……從戰爭中去尋找,不僅是尋找戰爭的事,也要尋找戰爭的人。”[2]由于文代會的推波助瀾,戰爭題材在東北解放兩年后,成為東北文學主要的題材潮流。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根據幾個不完全的出版統計材料看來,東北兩年多以來的文學,在數量上,‘為兵的’大大超過了‘為工的’,卻不少于‘為農的’”[3]。
在“東北文代會”上,中共東北局宣傳部也明確提出要“學習蘇聯創造英雄形象的現實主義方法”[4]。然而實際上,在沒有成為政策導向之前,東北解放區創作就已經受蘇聯英雄主義價值理念的感召了。在一定程度上,劉白羽的創作就是在與蘇聯文藝的對話和互動中完成的。他一方面秉持高度的非虛構和寫實主義的立場,以隨軍作者的身份,根據實地見聞,寫出了報告文學《人民與戰爭》《英雄的記錄》。對于當時有人認為報告文學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藝的指責,劉白羽以蘇聯文藝觀為自己辯護:“雖然也還有人把這種寫作排居文藝之外,但我堅決不這樣想,我堅決認為與時代斗爭同呼吸,是文藝最需要的特色。最近蘇聯文學報社論就提出:‘和現實的問題更接近一些!’”[5]另一方面,劉白羽的代表作《政治委員》也受蘇聯文學啟發。他在《西蒙諾夫談〈日日夜夜〉的創作》中說:“那是1946年嚴冬,我從哈爾濱經齊齊哈爾出發到前線去。在一節鐵罐軍用車廂上,我看見一位政治委員在車門口,就著光線,出神地讀一本書。……這本書就是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提起1946年,中國人民會記得那時我們正經歷著多么大的困難。……西蒙諾夫與中國讀者的結合,不是在寂靜的書桌上,而是在血肉斗爭中。”[6]而這個場面和經歷恰恰成為他創作的重要動機:“我作為一個軍事記者,經常不斷地在前方隨軍行動,到一九四六年冬天,那暴風雪的日子過去了,我才在一位政治委員啟發之下,又寫了這篇《政治委員》小說。”[7]
除戰爭題材外,東北解放區其他主題的文學也都在蘇聯文學中汲取養分:“四十年代后期,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改革和工業建設在廣闊的解放區轟轟烈烈地進行,中國文學出現了不少反映這種生活的作品。這些文學作品的創作者都有意無意地以蘇聯文學中同類題材的作品作為創作楷模。”[8]
周立波是以創作土地革命題材小說《暴風驟雨》聞名的。周立波不僅是作家,還是一位蘇聯文學翻譯家。早在1936年,他就翻譯了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他的代表作《暴風驟雨》是中國“土改文學”的肇始之作,雖然,因為周立波缺少東北和偽滿洲國生活的實際經驗,《暴風驟雨》在地方語言的使用方面有所偏頗。但是,其能在土地改革的現場寫出思想周至與格局宏大的作品,應該說得益于蘇聯文藝的滋養。有研究者總結道:“周立波將身體書寫以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融入在革命敘事之中,詮釋了紅色經典的身體詩學,讓我們看到了作家在觀念的政治規范與真實的生命本能之間所做的思考與取舍。”[9]也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文藝工作者,從蘇聯文學里學習了最進步的創作方法。這種方法教導著我們要有深刻的思想性。要緊緊的和人民連結在一起,要忠實的表現勞動人民的戰斗和生活。”[10]汪介之在《選擇與失落:中俄文學關系的文化觀照》中也指出,《暴風驟雨》中“元茂屯的眾多人物……差不多都可以在肖洛霍夫筆下的格列米雅其村找到形神相似的原形”[11]。當然,“除為相同的政治背景驅使進行創作外,周立波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實現自己的政治使命的文學觀念與肖洛霍夫發生了共鳴”[12]160。《暴風驟雨》在東北解放區的土改題材中脫穎而出,其厚重的思想與宏闊的格局,特別是在駕馭歷史大敘事過程中,結構人物的性質、位置及其結構關系的清晰與有力上,是同時期的《江山村十日》無法比擬的,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參照了蘇聯社會主義改造文學的現成經驗。
草明是中國解放區“工業文學”的代表作家,她的《火車頭》《原動力》等小說無論從主題還是創作模式上,都可視為中國當代工業文學的發端。左聯在20世紀30年代就翻譯了包括《士敏土》在內的一大批工業文學,而參與左聯活動的草明從那時起就開始自覺參照蘇聯文學創作涉工題材的作品。她的《原動力》在1950年代初期被翻譯成俄文,俄文序者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部小說在構思上與《士敏土》的同構性:“ 瑪克辛·高爾基在一封給蘇聯作家菲奧多·格拉特柯夫的信中,提到他的小說《士敏土》,寫道:‘我以為這是一本極有意義而且極好的書。這是革命以來能緊緊抓住并且照耀出今日最重要主題——勞動的第一本書。’這些話完全適用于《原動力》。格里勃·朱瑪洛夫,格拉特柯夫小說中的英雄,號召蘇維埃人民向他們所締造的新世界邁進。《原動力》的女作者和她所塑造的人物,也知道有這樣一個新世界,蘇維埃世界,‘一個屋宇堂皇機器神奇的世界,一個人不再是奴隸而是主人的世界’。”[13]由此可見,《原動力》在創作中顯然借鑒了《士敏土》嚴謹、明晰、鄭重和有序的關于對工人、工農關系和工業生產的一套完整的敘述模式。
三
蘇聯的政治抒情詩在東北解放戰爭期間也被大量翻譯過來,特別是早在延安時期就有很高知名度的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在這個時期獲得了更高聲望:“寫詩是得有充分的時間,從生活里體驗詩素,如馬耶闊夫斯基主張‘詩的貯藏’,意思就是把所有詩的題材、內容和詩的句節等, 孕育個相當期,然后再寫出來,而且要充滿了藝術的價值,這樣才成為一個詩人。”[14]受蘇聯詩歌現實性、戰斗性、樂觀性與理想性的鼓舞,東北解放區詩人在新詩創作觀念上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詩人們不再過多地專注于個人化趣味,而是通過詩歌鼓舞和團結群眾,使詩歌變得極具革命感染力。雖然東北解放時期的詩歌并未在藝術造詣上取得較高成就,但此時的詩歌卻能夠深刻反映出東北解放區政治、軍事與社會的現實情況,使詩歌呈現出獨特的時代性與現實性。
東北解放區的民間戲曲運動主要專注歷史使命與民間傳統的結合,但在民族和鄉土視野之外,仍會附以蘇聯的尺度。當時譯介過來的《斯大林論民間藝術》就是東北文藝運動汲取蘇聯社會主義戲劇實踐所依憑的范本。當時,東北文藝工作團編輯出版了《蘇聯演劇方法》,系統介紹了蘇聯話劇的組織方式和表演程式。1947年11月,東北文協文工團趕拍了大型蘇聯話劇《俄國問題》,“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進一步擴大了東北文協文工團的影響,提高了她的地位”[15]。《俄國問題》凝聚了1940年代后期國際關系和蘇聯政壇的諸多核心話題,反映了戰后美帝國主義走上戰爭與對抗之路,試圖對蘇聯發起戰爭,蘇聯呼吁美國有正義感的大眾要堅決反對與斗爭。在東北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富有時效性的翻譯和翻拍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東北解放區文藝運動借鑒蘇聯文學的敏銳性和及時性。
在文藝批評理論的建構方面。雖然東北解放區的文藝運動有毛澤東文藝思想和《講話》為指導,但仍有著較為迫切的理論自新的訴求,仍希望有更具稠密度的系統理論作為依持。當時的東北文藝界,缺少評價文壇狀況與諸多新作的有力的理論系統和話語平臺。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東北解放區文藝建構中,圍繞“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批判”以及《夏紅秋》《網和地和魚》《一個農民的故事》等作品的爭鳴和討論,就是指導文學創作的文學理論的不完整和未定型而導致的不協調與不一致導致的局面。整個東北文壇在創作和評論上都缺乏具有高度統一規范性的價值標準與理論尺度。而當時,蘇聯文學幾十年社會主義文藝實踐已經生產出一套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人民性原則和黨性原則為核心范疇的對社會主義文學的依據、本質和使命做出了清晰表述的完整理論系統,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東北解放區文藝界的理論需求。“譯介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理論直接指導了東北的文藝理論批評,在東北解放區,對蘇聯文藝理論的翻譯熱情空前高漲。《東北日報》《東北文藝》經常發表蘇聯《真理報》的文藝社論、文藝動態或評論文章,而且篇幅都很長,這在東北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是絕無僅有。蘇聯的文藝理論,特別是關于文藝的階級性、人民性、黨性等內容成為建構東北解放區文藝理論的直接參照系。”[12]349應該說,蘇聯文論的意識形態原則、理論框架、話語系統、批評策略促進了東北解放區批評話語的生長與成熟,對解放區的文藝理論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
東北解放區在文藝運動中非常注重青年人的改造與青年文藝骨干的培養,提出“改造舊部,培養新軍”的口號。“改造舊部”是對以偽滿作家為主的舊東北青年進行思想改造,而“培養新軍”主要是培育東北文壇新人。這兩者幾乎都可在蘇聯文壇中找到范本。例如,《青年作家在蘇聯》(《文學戰線》1949年第2卷第2期)一文中就系統介紹了蘇聯青年作家的培育和創作情況。當時的知識分子對蘇聯青年作家都非常欽佩:“蘇聯的青年作家,是蘇維埃文學的新的生命。凡是關心蘇聯文藝近況的人,都會驚喜從1945—1950年,有如群星燦爛,那樣多的青年作家,發射出無可媲美的異彩。蘇聯是怎樣培養青年作家的?”[16]東北解放區也師法蘇聯培育青年作家的現成做法,在東北解放區文藝運動中形成一套有利于發現新人和培植新人的系統模式,扶植了一批文壇新人。周立波、劉白羽、柳青和曲波這些當時只有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后來成長為新中國文壇的骨干,與東北解放時期的文藝實踐與文壇的培育有直接關系。
蘇聯文學生產的計劃性在解放區文藝運動中同樣被采用。蘇聯文學生產并不是自發的和松散的,而是統一在黨的領導、組織和建構中的,是具有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驅動下的組織化、集約化和標準化的:“蘇聯的作家訪問工廠、制造所、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他們有到任何地方去和研究本國的任何一個角落的方便。作家同盟致力于將此種研究導入一定的河床。他們做出旅行計劃。”[17]延安時期,作家在創作中就重視實地采風和調研,而東北解放區文學生產的頂層設計和調動性比以往更強,有著關于創作領域、創作主題和創作時間的系統組織和明確要求。作家都被納入一個分工明確的精密結構中,進行有規劃、有組織和有進度的調研和創作。東北解放區的代表作無不是在這種制度化的創作機制中完成的。這也是東北解放區文藝運動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生產大量作品,并大幅度地展開新的文化向度和拓寬題材格局的主要原因。
結 語
東北解放區文學在建構過程中不斷吸收和轉化蘇聯社會主義文藝經驗,是中蘇文學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和中轉站。在學習蘇聯文學的同時,東北解放區文學在建構過程中也表現出了很強的主體性。東北解放區文學并不是對蘇聯文學的簡單挪用、移植和模仿,以蘇聯文藝經驗對自身的文藝建構截長去短,而是始終在自我政治立場和文化建構的價值取向范圍內,以自我實用性為原則,進行有選擇性的創造性吸收。當時,東北文藝界翻譯了大量蘇聯衛國戰爭題材小說。其中既有《俄羅斯人》《盧德米娜》《一個女游擊隊員的經歷》《前面便是他們久待的目標》等表現革命青年成長和頑強斗爭的創作,也有《他的情人》《只不過是愛情》《等著我吧》《侵略》等表現戰爭與愛情,以及戰爭給人帶來創痛與創傷的悲劇性敘事。東北解放區文壇在第一類主題上形成了潮流,第二類主題則涉獵較少。從中不難看出,當時東北解放區文藝建構具有自身的價值邊界、審美規范和情感經驗,東北解放區文藝的翻譯與文學創作之間既有轉化關系,也存在著某種差異性和不對稱性。
無論如何,東北解放時期,蘇聯文藝的影響都是深遠的,這種影響不僅僅限于文學層面,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本身就以思想的維度和藝術的方式,參與到中國現當代的歷史文化轉型和發展的進程之中。蘇聯社會主義文藝的故事和經驗在解放區的各階層中都有非常高的認可度和經典性:“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年代。這時在敵后的斗爭中,文學方面重要的精神食糧,就是蘇聯衛國戰爭的文學譯作。時代出版社的一套數十冊的《蘇聯文藝》和一些單本,就成為八路軍、新四軍中每一個知識分子成員不能缺少的讀物。其間如A.托爾斯泰的《他們為祖國而戰》,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戈爾巴托夫的《不屈的人們》,李昂諾夫的《侵略》以及西蒙諾夫的《俄羅斯人》,對我們在敵后的堅持,勝利的信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18]
蘇聯文藝對中國文藝的影響是一個持續性的歷史過程。在東北解放區,無論是蘇聯文藝翻譯,還是東北解放區文藝對其的自覺借鑒,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高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經過二十多年穩定的和連續性的譯介積累,蘇聯文藝觀念得到了高度系統化的翻譯,文藝作品規模龐大,其影響開始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發展;另一方面,在東北解放過程中,特別是大規模的兵團作戰、土地改革運動和工業生產的政治主題,在蘇聯社會主義文學中都非常容易對標,并于其中找到自身的問題性。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身份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蘇聯文學的影響從解放區延續到了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