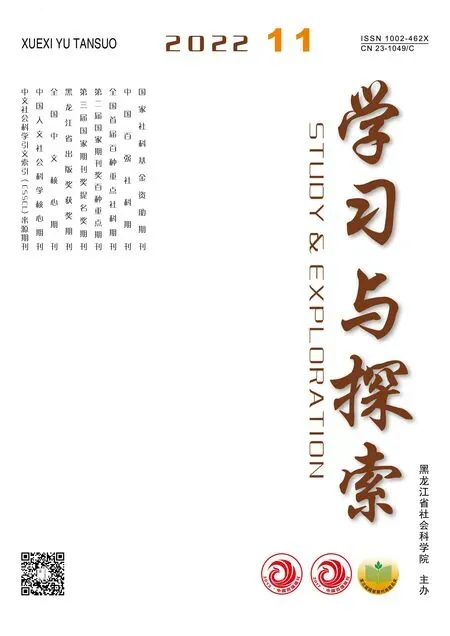李大釗文藝思想的基本要義與哲學根基
王 春 輝
(黑龍江大學 哲學學院,哈爾濱 150080)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李大釗作為革命先驅者與啟蒙思想家,其文藝思想無疑是重要的理論資源。李大釗文藝思想以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為旨歸,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后,開始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致力于以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探索十月革命的道路,呼吁民族自覺和民族解放。李大釗始終緊跟社會政治、現實問題、中國革命的步伐,“李大釗的思想發展過程,是和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的歷史過程相符合的,他的思想中的某些特點,正是這一歷史過程某些特點的具體而深刻的反映”[1]11。目前學界對于李大釗的民主思想、政治思想研究得較為深入,而對于李大釗的文藝思想研究相對零散,仍具有較大的闡釋空間。
李大釗文藝思想包含三部分,一是哲學思想,二是史學思想,三是文論思想。在《史學與哲學》的開篇,李大釗談及史學及文學與哲學的密切關系,強調三者之間的知識貫通性,“史學和哲學、文學的來源是相同的,都導源于古代的神話和傳說”,三者“同源而分流,可以共同幫助我們為人生的修養”[2]64。因此,本文試圖從哲學、史學、文論三個方面系統地梳理李大釗文藝思想的主要內容,在這一穩定的理論場域內,闡述李大釗哲學觀、唯物史觀、文論觀的基本要義。
一、李大釗文藝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大釗在《史學與哲學》一文中談道:“哲學仿佛是各種科學的宗邦,各種科學是逐漸由哲學分出來的獨立國。哲學的領域,雖然一天一天的狹小,而宗邦的權威仍在哲學。”[2]67由此可見,李大釗十分重視哲學所起到的引領與指導作用,這也奠定了李大釗哲學思想的核心地位。李大釗的哲學思想不是象牙塔式的抽象義理,而是從具體的社會現象與實際問題出發,以整體的、達觀的思路,分析問題的本質,給出科學合理的解釋。李大釗的哲學學說不為建立宏觀的理論體系,而是意圖啟發仍然以封建傳統觀念看待事物的民眾,讓人們能夠自覺地以客觀理性科學的態度去生活,以新的思想意識指導人們的生活方式。
1.唯物的自然觀與時間觀
李大釗認為自然是客觀的、發展著的,是能夠為人所認識的。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中,李大釗雖是討論在人類的歷史文化中,人們對于世界的認識往往來自于對某種學說的絕對信仰,但是仍能從論述中看出李大釗所秉持的自然觀,即他將自然視為真理,視為一種評判的標準。“吾人生于今日之知識世界,唯一自然之真理外,舉不足勞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倫理觀,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自然是事物發展的法則,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尊崇自然即是尊崇理性,李大釗認為人的倫理觀、道德觀皆應摒除舊的思想束縛,應該真正地認識自然規律,以理性客觀的精神建立倫理道德秩序。“吾人以為宇宙乃無始無終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實本體所生之一切現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機械的以漸次發生漸次進化。”[1]79唯物的自然觀明確物質的誕生與存在是在自然規律之中由社會群體所創造的,由此物質存在的本質、事物間的關系不再受到錯誤的落后觀念之蒙蔽,新的自然觀、世界觀得以建立,因此李大釗認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企于自然進化之程,少加以人為之力,冀其迅速蛻演,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1]80,可見唯物自然觀之重要。
時間觀在李大釗的哲學思想中居于根基性地位,如何認識時間是李大釗唯物主義哲學的根本問題。對時間意識的確認,一是為了堅持唯物主義哲學的客觀性,因為對于物質的正確認識,對于物質與意識兩者的辯證關系,對于唯物辯證法中聯系觀點、發展觀點、矛盾觀點的理解,都離不開客觀的時間觀念;二是通過樹立唯物的時間觀,形成正確的歷史觀、人生觀與世界觀。
李大釗從古語古字中考察人們記錄時間的方式及其歷史內涵,如《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中提出:“原人的‘秩序’‘恒久’的觀念,大概得自太陽的出沒和地球在太陽系中與其余諸星相保持的關系。云氣的變幻,日月的運轉,頗能與人以諧和、華麗、秩序、恒久的觀念。”[1]341再如,李大釗從《說文》《爾雅》等書中找出季、年、禾、期、歷等字的原義皆與禾田、年歲等含義有關,提出“中國以農立國,而周朝復以農開基;故以谷熟為年”[1]314。這表明,人們對表示時間的漢字的創造與書寫,正體現了對于時間所形成的自然心理和原始認知,形成了保留在人們集體無意識中的時間觀念。
李大釗為紀念晨報五周年著文《時》,主要討論的也是關于時間的觀念問題。首先,李大釗將歷史與事物的發展置于時間滾滾不停的洪流之中,認為歷史的興衰和人生的成敗皆是“時”的幻身游戲。在介紹唯物論時間觀之前,李大釗分別從玄學、心理學、數學、物理學、天文學方面闡述了時間在這些語境之中被闡釋的辯證玄思,在科學語境中對時間的認識偏于計算與統計,在研究意識、心理的語境中對時間的認識又限于相對和不定。李大釗意圖樹立的是關于時間的哲學認識,以此說明歷史的客觀流動性,肯定歷史的發展軌跡為“過去—現在—未來”,李大釗說道:“凡諸過去,悉納于今,有今為基,無限未來乃胎于此。”“過去未來,皆賴乎今,以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動力,今是行為,今是創作。”[1]486在《今》一文中,李大釗對時間范疇“現在”的哲學意義也做出了精準的界定:“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一掣現在的鈴,無限的過去未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1]94
李大釗以聯系的觀點看待時間,在連續的線性時間發展中,“現在”最富辯證性也最富創造性,對于此刻的人生,李大釗不僅號召大家竭力爭取,亦要牢牢把握,方法論即為,“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要拿出努力,謀未來的發展,善用今,努力為將來創造。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1]96“過去與將來,都是在那無始無終、永遠流轉的大自然在人生命上比較出來的程序,其實中間都有一個連續不斷的生命力。我們不能劃清過去與將來,截然為二。這中間不斷的關系就是我們人生的現在。”“我們要想實現自己的人生,應該把我們生命中過去與將來間的關系、時間全用在人生方面的活動。”[1]165
通過《時》《今》《現在與將來》等文章的思考,李大釗歸納出時間的兩個特性:異于空間的單一線性發展,即“時是有進無退的”;無論是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只可發生一次,即“時是一往不返的”,并相對應總結出幾種人生觀:面對時間的流動性,人們要杜絕徘徊躊躇,應邁往努進,“茍一剎那不有行為,不為動作,此一剎那的今即歸于烏有,此一剎那的生即等于喪失”[1]486;面對時間的一往不返,應珍惜當下,彼此互助團結友愛。
李大釗通過對時間的論證,既形成了完整、整體的歷史線條和時間運動的流淌軌跡,也確定了“當下”無可替代的作用——當下作為時間發展中的關鍵一環,為人類積極把握實踐創造了現實條件,充分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突出當下的歷史地位的同時,意在賦予人類平等的歷史地位,鼓舞人們拋開落后消極的歷史觀,努力奮進,樹立積極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李大釗吶喊道:“你不能旁觀,你不可回顧,因為你便是引線前進的主動。”“吾人是開辟道路的,是乘在這時的列車的機關車上,作他的主動力,向前邁進他的行程,增辟他的徑路的,不是籠著手,背著身,立在旁觀的地位,自處于時的動轉以外的。”[1]488可見,李大釗十分警惕對看待歷史的論調,對宣揚悲觀的、停滯的、主張逆退循環的歷史觀抱以痛斥的態度,堅持人的認識為螺旋式上升、不斷向前發展的客觀規律。
2.新與舊的矛盾觀
新與舊是李大釗牢牢扭住的一對相反相成的辯證概念,在許多批評時事的短文和政治性、學理性論文中,李大釗都習慣用新與舊的社會案例來表明觀點、批評時事。例如,李大釗認為對于阻礙社會發展的舊事物應不留余力地加以鏟除,提出“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余的東西,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1]117。而對于新事物,“人類的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擴張傳衍,流轉無窮,把那陳舊的組織、腐滯的機能一一的掃蕩摧清,別開一種新局面”[1]119。
在《新的!舊的!》一文中,李大釗將新與舊對立的辯證法運用于社會學觀察,從社會生活中的矛盾現象論述進化的法則,他提出宇宙的進化、歷史的更迭是憑借新與舊的運動來實現的,“這兩種精神活動的方向必須是代謝的,不是固定的,是合體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進化有益”[1]97。李大釗認為,在歷史發展的前進運動中,以新事物的誕生取代落后的舊事物,除舊納新、推陳出新是世界的進化法則,舊事物根深蒂固,新事物尚為萌芽,新與舊便呈現為矛盾對立的社會形態,阻撓事物的更新發展。正如李大釗所言:“矛盾的生活就是新舊不調和的生活,就是一個新的,一個舊的,湊到一處,分立對抗的生活。”[1]97李大釗以這種矛盾對立的方法看待社會生活中的諸種問題:如憲法、政治、法制習俗、社會生活等等。同樣,李大釗也提出了解決新事物力量薄弱的方法論:“鼓勵青年釋放創造力,打破矛盾生活,脫去二重負擔。”[1]100
在學理上,李大釗剖析了新舊兩種不同的歷史觀,道出舊歷史觀非科學落后的原因所在,以新的歷史觀將社會的進步與人的主動創造聯系起來。李大釗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談道:“舊歷史的方法與新歷史的方法絕對相反:一則尋社會情狀的原因于社會本身以外,把人當作一只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棄舟,漂流于茫茫無涯的荒海中,一則于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的推動力與指導力;一則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一則給人以奮發有為的人生觀。這全因為一則看社會上的一切活動與變遷全為天意所存,一則看社會上的一切活動和變遷全為人力所造,這種人類本身具有的動力可以在人類的需要中和那賴以滿足需要的方法中認識出來。”[1]339新與舊的對立是李大釗認識社會矛盾分析社會問題的主要手段,兩者作為一對互為依存、互為對立的矛盾概念貫穿著李大釗哲學的始終,對新事物與舊事物本質的辨別形成了李大釗唯物辯證法的揚棄觀點。
3.辯證否定觀的揚棄思想
李大釗善于運用聯系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比如他提出“一人之未來,與人間全體之未來相照應,一事之朕兆,與世界全局之朕兆有關聯”[1]101。再如《庶民的勝利》中“一個人心的變動,是全世界人心變動的征兆。一個事件的發生,是世界風云發生的先兆”[1]111。聯系的觀點意味著歷史不是個別的單一的特例,而是普遍心理表現的記錄。
李大釗還運用聯系的觀點看道德觀建立的問題,《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開宗明義提出:道德是什么?道德的內容是永久不變的還是常常變化的?道德有沒有新舊?道德與物質的關系是什么?李大釗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馬克思的辯證法來解決這幾些問題。指出道德是有動物的基礎之社會的本能,道德因時因地而變動,道德有新舊的問題發生,新道德的發生就是社會的本能的變化,物質開新,道德必跟著開新。今日需要的道德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實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創造的道德[1]273。可見,李大釗視新道德的建立為一個聯系的發展的辯證過程。
辯證法的否定觀點提供了揚棄的方法論,李大釗在多篇文章中都運用了辯證的思維方式,如提出天運人生周行不息,盈虛消長,相反相成,再如在《“晨鐘”之使命》一文中提出:“際茲方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吾以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環無已,生者不能無死,毀者必有所成,健壯之前有衰頹,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誕生,固常在累累墳墓之中也”[1]58。李大釗視事物的發展為循環更新的鏈條,從衰頹之中能見新生,在廢墟之中能見新事物的崛起,在衰老之中能見青春,在否定之中亦見事物的更新。
李大釗提出的青春之中國,體現的就是唯物辯證法的揚棄精神,以及事物自身所蘊含的更新與變革力量。“蓋嘗聞之,生命者,死與再生之連續也。今后人類之問題,民族之問題,非茍生殘存之問題,乃復活更生、回春再造之問題也。”[1]71在揚棄的過程中,事物否定自己,衰敗的必將被新生的所取代。正如“新興之國族與陳腐之國族遇,陳腐者必敗;朝氣橫溢之生命力與死灰沉滯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滯者必敗;青春之國民與白首之國民遇,白首者必敗,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1]70,而脫胎于舊事物中的新生命只是事物發展間的一環,新事物亦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變為需要裂變更新的舊事物,歷史便在無限更新無限循環的辯證否定之中得以發展。
五四時期的思想先驅皆重視青年對新中華崛起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大釗視青年為青春中華的建設者,青年亦要以辯證否定的揚棄精神磨練自己錘煉意志。在《今》一文中,李大釗認為青年唯一的責任,就是“從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實則歷史的現象,時時流轉,時時變易,同時還遺留永遠不滅的現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間,如何能殺得?所謂殺者,不過使今日的我不仍舊沉滯于昨天的我”。勉勵青年不沉溺于歷史的負累,秉持創新與揚棄之精神。
二、李大釗文藝思想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李大釗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很受海格爾的辯證法的影響,就是歷史觀是從哲學思想來的證明”[2]68。李大釗的現代史學研究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基礎上的,通過認識當下把握歷史的發展趨勢,認識歷史的本質,與舊歷史觀作對比,認清社會歷史的根本問題。自1920年起,李大釗開始在北京大學開設“唯物史觀研究”“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史學要論”“史學思想史”等課程。對馬克思主義經濟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革命、歷史哲學等問題做了學理性和系統性的深入研究,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將《共產黨宣言》與《資本論》結合起來,既蘊含經濟觀點,也容納革命的實踐經驗。
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李大釗談道:“唯物史觀也稱歷史的唯物主義。”這篇文章主要圍繞馬克思主義經濟論,比較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學(個人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與人道主義經濟學”,介紹“唯物史觀”“階級競爭說”以及經濟論中的“余工余值說”“資本集中說”,得出“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1]194。
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李大釗強調社會的進步也基于人類的感情,與社會進步基于生產程序的變動一說并不發生沖突。因為“除了需要的意識和滿足需要的愉快,再沒有感情,而生產程序之所以立,那是為滿足構成人類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識與滿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聯環中的不同步數罷了”[1]339。由此可見,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觀不是機械的死板的學說,而是結合了主觀與客觀、物質與精神的靈肉一體、物心兩面的科學理論。
在李大釗所倡導的歷史觀之前,存在兩種歷史觀形態:一是宗于神道天命,二是依托于神德者,這兩種都形成于道德教化之下沒有科學的歷史法則的認識。
李大釗將西方自康德已降的歷史法則總結為四大類: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與進步的歷史觀,個人的歷史觀與社會的歷史觀,精神的歷史觀與物質的歷史觀,神教的歷史觀與人生的歷史觀[2]3。第一種是價值本位,后三種則以歷史發展的動因為準繩。李大釗推演和總結各個歷史觀,得出了“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歷史觀可以稱為新史觀”[2]4的結論。新史觀主張以新史料、新智識重作歷史,樹立新的史學標準,以抗辯舊的史觀。故《史觀》中認為:“故歷史觀者,實為人生的準據,欲得一正確的人生觀,必先得一正確的歷史觀。”[2]1李大釗認為歷史是社會的時間的性象,亦是人類共同心理表現的記錄。人們賴以生存的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縱觀即為歷史,橫觀則為社會哲學。歷史不是陳編,而是“活潑潑的有生命的歷史”,是與社會“同質而異觀的歷史”[2]1。歷史的重要性在于:一切史的知識、史學研究、史的記錄,都要統攝在歷史觀之下。
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中,李大釗指出:“從前把歷史認作只是過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內容亦只解作憲法的和外交的關系。這種歷史觀,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窺其全體。人類的歷史乃是人在社會上的歷史,亦就是人類的社會生活史。”[2]25李大釗認為歷史學的研究應獨立在政治學或其他學科之外,在分科及界定歷史學的概念時,李大釗作以明確清晰的劃分,各個文化科學皆含有自身的組織學與歷史學,各種文化內容應獨立且形成自身的學科規范,而非受其他學科的隸屬和支配。“不得以一種組織學概組織學的全般,也不得以一種歷史學概歷史學的全般。”[2]22普遍的歷史學與各個學科的歷史學之間的關系不是歷史學的全部,離開了各個特殊的歷史學,也無法形成抽象的、整體的歷史學,兩者之間是普遍與特殊的關系。應該說,李大釗對學科的內部組織與學科間獨立性的認知,是科學的也是前衛的。
李大釗在《史學與哲學》中強調史學可以分為記述歷史與歷史理論兩個部分,記述歷史的目的在于收集歷史事實加以描寫,而歷史理論則是科學地考察零碎事實間的因果關系[2]66。在《史學要論》中李大釗更加細致地劃分出記述的歷史可以分為個人史(即傳記)、氏族史、社團史、國民史、民族史、人類史六大部分。歷史理論可以分為個人經歷論(即比較傳記學)、氏族經歷論、社團經歷論、國民經歷論、民族經歷論、人類經歷論六大部分。
唯物史觀以客觀物質的眼光探尋人類歷史、思想、社會生活變遷的根本原因,認為經濟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條件。強調人要在變化的、發展中的辯證法思維中看待事物更迭、認識事物的本質。在《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一文中,李大釗介紹了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理論,將帶有歷史意義的社會比喻為建筑,認為社會是由基礎(Basis)與上層(Uberbau)共同構成。“基礎是經濟的構造,即經濟關系,馬氏稱之為物質的或人類的社會的存在。上層是法制、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等,馬氏稱之為觀念的形態,或人類的意識。上層的變革,全靠經濟基礎的變動,故歷史非從經濟關系上說明不可。這是馬氏歷史觀的大體。”[1]293這種客觀理性地看待社會進程與歷史發展的學說,令歷史學研究帶有科學精神,從此歷史學從為英雄作傳轉向了科學研究。
唯物史觀的史學價值、人生觀意義重大,“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那個偉人圣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予我們,將來的歷史亦還是如此,現在已是我們世界的平民的時代了”[1]340。我們應該“應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1]340。“斯時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時時變動而且時時變動的原因”,這些變動都是“新知識施于實用的結果,就是由象他自己一樣的普通人所創造的新發明新發見的結果,這種觀念給了很多的希望與勇氣在他的身上”。“一切進步只能由聯合以圖進步的人民造成。”這種唯物史觀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就是將人從被動的被壓迫被否定的歷史地位、社會處境轉變為了自覺的、主動的生存處境,“這個觀念可以把他造成一個屬于他自己的人,他才昂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滿足而能于社會有用”[1]338。
李大釗在《研究歷史的任務》一文中重點研究了歷史的抽象意義,他通過反觀歷史本身的本體性質,區別了歷史材料與歷史本體,提出古籍史書的記錄并不是歷史的代名詞,而只是作為研究歷史的材料,明確了“歷史是整個的、有生命的、活動的、進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歷史學雖是發源于記錄,而記錄決不是歷史”[1]479。而歷史的這種生命性不是任意發展的,而是以經濟作基礎,隨著新的經濟關系的發生,人類生活也隨之“跟從新建筑”[1]480。
李大釗還吸取希臘歷史學家希羅陀德的觀點,提出歷史學家的兩大任務是:“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這種科學認識不僅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在今天對文學史整理工作、文學研究、歷史學研究也具有深刻的啟發性。正如李大釗所言:“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確的事實;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也就是說在進入歷史時,要充分的發揮后人的主動性,不怕改作重做,而是要堅定今人客觀的立場,秉持新的歷史觀念,揭開歷史的迷霧、遮蔽與謬誤之處,“推翻古人的前案,把那些舊材料舊紀錄,統通召集在新的知識面前,作一個判決書”[1]483。李大釗堅信歷史不是僵死的、一成不變的,以聯系發展的眼光來看,人們對于真理的認識也是發展著的,因此,李大釗才指出:“真理的見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較的。”[1]483
三、李大釗文藝思想中的文論觀
李大釗文藝思想的流露往往是伴隨著他的哲學思辨而展開的。因此,他的文論觀既不是鋪述式的,也不是曖昧含混的隱喻式的,而是凝練思想濃縮精華,在嚴密的邏輯與論點的輸出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方法,直抵事物本質,“以期獲得一種哲學的明慧,去照徹人生經過的道路”[1]505,以科學客觀的精神追尋真理,以求為后人做出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基礎。李大釗的這種治學態度受到其人生觀的影響:如果“你一旁觀,你一回顧,便誤了你在那一剎那在此不準退只準進、不準停只準行的大自然大實在中的進程,便遺在后面作了時代的落伍者”[1]487。李大釗認為人應該跟上歷史的腳步,以自己發展、變換的認知與智慧,開拓時代的疆土,盡好自己作為歷史發展中的一環的職責與義務。
在以往對李大釗文藝思想的研究中,《文豪》《什么是新文學》是必會提及的作品。《什么是新文學》無疑是李大釗文藝思想的核心,篇幅雖短,卻道出了新文學的本質內涵。李大釗認為新文學的本質在于為社會寫實、以博愛心為基礎、為文學而創作,單從文學語言或內容題材上進行的創新算不得具有新事物意義的文學。文學應該飽含真愛真美,尤其要以“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1]277為指導,以此培育新文學新運動的根基。《文豪》所談的是文學家的社會使命與責任擔當,也就是通過文學的感化力量凈化人心,將世間凄苦以藝術渲染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文學中傾注文學家的世界觀、同情心、悲憫與懺悔精神,讀之使人的心靈受到洗滌與凈化,直感“作者已先我而淋漓痛切出之”[3]70, “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運之中”[3]68。李大釗的《文豪》將文學的功用分析得鞭辟入里,文學模仿現實并加以渲染,在敏銳地觀察社會現象之后,發揮文學的感化功用,“以全副血淚,傾注墨池,啟發眾生之天良,覺醒眾生之懺悔,昭示人心來復之機,方能救人救世”[3]71。
如果說《文豪》《什么是新文學》是從理論層面論及文學的本質,那么《現代史學的研究及于人生態度的影響》與《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二文則體現了李大釗對于理論的實踐,是他將所吸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在文史學科研究的典型例子。李大釗將唯物史觀抽象的理論細化進中國的文史哲研究之中,不僅是學理上的緊密結合與生動應用,同時也體現出李大釗鮮明的文藝思想和治學態度。
《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是李大釗在北大授課時的講義,文章以詞源的形式考究了從原始社會起,人們對于時間的計算和表現方式,原始社會的經濟組織形態的變遷以及貨幣流通方式等問題。李大釗意在透過原始社會的文字書契之演變,以象形解意的方式,客觀地認識原始社會的經濟、社會倫理秩序等問題。“從文字語言上考察古代社會生活的遺跡”,繼而“考察當代社會生活的背景實在當代社會的經濟情狀”[1]355。借用中國遠古時期的神話傳說、《詩經》《說文》等經典著說、古文字、西學的歷史事例與學理界說等知識,梳理原始社會的基本形態及其演變過程,以文化風貌觀察民族的存在方式。在文章中,李大釗拋開了神秘主義的宗教闡釋方法,闡述傳統積習、宗教學說、圖騰起源等遮蔽在歷史深處的文化問題,將研究視角鎖定在原始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客觀的文字字形作為打開關竅的鑰匙,在說明文字的象形意義之時,道出建立在此經濟基礎之上的原人的社會意識。可以說,《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是李大釗對唯物主義哲學、唯物史觀的一場具體的文化實踐。
在文章中,李大釗首先明確的是象形文字的客觀性和物質性。李大釗不僅列舉了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同時也指出蘇格蘭、墨西哥、埃及等古跡上也存有象形文字,以說明“上古時文字都象形”[1]342。諸如伏羲畫卦始得記號文字、神農時代的結繩記事、埃及以椰樹樹葉表年數等實例,證明象形文字是上古時代人們生活的真實記錄,是人們生活的產物。可見,文字書契以象形的方式將生活形態凝練進文字表現之中,承載著事物存在的意義,是原始文化與經濟構成的一種客觀反映。正是文字的這一屬性,帶動了李大釗全篇的唯物分析。
李大釗指出,“人類最初的家庭是森林,后來遇見了一個冰期,變更了氣候,人類遂轉徙河岸海濱去”。生存環境的變更帶來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樣貌,遷徙的過程即人類原始文明的演進過程。李大釗考究了農耕文明、石器時代、“鉆燧改火”三種由物質生存方式而決定的紀年方式,以及受物質存在影響的、帶有鮮明印記的觀念意識,比如以農立國的中國以谷熟為年,季、期等字皆與稼穡、禾熟、年歲等寓意有關,因為重“黃色”,稱始祖為黃帝。再如“古代有鉆燧改火為歷歲一周的記號習慣”,將精于用火者奉為君主等。從中可見,李大釗對象形文字、遠古文明的認識帶有唯物史觀的鮮明烙印,強調物質存在對意識形態的決定作用。
其次,李大釗從經濟形態上來論述原人社會的唯物反映,古代以貝為貨幣,貝部文字多為經濟用語,亦有用石或骨仿造貝形用為貨幣。李大釗同樣通過《尚書》《詩經》等古籍的文字記載,推斷各個時期的貨幣流通方式。所強調的依舊是物質生活對意識觀念的決定作用,并將這種影響留存于文字形式上。
最后,李大釗還考究了圖騰的歷史由來,以及“感生說”背后的生理原因,更是以女子的婚娶為例,從“婦、娶、婚、嫁”等字中得出“男子在經濟上占了優越地位以后”女性地位所發生的變化。李大釗意在破除人們對于傳統所抱有的思維定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
此文的意義在于以科學、客觀的學理方法分析歷史,以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史觀治學,并運用大量人類學、考古學知識與實例論證文化的演變進程,形成客觀的科學的文化觀、歷史觀。李大釗的這一文論觀點在他的人文研究中是一種根本思路,在《研究歷史的任務》一文中,李大釗特別強調:今天的史學研究“必把這些神話一概刪除。特別注重考察他們當時社會的背景與他們的哲學思想有若何關系等問題”[1]484。李大釗通過吸收理解唯物史觀,將其應用到人文學科的研究當中,注重的便是物質與意識之間的相互關系,重視產生文化的社會背景與經濟基礎。在20世紀初的時代背景中,這種文論觀念是超前的也是科學的客觀的,具有理性精神的。
《現代史學的研究及于人生態度的影響》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在史學研究上的應用,體現了李大釗看待歷史、人生、時間三者之間關系的態度。《現代史學的研究及于人生態度的影響》同《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樣,是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找尋并列出實例,總結理法,破除偏信與誤讀,揭示文化研究、文學研究、史學研究中的真理性認識,啟發新智,是真理性認識與實踐的結合,體現了李大釗嚴謹求真的治學態度。在此文中,李大釗反對將文學創作中的想象、美化、虛構等“空筆”的手法運用到歷史書寫中去,這樣會導致對歷史真實的實在性認識不清,“本求邁遠騰高,結局反困蹶于空虛的境界,而不能于實地進行一步”[1]505。李大釗主張對待歷史的態度應是嚴肅認真的,將歷史作成哲學的樣子,以老成的科學的精神不斷進行訓練,給人以覺醒和啟發。
李大釗認為對待歷史、對待時間的態度在認識論意義上深刻地影響著人們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現代史學給予人們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態度方能塑造腳踏實地的人生觀[1]506。面對歷史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進路,人們應形成進步的世界觀,了解歷史的進程源源不斷向前發展,歷史由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歷史規律,人們自然就會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創造生活,發現自己、認識自我,這正是李大釗所揭示的唯物史觀對人生態度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結 語
在李大釗的文藝思想中,哲學、史學與文學這三種思想似三條河流,最后匯入“人生修養”的總體層面。也就是說,李大釗的文藝思想是為了塑造現代人的理想人格,實現趨于至善的人生修養。其中,文學可以啟發民族的社會的情感,哲學可以令人達觀對事物形成整體的本質認識,而歷史既能激發人的民族情懷,同時也能提高洞察世事的能力。也就是李大釗所說的:“史學教我們踏實審慎,文學教我們發揚蹈厲。”[2]71
李大釗在《“晨鐘”之使命》中勉勵自己:“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后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1]61李大釗呼吁以博愛的互助精神打破舊事物舊文化的束縛,打破人與人之間孤獨的生存狀態。正如《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中所言:“縱的組織的基礎在力,橫的組織的基礎在愛。我們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間一切關系都脫去力的關系,而純為愛的關系,使人間一切生活全不是爭的生活,而純是愛的生活。”[1]304這不僅是李大釗治學的理想目標,亦是他用生命來踐行的崇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