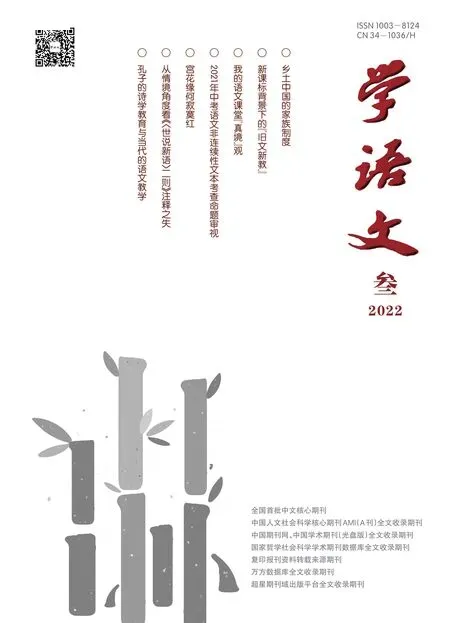從情境角度看《〈世說新語〉二則》注釋之失
□ 陳明潔
本文擬對統(tǒng)編語文教材七年級上冊課文《〈世說新語〉二則》(以下簡稱“《世說》”)中兩條注釋提出商榷。
一、“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因”
《世說》第一則文本《詠雪》中,“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因”,教材注釋為:“〔因風〕乘風。因,趁、乘。”在自然界生物中,柳樹花謝結(jié)實后,種子上帶有白色絨毛,隨風飄散形似綿絮,“柳絮”之名由此而來。但柳絮并非動物,其本身并不具有“起”這一飛揚于空中的行為能力,又怎么能主動“趁”或“乘”風來的時機翩翩“起”舞呢?
作為古漢語介詞的“因”,譯釋為“趁”或“乘”,是表示主體的動作行為利用一定的時機進行,古書中用例極為多見,如:
譯:晉軍趁他們極端恐懼而進攻曹國。
譯:吳子想乘楚國喪事的機會攻打它。
譯:不如趁此(天亡楚)機會消滅它。
譯:趁他們沒有防備,突然襲擊他們。
以上例子中“因”組成的介賓短語,用于動詞之前,而動作的主體皆是人,因而能發(fā)出“攻”“伐”“取”“擊”等行為。類似用法,在《世說新語》中也不乏其例,如:
譯:殷覬曾趁行散(服五石散后需散步)之機,迅速離開宅舍,就沒有再回來。
譯:謝安趁著子侄們聚會在一起時,問道:“《毛詩》里哪一句最好?”
譯:王君夫(愷)曾經(jīng)處罰一個不穿內(nèi)衣的人,趁此人值班時,將其關(guān)進深宮內(nèi)室里,不許別人把他帶出去。
譯:桓玄將要篡奪帝位,桓修想趁桓玄在桓修母親那里時襲擊他。
可見,當介詞“因”表示利用某一時機而主體發(fā)出動作行為的情境下,主體必定是具有自主實施動作行為的人或其他動物。由此反觀柳絮的“因風”,并不是主動趁著風來的機會而“起”,而是在風力的裹挾下被動飄飛,聽憑風勢的擺布而完全無自主能力。因而,“因風”并不等于帶有主動行為能力的“乘風”,不宜注釋為“趁”或“乘”。
古漢語中,與介詞“因”譯釋為“趁”或“乘”不同的另一種用法,是由介詞“因”組成的介賓短語用于動詞之前,表示動作行為發(fā)生或出現(xiàn)所憑借、依賴的條件,“柳絮因風起”當屬于這種用法。在這種用法中,主體既可以是有自主行為能力的人或其他動物,也可以是無自主行為能力的生物或其他物體。主體有自主行為能力的用例比較多見,如:
譯:從前夏朝剛衰落時,后羿從鉏地遷到窮石,依靠夏朝的百姓取代了夏朝政權(quán)。
譯:你輩平庸無能,正所謂是依賴別人而坐享其成的人。
譯:商人們憑借他們雄厚的財富,交往勾結(jié)權(quán)貴王侯。
譯:益州關(guān)塞險要,田野肥沃綿延千里,是物產(chǎn)豐饒的天府之地,漢高祖憑借這些條件建立了帝業(yè)。
正是介詞“因”用于動作行為所憑借、依賴的條件,故可譯釋為“憑借”“依靠”“依賴”等。在這種用法中,主體無自主行為能力的用例較為少見,如:
譯:生姜、菌桂依賴土地而生長,不依賴土地而獲得辛辣之味;女子依賴媒妁之言而嫁人,不依賴媒妁之言而與丈夫關(guān)系親密。
沖飆發(fā)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晉張協(xié)《七命》)唐李周翰注:“沖飆,急風也。此急風忽發(fā),故能回日光使卻行也。礫石此風而起,激拂于天。”(《六臣注文選》卷三十五)
譯釋:李周翰注“沖飆”為迅猛之“急風”,故釋“飛礫”為“礫石因此風而起”。此句可譯為:砂石憑借迅猛的急風飛向天空。
從以上前一例可見,第一個分句中的介賓短語“因地”,是表示依賴土地或憑借土地之意,生姜、菌桂類植物若離開了賴以生長的土地,是不可能長成的;但由其種性所決定長成后具有的辛辣之味,卻并不依賴于土地;第二個分句中的介賓短語“因媒”,同樣也表示“依賴”之意,雖然主語“婦人”具有自主行為能力,但古代社會受陳舊的習俗和觀念所制約,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等同于無自主行為能力,一般只能依從所謂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上后一例的注語中,“礫石因此風而起”的“因此風”也是介詞結(jié)構(gòu),動作行為“起”的主體是“礫石”,其能夠“起而灑天”的條件,無疑就是憑借“沖飆”即迅猛的急風,否則不可能飛向天空而“激拂于天”。很顯然,“礫石因此風而起”與“柳絮因風起”在句法結(jié)構(gòu)上可稱完全一致(前者多了連詞“而”,連接介詞結(jié)構(gòu)充當?shù)臓钫Z和動詞中心語,在古漢語中也是常見的語法現(xiàn)象,正如后者也可說成“柳絮因風而起”),兩者的主體“礫石”和“柳絮”都是無自主行為能力的事物,在各自的文本情境中若釋讀為“趁”或“乘”,變主體為能自行抓住時機發(fā)出動作行為的物體,是有悖大自然常情的。
綜上所述,“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因”,以譯釋為“憑借”方合乎文本情境。商務(wù)印書館1993年出版張萬起先生所編《世說新語詞典》,在詞目“因”字條下所列第一義項即為“憑借”,所舉例證正是“未若柳絮因風起”。
二、“友人慚,下車引之”之“引”
《世說》第二則文本《陳太丘與友期行》中,“下車引之”的“引”,教材注為“〔引〕拉,牽拉。”舉凡當今出版的《世說新語》全本、選本以及注譯的專著,包括教材和各類圖書中的選文,對該文本中“下車引之”的“引”所作注釋和今譯,基本上都是“拉”。我們認為不合常情與事理。
“引”的詞義,由造字本義“拉弓,開弓”引申為“拉,牽拉”,是完全合乎事理邏輯的固有義項,也是古漢語較為多見的常用義之一。如:
譯:馬能夠負重拉車到達遠方的路途,靠的是筋骨有力。
譯:所謂無為,就是靜靜地不發(fā)聲也不行動,拉他他不來,推他他不去。
譯:侍從中有的要拉藺相如離開朝堂加以處治。
譯:王辯于是騎馬過河,到河中流,被溺水的人拉扯落馬。
以上各例中的“引”譯釋為“拉”,似乎不用再作詮解,在特定的情境下句子語意皆能使人了然,毫無窒礙。然而,比較對照本文的情境,面對七歲小孩的批評已生羞愧之心的來客,若謂下車去“拉”孩子,是為了表示好感、友好或歉意,這在社會人際交往的情境中,因缺乏必要的前提條件而顯得很不真實。
我們的解讀是:來客已知所約出行對象(陳太丘)已先行離去,又面對七歲小孩對自己“無信”“無禮”的批評,自知理虧而感到羞愧,為擺脫在友人的孩子面前陷于尷尬的境地,消彌先前自己理虧給孩子帶來的負面印象,意欲營造一種大人與小孩之間表面上親昵融洽的氣氛,“下車引之”的行為是為了緩和氣氛并轉(zhuǎn)移話題,這里的“引”似應(yīng)理解為對小孩的“逗引”或“引逗”,才是文本情境下最有可能出現(xiàn)的一種行為現(xiàn)象。
“引”釋為“逗引”或“引逗”,主要存在于古今漢語的方言口語中,吳語、粵語及客家話等都有此語詞,尤以吳語中用得最多,如“引小囡”“引小人”“引老小”等(見《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1999年版)。書面語記錄“引”的這一義項出現(xiàn)得比較晚,所見始于唐五代的詩歌作品中,如:
譯:年方十六歲的少女長久地幽閉在閨房里,喜愛逗引小狗和鸚鵡嬉戲。
譯:把繡成的屏風安放在春天的花園里,竟引逗得黃鶯從柳樹枝條上飛下來(欲飛向屏風上所繡的花樹之中)。
譯:風忽然驟起,吹皺了春天池塘的水面。閑來在花間小路上逗引鴛鴦,手里揉搓著紅杏花蕊。
到了元明兩代,因“引”和“逗”同義而連用,則多見于戲曲作品中(也寫作“斗引”,“斗”通“逗”),如:
以上例子因語意淺白,無須今譯便能看出其“逗引”或“引逗”與現(xiàn)代漢語的意義相同。
雖然在南北朝時期,其他古書中尚未見“引”表示“逗引”之義,但唐代詩歌中出現(xiàn)此義,當不會突如其來,唐代以前最初存在于方言口語中,書面語偶有用例,可能性是很大的。南北朝時酈道元所作《水經(jīng)注》,就曾有“逗引”同義連用:
譯:又用石塊砌了一條彎曲的暗溝,導引大池中的水到住宅北面,造了個小魚池,小魚池長七十步,寬二十步。
此例的“逗引”盡管表達的是“導引”之義,但“引”和“逗”具有同義關(guān)系,卻由此可以確定在南北朝時即已形成。故在《陳太丘與友期行》中,出現(xiàn)“引”為逗小孩的“逗引”之義,是完全有可能的語言事實。
對本例“下車引之”句“引”的詞義,早在1931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由崔朝慶選注的《世說新語》(收入《萬有文庫》第一集)中,即已作出正確注釋:“引,逗引,大人對小兒示愛撫也。”(按:此前1928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該作者選注此書,尚注為“相牽曰引”,可見系后來糾正改注。)1989年出版的《漢語大詞典》第4 卷,對“引”的這一義項也有明確昭示,該卷第89頁“引”字條第○14個義項為:“逗引;誘引;吸引”,列出的三條書證對應(yīng)這三個釋義,第一條書證即:“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方正》:‘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這也是迄今為止的所有漢語辭書中,對“引”字義項難得一見的補苴罅漏,反映了編者對《世說新語》該詞詮釋的獨到眼光。此釋義雖屬少數(shù),但在文本情境的觀照下,其合理性卻不可忽視,足以供語文教學和教材修訂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