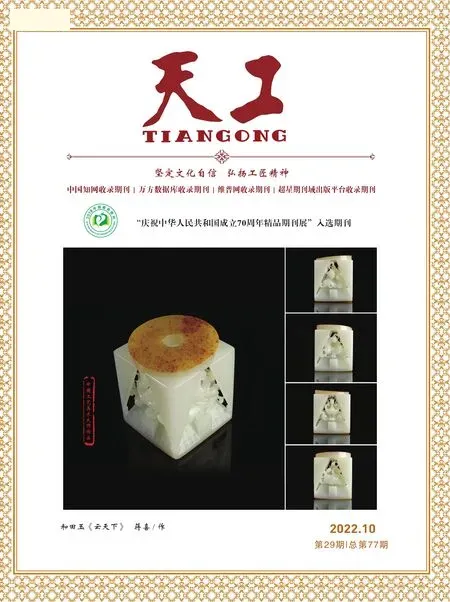論述漢代漆器器物造型的演變
李洪杰 天津美術學院
器物文化是物質文化,也是生活方式的文化,器物不是單純的物質,器物中蘊藏著與之相關的制度、心理和文化等的時代特性。器物造型是手工藝術創作中的重要一環,它作為較為“親民”的藝術形式,是一個民族乃至國家的審美體現。我們從器物上能看出擁有者的身份、階級,其也能反映出時代的生活美學,能體現一個地域甚至一個國家的審美標準。研究中國器物造型發展鼎盛的漢代,能為當下新時代的器物造型藝術提供更多的思考方式和審美經驗,為器物文化的傳承,為其當代化的發展提供借鑒。
一、器物造型的產生演變
器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數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原始先民根據生活的需要對各種石器和木制、骨制器進行加工,進而生發出器物的形態,并逐漸形成造型的觀念,通過手工的改造,得到了一個實體的物件,其過程是心與物的聯結。
中國古代器物造型的涵蓋范圍很廣,媒材介入豐富。從幾千年的發展脈絡中,不難看出其有較為明顯的階段特征。原始社會,人們注重器物的實用價值,受工藝技術及材料的限制,“輕藝重用”是原始社會器物造型的基本風貌。在夏、商、西周時期,青銅器作為禮器被大量創作生產,大量器物的造型與紋樣相輔相成,中國器物造型邁向了新的高度,青銅器物是中國美學領域重要的審美經驗,是奴隸制時代的藝術巔峰。春秋戰國時期的漆器,器物造型與彩繪合二為一,雖有延續青銅器的樣式,但也是時代美學下的器物造型階段性的體現。到了秦漢大一統后,社會政治制度確立,經濟繁榮,科學技術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從秦末漢初開始,漆器登上了器物造型的歷史主舞臺。漢代的漆器種類豐富,工藝精美,造型變化百出,是中國器物造型的早期典范。此后朝代的瓷器、玉器等更是為器物造型注入了豐富的器物造型元素。宋元以后,宮廷器物的審美價值與實用價值幾乎受到同等重視,器物造型的審美也被推到了新的高度。筆者選取漢代的漆器器物造型為研究對象,研究漢代的文化語境、政治形態、科技材料、宗教禮儀等方面對器物造型發展演變的影響。
二、漢代器物造型藝術——漆器不同時期的表現
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漢代國力鼎盛,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繁榮、文化的豐富令手工藝術發展欣欣向榮。在兩漢手工藝的發展中,漢武帝時代(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最突出。中國開始以文明、富強的大國著稱于世,手工藝術也空前發達,器物造型被推上了新的高度。
(一)漢初
漢初的美學思想以黃老的“簡約無為”作為中心。鑒于秦王朝亡國的歷史經驗教訓,漢代初期的地主統治階級實行與民休息的黃老政策,以鞏固統治地位。因此,漢初占統治地位的乃是道家哲學美學思想,兼及儒學等其他美學思想,作為鞏固封建統治制度與教化萬民的精神工具。于是,“簡約無為”成為漢初美學創作的時代語境,這對當時的文藝創作產生極大影響,在這個時期,漆器以木胎居多,夾纻胎數量有限,紋樣裝飾簡約,金銀箔貼在漆器中更少見。這種文化語境也為漢初手工業在秦代的廢墟上慢慢復蘇指明了方向。對于漢代器物造型特點突出的漆器而言,“簡易”是它的造物原則與生命。在器物的功能上也實現了質的飛躍——從先秦的神權走向現實生活,也反映出從青銅器物到漆器的歷史性進化原則:“用進廢退。”功能至上是漢初漆器的首要選擇,這是國家實施黃老哲學美學思想的使然,也是工藝健康發展的結果。
科技材料的發展進步,推動了漆器的進步。漢初社會完成了由春秋戰國青銅時代逐漸向鐵器時代的重大轉型,為手工藝的復出提供了物質準備與技術支撐。與此同時,隨著不斷發展的商業與城市,作為生活器皿的漆器需要大量天然漆,因此,漆樹成為主要的農業經濟作物之一。漆樹的大量種植為漆器設計與創造提供材料資源,加之鐵器技術的發達,漆器的加工技術也相應提高,因此,漢初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為包括漆器在內的手工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與技術的保障。漢初的經濟改革促使漢代的冶鐵業、農業、造船業、造紙等行業興盛。冶鐵業的發達使工具設計、陶鑄設計等手工業發生重大技術變革,由于技術的發達,“造物”成為漢代官府與民間的普遍概念與行為,更是為器物造型提供了技術和材料支撐。
政治結構形態的轉變,使得器物造型的時代性有所顯現。漢初社會完成了先秦以來的共主式聯盟制向中央集權制的重大轉型。這一轉型為包括漆藝在內的手工藝提供了堅實的社會政治保障。秦代集權政治就有力地促進了文化、經濟與社會共同體的形成,同時也為漢初乃至后世的工藝規范、統一與標準奠定了堅實的美學思想基礎,更為重要的是統一的中央政權的建立,在思想上為包括漆器在內的手工業提供了美學理論支撐與發展范式,進而推動了反映神權思想的青銅器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作為實用器的漆器應運而生。
總之,漢初社會的“大一統”政治思想、“為民”的科技變革與“簡約”的文化語境對包括漆器在內的器物造型發展產生深刻影響。漢初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轉型,為器物造型的創新與變革提供了廣闊的施展空間,漆器更是完善了自己的造物美學體系,也更好地為漢初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而服務。如果說器物造型是物質文化行為,那么,漢初的政治、文化、經濟則是這種物質文化行為復出的思想與動力保障。
(二)西漢中葉
此時期文化語境上,以董仲舒為首的儒學成為國家主流文化,文化的迭代使漢代藝術呈現一派繁榮景象,諸多領域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就,如畫像、漆藝、雕刻、繪畫、音樂等藝術都取得了長足進步。考古發現,西漢中后期,漆器、瓦當、畫像石與畫像磚之裝飾藝術開始流行。就手工業的器物造型而言,如果說西漢初期器物造型在“楚風遺韻”“秦制”“同制京師”的基礎上初步發展,西漢中期的漆器則進入了貴族化、宮廷化的自我發展與建構階段,真正形成了“深沉雄大”與“上下與天地同流”的漢代器物美學品格的建構時代。在這個時期,“天人感應”的儒教美學思想對當時包括漆器在內的器物造型活動產生極大影響,大量作品成為“頌神”與體現“天意”的載體。因此西漢中期的器物美學思想以“受命于天”為核心,以“法天象地”的“中和”之美為表現內容,形成了“明天命,見天功”的漆器創作發展思潮。于是,西漢中期的漆器“上下與天地同流”的造像原則、“崇文尚威”的創作風格以及“深沉雄大”的時代樂章,皆是“受命于天”的體現,可見當時的神學、美學對器物造型等審美創作產生的影響是何其深廣。
科學技術上,西漢中期冶鐵業進入第二次大發展時期,炒鋼技術的出現和百煉鋼工藝走向成熟使得產量和品質都有很大提高,冶鐵技術與炒鋼技術的進步無疑給漆器制造在工具上帶來技術革命。漆樹的栽種與收割技術日漸成熟,這為漆器的大量問世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保障。在宮廷化的生產創作條件下,漆器創作者的技藝越發精進,將貴族氣息與王室權力在藝術創作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政治結構上,西漢中葉,漢武帝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漢昭帝知時務之要,實行與民休息,于始元六年政府召開“鹽鐵會議”,收回鹽鐵罷酒榷。宣帝也是中興之主,在石渠閣召開盛大儒家經學會議,論“五經”同異,尤其是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為考工,手工業主要實行嚴格的國營政策,一定程度上使得手工業走向了規模化與大型化,為漆器進入鼎盛時期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西漢后期,東漢
西漢后期儒教神學、美學思想彌漫盛熾,尤其是西漢末年讖緯神學、美學思想幾乎籠罩西漢文化活動的天空。漢代漆藝經過西漢早期與中期的發展,此時進入了一個裝飾繁縟、千文華彩的鼎盛時期。在儒家神學、美學的影響下,一股裝飾之風使得漆藝走向“錯彩鏤金”與“黃口銀耳”之貴族之路,加之地方豪強地主的藝術思想,也使漢代漆藝走向神學、美學思想創作的歷史巔峰,漆器器物造型的輝煌也告一段落。
東漢時期,漢代儒教神學、美學思想盡管一直占統治地位,但也遭到了一些無神論者的批判。在此背景下,東漢漆藝經過了早期的短暫繁榮后,進入了一個追求宗教與世俗之美的歷史階段,宮廷漆藝開始下移,從表現“山神海靈”向“人物鞍馬”的唯物主義美學轉變。因此,受“致用為本”的漆藝美學思想的支配,漢代漆藝在遭遇青瓷器逐漸取代漆器之后,進入了歷史性的“另辟蹊徑”的新的發展時期,歷史的劃代再次顯現。
三、時代性對器物造型的影響
器物造型作為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一環,其時代性脈絡是對文化語境、科技材料、政治結構的映射,不同時期,在不同文化語境的影響下,呈現出獨特的面貌。
(一)文化語境對器物造型的塑造
儒學主導下的文化語境影響了幾千年的意識形態及文藝創作。文化語境對個體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對焦個體,每個個體的文化成長語境又是有所差異的。不同的文化語境塑造了不同的個體,匯聚成不同的時代。朱光潛在《談美》中列舉木商、植物學家、畫家三人同時感知古松,古松的形象隨觀者的性格、情趣而變化,而正是所處的文化語境的差異,使得三者的審美體驗有所不同,其創造性自然也有所差異。作為創作個體而言,去把握時代的文化語境脈絡,創作劃時代的作品,注重個人獨特文化語境下的個性化表達,是當代器物造型百花爭艷的重要因素。
(二)科技材料對器物造型的豐富
在器物造型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科技材料對其的影響是深遠的,漆器作為工藝復雜的手工藝術,材料天然大漆的提取供應是其長久發展的保障,更何況漆工藝之復雜,技術之精進,離不開科技材料的支撐。同時,從另一個角度也可看出,技術材料的發展,使得器物造型的更迭換代較為明顯。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青銅冶煉技術的發展使中國的青銅藝術出現了第一個高峰,青銅器物也開始以實用器物大量出現,以觚和爵為代表的青銅酒器繁榮發達,進而取代了陶器和玉器;西漢中后期,漆器制作工具的成熟和漆樹的大量種植,為漆器制作提供了豐富的原料,使得漆器可以批量生產,其以華美輕便的造型,淘汰了青銅器,大量實用漆器登上歷史舞臺;東漢,青瓷器物工藝的成熟使大量精美的瓷器應運而生,漆器的地位也被取代。可見,科技材料的發展會為器物造型的更迭提供動力。在當下科技材料極為豐盈的時代背景下,創作者也不應受限于此,而應激發對科技材料創新的動力,如3D 打印技術、數字化窯爐等,為器物造型的創新發展提供更多可能。同時,也要注意的一點是,器物造型觀念的體現與材料的運用要“表里如一”,不可盲目堆砌或炫技。
(三)社會政治背景決定著器物造型的方向
在大時代背景下,政治形態的轉變會對文藝創作“總路線”產生深遠的影響,甚至具有劃時代的顯現。歷代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繁榮的時代都會掀起文藝創作的高潮,器物造型的發展也會受社會及政治背景的影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之策,對藝術創作的影響是何其深遠。在當下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中,藝術發展與時俱進,展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體現出創作題材的多元化、材料的多元化,以及創作方式的多元化等,這與我們這個多元化、自由開放的時代背景是相一致的。這也為器物造型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基礎和靈感。隨著信息時代的不斷深入發展,人們思想的深度、廣度都在提升,手工藝術也在沉寂后開始受到越來越多人們的關注和喜愛。器物作為與人們生活較為接近的傳統藝術類別,應為人們帶去精神養分,弘揚社會的主旋律。
四、結語
在物質文化發達的今天,我們始終不能忘卻:“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時間上具有差異性,但在文化的共性上卻是一致的,都是物質文化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如何讓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共同為人類服務,是否明智地對待傳統、發揚傳統文化精神,這是衡量一個民族成熟與理性的標志。”這也是研究漢代器物造型,以為當代器物造型提供借鑒的意義所在。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與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精神需求日益提高。自媒體直播平臺的興起,極大程度上推動了藝術設計的普及化,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器物造型設計,對受眾的審美體驗影響深遠。面對市場化、普及化的需求,藝術創作者要將器物造型設計引領到時代新的高度,避俗重藝,通過自己的創作表達提高國民的審美體驗和生活品質。我們要把握時代藝術設計的脈絡,深刻體會文化語境的精神,積極利用和推動科技材料的發展,弘揚時代主旋律,繼承與發展,推陳與出新,走出一條屬于新時代手工藝人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