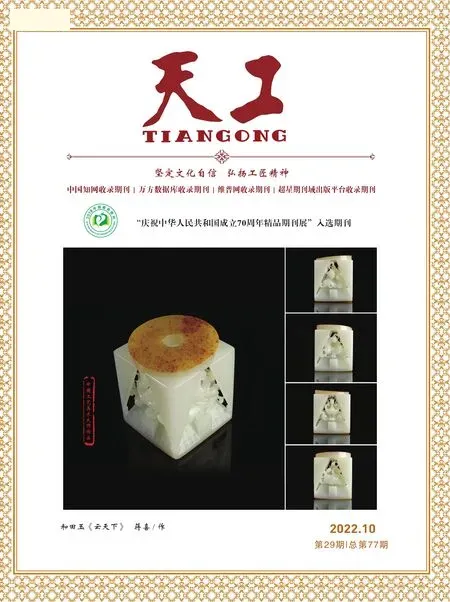生命的空間
——淺析中國陶器中的生命意象
吳昕煒 天津美術學院
一、生命意象
(一)“生”
“生”,《說文》:“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卜辭中“生”有三義:一為生長,這是本義;二為活義,如“生鹿”,即活鹿;另一義尚不明確。可見卜辭中“生”之義主要指生長以及用以形容生長的活潑狀態。《廣雅》:“生,出也。”《廣韻·庚韻》:“生,生長也。”《玉篇》:“生,產也,進也,起也,出也。”在古代漢語中,“生”之義主要與生命有關。從萬物生長過程來看,“生”不僅指出生,還指生長;從自然生命來看,“生”既指植物生命,又指動物和人的生命;從生命存在的狀態來看,“生”是相對于死而言的;從存在狀態而言,“生”是活潑的,而非僵硬的。陶器中的“生”,一指以“生”為內容,即以生命為表達對象,使用隱喻或擬象的手法表現有關生命的元素;二指以“生”為形式,形式上呈現生命或靈動或奔放等狀態;三指對“生”的追問,將內容與形式統一起來,抒發創作主體關于“生”之本源的感懷,向外的存在,或向內的探求。
(二)“意象”
“意象”一詞最早起源于《周易》,“意象”在中國首先屬于一個哲學概念。它不僅是古人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更是一種思維和手段。第一次運用“意象”這個詞的是南北朝時期的劉勰。劉勰之后,很多思想家、藝術家對“意象”進行研究,逐漸形成了中國傳統美學的意象說。《易傳·系辭傳》 中的“立象以盡意”也是中國傳統造物思想的核心。
(三)生命意象
本文中所探討的生命意象是藝術家在經過對客觀生命的感悟后營造出的生命的本原世界。它是一個格物致知、觸景生情的世界,它需要藝術家對生命進行體會,對生命發出感懷,發乎于情,把透過生命所體會到的慷慨悲歌或活潑優雅,化為一個審美世界,作為胸中之竹,經過一系列的物化手段,對其進行反復推敲以表情達意,化為手中之竹,將其凝結成一種永恒的藝術美。
二、生命意識的三個層次在陶器造型中的意象表現
所謂生命意識,是指人類對于自身生命所產生的一種自覺的理性探索和感性體驗。筆者在本篇論文中將生命意識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遠古先民在掙扎求生中所埋藏在潛意識深處的生殖與繁衍欲望;其次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從艱苦求生中掙脫出來,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自我存在的感知;最后是由于自我的覺醒所萌發的對不同生命狀態的追求,并在此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情感體驗與生命感悟。這三種狀態并不是此消彼長的,而是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相互交織的。
(一)生存與繁衍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義,文明在慘烈的生存斗爭中不斷演化,個體的肉體殞歿,而群體綿延的無限性可以超越個體生命的有限性,以保證群體的生存,生存深刻地埋藏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因此對繁衍的渴望也隱隱凝結成一種生殖崇拜,刺激著人類將基因傳承下去。
陶器的誕生與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原始人類的生存狀況。炊煮器對食物的熱加工極大地縮短了人類進食的時間,提高了營養的攝取率,保證了人類的生存。因此,陶器首先誕生于先民對生產、生活的實際需求,實用性是陶器的第一屬性。比如出土文物以及文獻記載中的汲水器、儲水器、儲存器、飲器、食器等大量的生活實用器物;而在陶器實用性的背后則隱含著對生命的觀照:陶器中大量的實用器極大地改善了先民的生活環境、飲食方式和飲食習慣,使先民逐漸由動物式生活轉向“人”的生活,由此可見,陶器的制作解決了中國古人的“生存困境”,也衍生出中國“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的文化傳統。其中,三足器的創造對原始先民而言是個偉大的進步。原始陶器的造型往往源于對自然的仿造,而三足器是自然界沒有的,我們的先民擺脫了對天然容器的模擬,開始進入“自主創物”的階段。磁山文化三足陶盂,被認為是最早的三足器。三足器隨后開始發展進化,出現了仿生三足器。龍山文化中有件鳥形白陶,通體仿鳥形,引頸昂首,尖喙,小圓耳,腹寬肥扁圓,底平,設三矮足,其造型憨態可掬又有著良好的實用性。因此,實用器形式本身就蘊含著對于生命的觀照。
其次,在實用性的基礎之上,陶瓷造型也追求實用性與某種精神性相結合。
就像三足器物的設計似乎不僅僅為了生活日用,同時也承載著作為禮器的重要作用。三足器之所以成為祭祀用器,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三足”并非直接來源于對自然的模仿,而是人們在造物過程中發現某種物理規律,并將其以物理存在形式保存在器物中,這仿佛是一種來自神明的意念,因此營造了一種穩定、莊重、神秘的視覺效果,這與祭祀的莊重、嚴肅、神秘的氛圍是切合的。三足器作為祭祀用器并不是偶然的,它體現了原始先民對生命的崇敬,寄托了希望神明賜福于生命的美好愿望。
從原始宗教信仰來講,遠古先民對大自然的一些神秘現象不能解釋,便通過模擬它(動物、植物)的造型以達到占有和崇拜的目的。一開始先民模仿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動植物形象,然后根據自己的需求進行改進。比如遠古先民對生命充滿敬仰與崇拜,但不懂得生育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于是他們觀察自然界生育力強盛或生命力頑強的動植物,有時也直接取象動植物,希望借助它們的生存之力保佑氏族,這點可以從原始陶器的造型和圖案上得到證實,如水紋、魚紋、鳥形等。最典型的是新石器時期仰韶文化陶鷹鼎,陶鷹鼎是仰韶文化中現存唯一一件鳥形器皿,其造型內涵說法不一,但總體來說是一直以來人們崇尚鳥意識發展的結果。一說其含義可能與當時的農業生產活動有關,即利用鷹護佑農業豐收,是距今5 500年前因農業生產活動而產生的一種崇尚鳥 (鷹) 意識的記錄。一說是祭祀神靈的祭器,人們希望老鷹能夠把鼎中的祭品帶給神靈,完成對神靈的祭祀,祈求神靈賜福免災。盡管其說法尚無定論,但可確定的是它寄托了當時人們對生存的渴望與美好希冀。
(二)自覺與存在
生命意識最直接的就是對生和死的認識和體驗。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人性大概起源于埋葬死者。”這種對于生與死的感悟和思索將原始人的心智從混沌狀態中喚醒了。可以這樣說,當人類認識到個體生命的存在與消失時,生命意識也就產生了。
在中國歷史中,人性的真正覺醒始于西周。“小邦周克大國殷” 動搖了絕對信天的觀念,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作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在西周人眼中,天命不是注定的、一成不變的,只有“修德”“敬德”才能“配命”“配天”。這時的人性開始向自我方向發展,紋飾主要是具有人神特征的回紋、幾何紋、云紋等,但仍沒有脫離神性,雖然陶瓷裝飾逐漸由“娛神”轉向“娛人”,但依舊是比較規范、嚴肅的。
西周人性的覺醒也表現在以陶俑替代人殉上。由于是奴隸社會,有時代的局限性,西周之前,存在大量用人及車馬殉葬的現象。從西周開始,人們逐漸以陶俑代替人殉,比如秦始皇用兵馬俑代替人殉的舉措,使許多人幸免于難。與同處于奴隸社會的古希臘相比,西周并沒有類似于角斗這類以人命取樂的行為,這體現了中國人所特有的生命情懷:對生命的尊重和珍惜。
東周時期,陶器的內容題材中娛人是重要的一方面,而不是只在禮儀祭祀中娛樂神靈或是祖先。從紋樣上來說,東周末期陶器仿青銅器的手法漸漸消失,裝飾紋樣開始以神話和民間生活場景再現為主,并且一改西周大量抽象、不可名狀的幾何紋,開始由抽象走向具象,從規范走向生動。從紋樣題材上看,重新使用大量的動物紋、植物紋,如柿蒂紋、龜紋、龍鳳紋等,活潑自然。陶器的器型除了簡樸規范的實用器外也有栩栩如生的仿生造型,如朱繪獸耳陶壺、虎頭形陶水管等。可以說這是“禮崩樂壞”的結果,在同時面對自然災害、頻繁的戰爭等一系列現實狀況時,人們開始主動回避,向內認識到自身的價值,從而更加注重現實生活的享受。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十分明確的自然死亡意識,并且已經把生死看作無法改變的必然。如《昭公三年》:“子產曰:人誰不死?”《論語·顏淵》:“自古皆有死。”《左傳·文公十三年》:“死之短長,時也。”說明這一時期出現了人對生命的自覺意識,戰國時期不同于前朝對生命有一種蒙昧的崇拜,而是認識到死亡,但并非一味地順從死亡,他們所追求的是“死且不朽”,追求一種超越肉身的自我意志的確立,試圖用不死的信念來超越死亡。
這一點對于陶器創作來說,即意識到生命的死亡狀態,生命既是短暫的又是永恒的。短暫在于生命肉身的脆弱性,永恒在于人在藝術作品中凝結的對于超越肉身的有限性,而達到精神的無限性的一種崇高。這種生命的崇高將永遠地凝結時間,超越時間的禁錮,達成一種精神的永存。
而儒、道兩家對此抱有不同的態度。正因生命短暫,儒家強調生的意義和死的價值,尋求的是個人價值對社會價值的作用,“克己復禮為仁”,因此儒家更重視器物的禮儀教化作用,因此在儒家思想下的器物具有一種沉郁的美感;道家認為生命產生于氣,《莊子·知北游》:“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將生命歸為一種物質,把死亡物化,因此對待生死就具有更超然的態度,因此道家思想下的器物具有一種飄逸的美感。
(三)自我與情感
六朝是“個人自我之覺醒”的時期。六朝時期社會動蕩,戰亂連綿不斷,朝不保夕,這引起了人們強烈的危機感和對生命、生活的深層反思。這時,蓮花紋和忍冬紋等植物紋成為陶瓷裝飾最常用的紋樣,以反映人們對世事艱難、生命無常的慨嘆。在器型方面,魂瓶是六朝青瓷中最典型的器型之一。人們相信,逝者的靈魂會寄居在這些魂瓶中,奇跡般地再現出一個從人間延伸至天堂的理想世界。
唐代繁榮強大,人們也在這個時期真正認識到自我的力量。如果說魏晉六朝是悲情的人性覺醒,感嘆生命無常和無力,那么唐代是樂觀的人性自我肯定,表現為自信樂觀、豪邁,陶瓷上表現為造型和裝飾都以清新、豐滿、圓潤、氣派為追求。如唐仕女俑,整體造型大氣飽滿、簡潔凝練。仕女俑身上流暢柔美的線條展現了人物內心自信舒適、嫻靜愉悅的內心狀態,以小窺大,見證了整個盛唐的恢宏氣勢與宏大氣度。
宋朝在文化上、思想上的解放更為深刻,進入了一個文化、藝術極其繁榮的歷史時期,市民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崛起使風格多樣的民窯瓷器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其藝術特色各具風格,藝術形式種類豐富多樣,官窯、民窯“百花齊放”,繁榮鼎盛。其中民窯藝術產品以獨特的藝術風格、自由豪放的個性深受市井百姓的喜歡。民窯瓷器通過其自身的裝飾“把制作工匠自身的個人情感和當時社會的審美情趣、思想意識表現了出來”。
由此,正如文人畫對個體生命的極度關注那樣,在整個社會的主流審美風尚之下,陶器有了更進一步的藝術風格的分流。
三、結語
生命意象與陶器關聯緊密,作為中國“生命的文化”的一種形式,陶器以特有的形式蘊含著生命情懷。在原始時期先民僅僅對生命有一種朦朧的感覺時,生命意識就已經反映在了陶器造型中,隨著生命意識的萌芽,出現了對生存的追問和對繁衍的渴求,對自我存在的反思和對人生終極問題的思考,衍生出關于生命價值的不同觀念與情感。從作為食用器對生命的觀照,到作為禮器以祭神明、祈求神明對生命的庇佑,再到作為生命情感的一種物理顯現手段,陶器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每個階段,都用一種溫情的、直接的方式記錄著人類對生命的潛意識的認知,我們也從中反觀宇宙萬物及自身的存在,并用陶器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生命意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