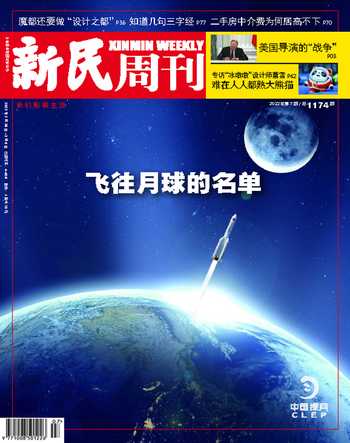白居易:但愿樂天無長恨
Anne
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出生。
前幾年看《妖貓傳》,死活無法說服自己,那位跟著個疑似嘴角抽風的倭國和尚,被一樁陳年情事攪得七葷八素的大唐中二少年,居然是阿拉的老白,阿拉的居易。
本可做千年的狐貍,怎么會看不穿聊齋式的謎題?初入長安,一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讓文壇大佬顧況化“米價方貴,居亦弗易”的調侃為“道得個語,居即易矣”的感嘆。慷慨陳詞“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卻終歸娶了京兆尹楊虞卿從妹為妻——男人可以不吃軟飯,遇上益處良多的親事,當“十動不拒”。半輩子操心要買房,“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五十多歲夙愿得償,安家洛陽豪宅,春風拂面真·樂天。因“無禮”被唐憲宗吐槽是死小子,因“亂說話”被貶,都不忘抽空聽聽神曲抒抒情——寫那么長的詩作甚?后世不肖學子越背誦越萌發“敲碎那把琵琶”的沖動……總之,經歷過一點坎坷際遇的白居易,混得不慘、活得挺爽,到頭來官也升了,錢也有了,在人間天堂的蘇杭也浪過了,歡度光陰七十余載,“今朝覽明鏡,須鬢盡成絲”“當喜不當嘆,更傾酒一卮”……開心嗎?開心。喝一杯,絕對值得再喝一杯。

張大千畫的長生殿。
白老師是倡導新樂府運動的“元白”之一;是作品淺切悠遠、“老嫗能解”的魔王級人物(有“詩魔”“詩王”之稱);是寫了《賣炭翁》《秦中吟》《村居苦寒》亦寫了“山寺月中尋桂子”“吳娃雙舞醉芙蓉”的大文青;是嗜美食愛美女討厭上班的古代公務員。白老師的天是晴朗的天,西京東都的人民好喜歡。
說起這文人中的吃貨呢,坡仔排第一的話,白老師前三肯定還是能進的。清晨,嘗嘗牛奶煮粥的味道;中午,蔬菜配飯,小酌怡情;晚上,雞鴨魚肉,滋補腸胃;半夜睡醒,喝喝茶,定定神。
伊表揚荔枝“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盛贊竹筍“素肌擘新玉”“經時不思肉”。關于竹筒飯,“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鵝鮮”。關于馕,“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他也很懂怎么吃魚:“魚膾芥醬調,水葵鹽豉絮”“秋風一筯鱸魚鲙,張翰搖頭喚不回”,講的是生魚片;“魴鱗白如雪,蒸炙加桂姜。佐以脯醢味,間之椒薤芳”,則系蒸魚之法了。“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朝暖就南軒,暮色歸后屋。晚酒一兩杯,夜棋三數局”等作,說明白老師對酒的欣賞與了解,不輸太白兄。
飽暖思淫欲。長久以來,部分讀者始終難以相信,深切掛念青梅竹馬湘靈妹,誠摯書寫《上陽白發人》《陵園妾》《井底引銀瓶》《繚綾》《太行路》的白老師,和萬花遍覽,“左顧短紅袖,右命小青娥”“小奴捶我足,小婢捶我背”“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渣男本男”,竟真的是同一個人。蓄養家妓、挖元稹墻腳給薛濤“豁翎子”、用筆誅心逼關盼盼走上絕路……丑聞、八卦、謠傳纏身,無中生有的,空穴來風的,導致白老師“偉大詩人”的光輝形象一度飽受詬病,危如累卵。
賦詩容易,做人難。動情容易,癡守難。白老師知曉如何品鑒女人們的妝容,“腮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卻畢竟無意深究“墻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宿空房,秋夜長”“百年苦樂由他人”背后因無盡不公引發的無盡苦痛。他的現實主義既體現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也匿伏在看似前后不一、精分曖昧的混沌態度里。
不過,比“污”的話,白老師的弟弟白行簡恐怕更勝一籌。敦煌出土過一篇題白行簡作的精彩小黃文《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通過生動細節引領“走近科學”,比白老師的“寓居同永樂,幽會共平康……結伴歸深院,分頭入洞房……索鏡收花鈿,邀人解袷襠”云云帶感多了。
據《酉陽雜俎》記載,荊州名葛清者,通體遍刺白老師詩句二十余處,且以畫配詩,故稱“白舍人行詩圖”。而蕩漾風流的白老師不光在本土擁有諸多瘋狂粉絲,在日本更是得到天皇巨星一般的待遇——每次刷《源氏物語》《枕草子》等平安朝名著,幾乎等于重溫“白老師教你吟詩撩妹”小課程,尤其《源氏物語》開篇就引用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影射宮廷悲戀,足見《長恨歌》對紫式部的影響之深。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樂天“長恨”,傳世佳話。猶記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畫過一幅《長生殿》送給新婚的小嬌妻徐雯波,殿堂富麗工細,隆基、玉環衣袂飄飄,遠景大片留白,若霧若夢——“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閣玲瓏五云起,其中綽約多仙子。”后來,大千之友溥儒特為此畫題白老師原作全文,舊王孫的蠅頭小楷精絕至極,沒有辜負哀感頑艷的詩意一片。
其實帝王與寵妃情天孽海的故事毫不新奇刺激,刺激的是歷史的反復無常。安史之亂,雄主遲暮,大廈將傾,盛極而衰……多么流量效應(一不小心即淪為地攤文學)的題材!難怪夢枕貘忍不住一鍋亂燉,鼓搗出了《妖貓傳》的原著小說《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這位日本作家別具一格的筆名,追根溯源,又能扯到白老師身上——白老師寫過一篇《貘屏贊》,道“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傳到東瀛后,大概漸漸衍生出食夢貘的傳說。江戶時代開始,百姓認為伴著“貘枕”睡覺,噩夢便會被食夢貘吞噬,噩運亦隨之消失。
《楊太真外傳》曰,玄宗于馬嵬驛將貴妃賜死后,繼續西行至扶風道旁,見端正可愛的大石楠樹一棵。觀望許久,念往昔華清宮端正樓里日夜春宵,如今天人永隔,遂賜名“端正樹”。“春芽細炷千燈燄,夏蕊濃焚百和香”,陽光灼燒炙烤,冉冉升起混合杏仁風味的玫瑰香,間雜一絲腥膻,何等熱烈馥郁!跟著白老師詠石楠的佳句,在花氣熏人的情境里,我們不妨發散思維:解語傾國薄命妾,彩云易散琉璃脆;那個女人撲朔迷離的命運,那場盛宴一并埋葬的帝國的青春與天真,究竟是最美妙的樂章,抑或是最蒼涼的幻術?
永不終結的從來不是極樂之宴,是眼淚成詩,樂天在詩外驕傲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