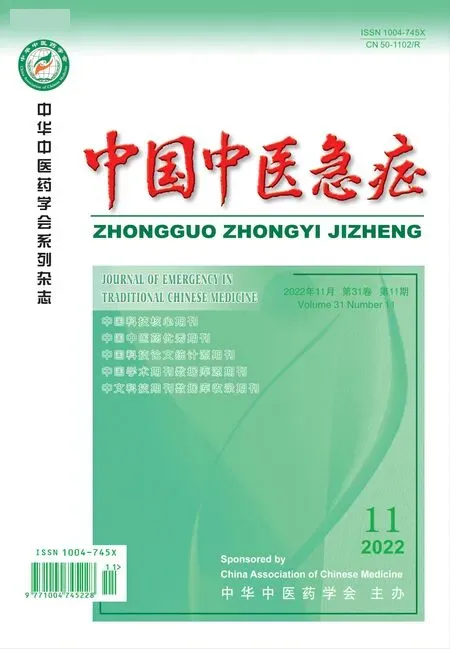符文彬教授整合思維“一針二灸三鞏固”模式治療支氣管哮喘的臨床經驗*
趙蜜蜜 寧百樂 黃熙暢 劉 露 指導 符文彬△
(1.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2.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廣東 廣州 510000)
支氣管哮喘發病時主要表現為胸悶、喘息、氣急、咳嗽等癥狀[1]。哮喘在各國中的發病率為1%~18%,根據WHO的最新統計,全球大約2.35億人罹患了哮喘,而2015年則有383 000人因此而喪生。《中國成年人肺病調查》是2012至2015年3年內開展的一項大型人群調查,結果顯示,我國20歲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4.2%,發病人數達到4 570萬[2]。在治療方面,哮喘急性期發作時,西醫多使用解痙平喘、β受體激動劑、激素等藥物治療;而在緩解期多使用霧化吸收劑持續治療,但是長期使用會引起療效下降,甚至藥物副作用。目前藥物治療主要以改善癥狀為主,尚達不到根治的作用[3]。因此,該病存在著長期難愈、易反復發作、影響生活質量等特點,給患者家庭及社會醫療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符文彬教授是廣東省名中醫、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針灸教研室主任、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導師,通過30余年的臨床鉆研和不斷創新的針灸理念,積累了寶貴的針灸臨床財富[4]。筆者師從符文彬教授,現將其整合針灸治療支氣管哮喘的經驗介紹如下,以供同道共思。
1 論治思路
1.1 中西互參,明確診斷
支氣管哮喘臨床上發作不典型時容易與其他疾病混淆,需要與其他諸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源性哮喘等疾病鑒別以明確診斷。支氣管哮喘與心源性哮喘的鑒別要點在于后者多有心臟病病史,可咯出粉紅色泡沫痰、端坐呼吸,兩肺可聞及廣泛濕啰音及哮鳴音,心尖聞及奔馬律等,臨床上需要注意鑒別;支氣管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鑒別要點在于后者多見于中老年人,多有長期吸煙和慢性咳嗽、喘息病史,雙肺呼吸音下降,有肺氣腫體征等可供診斷。而支氣管哮喘多有遺傳特征或外界激發因素,經常在夜間及晨間發作,可經平喘藥物治療后緩解或自行緩解,根據臨床發病的特點分為急性發作期、慢性持續期和臨床緩解期。符文彬教授強調診治該病應中西互參,兩者不可偏廢。治療前通過中醫四診,結合現代醫療的檢查手段以明確診斷,是所有疾病治療必不可少的一步。在中醫的診察方面,符文彬教授注重辨病與辨證相結合,以明確治則治法,確定取穴配伍。
1.2 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
在中醫學中支氣管哮喘屬于“哮病”“喘證”“痰飲”的范疇,《證治匯補》中記載“哮為痰喘之久而常發音,因而內有壅塞之氣,外有非時之感,膈有膠固之痰,三者相合,閉拒氣道,搏擊有聲,發為哮病”。該病的病因通常認為是宿痰伏肺,而外邪侵襲、飲食不當、情志刺激、體虛勞倦為其誘因。痰氣搏結,壅阻氣道,肺失宣降為其基本病機。符文彬教授在早期臨床中發現該病針刺治療后即時療效理想,但是過一段時間,患者往往又會以類似的病癥就診,疾病容易反復發作。符文彬教授認識到治療支氣管哮喘需要注意整體觀,不能局限于疾病本身的癥狀,并強調診治該病須根據疾病的不同分期有有所側重。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即哮喘急性發作時重點在于平喘,而在慢性持續期、臨床緩解期應偏重固護根本、調整臟腑氣血陰陽平衡。此外,符文彬教授對于支氣管哮喘合并情志異常的患者,主張疏肝調神治療;根據支氣管哮喘的發病機理,提出“心膽論治”理論,善用心膽相關的穴位治療過敏性疾患,療效顯著。
1.3 中西結合,改善預后
在支氣管哮喘急性發作期時,符文彬教授提出,要首先判斷病情的嚴重程度,如通過結合患者癥狀的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夜間的發作頻率和睡眠質量、體力受限的程度、肺功能檢查的結果以及查體時哮鳴音的分布情況來判斷,需要注意的是,嚴重的哮喘發作時,哮鳴音反而減弱,甚至完全消失,表現為“沉默肺”,是病情十分兇險的表現,此時則需要結合現代醫學技術,盡快緩解支氣管痙攣、糾正低氧血癥,以免進一步惡化而危及生命。臨床中,在哮喘中重度及危重發作時,針刺的同時亦需配合藥物積極治療,如使用SABA聯合SAMA、茶堿類藥物或激素類藥物等,以提高療效,改善患者不良預后。
2 “一針二灸三鞏固”整合針灸模式
2.1 一針
符文彬教授在治療支氣管哮喘時,從心膽論治,注重調神,并根據疾病的不同階段,選用眼針或針挑療法。基本選穴主要為百會、上星、印堂、內關、公孫、陽陵泉。頭面及四肢常選用25 mm×25 mm針灸針,腹部選用22 mm×40 mm針灸針,常規針刺得氣后,留針20~30 min即可。
符文彬教授主張從心膽論治,穴取內關、陽陵泉。支氣管哮喘是一種常見的過敏性疾病,受遺傳因素與外界環境因素的雙重影響,T細胞介導的免疫調節的失衡和慢性氣道炎癥的發生是其最重要的哮喘發生機制[5],支氣管哮喘在發病前有鼻、咽、肌膚瘙癢等癥狀,且具有急性發作和緩解交替進行的發病過程。《素問·太陰陽明論》曰“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不時臥,上為喘呼”。支氣管哮喘發病時與風邪致病有著相似的臨床特點,風邪是過敏性疾患的重要因素,外邪是致病的主要誘因[6]。中醫認為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素問·至真要大論》中“諸痛癢瘡,皆屬于心”,心包代心受邪,故符文彬教授常常選擇心包經內關穴以奏行血祛風之功。又過敏性疾患每由痰飲瘀血內停而致病情反復發作,究其根本,由于氣機不暢引起。元代著名醫家朱震亨主張“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其《丹溪心法》中記載的越鞠丸即以氣郁為六郁之首,《醫碥》云“百病皆生于郁,而木郁是五郁之首,氣郁乃六郁之始,肝郁為諸郁之主”。因肝主疏泄,肝膽相表里,且少陽主樞機,符文彬教授常選用膽經陽陵泉穴疏理氣機,行氣化痰。同時配合脾經公孫穴,既可健運脾氣,加強化痰散濁之功,又內關與公孫相配,為八脈交會穴,可治療胃心胸疾患。百會、上星、印堂可通竅宣肺,安神定志。支氣管哮喘作為一種慢性難治性疾病,極大地影響患者及其家庭的工作生活。情志障礙是支氣管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的常見并發癥,可使患者治療依從性下降,療效下降甚至病情惡化[7]。因此治療時,符文彬教授注重疏肝調神,常選用百會、印堂、四關等穴組進行治療。除此之外,在臨證時,配穴隨證加減,寒哮證選風門、合谷,熱哮證配大椎、魚際,痰多者配豐隆、中脘,肺氣虧虛者配中府、胃俞,脾氣虧虛者配章門,元氣虛損配引氣歸元。
2.1.1 急性發作,善用眼針 符文彬教授在患者哮喘急性發作期常在常規針刺的基礎上配合眼針療法,療效滿意。根據三焦辨證法及臟腑辨證法選擇肺區、上焦區,操作要點:用30號(1.5 cm)不銹鋼針,以左手拇指或食指壓住眼球并使眼瞼皮膚繃緊,右手持針在眼眶緣外0.5 cm的眼針穴區針刺,以達眼眶緣外骨膜為度,針下得氣后留針(酸、麻、脹、熱、涼等感應),留針15 min,每隔5分鐘行針1次。在操作時要注意避開眼球,以免刺傷,出針時要按壓2~3 min,防止出現眼部局部血腫。董文毅等在眼針療法的研究進展中指出眼部穴區與十二經脈的聯系密切,起到反映相應五臟六腑經脈的性能及治療相關疾病的作用[8],根據哮喘急則治其標,緩則調其本,發時治肺,肺居上焦的理論基礎[9],符文彬教授選擇肺區、上焦區來進行哮喘急性發作時的針刺治療,能有效控制和緩解患者喘息胸悶、氣急、呼吸困難等癥狀。
2.1.2 慢性纏綿,巧用針挑 符文彬教授在哮喘慢性持續期及臨床緩解期常輔以針挑療法進行后期鞏固治療。針挑療法是鋒針療法和半刺法的綜合發展,《黃帝內經》云“病在五臟固居者,取以鋒針”,《靈樞·九針十二原篇》中“四曰鋒針,長一寸六分。鋒針者,刃三隅,以發痼疾”,《靈樞·官針》“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針,無針傷肉,如拔毛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應也”。即淺刺及皮,迅速出針的針刺方法,以其所刺極淺,如常法之半,故名半刺。針挑療法常用來治療病在經絡而出現瘤痹的疾患,病在臟腑而出現五臟固居包括所屬器官固居的疾患。選穴選擇大椎、肺俞、中脘、膻中,臨床隨證加減,脾虛痰盛者加脾俞、喘甚者加天突,久病加膈俞、膏肓俞。操作要點:根據穴位不同選擇不同的體位,背部的穴位可選擇俯臥位,胸腹部的穴位可選擇仰臥位或者仰坐位。常規消毒后,用鉤狀挑治針刺入皮膚后進行上下左右的旋轉挑動,挑斷皮下纖維組織,以持續地疏通經絡之氣,發揮治病作用。操作時要注意無菌操作,術后要注意休息、飲食及局部護理,防止感染,選擇此療法要嚴格掌握適應癥和禁忌癥。如對于孕婦、局部皮膚有破潰感染、有血液病、嚴重心臟病或糖尿病等患者應避免使用。
2.2 二灸
符文彬教授師從嶺南針灸大師司徒鈴教授,他在繼承司徒老傳統灸法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艾灸技術——精灸,即將陳年精細艾絨搓成底面直徑2 mm×3 mm的圓錐形,將米粒大小的艾灸炷置于相應的穴位上,以治療疾病的方法,它具有刺激量大、透熱迅速、熱力集中,1壯可達普通麥粒灸多壯的效果[10]。當艾炷置于穴位上時,用線香將其點燃,根據患者病情、個人耐受程度選擇不同的灸度。一般分為輕度、中度、發泡,輕度:艾炷燃燒至有痛感時(1/2),將艾炷移開,此為1壯,一般每個穴位2壯,灸至皮膚潮紅為佳。中度:艾炷燃燒至有疼痛感,再過2 s后(3/4),將其移開,此為1壯,灸壯根據病情而定,以皮膚潮紅灼熱為佳疾。發泡:艾炷燃盡,此為1壯,以皮膚輕度發泡為佳[11]。支氣管哮喘急性發作針刺治療,待癥狀改善后,一般選擇中度灸、發泡灸,不能耐受者,視情況減少精灸刺激量,穴位可選擇肺俞、四花、引氣歸元、膻中、定喘、脾俞、腎俞、足三里、涌泉,每穴2壯。其中肺俞、腎俞補肺腎氣;引氣歸元[12]為中脘、下脘、氣海、關元組成,以后天滋先天;脾俞、足三里健脾化痰;定喘穴平喘;膻中為八會穴之氣會,可寬胸利氣、降逆利膈;四花由膈俞、膽俞組成,其中膈俞為血之會穴,屬陰,膽俞為膀胱經之背俞穴,屬陽,肝膽互為表里,膽俞可疏肝理氣,調一身之氣,兩穴合用,可調整臟腑陰陽氣血。涌泉可引火下行,補益腎氣。灸后大椎刺絡放血,加以拔罐,一般30 s左右,可泄體內有余之熱邪,又可疏通局部氣血。
2.3 三鞏固
符文彬教授在臨床中重視疾病的鞏固治療,皮內針療法可有效控制癥狀和減少疾病復發,因此在支氣管哮喘發病的各個階段均可應用。皮內針療法,亦稱埋針法,是用一種特殊的針具置入經穴局部皮下進行持續刺激,起到調節臟腑經絡功能的作用,是對傳統針灸的一種新的發展[13-15]。操作常選用大小為0.22 mm×1.5 mm的一次性掀針,貼置于背俞穴心、膽兩俞及耳穴心、肺、腎,一般留針2~3 d。
3 驗案舉隅
患某,女性,16歲,主訴:反復咳喘3年。于2014年6月24日首次就診。患者于3年前無明顯誘因下出現胸悶、氣急、呼吸困難,完善相關檢查后確診“變態反應性支氣管哮喘”,間斷使用藥物治療。疾病反復發作,每于天氣變化時癥狀加重,伴有鼻塞、流清涕、打噴嚏、鼻、眼癢等癥狀,發作聲如拽鋸。患者及家屬為求進一步治療,遂來診。患者訴近期情緒低落,學習興趣減退,口干不苦,納眠可,二便正常,舌淡紅,苔厚,脈浮滑。查體:雙肺可聞及少許哮鳴音。既往變應性鼻炎病史。中醫診斷:哮病(風痰哮證)。西醫診斷:1)變態反應性支氣管哮喘;2)變應性鼻炎。予針刺治療。眼針:肺區、上焦區。體針:百會、印堂、上星、內關、陽陵泉(雙)、公孫。精灸:肺俞、四花、引氣歸元、腎俞、足三里、涌泉各2壯。刺絡拔罐:大椎。埋針:心俞、膽俞。耳針:心、肺、腎。每周2次,連續治療6周后復診,患者打噴嚏次數減少,肺部未聞及哮鳴音。患者訴偶有胸悶、情志不暢,夜間睡眠質量不佳,于前方基礎上加照海、四關。后患者情志調達舒暢,睡眠較前改善,守前方鞏固治療,隨訪1年未見復發。
4 結語
符文彬教授在臨床中診治支氣管哮喘疾病時注重整體觀念,強調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注重疾病分期和預后調護。其診治該病主張從“心膽論治”,采用整合針灸思維模式,根據臨床分期、疾病輕重緩急選擇不同的治療方式。急性發作期時,善用眼針,效如桴鼓;臨床緩解期時,巧用挑針,以防復發。對于中重度及危重支氣管哮喘急性發作時,符文彬教授強調中西醫結合治療的重要性,以提高療效,改善預后。除此之外,支氣管哮喘患者常常會伴有情志異常,對于支氣管哮喘伴有情志障礙的患者,符文彬教授在治療時注重疏肝調神。日常調護方面,符文彬教授注意囑咐患者平時避免接觸哮喘激發因素并強調固護元氣。
支氣管哮喘的反復發作性仍然是目前臨床中亟待解決的難題[16]。符文彬教授在傳統針灸治療模式基礎上,提出了“一針二灸三鞏固”整合針灸思維模式,彌補了單一針灸療法的不足之處,對臨床上支氣管哮喘這種難治性、反復性疾病的診治開拓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