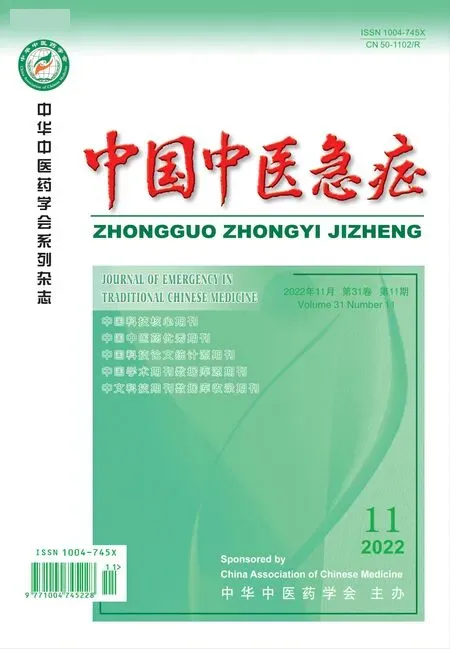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研究進展*
王海宇 王 宇 姚長風
(1.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安徽 合肥 230061;2.安徽中醫藥大學,安徽 合肥 230012)
周圍性面癱是發生在面神經核周圍或面神經核下游的神經纖維損傷類疾病[1],臨床表現為患者額紋變淺甚至消失、單側眼瞼閉合不全、鼻唇溝稍淺、口角向單側歪斜,無法完成抬眉、閉目、鼓腮、示齒等動作,還可能伴有舌體麻木、口腔食物殘留、味覺減退、迎風流淚等一系列癥狀,是急診科、針灸康復科、腦病科的常見病和多發病。西醫認為本病與特發性面神經麻痹相對應,國外報道發病率在11.5/10萬人~53.3/10萬人[2]。目前西醫治療周圍性面癱主要是通過糖皮質激素、抗病毒藥物、神經營養劑和外科手術減壓、神經康復等療法,恢復時間長,療效欠佳。大量臨床和實驗研究表明,中醫針灸對周圍性面癱療效確切,可有效縮短病程,改善預后。本文通過總結近5年的文獻,對周圍性面癱的發病機制、病因病機、治療現狀以及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的研究概況進行綜述。
1 中西醫對周圍性面癱的認識和治療
周圍性面癱發病原因及其機制尚不完全清楚,現代醫學認為與病毒感染、神經缺血、解剖異常、免疫缺陷等原因有關,上述原因可使面神經的供養血管發生痙攣、缺血,從而導致面神經水腫,使面神經受壓,引起面神經感覺及運動功能異常,引發面癱[3-6]。臨床根據病程的時間將周圍性面癱分為3期,分別為急性期、恢復期、后遺癥期。目前,西醫治療周圍性面癱主要是通過糖皮質激素、抗病毒藥物、神經營養劑和外科手術減壓、神經康復等療法,治療周期較長,對面神經及面部肌肉功能恢復的療效不甚理想,易延誤最佳治療時機,發展成頑固性面癱。且臨床發現眾多患者對糖皮質激素等藥物的敏感度較差,長期使用副作用不可避免,而大量臨床和實驗研究表明,中醫針灸對周圍性面癱療效較好,可有效縮短病程,改善預后。
2 針灸治療方法
2.1 普通針刺 針刺具有扶正祛邪、活血通絡、調暢氣機等作用,針刺治療周圍性面癱可興奮運動神經元,消除局部面神經水腫、促進自身免疫修復,進一步提高療效,早期介入針刺療法可加速局部血液和淋巴循環,緩解水腫,促進炎癥吸收[7]。高超等運用常規針刺配合淺針法治療急性期周圍性面癱患者,結果發現加用淺針法較單純使用常規針刺有效率高出75%,且加用淺針法能明顯改善患者的視覺模擬量表(VAS)疼痛評分、面動脈血流動力學指標、面神經及面肌損傷[8]。金鑫等在和單獨西藥治療周圍性面癱相比,針刺合谷、翳風、承漿、水溝、頰車穴,行平補平瀉法治療周圍性面癱,針刺組較單獨西藥組治療總有效率提高15.63%[9]。王中來選取周圍性面癱急性期(發病7 d內)患者,取對側合谷、迎香、陽白、四白、地倉等穴為主穴,辨證施針,治療組予以常規西藥加普通針刺,對照組在急性期只接受常規西藥治療,急性期后加用普通針刺,共治療兩周,結果示治療組降低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M(IgM)的水平程度優于對照組,表明針灸介入早期周圍性面癱療效較好,其可能通過降低血清IgG、IgA、IgM的水平進一步來調節機體免疫平衡來實現[10]。合谷穴治療頭面、口周疾病效果良好,是現代醫家運用合谷穴治療周圍性面癱的常用取穴方法。楊駿等研究發現針刺合谷穴治療周圍性面癱可能與通過激發靜息狀態下腦組織結構網絡和運動感覺網絡變化的機制有關[11]。張立志等從臟腑別通理論及經脈循行角度探討針刺合谷穴的應用基礎,考慮針刺合谷穴是通過刺激機體對不同感覺信息的匯集并在大腦皮層中實現功能重組而發揮療效[12]。
2.2 電針 電針是針刺相關腧穴后通過以一定的脈沖電流,并加用不同強度的電刺激作用于局部腧穴的一種針灸方法,具有調節肌張力、改善肢體麻木、加強止痛、促進血液循環等作用,臨床運用廣泛。研究表明,電針治療周圍性面癱的機制可能是通過刺激面部受損的神經再生,增加面部血流量,同時修復肌肉細胞[13]。王坤等認為疏密波可作為周圍性面癱急性期的首選波形,其可以促進機體代謝、加速局部血液循環、消除炎癥反應、改善面神經水腫[14]。李曉娟等取陽白-四白、地倉-頰車,以及翳風、合谷等穴運用電針療法治療周圍性面癱恢復期患者,治療后發現連續波、斷續波、疏密波治療周圍型面癱均有療效,連續波組總有效率為96%,斷續波組為80%,疏密波組為88%[15]。陳凡等在激素藥物治療基礎上聯合電針疏密波治療周圍性面癱急性期,結果發現聯合電針疏密波輔助干預后患者的House-Brackmann(H-B)面神經功能評分和VAS評分較單純藥物治療組評分更低,有效率更高[13]。楊聯勝等通過觀察攢竹-陽白、迎香-地倉的電針電興奮性來評估周圍性面癱預后,并通過電針的電反應敏感度調節合適的刺激強度[16]。臨床發現,電針療法對周圍性面癱療效確切,但選擇何種時機介入電針尚未明確。部分學者認為電針不宜過早介入治療周圍性面癱急性期,過早的介入不利于莖乳突孔水腫的消除和炎癥反應的吸收,可適時在恢復期或者難治性面癱時期使用。也有學者認為周圍性面癱發病初期即可加用電針,不僅可預防面肌痙攣等并發癥的發生,且可更早地安撫情緒,改善預后[17]。
2.3 特殊針刺 臨床治療周圍性面癱還常使用健患側同調針法、經筋排刺法、透刺法、開口針、口內針等特殊針刺療法,皆取得較好療效。李瑞超等選取印堂,患側陽白、太陽、下關、頰車、迎香、地倉、翳風、合谷、肘髎等穴,先后刺健側和患側腧穴,對照組僅患側取穴,每周治療3次,共兩周,結果提示健患側同調針法可以縮短周圍性面癱的病程時間[18]。郭春暉等合用用透刺法與經筋排刺法治療周圍性面癱,對照組局部選取太陽、地倉、頰車、下關、迎香、陽白、四白、翳風、牽正等穴,遠端取健側合谷穴,予以普通針刺,觀察組采取透刺法聯合經筋排刺法:取陽白向上星、頭維、絲竹空、攢竹各方向透刺、取顴髎、太陽透刺地倉,地倉、頰車之間采取經筋排刺,四白、迎香、下關、牽正、健側合谷穴予以普通針刺,結果提示透刺法聯合經筋排刺法療效較普通針刺組更優,總有效率高于普通針刺組[19]。梁思明等應用巨刺法聯合腹針治療周圍性面癱,結果發現巨刺法聯合腹針治療周圍性面癱的總有效率為96.67%,高于對照組的86.67%,且在改善癥狀體征評分(Portmann評分)、軀體功能指數量表(FDIP)評分及社會生活功能量表(FDIS)評分方面療效更優[20]。康愛蓮等選取開口針、口內針治療周圍性面癱,開口針取患側口角內0.5寸皮膚與口腔黏膜處為一點,第1針向巨髎穴透刺0.8~1.2寸、第2針向水溝穴透刺0.8~1.0寸、第3針向大迎穴透刺0.8~1.2寸,口內針取患側內地倉(地倉穴相應口內黏膜處)向頰車方向透刺0.8~1.2寸,對照組選取患側陽白、太陽、頰車、牽正、四白、水溝、地倉、承漿、翳風,雙側足三里、太沖,健側合谷,行普通針刺,結果發現開口針、口內針組患者治療后味覺障礙、食物殘渣、鼓腮漏氣、口角歪斜、鼻唇溝變淺的評分改善程度均優于普通針刺組[21]。
2.4 溫針灸 溫針灸是將針刺與艾灸有機結合起來的治療方法,具有散寒通絡、活血行氣的功效。王學軍等用溫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急性期患者,治療以局部選穴與循經選穴為主,取翳風、風池、陽白、魚腰、地倉、頰車、下關等穴,行普通針刺,溫針灸組在普通針刺基礎上,予以翳風穴、風池穴行溫針灸,每穴加2~3炷艾條懸灸,以面部潮紅為度,治療后發現溫針灸組有效率較普通針刺組有效率提高5.09%[22]。張加英等在常規口服甲鈷胺、維生素、醋酸潑尼松片以及常規針刺基礎上加用牽正穴溫針治療,結果表明加用溫針治療1周、2周后H-B評分、面神經功能評分以及痊愈率更高[23]。李明等認為翳風穴既是祛風要穴,又是面神經莖乳突孔在體表的投影區域,溫針灸翳風穴治療周圍性面癱可使局部神經病變部位炎性反應、水腫迅速消退,可以通過改善面神經周圍循環,促進面神經再修復來改善耳周疼痛[24]。湯紅等溫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急性期,其有效率97.67%高于常規針灸治療組的79.07%,面部神經功能評分亦高于對照組,結果提示治療急性期周圍性面癱時采用溫針灸能加速局部血液的代謝和循環,加速對炎性滲出物的吸收,促進水腫快速消退,恢復面部神經功能[25]。
2.5 針刺結合其他療法 針刺治療周圍性面癱方法多樣,臨床常相兼使用。佘暢等以鼻中隔、上唇方向、雙側風池穴對側為目標點斜刺作為對照組,治療組在普通斜刺基礎上加用梅花針扣刺出血,叩刺頻率可達70~100次/min,配合拔罐,治療結果顯示針刺配合刺絡拔罐較單純針刺有效率更高[26]。張鳳平將針灸聯合閃罐與單純脈沖電刺激、激光療法等作比較,結果發現針灸聯合閃罐治療周圍性面癱可更好地改善患者面部血供,縮短病程。嚴媚等[6]應用毫火針半刺聯合翳風穴中藥超聲導入治療周圍性面癱,治療后發現患者HB評分和面部殘疾指數軀體功能評分較常規西藥治療效果更優[27]。張波等治療63例周圍性面癱患者,對照組選取患側陽白、攢竹、太陽、承泣、顴髎、頰車等穴,以及雙側外關、合谷、足三里、太沖等穴行普通針刺,熱敏灸患側翳風穴,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熱敏灸神闕穴,共治療30 d,結果表明針刺加用熱敏灸神闕穴組愈顯率較對照組提高7.24%[28]。張聰等選健側地倉透頰車穴,常規針刺健側瞳子髎、太陽以及合谷穴,采取平補平瀉法,留針20 min,在此基礎上加用紫外線照射患者莖乳突孔,結果提示合理控制紫外線的治療量可以有效提高周圍性面癱患者的預后[29]。
2.6 分期選穴針刺治療 臨床上根據病程的時間將周圍性面癱分為急性期(發展期)、恢復期(靜止期)、后遺癥期(恢復期),根據不同時期,其面神經水腫程度不同,病性的虛實及病位的深淺不同,故不同時期選取的針刺方法也不盡相同。劉更等治療周圍性面癱急性期患者,治療組在西藥治療的基礎上予以分期針刺方法,在急性期(1~7 d)應用淺刺法,選取患側地倉、頰車、顴髎、陽白、翳風、瘈脈,在恢復期(8~14 d)采用普通針刺,選穴地倉、頰車、顴髎、攢竹、下關、陽白、太陽、翳風、牽正、瘈脈和健側合谷,并隨癥加減,在愈前期(15~28 d)采用電針治療,所選穴位為恢復期基礎上加兩側足三里,并于攢竹-陽白、翳風-牽正、頰車-地倉、顴髎-下關連接電針疏密波治療,對照組同樣在西藥治療基礎上使用常規針刺法,穴位選擇和針刺方法同恢復期。結果發現治療組面部殘疾指數量表軀體功能評分高于對照組,社會功能評分低于對照組,H-B面神經功能分級均優于對照組。說明分期針刺可降低急性期周圍性面癱患者血清IgA、IgG、IgM水平,改善面神經功能[30]。承淡安認為對于周圍性面癱的治療可分為初期(7 d內)、中期(7 d到1月)和末期(1月以上),且正常人初次選穴不宜超過10個,老弱婦孺及部分體衰患者選穴不超過5個[31]。黃文韜治療周圍性面癱急性期選取患側陽白、迎香、地倉穴予以毛刺法治療,淺刺患側翳風、太沖、風池以及健側合谷,恢復期以局部取穴為主,后遺癥期以透刺為主,外加電針,結果表明其療效優于單純普通針刺[32]。王韻等將120例急性期周圍性面癱患者分為4組,分別于3 d內,第4、6、8天進行針刺治療,觀察發病第7、14、28天的Portmann評分,發現小于3 d時間內針刺介入面癱的Portmann評分均高于其余3組,提示針刺越早介入周圍性面癱療效越、預后更好[33]。喻淑珍按照發病時間將周圍性面癱應分為發展期(1周)、靜止期(1~3周)和恢復期(3周至3月),發展期在淺刺基礎上辨證選穴,靜止期以透刺為主,恢復期可透刺、深刺、多刺,還可配合電針及雀啄灸法,結果提示,在發展期針灸介入其H-B評分更低、多倫多面神經功能評定表評分更高,可促進面部炎性滲出物吸收,緩解神經性炎癥水腫[34]。
3 討論與展望
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療效確切,不僅可以改善預后,還可縮短病程,其簡、便、廉、驗受到了病患的廣泛認可。但仍有幾點問題值得思考:首先,臨床上對周圍性面癱的分期尚無統一標準,其直接影響到針刺方法與穴位的選取,且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的發病機制尚未明確;其二,臨床對針灸量化的隨機對照研究較少,應進一步探討周圍性面癱的針灸刺激強度、針灸時間、針灸穴位等量化標準;其三,患者的情緒對于周圍性面癱的預后至關重要,臨床發現緊張、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會延長患者的治療療程及康復時間,且不良的預后會加重患者的心理負擔,降低生活質量。目前臨床上對本病的藥物、針灸等療法研究較多,但對周圍性面癱患者的心理治療研究較少,今后可疏導患者心理協同治療周圍性面癱。
筆者建議:第一,針灸可在早期介入周圍性面癱的治療,急性期(1周內)予以局部遠端取穴,取穴宜少,針法宜輕刺,此外還可取對側合谷、顴髎、牽正穴施以溫針灸,此階段可迅速減輕局部水腫壓迫促進面神經恢復;周圍性面癱恢復期(7~30 d內),治療上可于患側局部取穴,常用陽白、四白、顴髎、頰車、地倉、迎香、內庭、健側合谷穴,加用百會、四神聰、神庭、關元引氣歸元,足三里補脾益氣,在患側翳風穴予以溫針灸,結合閃罐療法;周圍性面癱后遺癥期(發病1個月以上),如不重視易發展為難治性面癱,治療上可在常規針刺基礎加用透刺、電針、閃罐、按摩灸等方法治療,選穴在精不在多,且后遺癥期患者可在局部透刺基礎上加用平衡對刺,滯針提拉等針刺方法;第二,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療效確切,應進一步加強周圍性面癱的機制研究;第三,在開展臨床觀察的同時引入多種評價系統,客觀評價治療的療效;第四,完善并細化周圍性面癱的分期及診療方案,發揮針灸最大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