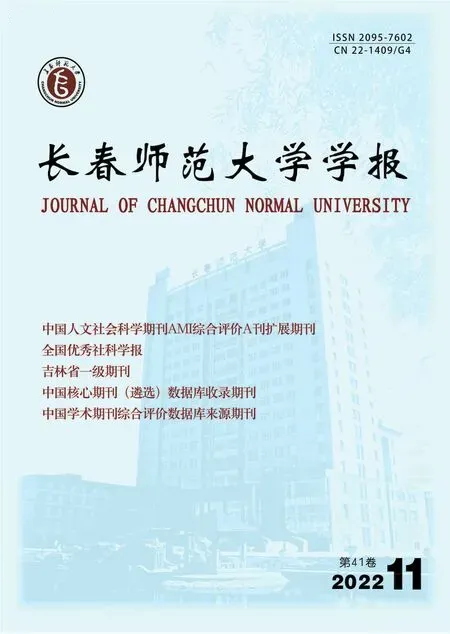福建紅色文化研究述評
鄭超群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 社會與文化學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001)
紅色資源是我們黨艱辛而輝煌奮斗歷程的見證,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紅色血脈是中國共產黨政治本色的集中表現,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源泉。[1]福建作為擁有光榮革命傳統和豐富紅色文化資源的“紅土地”,不僅留下了眾多的革命遺址、革命文物等物質財富,還有許多值得傳承發揚的紅色精神財富。
福建紅色文化研究肇始于21世紀初,經過近20年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本文從紅色文化內涵的界定,福建紅色文化的總體研究,福建紅色文化的意義、價值研究,福建紅色文化的傳承、開發研究等方面,對福建紅色文化研究成果作梳理與述評,以期助力福建紅色文化的進一步研究與更好的傳承。
一、紅色文化內涵的界定
學術意義上的“紅色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草原上的紅色文化工作隊——記內蒙古“烏蘭牧騎”》一文中。該文對紅色文化的定義是社會主義新文化,以區別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前的舊文化。[2]
較為系統的紅色文化研究始于21世紀初。2002年,譚冬發、吳小斌提出“紅色資源”的概念,從廣義、狹義兩個角度闡述了紅色資源的內涵[3],開啟了紅色文化研究的濫觴。此后,張茂枝[4],彭央華、項波[5]分別介紹了四川廣元市和江西的紅色文化資源,并討論了紅色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問題。
劉壽禮《蘇區“紅色文化”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豐富和發展研究》一文最先提出“紅色文化”的概念。作者認為紅色文化在很大范圍上來說,就是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井岡山、瑞金等蘇區形成的人民的、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6]不過,其將紅色文化的發生地局限在井岡山和以瑞金為核心的中央蘇區,顯然是不完整的。
隨著紅色文化概念的生成,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紅色文化的研究隊伍,從不同的角度定義紅色文化,紅色文化的概念和內涵也逐漸完善和豐富。鄧顯超、鄧海霞將學界關于紅色文化概念的定義歸納為四個方面:文化資源論、革命文化論、先進文化論、特色文化論。[7]
“文化資源論”認為,紅色資源即紅色文化。李實指出,紅色文化資源由物質載體和精神內核兩部分構成。[8]此外,舒毅彪[9]、陳世潤[10]等學者從紅色資源的角度闡述紅色文化的概念和內涵。不過,文化資源論把較多的關注點放在紅色文化的資源性、效益性上,而忽略了紅色文化的精神內核。“革命文化論”認為,紅色文化形成于革命戰爭年代,是一種革命文化。湯紅兵指出,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一種革命文化。[11]劉琨[12]、李康平[1]25等人也持此觀點。“先進文化論”認為,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在實現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偉大歷程中創造出來的先進文化。如王以第認為,紅色文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中國共產黨人、一切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14]王權芳[15],鐘英法、舒醒[16],劉潤為[17]等也持此觀點。“特色文化論”認為,紅色文化具有中國特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如王國梁、帥建平指出:“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階段的活動中創造的特定歷史文化”[18]。黃光文、朱龍鳳認為紅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的“文化現象的綜合體”[19]。江峰、汪穎子指出紅色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是由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等交互作用而形成的。[20]曲鴻亮[21]、管仕廷[22]、韓延明[23]等學者也持這種觀點。此外,還有學者提出“政治文化論”的觀點。如李水弟等認為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代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無產階級政治文化。[24]
上述五個方面對紅色文化概念的界定,只是著眼于紅色文化中的某一項內涵,顯然不夠全面。之后,學界針對這一問題又展開了較大規模的討論。如有的學者將紅色文化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以期完整地呈現紅色文化的全部概念指稱。賴宏、劉浩林[25],渠長根[26]等認為廣義的紅色文化應該擴展至全世界,指在世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創造的各種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狹義的紅色文化特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民族解放與獨立,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形成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周宿峰認為廣義的紅色文化包括所有的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狹義的紅色文化特指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以后,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創建革命根據地地過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27]
隨著紅色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界對紅色文化概念指稱的歸納也逐步完善。不過截至當前,學界對紅色文化的概念指稱和內涵仍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這也是今后紅色文化研究領域可以著力加強的方向。
二、福建紅色文化的總體研究
福建是原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核心區域,是全國紅色文化最為集中和最為凸顯的地域之一。201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民政部共同認定的97個原中央蘇區縣中福建占37個,數量僅次于有“紅土地”美譽的江西。除37個原中央蘇區縣外,福建還有67個革命老區縣、2502處革命遺址、33處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以及14處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紅色文化底蘊十分深厚。
伍延基是較早對福建的紅色文化進行專門性研究的學者,先后發表《國內紅色旅游資源開發戰略研究——以福建省為例》《保護與開發福建紅色文化遺產》等文章,著重討論了福建紅色文化的開發與利用,開啟福建紅色文化研究的先河。
黨的十八大以來,福建紅色文化的研究逐步繁盛。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科研機構編寫了一系列介紹福建紅色文化的叢書,例如《福建省重要革命遺址通覽》《紅土地見證——福建中央蘇區遺址遺跡巡禮》《紅色福建叢書》《中央紅色交通線研究》等,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其中尤以《紅色福建叢書》影響最廣,該叢書分為《福建紅色遺址》《福建紅色文物》《福建紅色詩文》《福建紅色歷史》《福建紅色人物》《福建紅色文化》六卷,系統而全面地介紹了福建的紅色文化。以《福建紅色詩文》為例,該書分“詩詞文賦”“家屬遺言”“軍歌民謠”三輯,較全面地收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領袖、革命先烈在福建戰斗時寫就的詩詞、書信、文章等,以及福建中央蘇區傳唱的民謠和軍歌。[28]
隨著福建紅色文化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者開始具體分析福建紅色文化的特點,總結福建紅色文化體現的精神。湯家慶是較早進行此項研究的學者之一,他指出“福建紅色文化是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29],并將福建的紅色文化按照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進行了分類。吳鴻雅認為福建紅色文化是指福建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時期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30]。陳再生指出,福建紅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在福建省區域內創造并加以整理的革命文化,具有首創性、多元性、融合性特點。[31]曲鴻亮總結了福建紅色文化所體現的精神。[21]此外,劉傳標[32]、游孫權[33]、鄢姿[34]等學者先后對福建的紅色文化加以詳細的介紹和研究,總結了福建紅色文化的特點。
近年來,福建紅色文化研究進入新的階段,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王建南《福建紅色文化》。該書從歷史考察的角度,對歷史文獻進行了全方位梳理,并從福建革命歷史、紅色思想理論、紅色精神、紅色歷史名人、紅色文化教育事業、紅色文化遺址等六個方面,較為系統地概括了福建的紅色文化,指出并總結了福建紅色文化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35]此外,還有《福建紅色文化實踐教學指南》《福建紅色文化》《福建紅色文化的歷史與傳承》等成果。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問世,體現了福建紅色文化研究的水平,推動了福建紅色文化研究的不斷進步。
三、福建紅色文化的價值、意義研究
當前,諸多學者討論了福建紅色文化的價值,成果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福建紅色文化體現出的價值及其內涵;二是分析福建紅色文化的當代價值,主要表現為福建紅色文化對青年學子的教育意義。
(一)福建紅色文化體現的價值
湯家慶以“紅色小上海”長汀縣為例,從歷史、文化、時代三個視角討論了中央蘇區紅色文化的精神內涵和價值。他認為福建蘇區紅色文化的精神內涵體現了兩個“交融”:其一是當地的客家文化與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的交融;其二是長汀的“客家精神”與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革命新風尚的交融。[36]陳再生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次具體分析了福建紅色文化的價值意蘊。[31]鄢姿從歷史虛無主義的新特點出發,指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需要有一種與其相對的正確文化,即紅色革命文化。[37]鄢姿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福建紅色文化所體現出來的全局意識、創新意識、堅守意識,可以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精神指引、動力支持和意志支撐。[34]蘭躍銀以福建長汀為例,認為長汀紅色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間具有關聯性,二者之間價值取向相近、價值觀精神相通、價值觀目標相合。[38]
(二)福建紅色文化的教育價值
楊玉鳳是較早進行此項研究的學者。他認為《古田會議決議》生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則,也是新時期進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創新應當遵循的原則。[39]陳德欽則是較早關注地方紅色文化與高校思政教育結合的學者,他以福建三明地區的高校為例,指出紅色文化真正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創新紅色文化資源挖掘利用的聯動機制、完善紅色文化多元傳播平臺、遵循紅色文化傳播規律。[40]陳德欽在另一篇文章中認為蘇區精神與思想政治教育有機結合,既有利于蘇區精神在廣大青年學子心中“生根發芽”,又有利于引導青年學子從“思想世界”回到“生活世界”。[41]
對于地方紅色文化與思政教育的結合,李勁松指出要以福建紅色文化為抓手,將福建紅色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讓學生“真懂”“真信”“真用”,助力青年學子樹立正確的“三觀”。[42]陳暉濤以福建紅色文化資源的運用為例,認為紅色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流,以紅色文化為載體,可以有效地加強思政課教學的針對性和有效性。[43]
此外,呂雅蘭、楊小霞討論了福建紅色文化資源在高中政治課堂中的教學問題[44];馬春玲討論了《古田會議決議》對大學生思政教學的啟示[45];陳春華分析了紅色文化融入公安院校忠誠教育的實踐路徑[46]。
四、福建紅色文化的傳承、開發研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紅色文化的傳承與利用,習總書記曾多次對紅色文化的傳承作出重要的指示和批示。在此背景下,福建紅色文化的傳承與開發研究進入新的高潮,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福建紅色文化的傳承和保護研究;二是福建紅色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研究。
(一)福建紅色文化的傳承、保護研究
吳鴻雅從文化記憶、文化認同、新文化的衍生視角考察福建紅色文化的發展與傳承,認為福建紅色文化體現著“閩人的紅色文化精神與個性”,要通過福建文化遺產來傳承福建紅色文化。[30]苗圃則從文化記憶、文化傳播、文化衍生三個方面著手,指出必須創新路徑,在體制建構、基礎保障上著力,鼓勵社會積極參與紅色文化的傳承、保護。[47]梁偉鳳從構建平衡的文化生態系統視角出發,認為需要拓展紅色文化的發展途徑,構建新的紅色文化發展生態環境。[48]謝彪從現實維度、思想維度、政治維度三個方面討論了傳承好福建紅色文化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指出要創新路徑,多措并舉,加強紅色文化的保護、傳承和弘揚。[49]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在對福建省紅色文化大普查的基礎上指出,福建紅色文化的弘揚、保護需要從深化紅色意識、加強品牌建設、堅持創新思維、實現融合發展等方面努力。[50]涂瑩、徐丹丹認為應該將福建紅色文化作為福建文化形象塑造與傳播的著力點,促進福建文化形象的吸引力、競爭力、影響力。[51]
除此之外,劉傳標[32]、代媛媛[52]、邱明華[53]等學者也分析過福建紅色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問題。
(二)福建紅色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研究
陳建輝是較早分析研究福建紅色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學者。他以閩西紅色旅游資源為例,認為閩西發展紅色旅游具有獨特的紅色資源和綠色資源優勢、區位優勢、交通優勢和政策優勢,在科學規劃、資源整合等條件下可以打造紅色旅游的知名品牌。[54]伍延基指出應在“保護第一”的原則下,大力開發紅色旅游,并針對紅色文化遺產的開發利用提出了若干建議。[55]高居華認為紅色資源良好的開發利用,“是教育人、塑造人、激勵人、啟迪人和服務區域科學發展、推動海西率先跨越”的重要助力。[56]毛立紅認為開發利用紅色文化資源,首先要樹立正確的紅色資源觀,善待紅色文化資源,科學規劃整合紅色資源,走可持續發展之路。[57]吳珍平、周潔指出紅色是閩西最鮮亮的底色,必須開發好、利用好閩西紅色文化資源。[58]方麗真以福建閩西老區的紅色檔案資源為例,指出要“發揮閩西豐富紅色檔案資源資政、育人、勵志的作用”[59],為福建紅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另外,不少學者從文化產業發展角度研究福建紅色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如劉雙對福建紅色文化資源的產業化發展進行了SWOT分析,認為福建紅色文化資源的開發應該堅持文化發展和產業發展相結合的路徑。[60]黃金海從福建區域文化特色角度出發,認為在福建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中要彰顯紅色文化的價值,“變紅色文化為紅色產業、紅色產品和紅色財富”。[61]黃敏以三明市紅色文化資源保護開發為例,從文旅融合視角討論了紅色文化思想內涵的挖掘和時代價值。[62]姜宏從產業融合的視角指出要打造閩西紅色文化旅游品牌文化,加快區域紅色旅游產業融合。[63]
此外,《福建黨史月刊》雜志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集中討論了福建紅色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吸引了學界的關注。如易向農《弘揚紅色文化,助力福建發展——福建省紅色文化建設的歷史資源、時代實踐與前瞻思考》、石仲泉《修好福建蘇區黨史,弘揚蘇區紅色文化》等。
五、福建紅色文化研究展望
福建紅色文化研究發軔于21世紀初,近20年來經過諸多學者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別是關于福建紅色文化的本體研究成果最為豐富。
紅色文化的本體研究是指對紅色黨史人物、紅色文件資料、紅色遺址遺跡等方面的研究。《福建黨史月刊》雜志曾發表過一系列關于福建紅色文化本體的文章,在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毛澤東潛行閩西山村》《鄧子恢與閩西三年游擊戰爭》《張鼎丞的風范》等。此外,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研究機構先后編寫了一系列反映福建紅色黨史人物、紅色遺址遺跡等內容的書籍。關于福建紅色文化本體研究的內容,張埔華[64]曾有過較為詳細的述評,本文不再贅述。
近年來,紅色文化研究進入新的高潮,成為新時期的顯學。但通過仔細檢讀已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我們發現福建紅色文化研究仍存在一些缺憾,留待學界進一步研究。
(一)高水平研究成果較少,重復性研究多
福建是紅色文化資源最為集中和最為凸顯的地域之一,但與其他省域的紅色文化研究相比,福建紅色文化研究不論在研究成果數量上還是在高水平研究成果上都有不小的差距。以同樣是紅色文化資源豐富的江西省為例,我們通過中國知網以“福建紅色文化”“江西紅色文化”為主題進行檢索,分別檢索到101篇和318篇文獻。在檢索到的文獻中,以“福建紅色文化”為主題的學術期刊發文量有63篇,其中核心期刊發文量僅4篇,占6%;而以“江西紅色文化”為主題的學術期刊發文量為189篇,核心期刊發文量為27篇,占14%。
此外,福建紅色文化研究還存在重復性研究多的情況。學者們的關注點多集中在紅色文化資源較為集中的閩西、閩北地區,對閩東、閩南等地的紅色文化研究涉獵較少。而在閩西、閩北地區的紅色文化研究視角多集中在少數知名度高的紅色文化,例如蘇區精神、古田會議、才溪鄉調查精神等,對一些知名度不高的紅色文化的研究較少。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復性研究的情況。
福建紅色文化研究之所以存在上述缺憾,主要原因是對福建紅色文化史料的挖掘不夠。福建的紅色文化資源非常豐富,紅色文化資源的歷時分布基本涵蓋中國共產黨從土地革命戰爭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但長期以來,福建紅色文化的專門性史料較為缺乏,尤其是缺乏能夠總覽福建全省的紅色文化史料。例如,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的討論中,由于相關史料挖掘不夠和記載的缺乏,福建長汀、寧化是否是長征出發地還存在較大的爭議。
材料是研究的基礎,是新觀點、新發現的前提,是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紅色文化研究的基石。對此,學界還需要在大力發掘福建紅色文化史料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發展福建紅色文化研究。
(二)紅色文化研究成果受眾面窄
研究紅色文化的,最終目的是講好紅色故事,弘揚紅色文化,發揮好紅色文化的教育引導作用,把紅色精神融入民族血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紅色文化的傳播要“用事實說話,增強表現力、傳播力”。[1]但就當前福建紅色文化研究的情況而言,福建紅色文化研究存在受眾面狹窄、傳播力薄弱的情況。雖然學者們在福建紅色文化研究過程中有意識地與當代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相連接,但這類研究大多是在綜合性歸納的基礎上籠統地介紹福建紅色文化,粗略地總結福建紅色文化精神的特點,很難使青年群體產生情感共鳴,因而也就很難真正滲透至學生群體和人民群眾的心中。因此,如何擴大紅色文化研究成果的受眾面,真正發揮紅色文化的教育作用,讓紅色精神融入民族血脈之中,是今后紅色文化研究有待進一步探索的重要內容。
(三)紅色文化研究程度深淺不一
福建紅色文化存在研究程度深淺不一的情況,具體表現為對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研究較多,對重要文件研究較少;對知名度較高的紅色文化研究較多,對知名度較小的紅色文化研究較少;對原中央蘇區的紅色文化研究較多,對非原中央蘇區的紅色文化研究較少。例如1947年中共閩浙贛委員會召開的龍山會議知名度較小,也不是發生在原中央蘇區,但它卻是閩浙贛區黨委城市工作的轉折點,在我黨組織開展城市工作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65]然而,學界在論及福建紅色文化時,很少涉及龍山會議以及會議文件《論開辟第二戰場》。因此,今后的福建紅色文化研究既要鞏固已有成果,更要深入挖掘那些雖然名氣不大但意義重大的紅色文化資源。只有這樣,才能使福建紅色文化體現的精神譜系更加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