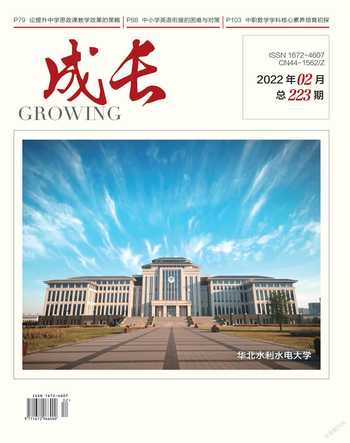黔東南中部苗族地區蝴蝶圖案系統搜集與數字化記錄
李周穎 周朝翔






摘 要:蝴蝶圖案在貴州省黔東南中部地區的苗族中是具有獨特寓意的民族圖案,其上承載了苗族幾千年的歷史傳承,也承載了少數民族的精神內涵和文化內涵。系統地收集整理蝴蝶圖案的現狀和研究情況,并進一步拓寬思維,發現未來研究的方向和發展前景,是我們這一次項目研究的目的。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完善民族傳統圖案庫,為蝴蝶圖案應用研究發展新方向,傳承苗族傳統文化。
關鍵詞:蝴蝶圖案 苗族文化內涵 民族文化現代應用
1 引言
苗族是黔東南中部最主要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文化傳承悠久,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誕生了許多獨屬于其民族的優秀文化。由于沒有文字,“傳承”這一責任被賦予在苗族的圖騰上,蝴蝶圖案便是其一。圖騰文化在苗族的手工藝品中的應用除了最基礎的花紋美化作用之外,還蘊含著原始審美意識,有輸出文化內涵和傳承民族精神的作用。時過境遷,少數民族文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遭遇了沖擊,苗族的圖騰文化漸漸淡出人們視野,蝴蝶圖案在如今鮮少被人知曉。近年來,學者們聚焦苗族文化,圖騰文化,發表了大量相關文獻。本文將基于研究現狀綜合論述蝴蝶圖案及其發展前景。
2 蝴蝶圖案造型分析
在現今的研究文獻中,對于苗族蝴蝶圖案的具體造型分析已經趨于完整。蝴蝶圖案有著不同的線條結構和色彩組合,蝴蝶圖案的造型樣式反應著苗族人民的審美意識。
2.1 造型樣式
黔東南中部苗族的蝴蝶圖案不是完全的來源于大自然的實物呈現,也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想象和自我表達。創作者通過各種線條和多樣的幾何圖形來將蝴蝶的形象具體呈現在苗族的各種民間作品中。蝴蝶圖案的藝術美感具體就表現在虛與實之間的變幻和結合。具體表現在以下幾種方法:
主觀造型——通過作者主觀的依托自然界的蝴蝶外形特征或者是想象中的蝴蝶媽媽造型,呈現著虛與實的變幻交錯,但整體造型呈現出完整的蝴蝶圖案,雖然略顯夸張,但主要沒有脫離蝴蝶的形象。
代替造型——不再是作者主觀看到的,而是用其他動植物的形象代替,用別的事物間接地“制作”出一個別有趣味的蝴蝶圖案。借用其他圖案的可變幻性結合成一個整體上完整且視覺上具有蝴蝶特征的圖案。
轉換造型——此種蝴蝶圖案的造型將“蝴蝶”這個形象進行了解構,苗族人民奇思妙想,用各式圖案替代蝴蝶圖案中的一部分,代替后的部分與蝴蝶原有的部分相差較大,夸張而充滿想象力。此時的蝴蝶圖案已經超脫了現實中原本具有的生物物種,而是與傳說中的神靈所聯系,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圖騰,承載了更多苗族藝術家想象的部分。
此外,蝴蝶圖案中符號構成豐富,主要從點和線兩方面得以分類分析。[1]點多用于細小的元素點綴,靈動多變,也出現在幾何狀的蝴蝶圖案中,起到平衡和畫龍點睛的作用;線連接了蝴蝶圖案的整體,任意舒展的線條也展現出圖案中所蘊含的生命和自由精神。
2.2 蝴蝶圖案的色彩美學
蝴蝶圖案在苗族服飾紋樣和苗族蠟染中的色彩搭配體現出極具特色的民族美學。苗族蝴蝶圖案的色彩運用上非常大膽,多用紅,白,綠,藍,黑,黃等顏色[2],特別是象征著熱情與生命力的紅色。生于山林長于溪河的苗族人民,在創造藝術品的時候將與自己共同生活的大自然融入其中。民間的藝術往往由創作者的內心而發,色彩的多變體現出苗族人民對于生命和自然的熱愛。
現今社會的發展將原始傳統的蝴蝶圖案本就多變的色彩中融入了更多新的花樣,也給未來蝴蝶圖案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無限可能。
3 意象與圖騰崇拜
3.1 “蝴蝶媽媽”的圖騰意象
“妹榜妹留”即苗族口語中的“蝴蝶媽媽”,“蝴蝶”并不僅是自然界中真實存在的生物意義上的蝴蝶,而是一種圖騰意象。
圖騰崇拜的先決條件便在于人們賦予圖騰寓意。《楓木歌》中:“媽媽妹榜留,心愛小水泡,同他去游方,和他配成雙”“游方十二天,成雙十二夜,懷十二個蛋,生十二個寶”[3]蝴蝶媽媽被黔東南苗族稱為祖先,孕育萬物,是自然的神靈,也是萬物的母親,蝴蝶媽媽這個意象也被苗族的祖先賦予了生命,繁衍,自然等寓意。
事實上,在古歌的研究中,語言的“蝴蝶”所代表的實物有很多,例如蛾,蠶,蝴蝶等等,可知苗族語言中的“蝴蝶”很有可能指的是肉眼可見的大部分由卵到雙翅的昆蟲,這也是黔東南苗族生活環境中極容易見到的生物,與苗族人民息息相關。雖然“蝴蝶”這一語言所代表的意象不僅僅是生物意義上的蝴蝶,但沒有改變的是“破繭成蝶”,生物從蛋之中誕生這一概念。這一意象代指了多年以來苗族人民熱愛生活,渴求突破,渴望新生,想要和蝴蝶一樣自由飛翔的愿望和民族信念。
3.2 圖騰崇拜
圖騰崇拜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藝術則起源于生活。卵生,破繭,飛翔,這樣與人類生存繁衍截然不同的方式,又恰恰是苗寨附近的山野間生物與大自然聯系最緊密的方式。長期以來的自然生活中,苗族的祖先會試著去觀察蝴蝶這樣的卵生動物的生長過程,或因為好奇,或因為不經意間,這些卵生生物生于山林淺水,在自然里破繭,最終實現自我。在歷史的變遷中,好奇變作崇拜,原始崇拜由此誕生。在古老的先祖的眼中,進入“蛋”既是新生,從而變成自由飛舞的蝴蝶。苗族先祖虔誠地將圖案繪制下來,原始崇拜開始上升為民族圖騰,新生,自由,與自然相連成為了民族信念,他們希望自己如同蝴蝶一樣,用繭包裹而最終能夠飛上天空。
另外,生殖崇拜也是圖騰崇拜中的重要因素。苗族歷史艱辛,人民長期生活在征戰遷徙中,苗寨所在的山區的環境惡劣,繁衍人口是民族立足的根本,而蝴蝶廣泛寓意著多子多福,“生殖”這一概念在苗族古歌的故事中也能夠體現。
3.3 蝴蝶圖案的多民族對比
蝴蝶圖案在多民族的刺繡等手工藝作品中都有體現,例如中原漢族同樣喜歡并且習慣繪制,刺繡蝴蝶。與中原漢族相比,黔東南苗族地區的蝴蝶圖案最大的不同就是將蝴蝶圖案賦予意象并升華為民族圖騰。
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中原漢族,其服飾,首飾上的圖騰形狀都不是憑空想象,是按照自然界中的生物或景物形象轉變而來的。生物形態轉變為圖案造型的過程緩慢而充滿變數,無形之中,最后各民族形成的圖案造型雖然個體上有所不同,背后承載的文化內涵也不同,但是究其根本是有所關聯的。
苗族在歷史變遷中不斷與其他民族接觸,交流,文化也因此產生沖擊碰撞。中原漢族對于蝴蝶圖案的喜愛與苗族相通之處便在于都看重其寓意,而不同之處則在于中原對于蝴蝶圖案止于蝴蝶本身,苗族地區對于蝴蝶圖案的崇拜更是如上文所說,以“蝴蝶媽媽”作為意象,擴大到卵生動物。在造型樣式上,兩者之間也有區別,中原的蝴蝶圖案色彩斑斕多用于刺繡品上,與自然界生物形象一致,多與相關聯的花鳥樹等形象同時出現,而黔東南中部的苗族地區則將“蝴蝶”意象剝離,在藝術作品中幾乎是單獨存在。上文對于黔東南苗族地區蝴蝶圖案的造型分析中,也論述了苗族的蝴蝶在虛與實之間變換,不是單純的自然界的蝴蝶,并不注重寫實,賦予了更多精神意義。
4 蝴蝶圖案的現代應用方式
圖案給人的是視覺傳達,蝴蝶圖案作為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群體意識和民族精神。在蝴蝶圖案的發展應用中,不能脫離圖案的本質內容和形態。
迄今為止,市面上少數民族圖案的應用多被運用于旅游景點的紀念品和民族特色產品包裝中,但買的人少之又少,基本上整個中國都是這樣,設計都大同小異,千變一律,都沒有合理利用民族文化和民族圖案進行設計應用,不僅體現不出民族文化特色和圖案特征,更談不上文化傳承。[4]
結合當今社會發展方向,依靠互聯網傳承蝴蝶圖案是絕佳途徑,其次還有建筑設計,服裝設計,首飾設計,家居設計,產品包裝設計等。圖案的設計應用固然重要,但對于傳播群體和消費群體來說,經濟價值、實用性、視覺美觀才是關注的重點。
想要傳統蝴蝶圖案的創新,應用新的物質載體必不可少,它的價值,需要物質載體來體現。
結合當下社會現狀,傳統蝴蝶圖案的創新設計應用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
4.1 服飾紋樣的創新設計
傳統民族圖案誕生之初,受到當時文化、思想和技術的影響,大多呈現出抽象、復雜的形態。而當今社會,服飾圖案以簡潔、明快為美,對大多數人而言,繁瑣復雜的傳統圖案,并不能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因此,蝴蝶圖案在服飾紋樣設計中的創新,因遵循簡潔明快的風格,在此條件下,可以把復雜圖案分解成個體元素,直接、或組合個體元素應用于服飾之上。(如蝴蝶圖案、印花系列民族風格服裝、民族文化聯名服裝等)
4.2 蝴蝶造型的首飾設計
傳統圖案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如同當今的平面設計,傳統的圖案造型比現代的平面設計或許更勝一籌。傳統圖案的造型復雜多樣,但它們的設計大都遵循幾何性規律。與服飾紋樣相同,現代人對首飾的要求,同樣崇尚簡約風格造。
傳統圖案紛繁復雜的特點很明顯,構成一幅完整的圖案可能包含著成百上千的設計元素,將其應用到現代首飾設計中時,可以拆解整幅圖案,劃分成個體元素,將不同的紋樣元素應用到不同種類的首飾中去;結合現代美學設計,將蝴蝶圖案象形化,設計改造成具有現代美學風格的新形象,再應用于首飾設計。傳統紋樣與現代設計完美結合,既保留蝴蝶圖案的基本造型紋樣,又符合了現代人的審美需求。
4.3 蝴蝶紋樣產品包裝設計
產品包裝注重實用價值和經濟價值,最重要的是滿足消費者心理需求,吸引顧客消費,為企業盈利。傳統圖案色彩鮮明,圖案復雜,具有視覺美感,文化底蘊深厚。將傳統蝴蝶圖案應用到商品包裝上,能使消費者感受到濃郁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美妝產品“花西子”,整個產品主打東方古典風格,將民族各種傳統元素應用到產品造型、產品包裝上,這種民族韻味濃厚的風格,吸引了不少消費者。產品也不能盲目的選擇傳統圖案包裝,不同的傳統圖案具有不同的蘊意,作為一個消費者,包裝往往是定義一件產品好壞的第一要素,是考慮買或者不買的第一道把關。
4.4 蝴蝶圖案文創設計
近幾年,文創產品成為當下熱大門。“文創”顧名思義,文化和創新。各地的博物館緊跟熱潮,將自己館中的藝術品用新鮮的方式展現出來,其中故宮就是文創的代表。從杯墊,包包,發簪等日常用品到融入了故宮元素的口紅等,這些文創作品能夠深刻地體現傳統文化,讓現代產品被賦予了更多傳統寓意,也讓消費者重新認識了自己身邊的優良傳統文化。優秀的文創產品打破了人們對于這些圖案老舊,落后的刻板印象。蝴蝶圖案作為代表苗族人民民族文化與信念的圖騰,同樣也可以通過文創產品設計的方式融入到現代社會中。同時,黔東南中部苗族的刺繡,蠟染等技術也可以借此發揚。如何將民族文化融入現代生活這一問題便可以通過文創產品來解決,設計優良且極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打開了新的交互形式,用新鮮的技術來傳播民族文化。
互聯網是當今社會的潮流前線,在此背景下,未來對傳統民族圖案的記錄可呈現出更多的形式,如以蝴蝶圖案為主的IP形象設計、網絡藝術品、互聯網文化產品、網絡游戲設計元素等等。
5 蝴蝶圖案的數字化記錄
對蝴蝶圖案的收集和數字化整理都需要對圖案進行采集工作,根據已有條件,圖案的采集工作基本由相機攝像完成,在有限的條件下,對數量不詳圖案的收集,是一項困難的工作,且存在我們尚未擁有的技術條件,對收集效果有不小的影響,致使我們對蝴蝶圖案的收集和數字化整理仍不完善。在實地收集圖案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由于自然條件和人為原因,很多原生態的圖案殘缺不全或丟失,只流傳于老輩人和研究人員的口中,并未見過實物。對于這些殘缺和丟失的蝴蝶圖案的收集,均未能達到圖片歸庫收集和數字化收集整理的目的,僅存于文字記錄。攝像不能記錄沒有圖像的東西,雖然文字記錄達不到攝像記錄的視覺效果,但對蝴蝶圖案文化的追本溯源,我們便采用文字記錄的方式,通過口錄、古籍,整理成文獻記錄資料。史料古籍記錄不全、調查口述記錄不一,文字記錄也有缺陷。
新興技術不斷出現,未來可采用的記錄方式也會不斷完善。VR技術、3D技術,是當前新興科技中的熱門數字化技術,在很多文物保護中,都采用了這些技術(如山西云岡石窟,通過3D掃描,獲取石窟、石像的尺寸、色彩、空間結構等一系列數據,給石窟建立一份“數字檔案”,再結合這些數據,打造了一套基于VR眼鏡的沉浸式石窟體驗系統以及3D打印復制的石像。觀賞者不僅能看到完整的石窟形制、精美逼真的造像,甚至連石窟歷經千年風化的痕跡都清晰可見。),這些技術的運用對我們后續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隨著科技發展,技術革新,我們會不斷借助新技術,不斷完善蝴蝶圖案的收錄工作。
5 結語
現今國內外對于黔東南中部苗族蝴蝶圖案的研究趨于完整,多數文獻都圍繞著歷史文化內涵進行了整體的分析,只有少部分從其造型,應用等方面深入研究。在現今的研究基礎上,蝴蝶圖案總體的形象和文化內涵已經基本完整,但研究現狀止于蝴蝶圖案本身,沒有對未來的造型應用以及蝴蝶圖案的系統搜集與記錄進行更多的分析研究。苗族蝴蝶圖案的搜集與研究以及其未來生存方向還要依托現代技術的革新發展,民族研究學者的不懈努力。
大創項目:本文系2020年貴州師范學院省級課題“黔東南中部苗族地區蝴蝶圖案系統搜集與數字化記錄——丹寨、雷山、臺江、施秉、黃平”(編號:S202014223048)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盧超.黔東南苗族刺繡蝴蝶紋樣裝飾設計研究[C].湖南工業大學,2015.
[2] 彭川.黔東南苗族蝴蝶紋飾研究[D].重慶師范大學,2016.
[3] 石朝江.云霧·楓木·卵生──苗族早期唯物主義思想萌芽[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04):.
[4] 趙浩.少數民族圖案的收集和創新[J].時代教育,2012(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