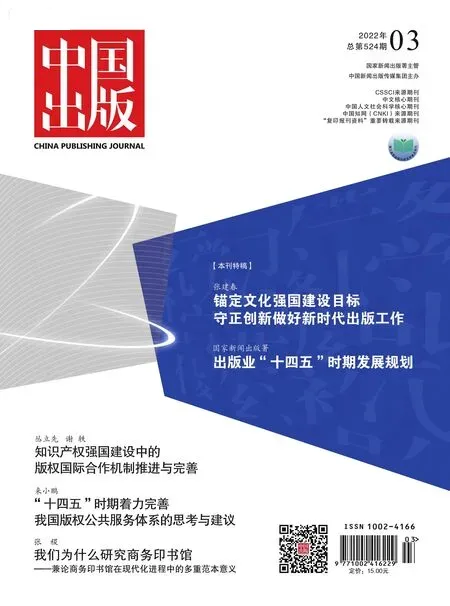基于圖書海外館藏分析的學術出版走出去發展策略研究*
□文│徐立萍 李 旦
作為國家文化發展戰略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出版業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學術出版是出版業的重要板塊,是國家思想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傳承的直接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引起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當下,需要學術出版積極推動反映中國核心價值觀和當代中國各項事業發展創新的思想成果、科技成果、文化成果等走向海外,“努力進入主流市場、影響主流人群”,[1]構建中國學術國際話語體系,也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要求。圖書海外館藏是出版走出去國際影響力評價的重要因素,本文試圖以此為切入點展開研究,探求近年來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現狀及其海外影響力的真實狀況,為未來學術出版走出去戰略實施建言獻策。
一、中國圖書海外館藏數據分析
1.研究背景
海外圖書館館藏量是衡量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出版物出口情況”的重要指標之一。之所以選用這個指標作為重要衡量依據,是因為世界圖書館系統采選、入藏一本圖書有嚴格的篩選體系和標準,雖然各國情況各有不同,但就其采選方針而言,學術水平和創新性是圖書質量評價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世界圖書館系統的圖書收藏數據,是我國學術出版機構國際出版水平的集中、客觀體現,是其學術出版國際影響力的核心指標之一。[2]
本文基于近年來在學術出版走出去領域具有一定影響力的5個項目:輸出版引進版優秀圖書推介活動、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絲路書香出版工程,選取2016—2019年曾在這些項目中立項的117家出版機構作為研究對象,剖析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報告中2016—2020年上述機構的海外圖書館藏數據,以透視近年來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概貌。
2.全國圖書海外館藏總量分析
研究對近5年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研究報告披露的117家學術出版機構的數據進行匯總處理,對2016—2020年中國圖書入藏世界圖書館種數及其占當年出版圖書種數的比例,勾勒近年來我國出版走出去的總體實力狀況;通過不同年度學術出版機構海外館藏量情況的變化,分析我國學術出版機構走出去戰略能力的變化趨勢;通過近年來“走出去”能力提升較快和步伐放緩趨勢較為明顯的出版機構,歸納其變化的共性與差異點,有針對性地為對策提供論據支撐。
根據2014—2021年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研究報告[3]披露的數據和官方披露的我國出版總量數據,整理2016—2020年我國出版圖書種數和進入世界圖書館收藏系統的種數,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2016—2020年我國出版圖書海外館藏量統計表
表1數據顯示:2016—2020年我國出版圖書海外館藏量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在2020年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報告中提到,海外圖書館藏品種的下降,主要是內外因的雙重作用。一方面,限于館藏空間以及采購經費,海外機構用戶對于紙質圖書的采購,特別是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的圖書館一直呈現逐年下滑狀態;另一方面,近年來我國出版機構著力于優化圖書結構,改變了多年來依靠新品種拉動產業規模的發展模式。
3.學術出版機構圖書海外館藏量變化趨勢分析
自我國實施出版走出去戰略以來,各家出版機構積極響應,經過不斷探索和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本文就117個研究對象中2021年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報告中排名前20的學術出版機構2016—2020年圖書海外館藏數據進行整理,形成表2。

表2 2021年報告中排名前20的學術出版機構2016—2020年館藏數據統計表
表2數據表明,20家出版機構館藏總量變化跟全國出版機構海外館藏量總體情況保持一致,海外館藏品種數出現逐年下降,總體趨于平穩的趨勢。進一步分析這20家出版機構2016—2020年排名變化趨勢可見,排名第5位的科學出版社、第9位的化學工業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2位的法律出版社近年來海外館藏量走勢起伏較大,經歷了從2016年的高位到后4年的急劇下降。與此同時,排名第3位的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第14位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第17位的浙江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第18位的貴州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近年來海外館藏量走勢相對平穩,國際出版能力一直處于較好的狀態,這些機構在出版走出去戰略推進過程中所做的工作和策略值得研究和分析。
4.走出去能力提升較快的出版機構
自2003年實施出版走出去戰略以來,各家出版機構做了各種探索提高自身走出去能力,在這個進程中,學術出版機構也在不斷地努力。不過從實際結果來看,不同機構差異較大。在本文117家研究對象中,2016—2020年館藏量排名提高速度較快的6家出版機構,按照其提高位次比率由高到低的順序排名依次為: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從2016年排名第10位躍升到2020年的第3位,提高了7位;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從2016年排名第99位躍升到2020年的第38位,提高了61位;中國書籍出版社有限公司從2016年排名第90位躍升到2020年的第40位,提高了50位;貴州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從2016年排名第56位躍升到2020年的第26位,提高了30位;機械工業出版社從2016年排名第39位躍升到2020年的第19位,提高了20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從2016年排名第63位躍升到2020年的第31位,提高了32位(見表3)。

表3 2016—2020年我國圖書海外館藏量提高較快出版機構排名
在全國圖書海外館藏總量呈下降趨勢的背景下,上述6家出版機構2016—2020年整體館藏總量呈現上升趨勢,從這6家出版機構的排名綜合表現來看,近5年在全國近600家出版機構總體排名中海外館藏品種數均位列前100以內,有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排名一直保持在前10以內,說明這些出版社在學術走出去方面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獨特優勢,形成了一定的海外影響力,反映了其在走出去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努力,通過實踐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5. 走出去穩步發展的出版機構
從2016—2020年海外館藏排名變化情況來看,有7家出版社整體發展較為穩定,始終處于行業發展引領地位,包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科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等,它們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模式對其他出版機構推動走出去工作具有一定意義。
二、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變化現象解析
從我國學術出版機構海外館藏數據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近年來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一些共性特征與個性差異,歸納總結起來,可為未來我國學術出版更好地走進去提供一定的思路、啟示。
1.學術出版走出去受國家宏觀政策驅動,發展逐漸趨于理性
2001年我國第十個五年計劃明確提出“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在積極‘引進來’的同時,實施‘走出去’戰略”。[4]我國出版業積極貫徹響應,一些國家級的走出去項目和活動有力地助推了中華文化的對外交流。如由中國版協、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出版參考雜志社聯合主辦的“年度輸出版引進版優秀圖書推介活動”;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原新聞出版總署組織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自2006年正式實施以來強有力地打造了我國圖書實物出口平臺;2009年由原新聞出版總署正式組織實施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鼓勵資助大量優秀圖書走向國際,這些工程的持續發力,是近年我國圖書海外館藏量持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2015年3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就沿線國家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重點作了詳細安排和部署。[5]新聞出版業積極作為,重大項目“絲路書香出版工程”有力地拓展了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發展空間,為我國學術出版在絲路沿線國家搭建了強大的平臺。
同時,根據《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研究報告(2016版)》的分析,2015年中國圖書進入海外館藏量創歷史新高,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關當代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法律等中國主題圖書持續成為全世界各個方面高度關注的熱點,主題出版的帶動性作用十分明顯”;加之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有關歷史史料、檔案文獻、回憶錄以及專題學術研究著作的出版大幅增加”,[6]這些因素共同帶動了2015年的數據高調上揚。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國家宏觀政策驅動和相關資助項目支持,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成效明顯。但近年來,學術出版走出去呈現理性供需匹配的發展模式。我國出版業近年來著重優化圖書結構,因控制圖書品種數量的影響,圖書供應側數量有所減少,同時海外圖書館囿于館藏空間和采購經費的限制,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出版業的沖擊,我國圖書海外館藏數量出現下滑趨勢;但另有一些出版機構通過優化圖書質量,實施有效的走出去發展策略,實現了館藏品種數增加和海外館藏量排名提升的突圍,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2.學術出版走出去能力的提升依賴于好的戰略
有效的戰略有助于提高學術出版機構的國際化能力。近年來學術出版國際化能力發展較好及提高較快的出版機構著眼于戰略的制定與執行,為整個行業有效實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經驗。
其一,選題特色明顯,注重學術品牌錘煉。長期耕耘于學術出版的專業機構,能夠將中國優秀文化資源與自身的出版優勢完美結合,運用長期積累的品牌影響力形成集群效應,打造獲得國內外廣泛認可的高端學術出版品牌,服務于國家的戰略決策。如中華書局的歷史典籍圖書已經被世界公認為是中華書局的“金字招牌”,其出版的《隋書》《遼史》等一大批歷史典籍在世界圖書館收藏數量排名中一直遙遙領先,[7]凸顯其穩定強大的知識生產能力和輸出能力。再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長期致力于高端學術作品版權輸出,該社出版的《何以中國》(俄文)等5個項目獲批“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生死關頭》(越南語、白俄羅斯語、泰語)等12個項目獲批“絲路書香工程重點翻譯資助項目”,《火槍與賬簿》(英文)等5個項目獲批“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建筑史》《中國雕塑史》《圖像中國建筑史》(英文版)獲“國家版權輸出優秀獎”。[8]尤其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國學流變與傳統價值觀》一書,已累計簽約20個語種出版12個版本,該書版權輸出簽約量自2015年以來逐年增加,如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出版的該書英文版電子書下載量,2016年是17次,到2018年已增加到1096次。該書獲評第16屆輸出版引進版優秀圖書推介活動優秀輸出版圖書及中國出版集團優秀走出去獎,同時其版權輸出的成功還帶動了該社一大批同類學術圖書的多語種版權輸出,如“文史悅讀”“三聯講壇”等系列,得到海外出版商的關注與青睞。[9]
其二,陣地布局意識強[10],廣泛開展海內外合作。將中文版優秀圖書版權成功輸出海外并與海外出版機構建立形式多樣的合作伙伴關系,是學術出版走出去的重要路徑。如以專業學術研究見長的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在版權輸出方面成績令人矚目,其已與新加坡、韓國、尼泊爾等國家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系,如與新加坡圣智學習集團數字平臺合作出版的《呂思勉全集》、與韓國研究基金會合作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等。該社出版的不少學術專著獲得版權資助,如輸出版權的英文版《金匱要略譯注》入選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波蘭語版《品味書法》入選2016年度“絲路書香工程重點翻譯資助項目”,該書已于2017年8月出版;韓文版《周易鄭氏學闡微》入選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11]
其三,打造地方歷史文獻精品,擴展區域文化世界影響力。據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研究報告分析,近年來由于各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特色區域文化品牌建設,越來越多的地方出版機構主動作為,在助力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挽救整理地方歷史文獻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這些文獻適于館藏,加之紙質版圖書與數據庫建設同時進行,使得近年來地方出版機構在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一些實力強的機構的優勢日益凸顯出來。如廣東省出版集團以嶺南文化為根基,在內容建設和出版社建設中實施專業化、板塊化、特色化、品牌化思路,積極推動嶺南文化出版創新和轉化發展,創建“嶺南文化研究發展基地”,打造“大灣區區域簡史”“嶺南學派叢書”等品牌。其旗下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全球定位》《嶺南文化》等著作均成功實現版權輸出,[12]其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全球定位》一書入選2018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立項名單。
其四,嚴守學術出版規范和標準,保障學術出版物高品質。與國際學術出版規范接軌,是保證出版物質量獲得國際認可的重要環節。比如國際通行的學術著作匿名評審制度,執行力度不同必然會影響出版物品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堅持嚴格執行此項制度,其出版的《天朝的崩潰》入選劍橋出版社的“劍橋中國文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該書在中國出版時進行了匿名評審。[13]
3.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面臨的短板
其一,專業科技類學術著作譯本語種較為單一。專業科技類出版機構憑借其在專業科技領域的耕耘與積淀,其科技類專著一直是獨占優勢的出版品種,中國相關領域著名學者的英文著作或中文版的英文譯本是學術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近幾年有關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主題出版類圖書廣受海外關注,加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大家把走出去重心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一方面,當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注的重點是我國的“改革開放的經驗”和“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等;[14]另一方面,雖然英文為世界通用語言,但如果僅以這一種語言作為專業科技類學術專著的輸出文種,勢必影響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傳播和推廣。
其二,部委所屬專業科技出版機構的產品載體過于單一。據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報告披露,新世紀以來,一些知名部委社憑借其長期積累的品牌優勢成為國家各類出版資助的主要受益者,而與此同時表現搶眼的還有少兒類和文藝類圖書。相較于部委社,文藝社和少兒社的“文化創新與知識生產水平是在市場拼搏中形成的”。[15]從這個角度講,這幾年恰逢國家資助向走出去傾斜,部委社產品中紙質教材類又占相當比重,在數字出版、數據庫出版等產品群還不甚豐富的當下,其走出去呈現出下行趨勢也成為必然。
其三,一些高校出版機構國際出版平臺搭建不夠寬廣。當前出版走出去最主要的幾種途徑中,更多集中在版權輸出、合作出版以及出版物出口等方面。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前提下,很多實力雄厚的出版機構尤其是高校為了提高其學術出版走出去的效果,積極與海外著名出版機構展開各種合作,同時為了提高針對性和本土化能力,紛紛在海外設立編輯部,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以色列、羅馬尼亞、蒙古設立海外分支機構,通過搭建國際出版平臺,不斷增強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軟實力;又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自2018年正式成立國際業務中心以來,已經在世界范圍建立了保加利亞中國主題編輯部、波蘭中國主題編輯部、法國中國主題編輯部等10多個海外編輯部,拓展海外業務,服務國家走出去戰略。相比而言,還有一些高校出版機構在這方面步伐邁得不夠大,思路還不夠寬,直接影響其學術出版走出去的效果。
三、學術出版走出去的未來發力點
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建設文化強國是我國文化建設的核心要求,新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已取得一定成績,但仍有很大可拓展的空間。未來學術出版走出去的發力點,可以從這幾個方面加大探索和實踐力度。
其一,建立出版走出去政策導向長效機制。出版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從國家到各相關職能部門,從高校、學術研究機構到行業協會等都積極作為,政策與資金配套支持等不斷增加協調完善,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從目前看,各項目之間尚未形成高效協同機制和效果評價機制,還不能很好地調動我國出版業的行業聯動;結合各出版機構的突出特點進行戰略布署存在不足,我國西部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地緣優勢和民族同源優勢未得到充分發揮。未來應建立政策導向長效機制,從全局視角協調各方資源形成合力,有的放矢地給予支持,努力構建我國學術出版的國際話語權。
其二,技術加持,打造學術出版走出去新型模式。新技術的日新月異不斷為出版行業提供新的契機,但客觀上對我國圖書海外館藏量也形成一定的沖擊,只有充分利用新技術,大力開發數字產品形態,實現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升級,方為可持續發展之道。我國學術出版機構應該在搭建數據庫產品群上下功夫,打造凸顯我國學術話語權的知識譜系。
其三,加強人才隊伍培養,提高國際出版能力。具有國際視野、學術造詣深厚、通曉學術研究前沿的編輯策劃團隊,享譽海內外學術圈的各領域頂尖作者團隊,精通國際出版貿易規則同時對走出去業務熟悉的版權貿易運營人才團隊,高水平的翻譯團隊等,都是學術出版走出去的有力支撐。從我國74家學術出版機構的學術出版問卷反饋信息可知,大部分出版機構從事走出去項目的工作人員非常有限,國際化人才短缺成為制約出版走出去的一大困境。
四、結語
本文的統計基礎是全國近600家出版機構2016—2020年海外館藏數量變化總體情況,同時由于本文研究時間范圍取值僅5年,結果受當年各種因素綜合影響較大,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僅作為總結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近年來的實踐成果與經驗教訓的一個視角。此外,本文從中國圖書海外館藏量近幾年的變化趨勢入手展開分析,未涉及國際出版能力其他方面,研究視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結論也會有不盡全面之處,是后續繼續此方面研究的依據和動因。
注釋:
[1]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55
[2][15]“海外館藏:中國圖書世界影響力”報告(2014版)[N].中國出版傳媒商報,2014-08-26
[3]參見公開披露的歷年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報告(2014—2019年)。該報告是由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社、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評估中心課題組研究并發布,自2012年首次發布以來,持續每年發布更新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EB/OL].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699.htm
[5]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EB/OL].https://www.yidaiyilu.gov.cn/yw/qwfb/604.htm
[6]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研究報告(2016版)[EB/OL].http://www.cbbr.com.cn/article/106080.html
[7][14]何明星.從中華書局海外館藏看中國學術圖書的世界影響力[J].出版發行研究,2012(12)
[8]張嘉薇.《焦點訪談》報道三聯書店走出去成果[EB/OL].http://www.cnpubg.com/export/2018/0524/39378.shtml
[9][11]尋找中國出版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徑——海外館藏影響力TOP30案例推介[EB/OL].http://www.cbbr.com.cn/article/130290.html
[10]周慧琳出席第四屆中國學術出版走出去高端論壇并致辭[J].今傳媒,2017(8)
[12]倪成.專訪廣東省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譚君鐵[EB/OL].http://www.gdpg.com.cn/index.php?g=&m=article&a=index&id=861&c id=19
[13]李旦.學術出版走出去與對外話語體系建設[J].出版廣角,2017(9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