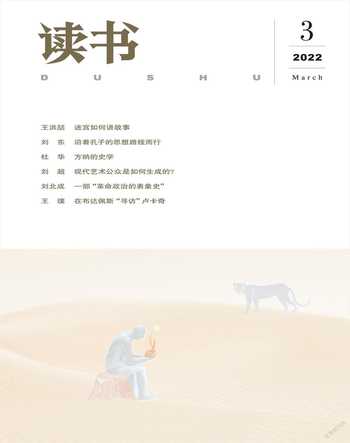一九四三年陳寅恪的中山大學之行
李欣榮
抗戰軍興以后,沿海高校紛紛內遷,開始流徙不定的非常態辦學。廣州中山大學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播遷,先經粵西羅定,復遷云南澄江。一九四0年八月,在代理校長許崇清主持下,中大啟程回遷粵北樂昌縣的坪石鎮。至十二月,全體師生經過滇、黔、桂、湘數省安抵坪石,并于次年一月正式開課。
坪石地處樂昌縣的西北角,北鄰湖南宜章縣,南通廣東乳源縣。粵漢鐵路在鎮圩西南四公里處經過,設坪石站,附近兼有武水航運,與戰時省會韶關城水陸相通,交通甚為便利。當地宗祠、會館、民宅被校方租作教室、宿舍,因師生人數眾多而不敷使用,各院系只能在以鎮圩為中心的方圓百里內分散辦學。
中大之后,嶺南大學農學院、培正中學、培道中學(聯合設立培聯中學)等廣州學校也相繼遷來,中大教授吳康又在此創立中華文法學院,使得坪石弦歌不輟,成為粵北著名的文化中心,與同處南嶺的文化城桂林交相輝映。引人矚目的是,抗戰時期南嶺的崇山峻嶺之間,各地學校的學術交流密切,田野考察頻繁進行,呈現出和平時期難得一見的“山中”文教興旺的歷史場景。一九四三年夏天陳寅恪從桂林坐火車穿行于南嶺,冒險赴坪石講學,生動詮釋了這段歷史的特殊性與豐富性。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已執教廣西大學一年的著名史家陳寅恪,在學生李堅的陪同下抵達坪石中山大學。陳氏此行以文科研究所特約教授的身份講學一周。歷史系刊物《 現代史學》 報道當天盛況,“全所同學郊迎十里,親赴車站迎接”。次日,研究所主任楊成志開會致歡迎詞,其中有譽陳氏為“友機照明彈”句,感謝其長途跋涉,冒險來坪講學。
其時研究院設在坪石鎮圩。下屬的文科研究所分為中國語言文學部和歷史學部,共有專任教員七人,兼任兩人。文學院在鎮圩旁之鐵嶺,包括中文、外文、哲學、歷史諸系,共有專任教師三十五人,助教十人。相較文學院,研究所的師資顯得尤為薄弱。
一九四二年六月陳寅恪從香港抵達桂林,中大聞訊即聘其為研究院教授。七月一日,鄭師許教授受楊成志委托,由研究所先行墊支四百元旅費,前往桂林邀請陳氏來坪任教。校方以“敦促新聘教授來校,盡可用函電商議,且事前未向校方報告”,并未發還墊支旅費。九日,院長崔載陽提出陳氏乃“國內著名學者,聘請不易”,特別為其申請旅費一千五百元,但校方以“經費奇絀,似難照辦,且以前亦無付過是項費用”為由否決此議。楊成志、崔載陽等人深知陳寅恪來校任教的學術價值,盡力邀請,但校方恪守程序未能通融。其時陳氏患病,此次邀請終未成功。
九月,校方改聘陳氏為特約教授。主任楊成志以陳氏“學長文史,名蜚中外,為我國文史學家之威權者”,提出頗優厚的聘任條件,令其最終受聘。中山大學檔案顯示,聘期從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七月,校方每月致送講學禮金四百八十元,陳氏每學期來所講學一次,由積存禮金一次性致送講學旅費兩千四百元,余款四百八十元作為招待之用。陳寅恪本擬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下旬前來而未果,此次來坪將兩次講學并作一次。雖然不符當初的聘任條件,中大仍以兩次經費的總和五千七百六十元接待陳氏,并將旅費先行匯至桂林。楊成志申請經費時強調:“此關系本大學延攬著名學者及尊師重道之舉!”
七月一日的《國立中山大學日報》這樣介紹陳寅恪:“氏以專門研究南北朝史、隋唐史與以梵文比對漢譯佛經,及精通十余種語言文學,蜚聲中外,其專門著作因欲矯今日輕易刊書之弊,甚少刊行,僅出版《唐史概要》一書。其重要論文散見《清華學報》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這篇報道的認識相當到位。特別是提到《唐史概要》一書(初名《唐代政治史略稿》,出版時改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九四一年底大體方告完成,自序作于一九四二年七夕,初版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刊于一九四三年五月,顯示文科研究所方面對于陳氏研究動態相當了解。
其時文科研究所以楊成志為首,與鐘敬文、容肇祖、岑麒祥等教授皆是偏向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或下層民俗、思想等方面,創辦的《民俗》季刊頗有影響;朱謙之的“現代史學”派(包括陳嘯江、陳安仁、董家遵等),注重現代史、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研究,皆與陳寅恪的研究方向相距較遠。
文科教師中,與陳氏有舊、淵源最深者,當數羅香林。羅氏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論文《客家源流考》得到陳的指導與肯定。隨后升讀清華研究院,兼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肄業。畢業后長期任教中山大學,隨遷澄江,再返坪石。一九四二年一月以留職停薪的方式離開中大,至重慶講學,與傅斯年、顧頡剛等發起“中國史學會”。中大對陳寅恪動向之了解,似與羅香林有關。關于陳氏此次長途講學,羅香林后來回憶:“陳師以遷在粵北的中山大學,堅約他前往演講,乃由桂林搭火車,經衡陽至坪石,住了幾日。”事后,中大的舊同事還告知羅氏:陳寅恪在演講中提及推薦羅撰寫《唐太宗傳》之事,末說:“我料羅先生于開始撰作時,對李唐皇室的姓氏問題,也必極難下筆:到底依照老師的說法好呢?還是依照岳丈的說法呢?”說完便哈哈大笑。因為羅香林岳丈朱希祖堅信舊史官書所言,認為李唐皇室父系出自隴西李氏,而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則論證李唐皇室或是北魏李初古拔之后裔,或出自趙郡李氏“破落戶”。兩說相左而學界意見傾向于陳,如王育伊在《燕京學報》的書評指出,“此千余載史家未發之覆”。陳寅恪對于前輩朱氏的詰難心知肚明,卻私交仍篤,羅香林身處其間并不為難。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引陳流求筆記:“父親曾冒轟炸的危險,到粵邊坪石當時的中山大學臨時校址短期講課。”其時右眼失明、行動不便的陳寅恪接受中大研究院的禮聘,冒險行此次講學之旅,原因耐人尋味,此須追溯其在廣西大學的教研狀況才能明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陳寅恪攜妻女歷盡艱險,從香港經廣州灣抵達桂林。其本擬繼續入川,至李莊史語所與傅斯年會合。然其抵桂以后兩月臥病在床,困居旅社。嘗作詩賦此境遇:“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夢過。殘剩山河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遂決定暫留廣西大學一年,任教法商學院政治系,并請中英庚款會出資設一講座,每周三小時,以補貼個人收入。
一直力勸陳氏迅速入川的傅斯年對此甚為不滿,認為這是囿于出身廣西名門的陳夫人唐筼之故。傅在信中有言:“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處,恐嫂夫人在彼比較方便,但從遠想去,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遲)來川為宜。”同時因陳氏未到李莊,傅斯年堅決反對核發其專任研究員薪水,不惜以去就相爭,力主沿用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的辦法:以專任研究員名義支取兼任研究員薪水。
其時武漢大學資深教授張頤去信傅氏,請其允許陳氏離職史語所,讓其過來主持研究所工作。傅氏特將致張頤回信抄與陳氏一觀,其中有數言頗形突兀:“寅恪歷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內地,而寅恪倫常甚篤,故去年幾遭危險。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又謂:“為貴校辦研究所計,寅恪先生并非最適當者,因寅恪絕不肯麻煩,除教幾點鐘書以外,未可請其指導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創辦一研究部,寅恪決不肯‘主持’也。”
傅與陳既是姻親,又是同學兼同事,此事處置在人情上稍欠斟酌,不但向外人點破其猜測的夫人因素,而且有斷絕陳氏去往高校之意。傅斯年稍后致信中研院總干事葉企孫說明此事經過,亦意識到此言不妥,“弟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也”。
陳氏回信雖然贊同傅之決定(此前已速將專任聘書寄還),對于不肯指導研究事亦未反駁;但卻“聲明”滯留桂林乃是出于己意而非唐筼,“內人前在港,極愿內渡;現在桂林,極欲入川。而弟卻與之相反,取拖延主義,時時因此爭辯”。
陳寅恪在信中強調拖延入川乃為生活所迫:“現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過八九百元之間,而弟月費仍在兩千以上,并躬任薪水之勞,親屑瑣之務,掃地焚(蚊)香,尤工作之至輕者,誠不可奢泰。若復到物價更高之地,則生活標準必愈降低,臥床不起乃意中之事。”僅以住所為例,陳氏任教廣西大學一年,前半年居良豐山中的“雁山別墅”(陳氏命名)。陳美延后來回憶所謂“別墅”之簡陋,有一次風雨來襲,竟將廚房的墻體吹倒,幸未傷人。后半歲遷入校內條件較好之“半山小筑”。多年以后,唐筼寫下詩作《憶故鄉二首》。第一首《憶良豐山居》:“日暖桂香穿澗樹,夜深楓影上簾櫳。山居樂事今成夢,欲再還山只夢中。”第二首《憶半山小筑》:“群雞啄食竹籬下,稚女讀書木榻前。此是雁山幽勝景,名園回首已風煙。”可見其時物質生活甚為艱苦,但唐筼身在故鄉,精神上頗為放松,有益其心臟病之療養。
對于陳寅恪而言,居住桂林最大的不便在于無書可讀。桂林雖有戰時文化城的美譽,但是廣西大學缺少中古史研究可用之書。其致傅信有云:“弟在此無書可看,但翻閱四庫珍本中宋(集部)耳,所以思入蜀。”其時四川岳池陳樹棠的“樸園書藏”向大學師生和外來學者開放,林森、于右任、郭沫若、張瀾等名流賦詩品題。陳氏亦有詩寄題:“滄海橫流無處安,藏書世守事尤難。樸園萬卷聞名久,應作神州國寶看。”透露出戰時陳氏對于研究書籍的渴望之情。
正因為戰時無書可讀及自身藏書的散失,陳氏無法撰寫窄而精的專題論文,而開始著手通論性的著作,先后完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名著。陳氏經歷了抗戰五年的亂離歲月之后,對于指導與提攜后學變得不遺余力。抗戰前,陳氏閉門著書,不理外事,亦如傅斯年所言甚少指導后學。但是到達桂林以后,情況大不相同。羅爾綱其時作為中研院社科所的助理研究員,因工作關系在桂林旅館暫住。陳氏看到住客牌便主動過訪。陳氏逐篇評論其考證文章,從晚上七點半一直談到十一點旅館關門。羅爾綱事后“深感榮幸,也極感驚奇。陳先生是研究教導隋唐史和撰著文學考證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國和他距離那么遠,我又不是他的學生,他為什么這樣關心我的著作呢?”陳美延亦注意到其父在山上散步時,如果遇到研究所的同事,“則會站著談個不休”。這在戰前的清華園,恐怕難以想象。若細心梳理陳氏的酬應文字,不難發現,為后學陳述、朱延豐、鄧廣銘、姚薇元、張蔭麟寫序跋或挽詩,均在桂林時期。失明、無書和戰爭,明顯改變了陳寅恪待人接物的方式。
陳氏在廣西大學一年合約期滿之時前往坪石,除了履行特約教授的職責,恐怕還有考察中大環境,考慮能否安身之意。如果合適,則可免長途跋涉入川之苦。就書籍而言,文學院所藏中西圖書、雜志數量達一萬五千多冊,雖不如史語所的十三萬余冊,但似優于廣西大學“無書可看”。不過,中大教師在坪石的生活極為艱苦。容肇祖的教授工資每月三百六十元(一九四三年七月升至四百二十元),戰后向乃師胡適訴苦,在粵北中大“敝衣鶉結,風雨敝廬,這樣的又經歷三年”。陳氏來坪固然可得優待,恐怕也是改善有限。更關鍵的是,坪石地處粵漢鐵路入粵之要沖,日軍若要打通大陸南北交通線,坪石肯定不能幸免。一九四四冬的豫湘桂戰役導致中大再次遷徙四散,也印證了這一點。作為行動不便、挈家帶口的長者,陳氏為安全考慮,入川可能才是長久之計。
陳寅恪此次講學以“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為主題,原定在研究所演講五次,分別為:一、《五胡問題》;二、《清談問題》;三、《魏晉南北朝讀書方法之一——合本子注》;四、《南朝民族與文化》;五、《宇文泰及唐朝種族問題》。張為綱時為中大語言學系講師,兼文科研究所研究員,將前兩場的講座記錄刊于報端(收入《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附錄),名為《五胡問題及其他》與《清談與清談誤國》,且附言云陳氏演講只有兩個專題。考慮到陳氏在坪石只是逗留一周,其中還有兩天赴曲江,參觀與唐代佛教極有關系的南華寺,很可能因為時間倉促,而將后三講省略了。
抵坪之次日,陳寅恪首講《五胡問題及其他》,內容為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胡人的種族問題。《國立中山大學日報》報道:陳氏演講“語氣透辟,闡發無遺”。研究所諸教授、研究生為此開展討論,“一時論學空氣極為濃厚”。張為綱的聽講記錄有一段相當重要,今引用如下:
羯人石姓,系以居石國得名。……羯人與歐羅巴人為同種,其語言亦屬印歐語族,尤以數詞與拉丁文近,僅“萬”字系自漢語借入,讀若Tinan。此由漢語“萬”,古本為復輔音,如“躉”“邁”二字聲母之別為“T”“M”,即系由此分化而成。今藏文“億”為Hman,“H”即“T”聲變;俄語“萬”為Toman,則又自蒙古語間接輸入者也。
這是從“萬”的古漢語、拉丁文、藏文、俄語和蒙古語等語言比較入手,證明羯人與歐羅巴人同種,其語言亦屬印歐語族。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五年秋天周一良第一次往聽陳氏課程,內容正是五胡的羯人,“論證羯族來源及石氏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國,謹嚴周密,步步深入,尤其涉及中亞各族問題,為我聞所未聞”。陳氏展現出的比較語言學之卓識令其折服。若比較萬繩楠整理的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陳氏《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在羯人部分,卻看不到利用多種語文論證民族異同的論述。或為陳氏主動略去不講,也可能因為記錄者缺乏語言學知識而漏記。坪石演講的記錄者張為綱專攻音韻訓詁學,著有專書《古音探源》,具備相關學養,故能為我們留下重要證據,說明陳氏在四十年代初猶未完全放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而將之作為輔助論證中古民族、文化問題之工具。
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為朱延豐《突厥通考》作序時,宣稱自己于西北史地之學,“但開風氣不為師”。借以告知并世友朋:“年來自審所知,實限于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于其間。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謂馮軾而觀士戲者。”揣測其真意,一方面婉拒評價朱著的學術水準,暗示因為十年前的師生緣分和選題而作序;另一方面,表明自己仍愿對西北史地做局外之觀察,但不再專門從事相關的研究。
這一轉向背后實有深遠的學術思考。在西人東方學的推動下,西北史地的研究已進展到比較語言學的階段,必須通曉梵、藏、突厥、回紇、拉丁等多種語言,才有可能進入一流研究者的行列。陳寅恪在語言工具上,在國內學者中固不作第二人想,但終不能較西人獨擅勝場。而且陳氏已意識到“語文學”治史有其危險性,“許多碑文都是用藏文、回紇等文寫的,如無專門的語言學造詣,不小心很易出錯,用此類史料必須十分謹慎。本人‘愿開風氣不為師’”(李涵一九四四年唐史課筆記)。因此其研究領域才會從四裔回歸本部,投入“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陳寅恪在坪石的第二講《清談與清談誤國》,討論魏晉時代“清談”與政治的源流關系,論及“竹林七賢”和陶淵明等人之事例,內容大致不出一九四五年發表的《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作于桂林,哈佛燕京學社在成都出版單行本)之范圍。未曾演講之第三題《魏晉南北朝讀書方法之一——合本子注》,可從陳氏《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序》(一九四八年)窺知其主旨。所謂“合本子注”之法,正如裴松之所示:“凡承祚(陳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又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而疑不能判者,則并皆抄內,以備異聞。”裴注《三國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酈道元注《水經》,均用此法而成名著。第四題《南朝民族與文化》與第五題《宇文泰及唐朝種族問題》,應屬隋唐史“兩稿”的內容,茲不詳論。可見陳氏對于授課講學,準備頗為精心,所講皆是研究有素或最新完成之研究,決不肯敷衍了事。
一周以后,陳寅恪結束在坪石的講學活動返回桂林,八月踏上艱難的入川之路。其與中大的緣分,要等到一九五二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才重新接續,開始其在康樂園最后十八年的跌宕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