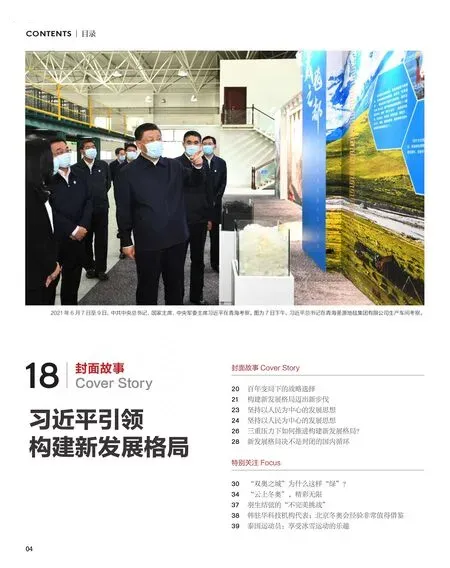省域、城市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
陳珂

2021年5月9日,在海南海口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上,湖北館內的“海百合”智能音樂機器人正在用揚琴演奏中國古典民樂。?
隨著吉林省和河北省公布2021年經濟數據,31省份的經濟數據全部出爐。此前1月17日,2021年中國經濟“成績單”公布,以全年增速8.1%超過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6%以上”的預期目標。
“從增速看,偏離全國平均增速的省份不多,基本上向全國平均水平收斂、趨近。”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耀在接受《中國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疫情散發等多重考驗,2021年我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趨穩特點在各個省份的經濟數據上也得以體現。但在經濟總量和增速等某些具體指標上,一些省份、城市實現跨越式突破和恢復性增長。
去年,廣東省迎來經濟總量連續領跑全國其他省份的第33個年頭,成為國內唯一一個GDP超12萬億元的省份,占到全國GDP總量的10%以上。值得關注的是,根據公開數據,自1998年超過新加坡、2003年超過香港、2007年超過臺灣,如果以去年平均匯率計算,廣東GDP總量如今又超過韓國,對“亞洲四小龍”均實現超越。
決定區域發展快慢的關鍵因素包括創新能力、利用外部要素資源和市場能力。廣東省外向型經濟拉動大,近些年在創新驅動上取得了明顯的成果。“比如深圳的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大疆等企業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領軍企業,研發專利的成果轉化以企業為主體,對市場非常敏感。這跟北方城市有明顯的不同。”陳耀向記者表示。
2021年,北京、上海的經濟總量分別以40269.6億元、43214.8億元聯袂突破4萬億元。“這種狀態可能會維持幾年不變,也有可能被追趕上。”陳耀表示,2021年深圳以30664.85億元、廣州以28231.97億元的總量緊隨其后,且北京、上海目前處在成熟階段——北京謀求減量發展,上海也在控制人口,這種情況下一是發展空間受限,二是發展結構面臨向高精尖轉變的現實需求。
副省級城市是我國中心城市中僅次于直轄市的重要一環。2021年,GDP排在前十的省會城市依次為:廣州、成都、杭州、武漢、南京、長沙、鄭州、濟南、合肥、福州,所有上榜城市均為萬億俱樂部成員,前五名屬于全國GDP十強市,后五名則屬于全國GDP二十強市。2020年時為萬億俱樂部成員的西安,去年則由于疫情原因被擠出前十。
《中國報道》記者梳理發現,隨著東莞市的加入,目前全國已有24個萬億城市。“常州、煙臺、唐山、徐州等城市去年經濟總量在8000億元左右,如果增速穩定,萬億成員有可能在今明兩年擴充為28個。”在陳耀看來,萬億成員未來會不斷增加,但城市發展不僅是經濟總量的增長,也是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
“城市規模擴大、人口增加會帶來消費能力和消費規模的提升,經濟形態便會發展為以服務型經濟為主導,但這種趨勢往往對制造業帶來巨大的沖擊。”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基礎,陳耀提醒,進入萬億城市俱樂部的成員,制造業占比不能下降過快,保持占比在25%~30%。他舉例稱,上海市制定的“三個底線”中,制造業占比不能低于25%的底線一直堅持到現在,使其經濟總量規模保持穩定。他同時強調,大城市的制造業不是普通制造業,一定是高精尖結構的先進制造業、高端制造業。
以省為基本單元,2021年經濟增速超過兩位數的一個是湖北,一個是海南。
2020年,湖北遭遇嚴重疫情沖擊,GDP增速一度創下1978年以來的新低。2021年,湖北經濟實際增長以12.9%領跑其他省份,總量達到50012.94億元,重回全國第七,其中武漢城市圈經濟總量也跨入3萬億元規模。
“湖北從疫后重振中站起來,回歸常態。”湖北省政協常委、武漢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鄒薇表示,2021年湖北新增高新技術企業4100戶,在兩年內實現了高新企業數的倍增,背后不僅體現“湖北速度”,更是質量提升。
2020年以來,疫情之下經濟數據的同比增速出現劇烈波動,2020年、2021年的“兩年平均增速”被用來刻畫我國經濟復蘇的進程。在陳耀看來,受2020年負5%低基數效應影響,湖北經濟增長迅速,但兩年平均增速只有3%,不及5.1%的全國平均水平,“完全恢復到疫情前水平還需要時間”。
2021年,海南地區生產總值以11.2%的增速僅次于湖北,兩年平均增速排全國第一。有數據側面顯示,2021年海南11個重點園區的營業收入第一次突破萬億元,以占全省不到2%的土地實現了全省四成以上的稅收。陳耀認為,盡管海南經濟總量在全國排第28位,但其經濟增長的明顯特點是投資型驅動。“海南自貿港的財稅優惠政策大大放寬和降低了投資準入門檻,很多建設項目在2021年集中分批次開工,帶來了較大的投資增量。”
受訪專家還注意到,山西省去年的經濟增速可謂亮眼——名義增速以27.98%領跑全國,增速處于第二位的內蒙古為18.2%。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所黨委書記楊開忠在接受《中國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山西的好成績離不開去年煤炭和鋼材價格的上漲,“要想保持或者在站位上再往前,必須加快產業轉型步伐,過度依賴煤炭是行不通的。”他還表示,貴州8.1%的增速也符合資源型城市的屬性,“我國重化工業發展較快,能源需求大,貴州不僅能提供煤炭,還有豐富的水電資源”。
2021年7月,河南的特大暴雨災害被自然環境部列為2021年全國十大自然災害之首,造成全省1478.6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1200.6億元。受此影響,河南省2021年經濟增速在全國省份GDP增速中排在第10位。日前,河南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強調“加快災后重建”,并在其他重點任務中增加了對應急防災的相關表述,包括推進省氣象防災減災中心建設、構建防澇工程體系、建設一批調蓄工程等多項舉措。
透過數據,區域發展差距再次得到印證。從GDP增速看,自第21名往后的甘肅、寧夏、天津、吉林、河北、陜西、河南、內蒙古、黑龍江、遼寧、青海等都位于我國東北、西北或華北地區。
陳耀認為,格局和往年相比沒有太大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因疫情和極端天氣沖擊最終加入進來。據他長期觀察,南北間相關指標的差距真正開始拉大是在“十三五”以后。“一般來講,一兩年內的短期波動不能算作地區間差距,如果是長期持續的下降,就表明經濟發展處在衰退狀態。”
但就東北三省而言,吉林6.6%、黑龍江6.1%、遼寧5.8%的增速雖然都低于全國平均,不過總體上有所加快。數據顯示,2021年吉林省投資同比增長11%,位列全國第四。陳耀表示,去年東北的外資外貿增速也較高,比如在進出口貿易方面,黑龍江為29.6%,遼寧為17.6%;外資方面,遼寧為27.1%,黑龍江為10.8%,表明通過開放拉動經濟振興效果比較突出。
“當然,去年全國的進出口貿易形勢也較為不錯。”2021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39.1萬億元,貿易規模第一次突破6萬億美元。陳耀認為,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東北的外貿依存度較低、外向型經濟弱,從2021年的數據來看,東北振興正處在提速期。但他也表示,東北作為老工業基地,工業增速備受關注,“黑龍江工業增速7.3%,遼寧略微低一些,從側面說明東三省的經濟恢復不平衡”。
楊開忠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由于結構性和區位性差異,一些重要的戰略性機制主要在南方布局,北方的活力釋放相對就慢一步。“比如自由貿易港,南方的海南有區位優勢。當然也有國際性的因素,最終體現在戰略性機制安排上,比如北京證券交易所2021年掛牌,晚于上海、深圳、香港很多年。”
他向記者分析稱,南北差距擴大問題歷來受到重視。針對上一輪南北差距擴大,我國出臺了東北振興戰略,新一輪南北差距擴大下,又先后于2014年出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2019年出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目前,南北差距擴大受到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重視是合乎情理的,但客觀講,南北差距沒有想象的那么大,目前還不構成我國區域差距的第一特征。”楊開忠表示,未來對北方戰略性機制的安排上要加快。
2022年一季度已經進入下半程,截至目前,全國31個省區市均制定出了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
記者梳理發現,絕大多數省份的新目標都低于2021年的實際增速。其中湖北省降幅最大,從12.9%下降到7%左右。“考慮到疫情目前仍在反復,無論從投資、出口還是消費拉動來看,湖北省都不可能達到2021年的水平,2022年目標設定相對來講要保守一些。”

也有一些省份將目標上調,如河南提速到7%,西藏設定在8%左右。對此陳耀分析說,極端天氣災害是偶發因素,河南提高預期目標較為客觀,西藏的經濟增長構成比較特別,增速設計上更多考慮到川藏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工程的投資、建設落地,會在今年有明顯的拉動作用。“總體來說,考慮到疫情和穩增長因素,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是高質量,而不是過度追求GDP總量。”
此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判斷,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無疑會受到影響,因此可以看到它們的增速設計大概是在去年增速的60%上下波動。”陳耀表示。
“三重壓力”下,經濟發展如何破局,各省份能否如期甚至超額完成經濟預期目標?在陳耀看來,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作為一個整體的大環境在施加影響,對于經濟活躍的廣東、江蘇、浙江等會產生影響,但它們的抗壓能力也比較強,“真正受沖擊大的是那些經濟韌性不強的地區。”
陳耀表示,應對“三重壓力”的路子已經很清晰,核心是要在創新驅動上繼續發力,同時產業支撐也很重要。“對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是應對壓力非常好的經驗,等同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能和需求端匹配,提高發展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