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腎健脾湯治療Ⅳ期糖尿病腎病臨床研究
李小健 石寶成 蘇朝東 莫 超 李國源 陶志虎△
糖尿病腎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病最為常見的慢性微血管并發癥之一[1]。本病早期可表現為腎小球濾過率增高,繼而出現蛋白尿、腎小球濾過率下降,若不積極干預則可進展成為終末期腎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2]。本研究從中醫經典立意,結合臨床經驗以及現代藥理學研究,采用益腎健脾湯治療DN Ⅳ期患者,取得良好效果,現將研究匯報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擇2019年1月—2019年9月在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腎、風濕、內分泌科門診和住院的70例DN Ⅳ期患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及對照組各35例。治療組中男16例,女19例;平均年齡(67.97±7.50)歲。對照組男18例,女17例;平均年齡(68.37±5.97)歲。2組患者在此次研究前均已經臨床、生化、病理診斷明確,診斷標準如下文所述。2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2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 (例,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符合2型糖尿病合并DN的診斷標準,參照2013年出版的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分會《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3]中所采用的1990年WHO頒布的糖尿病診斷標準,明確診斷2型糖尿病并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腎臟損害,同時符合Mogensen診斷分期中DN IV期的分期診斷標準[4]:尿常規檢查尿蛋白顯性,尿蛋白定量>300~500 mg/24 h,腎小球濾過率下降,病理可見部分腎小球硬化,灶狀腎小球萎縮并出現間質纖維化。
1.2.2 中醫診斷標準依據“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田德祿主編的《中醫內科學》[5]及《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6]中消渴的相關內容,參照2002年《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6]及《中醫診斷學》[7]的有關內容制定脾腎兩虛證型作為觀察證型,必備主癥和次癥中的2項及以上癥狀者,同時參考舌相、脈象,并通過對患者的證候分析判定為脾腎兩虛者,即可診斷。主癥:尿濁、神疲乏力、少氣懶言、肢體浮腫、面色晦暗。兼癥:納呆嘔惡、便溏泄瀉。
1.3 納入標準①符合中醫、西醫診斷標準;②年齡在大于30歲而小于90歲,性別不限;③有獨立行為能力且自愿參加本研究的患者。
1.4 排除標準①近半年內出現過酮癥酸中毒等嚴重的糖尿病急性并發癥的患者;②尿量<700 ml/24 h或者內生肌酐清除率<15 ml/(min·1.73 m2),或需要透析者;③患有嚴重的心、腦系統或其他系統疾病者;④孕婦、過敏體質等不能使用相關藥物者;⑤正在使用其他可能影響觀察指標的藥物者;⑥3個月以內參加其他臨床試驗的患者。
1.5 治療方法對照組予以常規治療,包括一般飲食控制(優質低蛋白、低鹽、低磷、糖尿病飲食)及對癥治療(控制血糖、控制血壓、控制血脂等治療),降壓藥物方面,2組均給予厄貝沙坦片(賽諾菲(杭州)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20140006)口服治療,每日1次,每次1片,若血壓仍需要加藥,則根據臨床醫師進行調整(不可再用ACEi/ARB類藥物)。治療組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內服益腎健脾湯(方藥組成:黃芪30 g,黨參15 g,茯苓12 g,炒白術12 g,巴戟天8 g,黑豆15 g),每日1劑,濃煎200 ml,早晚分2次溫服(每次75 ml),療程為3個月。2組患者基礎治療均根據患者的實際情況和醫師的指導適當更改用藥量,使患者空腹血糖水平控制在4.4~6.1 mmol/L,餐后血糖<8.0 mmol/L,膽固醇<4.8 mmol/L,血壓<130/80 mm Hg(1 mm Hg≈0.133 kPa)。
1.6 觀察指標
1.6.1 證候積分參照2002年《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6]的有關內容制定。脾腎兩虛型患者癥狀包括:主癥:尿濁、神疲乏力、少氣懶言、肢體浮腫、面色晦暗。兼癥:納呆嘔惡、胸悶脘痞,便溏泄瀉。共8項,所有癥狀分為無、輕、中、重4個等級,分別對應0、1、3、5分。
1.6.2 實驗室指標檢測治療前后血肌酐、尿素氮、24 h尿蛋白定量。
1.6.3 療效評定標準參考《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療效評價標準制定:顯效:中醫臨床癥狀、體征明顯改善,積分減少≥50%;有效:中醫臨床癥狀、體征均有好轉,積分減少≥30%(但<50%);無效:中醫臨床癥狀及體征無明顯改善甚至加重,積分減少不足30%。以(顯效+有效)的例數與總例數的比例作為治療總有效率。
1.7 統計學方法采用IBM SPSS 22.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根據資料特點采用相應的統計學方法: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以百分率表示,各檢測指標統計數據均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結果判讀:若P<0.05,提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若P>0.05,則提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2組患者尿蛋白定量、肌酐、尿素氮等指標比較單純降壓、降糖、飲食控制3個月后,患者尿蛋白、肌酐、尿素氮均無明顯下降,這與臨床糖尿病腎病Ⅳ期患者的特征相符,也說明了此病為緩慢進展的過程,需要積極防控。治療組在普通治療的基礎上,聯合中藥治療,在降尿蛋白、肌酐、尿素氮等方面均有其獨特的優勢。見表2。

表2 2組患者尿蛋白、肌酐、尿素氮比較 (例,
2.2 2組患者中醫證候積分比較治療組與對照組在中醫證候方面的治療均有效果,分析其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患者為首次就診,經過系統的治療,癥狀均能得到改善,但治療組有著更好的效果,2組效果的對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顯示出中西醫結合治療的優勢。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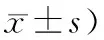
表3 2組患者治療前后中醫證候評分比較 (例,
2.3 2組患者療效比較從中醫證候進行療效的組間對比,中西醫結合治療總有效率更高,2組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2組患者療效比較 (例,%)
3 討論
糖尿病腎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的發病率在我國已經越來越高,中國不同地區的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DN的發病率不一,在最高的西部地區高達41.3%而最低的中部地區也高達15.6%,平均患病率為21.8%[8],而且呈逐年升高的趨勢,已成為ESRD最常見的病因之一。關于本病的發病機制,到目前尚無明確結論,目前研究認為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遺傳因素、代謝紊亂、氧化應激、炎性反應及細胞因子趨化、自噬、足細胞變性等[9]。DN在Ⅰ、Ⅱ期診斷難度較大,因此,在開始出現癥狀的Ⅲ、Ⅳ期積極干預,成為目前延緩甚至逆轉DN的潛在可能以及醫學工作者研究的重點。然而,目前對于本病仍無確切有效的治療方法,在本世紀初的RENAAL研究、AVOID研究等著名研究結果,提示長時間使用RAAS系統阻滯劑,可減少DN患者進入ESRD的風險,但也存在出現高鉀血癥、短時間肌酐升高等風險[10,11]。現代醫學對于本病的治療用藥除了有控制血壓血糖、使用RAAS系統用藥以外,還有近年出現的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SGLT-2)抑制劑、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受體激動劑和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劑等[12]。雖然新型的治療用藥已有較大的進展,但單純采用西藥治療DN仍未能達到人們的預期,隨著病程進展其療效更是收效甚微,因此,目前DN的治療仍然是一個重大難點問題,若不積極干預,進入ESRD的比例甚至高達50%[13]。DN相對于一般的腎小球疾病而言,患者出現水鈉潴留的情況更常見,更早進入腎臟替代治療階段。因此,ESRD對于患者而言,無疑導致生活質量嚴重下降、造成很大心理負擔,導致對家庭、社會經濟的壓力,因此,在DN的早期盡早干預,遏制、延緩病情的發展,是我們醫療工作者的工作重點[14]。
筆者認為DN IV期處于消渴向水腫發展的過程,與脾腎功能障礙關系密切。《黃帝內經》指出“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脾脆,善病消癉”,點明了飲食引起脾胃受損、脾氣虧虛是消渴發病的重要機制,到后期可出現水腫,病機也有云:“諸濕腫滿,皆屬于脾”。久則脾傷及腎,如宋代趙佶所著《圣濟總錄》提到:“消渴病久,腎氣受傷”。脾虛則不能統攝水谷、繼而水濕停滯;腎為精之處,為胃之關,腎虛則封藏失司、精微外漏,腎虛關門不利,聚水而從其類,出現水腫;到后期,脾腎氣虛更甚,加上瘀血、濁毒等病理產物隨之而生,甚至發生關格、喘脫等危急重癥。總之,脾腎氣虛貫其始終。現代眾多醫家也根據臨床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如王震宇等[15]統計了大量病例,認為DN Ⅳ期患者最常見氣虛血瘀;鄭宋宋等[16]統計了2598例DN各期病例得出數據,認為氣陰兩虛證型最為常見,但脾腎兩虛是導致DN發生的關鍵。因此,DN 病位主要在脾腎二臟,脾腎兩虛尤有代表性,根據不同患者可有陰虛、血瘀、濕濁等不同的兼證。DN Ⅳ期以大量蛋白尿為主要臨床表現,是消渴病向水腫演變的時期,這一時期脾腎兩虛是關鍵病機,把握住這一病機演變的特點,正是控制DN Ⅳ期病情進展的關鍵。這也是國內眾多醫家的共識[17]。
本研究觀察了為期3個月的臨床觀察并得出數據,證明益腎健脾湯聯合西醫治療相比單純西醫治療DN患者臨床療效更佳。此方以四君子湯作為底方,加用了補腎氣、化濕濁等藥物化裁而來。由于糖尿病腎病的患者兼證繁雜、臨床癥狀變化多端,治療的關鍵就在于抓核心、攻要害,正如前文所述,無論有何兼證的患者,脾腎兩虛是其病機核心,本方組方的思路正是抓住這一核心。此方中,黃芪性微溫,歸肺、脾經,長于補益中土、大補脾腎元氣而為君藥;黨參性平,味甘、微酸,歸脾、肺經,功能補中益氣,健脾益肺;白術性溫,歸脾、胃經,長于健脾益氣,燥濕利水,脾健則水津四布;茯苓甘、淡、平,歸心、肺、脾、腎經,長于利水滲濕不傷正氣,又可健脾,助補土之效;白術以健脾燥濕為主,茯苓以利水滲濕為要,一燥一滲,運利結合,使水濕有路出而脾氣健,脾氣健則水氣之病立除;巴戟天辛、甘,微溫,入腎經,功能補元陽、益腎氣,意在助脾腎之陽以溫化體內濕濁之邪;黑豆甘、平,入脾、腎經,具有補腎益陰之功效,可治腎病,利水下氣。
現代研究表明,黃芪、黨參等藥物具有調節免疫、控制血糖、改善微循環、保護腎臟等功效[18,19]。白術中能提煉出多達79種有效成分,可改善胃腸功能,但同時對于改善微炎癥狀態、改善微循環、抗氧化、調節免疫等都有著良好的效果[20]。現代研究表明,巴戟天的主要成分為單托品和脫乙酰基青楊酸等,可廣泛分布于多種器官,能起到改善心腦腎血管的循環、抗氧化和調節免疫功能等作用[21]。黑豆在近年以來悄然受到廣大腎病患者的推崇,有學者進行黑豆的藥理學研究,發現黑豆含有3種花青素化合物分別為C3G、飛燕草苷-3-O-葡萄糖苷(D3G)和芍藥苷-3-O-葡萄糖苷(P3G),具有抗氧化的效果,而且屬于比較優質的蛋白,適合腎病患者服用[22,23]。
綜上所述,全方補氣、健脾、益腎,兼可利水、瀉濁,標本兼顧,補泄并施,不僅沿用了中醫經典理論,而且結合了現代中藥藥理最新的研究結果,因此能達到本方預期的治療目的,即益腎健脾湯能改善DN IV期患者的血肌酐、尿蛋白定量及中醫證候,達到改善病情的目的。
糖尿病腎病的早期治療,延緩甚至逆轉進入ESRD階段甚至腎臟替代治療階段,減少患者家庭、社會的負擔,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及預后,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健脾益腎湯從經典立意,結合現代藥理學研究,經過了臨床驗證,在治療脾腎兩虛型DN的效果顯著,提示著中西醫結合治療的前景光明,具有臨床推廣的價值。然而,拘于條件所限,本研究樣本量小、研究時間短,未能進行更細化指標的探索對比以及動物實驗的研究,以深入闡明具體的作用機制。因此,在后期進行大樣本、多中心的臨床研究,深入探討藥物效應的靶點、作用機制,這將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