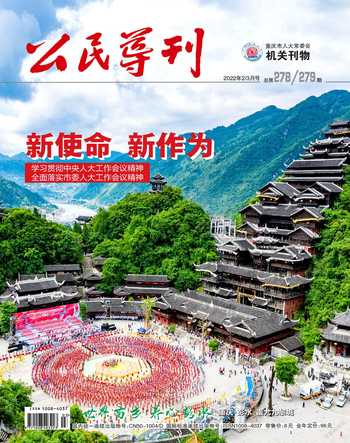揚谷風車
邱俊霖
記憶中的故鄉,肥沃土地上種著大片水稻。每到豐收的季節,就到了打風車的時候。
打風車是指用風車揚谷子。記得小時候,家家戶戶都有一臺木制風車,就是用來去除谷物中雜質的。
每逢稻谷收割曬干后,外公便將他的風車從倉庫里搬出來,將谷子打一遍風車,碾成米,之后再用風車吹走糠。
外公告訴我:“收割的稻谷雖然大部分顆粒飽滿,但也有空癟的,無法食用。碾完后的米粒中不可避免地會摻雜秕糠、谷殼等雜質,只有用風車‘風’過后的稻米,蒸熟了才香!”
于是,在一次次帶著獨特韻律的轉動聲中,我愈發覺得風車是一種神奇而又充滿趣味的農具。
一臺風車通長近兩米,高一點五米,寬則為一米左右,構造精細巧妙,由風箱、搖柄、漏糧斗、排風口等組成。站在遠處一看,如一頭健壯的黃牛。
風車的頂部是梯形的漏糧斗,連接著下方的一個出糧口,木制圓形風箱里便是一架裝有四片扇葉的風扇。扇葉的一邊高,另一邊低于風來的方向,這樣產生的氣流才能在扇葉表面由高到低順著吹動。
打風車時,將糧食倒進漏糧斗里,搖動搖柄使風扇的軸承迅速轉動起來,帶動扇葉飛速旋轉產生強勁的氣流。
此時,飽滿的谷粒由于重量足,經過風箱時會從出糧口垂直落下,落到出糧口下方的籮筐里。而輕飄飄的草屑、秕糠和癟粒,便隨著風從側面的排風口飄出。
經風車“風”過,稻谷和雜質分開,糧食變得純凈起來。
外公是打風車的高手。受外公的影響,我對打風車有著很強的好奇心,每次打風車的時候,我總是搶著搖搖柄。
起初,看到風車在我的操作之下有條不紊地運轉著,我的內心說不出的喜悅。然而搖了一會兒后,我的手臂便有些酸痛,想要放棄。外公對我說:“做事情不能中途放棄,再說了,你想吃到帶糠的米嗎?”我只得硬著頭皮斷斷續續接著搖搖柄,外公則扛著谷筐,把粗米倒進漏糧斗里。
或許是我打風車技術太差,外公看不下去了,便自己接手,同時跟我講解起來:“搖動風扇必須勻速。太快了,大風會把米吹走;搖慢了,風太小又吹不凈糠。開始速度快些,待軸承和扇葉依靠慣性轉動起來后,就輕松多了!”
于是,我照著外公的方式再次轉動搖柄,果然輕松了許多。
一天下來,落入衣領內的雜物混合著汗液,會讓人覺得身上奇癢無比,非常難受。但是,看見白花花的稻米不斷落入籮筐,我仿佛聞到了米飯的香氣。
后來,年紀稍長,打風車的時候能一口氣把風車搖到底了。除了稻米,像黃豆、芝麻等有一定重量的糧食都能用風車吹雜質,吹兩遍就干凈了。
看似很普通的風車,實際上有很長的歷史。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出現了旋轉式揚谷扇車。不過,早期的風車是開放式的,至明代才改為全封閉式。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就記載了閉合式的風車,當時的風車和一直沿用到現代的風車已沒有多大區別。
外公的那輛揚谷風車一直陪伴了他幾十年,雖然偶爾換換零部件,但是用起來一直很順暢,搖起來仍霍霍生風。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像風車這樣的農具已慢慢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先進的機械設備。
打風車的艱辛,早已消逝在光陰的長河里。但外公把他的風車留在他的小倉庫中,一有時間便搬出來緩緩地搖一搖,偶爾還給軸承上上油。
這時,他總會念叨:“只有用風車‘風’過的稻米,蒸熟了才會香到人的心里去!”
349450033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