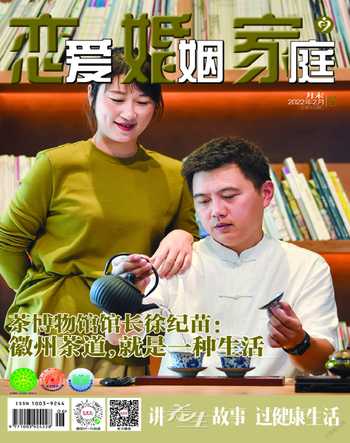普救寺:千年明月照西廂
有人說它是一座“不務正業”的古寺。這里是元雜劇扛鼎之作《西廂記》的故事發生地。故事的主人公張生和崔鶯鶯就在寺院的佛殿前巧遇。崔鶯鶯在太湖石畔燒香,張生則在花園外隔墻吟詩。它便是位于山西省永濟市蒲州鎮的普救寺。
寺前立著巨大的同心鎖,寺中能買到玫瑰花。俗語道:天下寺廟不談情,談情唯有普救寺。今時的普救寺景區楹聯亦寫道:“佛家無欲則剛,偏成就書生意氣,一段西廂佳話;禪院有容乃大,故任憑香客情緣,三春人面桃花。”1200多年前的普救寺里究竟發生了什么?
大多數人有關普救寺的印象,都來自元人王實甫的《西廂記》。在王實甫的筆下,這是一座氣勢宏偉的寺院。“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漢。”早春二月時,河南洛陽書生張君瑞取道此地,欲往長安,聞說普救寺的香火繁盛,于是前來游玩,恰好在舍利塔下佛殿中看見了崔鶯鶯,驚為天人。“魂靈兒飛在半天”,以為自己看到了觀音菩薩,問僧人道:“和尚,恰怎么觀音現來?”……《西廂記》里描述兩人在初見時張生的驚艷是“正撞著五百年前的風流業冤”。


《西廂記》中為了追求鶯鶯,張生租下了寺廟中與鶯鶯所住之“西廂”僅隔一墻的“西軒”。于是一份“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的期盼與相思,就像是一個無法解開的心結,終日纏繞在張生的心頭。
一天晚上,張生見鶯鶯正在后花園中燒香禱告,隔墻的他便趁機高聲吟詩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鶯鶯知道吟詩者是張生,便回詩一首:“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一來一去,詩中遇知音,二人已暗生情愫。《西廂記》中的鶯鶯夜聽琴、寄情詩、花園祭月、月下焚香和張生隔墻吟詩等都是發生在普救寺后花園中這個秘密的地方,如果沒有這個特定的花園,或許張生與鶯鶯千古傳世的愛情故事就要少了幾分迷人的色彩。
張、崔兩人相遇之后,張生遭遇了難題:最先是叛軍孫飛虎聽說鶯鶯貌美,前來搶親,率領人馬圍困普救寺。崔鶯鶯之母崔夫人許諾誰能退兵,即將鶯鶯許配給誰。危急時刻,張生挺身而出,給同窗好友白馬將軍寫了救急信。一干人等登上了寺內的大鐘樓,盼望白馬將軍的救兵。
這個大鐘樓在寺院一入山門處,登樓可看到山下的全貌。如今,樓中最別致的景觀不是懸掛在樓內的大鐘,而是那些掛在樓梯兩側鐵鏈上的同心鎖。同心鎖扣住鐵鏈,一把連著一把,數以萬計,蔚為壯觀。這是慕名而來的游人們祈求愛情同心的結果。
白馬將軍解圍之后,崔夫人卻不愿兌現承諾,而是要張生和鶯鶯兄妹相稱,致使張生一病不起。后來丫鬟紅娘牽線搭橋,巧妙安排二人相會。夜晚張生撫琴一曲《鳳求凰》表相思,鶯鶯也向張生訴說愛慕之情。老夫人無奈松口,稱張生若能考取功名即可迎娶鶯鶯,最后的結局便是“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皆大歡喜。從此“紅娘”一詞也被泛指為力促金玉良緣之人。
如今的普救寺里人最多的地方不是菩薩洞或大佛殿,而是張生攀過院墻,與鶯鶯相會的“西廂”。西廂在梨花深院中,這是寺院后一處單獨的三合院。按照戲曲中的說法,崔夫人住在正房,西廂房則是鶯鶯和紅娘的住所。《西廂記》中“請宴”“賴婚”“逾垣”“拷紅”等重要戲份,皆發生在梨花深院。
普救寺最后一次重建是在1986年。其時,寺院早已在過去的戰火中成為一片廢墟,大鐘樓和西廂都是那次復建后的建筑。
“有情人終成眷屬”,這結局符合多數中國人的心理。寺院屢廢屢建,事由寺生,寺因事存,如果故事僅僅到此,也算得上圓滿了。
但在1986年復修普救寺時,在地基中出土了一塊石碑,上刻有《普救寺鶯鶯故居》律詩一首,這是金代大定年間河中府王仲通游寺時所寫。“花飛小院愁紅雨,春老西廂鎖綠苔。”詩中情調哀怨,似乎并不像結局圓滿的有情人語調,倒像是遺婦在自怨自艾。這也難怪,在王仲通游寺時,《西廂記》還沒有誕生,他那時聽到的故事應該是唐代元稹的筆記小說《鶯鶯傳》。
王實甫作品全名為《崔鶯鶯待月西廂記》,西廂記故事在王實甫作品中做到了極致表達,但在那之前這個故事已流傳演變了500年。
最初作品是唐傳奇《鶯鶯傳》,作者元稹后來和白居易并稱“元白”,今天看來他的成就和影響不如白居易,但也有名句傳世:“曾經滄海難為水”“貧賤夫妻百事哀”,都出自他的悼亡詩,體現他對原配妻子的深情。不過他和女詩人薛濤、劉采春等人的韻事也流傳頗廣,還有這個《鶯鶯傳》。
《鶯鶯傳》有3000多字,后世流傳的關鍵情節都有描繪,如“普救寺相遇”“白馬解圍”“逾墻西廂”,等等,所不同的則是兩者的結局。
在《西廂記》中,張生和鶯鶯在西廂幽會之事最終被老夫人發覺,老夫人提出條件,要張生赴京趕考,張生最終得中狀元歸來,與鶯鶯喜結連理。而在《鶯鶯傳》中,張生赴京后并未回轉,崔鶯鶯在等不到張生之后嫁給了別人。后來,張生偶然路過崔氏之門,上門求見,崔鶯鶯賦詩一首:“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當時拋棄我,為什么今日還要來見我,還是把你的心意,多憐愛眼前的人吧。從此兩人之間再也沒有消息。
張生為什么一去不還?在《鶯鶯傳》中,他如此自辯:大凡美貌的女子都是上天的尤物,她們或是禍國或是害身,自己福德淺薄,駕馭不了這樣的尤物,所以只有放棄。一見鐘情的愛情喜劇,原來卻是始亂終棄的蒼涼悲歌。
但若知道張生沒有回轉的真正緣由,讀者也許就不難理解了。《鶯鶯傳》雖然托名是張君瑞的故事,但后世的不少文史學者考證,實際上寫的是作者元稹自身的經歷。魯迅曾說:“元稹以張生自喻,述其親歷之境。”
元稹出生于唐大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到貞元十七年,恰好23歲,這與故事發生時張生的年齡一樣。他15歲登明經科,在貞元十五年來到河中府,也就是普救寺所在的蒲州為吏。后赴長安應試,三年后得以選中,獲任秘書省校書郎。
《鶯鶯傳》中寫到,張生到長安后,“文戰不勝,遂止于京”。數年之后,他別有所娶。文中并沒有寫張生到底娶了誰。而在現實中,元稹在獲職秘書省校書郎后,娶了當時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女兒韋叢。一個是寄居寺院的癡情女, 一個是當朝權貴的美嬌娘。當選擇來臨時,想必大多數書生的答案不言而喻。
對西廂故事來說,元稹是不是張生原型不應是重點,重點是這個發生在普救寺里的故事,引起后人持續關注、不斷演繹。
金代章宗時人董解元將《西廂記諸宮調》原來始亂終棄的結局改為大團圓,諸宮調有說有唱、多人合演,已接近成熟的戲劇演出。在此基礎上,一百年以后,元代王實甫《西廂記》問世。普救寺里的月下故事,通過這一佳作廣為人知。明初賈仲明稱:“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清初金圣嘆將《西廂記》列為“天下第六才子書”進行評點,并稱:“讀《西廂記》畢,不取大白(酒杯名)自賞,此大過也。”《紅樓夢》“西廂記妙詞通戲語”一回中,有賈寶玉和林黛玉共讀西廂的情節,稱其文“辭藻警人,余香滿口”。
那輪西廂明月,在漫漫歲月里,不知裝飾了多少人的夢。“你看那淡云籠月華,似紅紙護銀蠟;柳絲花朵垂簾下,綠紗茵鋪著繡榻……”
在唐代,蒲州是熱點城市,普救寺屬景點,張生和崔氏作為流動人口住在普救寺,在清修之地成就綺麗之思,現在看來有些怪異,放到當時環境中卻不難理解。在南北朝時期,佛寺就常接納俗客住宿,唐代這更是成了佛寺的一個收入來源。那時寺院相當于有賓館的景區,在這樣的地方發生點浪漫故事并不奇怪。
普救寺現存明代碑刻稱寺院“創于隋唐”,唐初一些佛家著作和詩文中都提到普救寺,《三藏法師傳》載,玄奘取經回來后,參與翻譯的有蒲州普救寺僧人鐘秦、神宮。元稹的朋友楊巨源是蒲州人,寫過《同趙校書題普救寺》云:“東門高處天,一望幾悠然,白浪過城下,青山滿寺前。”

《鶯鶯傳》傳世,西廂成了普救寺名片。金代王仲通《普救寺鶯鶯故居》這詩作于1204年。300多年以后,明嘉靖四十三年(1555年),蒲州大地震,崔鶯鶯的西廂、張生的墻頭均蕩然無存。9年后開始重建,建成后,主持此事的蒲州知州張佳胤作詩:“勝地曾為瓦礫場,浮圖今放海珠光……莫向空門悲物理,從來吾世有滄桑。”
又300多年過去,1920年普救寺大火,勝地重為瓦礫場,僅存明代所建舍利塔(因西廂故事緣故被稱為鶯鶯塔)。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曾作《題鶯鶯塔》:“來到西廂下,頹然無片瓦。紅娘何處去,獨有鶯鶯塔。”
1986年,普救寺再次重建,重建緣由和依據是《西廂記》。重建前時任山西省領導的白清才說:“《西廂記》里的普救寺在運城永濟西廂大隊,現在只剩下一個鶯鶯塔……把普救寺恢復起來,按張生游西廂的格局,肯定會吸引很多游客。”
西廂大隊由寺坡底等村合并而成,因西廂故事而得名,那是1956年的事,現稱西廂村。1990年,普救寺又一次建成,趙樸初先生題寫山門楹聯:“普愿天下有情,都成菩提眷屬。” 此聯來源于《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也許王實甫是了解《鶯鶯傳》背后的故事的,但那太凄涼了,他不忍鶯鶯落得如此境地,現實既然已經成了悲劇,戲曲何妨改為喜劇?雖“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但相信大家還是會選擇溫暖的大團圓吧。夢想,總是要有的。
308750190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