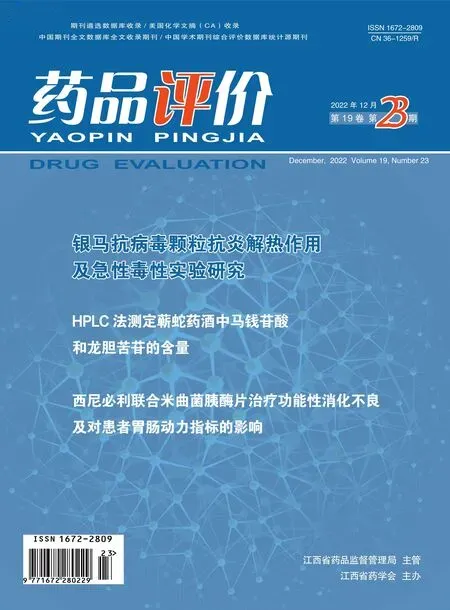吡咯替尼聯合卡培他濱治療晚期HER2 陽性乳腺癌的效果及對腫瘤標志物、無進展生存期的影響
葉華斌
贛州市腫瘤醫院,江西 贛州 341000
乳腺癌作為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近年 來在國內呈高發趨勢。乳腺癌包括HER2 陽性型、LuminalA 型、LuminalB 型及基底型等4 種亞型,其中20%左右患者為HER2 陽性型[1],與其他類型乳腺癌相比,HER2 陽性型侵襲性高,增殖快,生存期短,預后差,病情更加兇險。在臨床中常使用拉帕替尼、曲妥珠單抗等抗HER2 靶向藥物結合化療等其他治療方式進行治療,但由于部分患者對曲妥珠單抗存在耐藥性,以及拉帕替尼、曲妥珠單抗等藥物副作用大等情況[2],仍存在部分患者治療效果不理想。吡咯替尼是一種不可逆的雙重酪氨酸激酶抑制劑,由于其作用機制與曲妥珠單抗及拉帕替尼等藥物相比具有不同之處[3],對于曲妥珠單抗具有耐藥性的部分患者仍適用,作用機制更確切;卡培他濱作為氟尿嘧啶衍生物,對于腫瘤治療同樣具有較好效果。本研究應用吡咯替尼聯合卡培他濱治療晚期HER2 陽性乳腺癌,觀察其治療效果及對患者腫瘤標志物、無進展生存期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1 月至2020 年1 月贛州市腫瘤醫院收入初治后復發轉移晚期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80 例,所有患者均隨訪1 年。納入標準:(1)病理學證實為乳腺癌晚期,且熒光原位雜交(FISH)監測或免疫組織化學檢查確認為HER-2 陽性,激素受體ER、PR 陰性或陽性均可;(2)心臟、肝臟、腎臟等各器官功能正常;(3)年齡為20~55 歲;(4)至少存在1 處可檢測病灶;(5)患者及近親屬均已知情且簽署知情同意書;(6)預計生存期≥1 年者;(7)初治后復發轉移;(8)輔助及新輔助階段使用曲妥珠單抗。排除標準:(1)妊娠及哺乳期婦女;(2)身體情況無法耐受化療者;(3)合并有嚴重心腦血管疾病或其他部位腫瘤者。按照奇偶分組法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其中觀察組40 例,均為女性;年齡(35.37±5.64)歲;TNM 分期:Ⅲ期28 例,Ⅳ期12 例;已接受的治療:圍手術期接受新輔助曲妥珠單抗治療;左側21 例,右側17 例,雙乳癌2 例;絕經前26 例,絕經后14 例;浸潤型導管癌25 例,黏液癌4 例,小葉癌11 例。對照組40 例,均為女性;年齡(35.21±5.38)歲;TNM 分期:Ⅲ期26 例,Ⅳ期14 例;已接受的治療:圍手術期接受新輔助曲妥珠單抗治療;左側23 例,右側16 例,雙乳癌1 例;絕經前24 例,絕經后16 例;浸潤型導管癌26 例,黏液癌5 例,小葉癌9 例。兩組患者年齡、性別、TNM 分期、已接受的治療、發病位置等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贛州市腫瘤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
1.2 方法
對照組患者應用注射用曲妥珠單抗(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J20180073,規格:440 mg/瓶)8 mg/kg+口服卡培他濱片(正大天晴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43044,規格:0.5 g)治療,1.0 g/m2,分早晚2 次于餐后30 min 以水吞服,每連用14 d 需休息7 d,每個治療周期為21 d。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更換曲妥珠單抗為口服馬來酸吡咯替尼片(江蘇恒瑞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80013,規格:80 mg)治療,每次400 mg,每日1 次,于餐后30 min 服下,每天需同一時間服藥,持續服用。兩組患者治療開始后隨診觀察1 年。治療期間,醫生參考常見不良時間評價(CTCAE)標準,觀察患者毒副反應發生情況。
1.3 觀察指標
根據實體腫瘤療效評價標準(RECIST)[4],由醫生在治療后對兩組患者臨床療效進行評估,見表1。

表1 實體腫瘤療效評價標準
無進展生存期(PFS)為首要終點,以客觀療效、不良反應及疾病控制率為次要終點;由醫生根據國際癌癥組織通用不良反應標準[5],觀察患者有無可逆性胃腸道反應、手足綜合征、全身不良反應及脫水、厭食等,并對毒副反應發生情況進行記錄;于治療前后,取患者靜脈血,制作細胞懸液并分離淋巴細胞,利用流式細胞檢測儀,檢測CD3+,CD4+,CD8+,抽取患者靜脈血4 mL,分離血清,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癌胚抗原(CEA)、癌相關糖蛋白抗原(CA15-3)。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經SPSS 18.0 軟件包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例(%)表示,以χ2檢驗,計量資料以表示,以獨立樣本t進行檢驗,生存曲線以GraphPad Prism8 制作,通過Kaplan-Meier 曲線描述,組間生存期比較采取Breslow 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后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客觀緩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大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后臨床療效比較[例(%)]
2.2 兩組患者PFS 比較
兩組中位PFS 均為9 個月,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2,P=0.724)。
2.3 兩組患者治療后毒副反應發生率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后毒副反應發生率比較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后毒副反應發生率比較[例(%)]
2.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T 淋巴細胞表達率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CD4+/CD8+、NK、CD3+表達率比較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CD4+/CD8+、NK、CD3+表達率均大于同組治療前(P<0.05),且觀察組大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細胞因子比較()

表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細胞因子比較()
2.5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腫瘤標志物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CEA、CA15-3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CEA、CA15-3 均小于同組治療前(P<0.05),且觀察組小于對照組(P<0.05)。見表5。
表5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CEA、CA15-3比較()

表5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CEA、CA15-3比較()
3 討論
在晚期乳腺癌群體中,HER2 可通過影響細胞凋亡來影響腫瘤細胞生長,抑制HER2 過表達,降低腫瘤細胞侵襲力,是治療乳腺癌的靶點之一。本研究中兩組患者治療后ORR、DCR 小于同組治療前,且觀察組小于對照組;治療后CD4+/CD8+、NK、CD3+表達率均大于同組治療前(P<0.05),且觀察組大于對照組;說明吡咯替尼聯合卡培他濱及曲妥珠單抗聯合卡培他濱均可有效抑制腫瘤細胞增殖,且吡咯替尼聯合卡培他濱相比曲妥珠單抗聯合卡培他濱抑制效果更顯著。HER 家族受體除HER2 外,還包括有HER1、HER3、HER4[6],吡咯替尼通過與HER1、HER2、HER4 胞內激酶區ATP 結合位點共價結合,來阻止HER家族同源或異源二聚體形成,抑制自身磷酸化,進而阻斷下游信號通路的激活,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7]。NK 細胞是一種廣譜殺傷細胞,對于腫瘤細胞具備高度毒性作用,在抑制腫瘤細胞增殖中占據重要部分[8],因此,當HER2 過表達受到抑制時,NK 細胞表達下降,而本研究結果正是佐證這一點,且NK 細胞在T 細胞亞群比例調節方面同樣發揮重要作用,是反映機體細胞免疫狀態的重要指標[9]。CD4+/CD8+則反映機體淋巴系統功能狀態[10],當腫瘤細胞增殖過程中,產生免疫抑制因子來抑制CD4+的產生、同時誘導CD8+形成,從而致使機體免疫功能處于被抑制狀態,因此當腫瘤細胞增殖受到抑制時,CD4+/CD8+比值升高,機體免疫水平得以恢復到正常狀態。因此,吡咯替尼對腫瘤細胞生長的抑制作用,可有效促進患者CD4+/CD8+、NK、CD3+表達增高,而本研究結果可佐證這一觀點。
在腫瘤增殖期間,CA15-3 會在被裂解后進入血液循環,從而隨病情的發展,CA15-3 水平會呈升高趨勢[11],而CEA 則分別是反映腫瘤細胞增殖活力的敏感指標與特異性抗原[12],在本研究中,兩組患者治療后CEA、CA15-3 均小于同組治療前,且觀察組小于對照組,這說明吡咯替尼聯合卡培他濱與曲妥珠單抗聯合卡培他濱均可有效抑制腫瘤增殖,且吡咯替尼聯合卡培他濱對腫瘤增殖抑制作用大于曲妥珠單抗聯合卡培他濱。卡培他濱作為氟尿嘧啶衍生物,進入人體后,在逐級酶聯反應作用下轉化為5-氟尿嘧啶,再加上腫瘤細胞內豐富的氟尿嘧啶酸化酶[13],致使卡培他濱對腫瘤細胞具有特異性殺傷;以及吡咯替尼對腫瘤細胞生長的抑制作用,兩種藥物聯合應用,促使患者CEA、CA15-3 水平明顯下降,患者腫瘤細胞得到有效抑制。
本研究出現毒副反應主要以胃腸道反應、脫發、中性粒細胞減少、白細胞減少、頭痛及厭食等為主,然而在本研究中兩組患者PFS 及毒副反應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說明吡咯替尼聯合卡培他濱與曲妥珠單抗聯合卡培他濱對患者PFS 及毒副反應發生影響無明顯差異。初步推測是研究樣本量過少,隨訪時間過短。理論上講,腹瀉等毒副反應可能與吡咯替尼阻斷HER 家族信號通路有關[14-15],然而具體機制尚不明確,有待后續擴大樣本量開展多中心研究加以證實。
綜上所述,吡咯替尼聯合卡培他濱可有效抑制晚期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腫瘤細胞增殖,加速病情康復,具有良好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