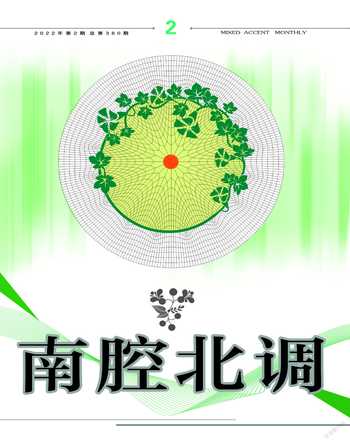《人生果實》:“生活流”電影的美學意蘊
魏修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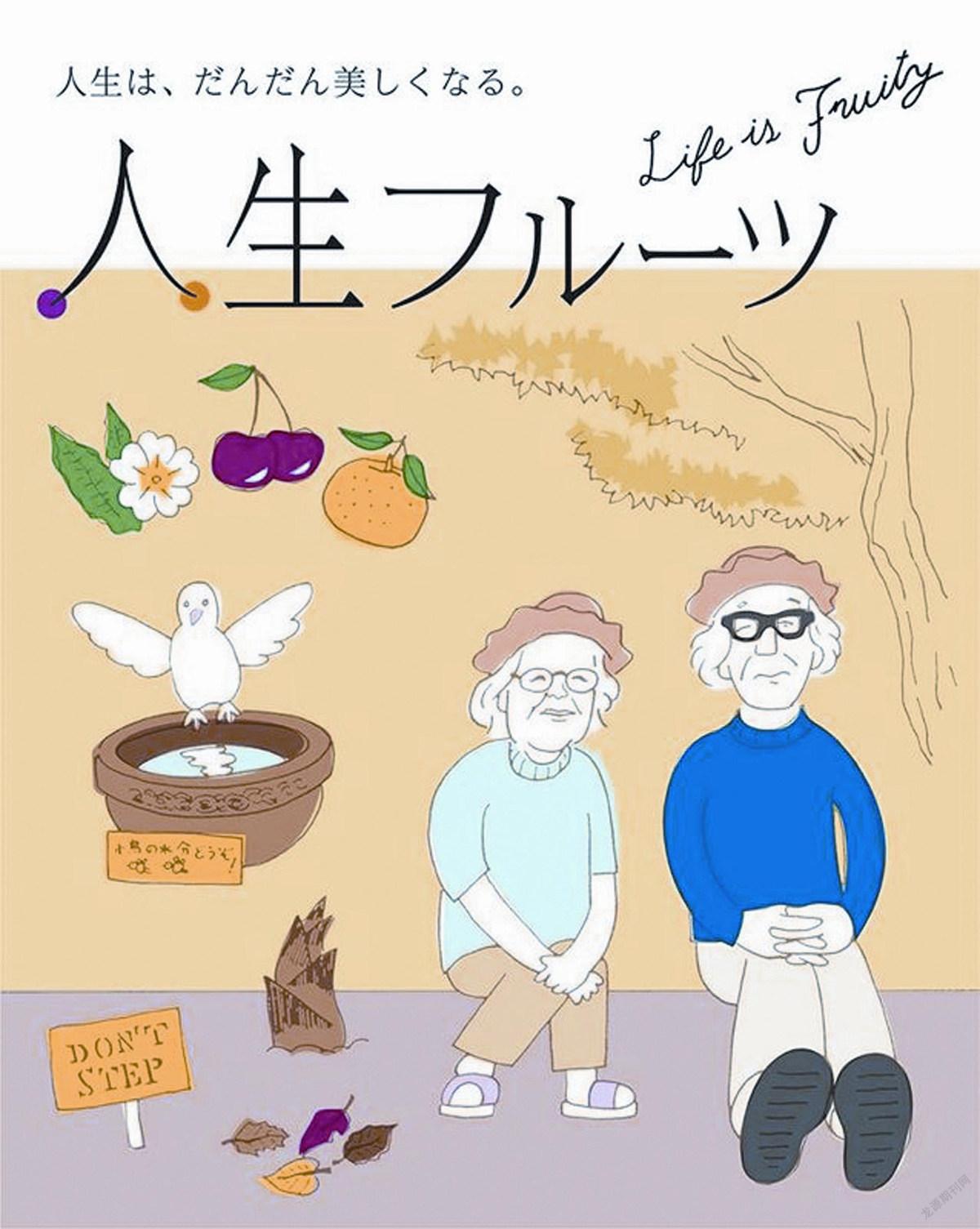
摘要:《人生果實》是日本東海電視臺拍攝的一部紀錄片,影片借由一幢深居林間的小屋,將建筑師津端修一及夫人英子的晚年生活,不加修飾地展現在觀眾面前,是一部典型的“生活流”電影。影片以碎片化的敘事風格、崇尚自然的生活元素以及反復詠嘆的主題旁白,將導演的拍攝意圖與構建的電影美學相融合,呈現出簡約的生活之美,傳遞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理念和文化內涵,同時引發人們對生活方式、自我認知和老去、死亡等話題的思考。
關鍵詞:《人生果實》 “生活流” 日常瑣事日式美學
《人生果實》是日本東海電視臺拍攝的一部紀錄片,由新聞工作出身的導演伏原健之執導,日本影后樹木希林擔任旁白,講述了有“現代陶淵明”之稱的日本建筑師津端修一夫婦的晚年生活。影片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沒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和情緒沖突,更沒有復雜的敘事技巧,始終以一種潺潺流水般的節奏,將兩位老人的一日三餐、飲食起居等日常行為,不加修飾地展現在觀眾面前,是一部典型的“生活流”電影。電影透過瑣碎的日常生活,以樸實、簡單、靜宜的鏡頭語言,將導演的拍攝意圖與構建的電影美學相融合,傳遞出“生活流”電影內涵的美感與意蘊。
一、碎片化的敘事風格:呈現簡約生活之美
“生活流”電影是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出現的一種自然主義傾向電影。主張直接拍攝落入電影攝像機視野范圍內的生活場景和事件,既不作選擇,也不作評價,追求電影的日常生活化和原生態表現。張德林認為“生活流”的敘事方式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自然形態,不加粉飾地如實地把它再現出來”,在拍攝手法上“重客觀,重再現,重社會生存態的準確把握,重細節、場面、情景的逼真描繪。”[1]而其中表現細節的鏡頭或鏡頭的組合,又有著超越生活本身的內涵和意義。碎片化敘事是“生活流”電影中常見的一種敘事方法,是在一種日常的、零散的敘事碎片中形成一種非線性的影片敘事模式,將導演的拍攝意圖融入作品的美學構建中,使影片內容打破觀眾的定向思維,給予觀眾以更廣闊、多維的想象空間,同時賦予影片更豐富的內涵。
《人生果實》以90歲的建筑師津端修一及其87歲的夫人英子這對老年夫婦的日常生活為主線,采用碎片化的敘事手法,構建立體的敘事空間,將兩位耄耋老人的家常瑣事娓娓道來。跟隨影片緩緩的敘事節奏,兩人的生活經歷和生活態度也被鋪展開來。鏡頭下他們的生活樸實而平淡,每一個細節卻又生動而精彩,令人感覺溫暖。
修一先生是一位建筑師,性格沉穩細致,做事一絲不茍,一生酷愛帆船。英子女士是愛知縣半田一個有著200年歷史的釀酒坊主家的千金,自由隨性,不拘小節,熱愛手工,從小就有一個田園夢。影片借由修一夫婦豐富的生活閱歷,一幢深居林間的小屋,探索那些深藏于時間長河中的真正瑰寶。樹林外是喧囂嘈雜、車水馬龍的城市,樹林里是他們孜孜不倦、不緊不慢的耕讀生活,他們已在這遠離都市喧囂的“世外桃源”生活了40多年,以自然為友,享受著平靜、安穩的田園生活。
身為建筑師的修一先生為園子做了布局規劃,分成了不同的區域,周圍種植了高大的橡樹,還種了梅子、酸橘、無花果、草莓、竹筍、土豆、玉米、芋頭等50多種水果和70多種蔬菜。雖然樹木植物種類繁多,卻井然有序、彼此協調。整個園子錯落有致、生機盎然。兩位老人一起侍弄園子,照顧蔬果。拔草除蟲、澆水施肥、挖土豆、刨竹筍、摘櫻桃、撿落葉……由于蔬菜品種眾多,為了方便辨認,修一逐一制作了小巧的標識牌,并把標識牌仔細地粉刷成醒目的黃色,在上面寫上“竹筍,你好”“報春花,春天來了”等溫暖的標語。房屋結構簡單,室內布置簡樸而溫馨,生活處處用心,為了在客廳里看到院子里的花,他們隔段時間就會調整餐桌的位置。英子喜歡烹飪,會做各種各樣的飯菜和甜點,普通的食材經由英子的巧手,就會變成一道道美味的佳肴。英子聽到修一說“真好吃”,會特別滿足,更加充滿動力。每當果子成熟,蔬菜豐收,英子都會把吃不完的果蔬,腌制在玻璃罐里,精心整理分裝,仔細貼好標簽,打包成一份份的禮物,郵寄給遠方的親人和朋友,與他們分享收獲的果實;她給朋友寄信、寄明信片,通過這些片段連綴起親情、友情、回憶以及喜怒哀樂。在幾十年的歲月中,兩人相知相伴,相敬如賓,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英子對修一的愛,不會掛在嘴上,而是融入生活的每個細節。英子不愛吃土豆,但會經常做土豆料理,因為修一喜歡吃。英子習慣于西式的早餐,喜歡面包加果醬,而修一則喜歡吃傳統的日式料理,因而每天早上英子女士都會準備兩份不同的早餐。修一不愛吃水果,英子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園子挑選水果榨成果汁,并且每天都要陪著修一一起喝果汁。她不愛喝粥,但每天早上必煮,因為她想看修一津津有味喝粥的模樣。導演伏原健之在被采訪時曾這樣說過,整部片子幾乎沒有“拍到精彩片段”的感覺,但后期在編輯整理的時候,修一夫婦細微的語言、如老友般平和的相處方式、對待生活的熱愛、從容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態度卻無一不讓人覺得珍貴。他們的生活雖然樸實而簡單,卻呈現出一個安詳平和、充滿意趣、相互包容的兩個人的世界。
耕種、采摘、收獲、烹煮、享用……一日三餐,日影長短,拍攝的重心都放在兩位老人的這些日常瑣事中,碎片化的敘事段落,支撐起全片的主題。極致的簡素意味著無限的豐富,蘊含著余味悠長的美感。這種將日常生活元素發揮到極致的藝術手段成為“生活流”電影重要的美學風格。對極簡與細節美學的關注,也是日本電影藝術最核心的美學特征之一。同時,影片中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耕自收、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帶給現代都市人一份返璞歸真的感動。在這個方方面面都加速的時代,對于被各種欲望和利益追逐著的現代人來說,有著莫大的吸引與誘惑,在生活日常的細水長流中傳遞出蘊含的生活哲理,引發人們的反省和思考。影片從春天拍到次年春天,春種秋收任四季更迭,周而復始。在時間變換中,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極簡而又優雅的生活方式,傳遞出一種經過時間洗練的處世哲學。“生活流”在整體上呈現的是一種素樸平淡,但它的真實感和鮮活性更能喚起觀眾的共鳴。它追求現實生活與意蘊內涵的統一,二者的互相融合呈現出一種質樸、含蓄的,內在意蘊和外在形式交融激蕩的美學風格。
二、崇尚自然的生活元素:詮釋日式美學
“生活流”電影沒有大起大落的戲劇沖突,未經特殊加工過的原始素材,記錄著人物的日常生活,還原了攝影機前的生活的本真面貌,但這并未影響作品的藝術表現力,看似平淡無奇的情節背后往往隱含著深刻的主題思想。正如德國電影理論家克拉考爾所說的那樣,“‘生活流’的概念包括具體的情境和事件之流,以及它們通過情緒、含義和思想暗示出來的一切東西”[2]。《人生果實》注重感官的直覺,滲透出特有的美學意蘊。日式美學強調“從有形的事物進入內在世界。以外物景致與人的情趣的交融、天地之間的氣韻與人的生命節奏的契合為至境” [3]。小屋、雜木林、果樹、菜地……構成一方幽靜的院落。《人生果實》以這幽靜的院落為依托,承載著電影的主題與敘事載體。
此院落雖不同于日本傳統的庭院,卻是萬物競生、生機盎然的自然界的縮影。院子里除了雜木林,還栽植著上百種蔬菜水果,這里一年四季景致萬千,小屋、雜木林、果樹、菜園渾然一體,相映成趣,使影片平添了許多視覺上的美感。掛滿枝頭的櫻桃、讓人垂涎欲滴的草莓、碩大鮮嫩的竹筍、碩果累累的栗子……秋實冬藏之中隱含著春生夏茂之意,以不同的蔬菜、果實,表現時間的輪回,季節的變換。這種電影化的時間流轉,與日本傳統文學有類似的特質,在不經意間透露出日本人的審美意識和文化精神。
日本人最初的美學意識是來自人與自然的共生,他們把天地人作為一個有機的、統一的整體去看待,并自覺地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在日本人的觀念中,“自然是生命的母體,是生命的根源,他們對自然懷有一種特別親和的感情,對自然的愛,帶來生活與自然的融合。人的生活與自然密不可分,這是日本人對自然的根本感情。可以說,人與自然的親和與一體化,人與自然共生成為日本人的美學意識的一個特征。”[4]這種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哲學意識,使得日本民族對自然有著深厚的依戀和感性認知,這種狀態也滲透到藝術創作等領域。電影中以小院景致為對象的影像元素,成為創作者傳達影片理念的工具與媒介,展現出的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互依互存,不僅體現出修一夫婦的生存模式,也是人類最本真的生活狀態的呈現。
同時,這種“與自然共生”的意識,也與津端修一先生的建筑理念不謀而合。修一是一位建筑師,年輕時曾參與日本愛知縣春日井市高藏寺新城的設計,他提出“城市需要森林”的理念,想把高藏寺變成一個森林覆蓋的城市,希望新城能與自然共生。然而他的想法不為當時優先發展經濟的政府所采納,高藏寺最終成了一片片了無生氣的集合住宅。于是他在新城中買下一片空地,建屋植樹,改善土壤環境,種植果蔬花草,用自己的一生去踐行理念的合理性。他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中,堅持著自己的理想與認知。影片中的這幢小屋,就是修一先生在高藏寺新城買下的空地上建造的。小屋仿照了修一先生最敬仰的德國建筑師安東尼·雷蒙德的住宅兼工作室的雛形設計而成。修一先生認為建筑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應包含自然。基于這種觀點,小屋在選擇材料、設計構圖、興土建造、居住使用上,處處都凝聚了這種理念。小屋采用最容易獲取的木材作為主材料,高高的房頂,粗粗的房梁,甚至連窗戶、地板都采用木質原料。打開窗戶,隨著季節變化的雜木林景色映入眼簾。春有枝頭新綠,秋有紅葉滿園,夏天茂盛的枝葉遮擋住陽光,帶來天然的清涼,冬天樹葉飄落、暖陽西照。一年四季,享受著自然的恩惠與饋贈。隨著時光的流逝,大自然將房屋的一切慢慢融入其中,成為一體。
除了原木小屋,在修一夫婦的日常生活中,也處處體現出這種崇尚自然的審美意識。依照時節的交替,緊跟時間的步伐,珍惜和享受屬于每一個時節的時令變化。每到夏天來臨,修一和英子會把拉門貼紙換成適合夏季的和紙,床榻換上麻質的寢具,餐桌鋪上清爽的白色桌布。在他們的生活中大到木造的房屋,小到所使用的碗、筷、木勺……無不體現出對自然美的追求。所有這些細節,經由創作者的電影畫面傳遞出一種簡樸自律的生活態度、傳遞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
三、反復詠嘆的旁白:蘊含生命主題
電影中“風吹枯葉落,落葉生肥土,肥土豐香果。孜孜不倦,不緊不慢” 的旁白貫穿始終,將整部影片分成了四個部分,不僅讓整部影片的邏輯變得清楚明了,同時升華了影片的主題思想和創作理念,為觀眾營造了更為廣闊的想象空間。這富有哲理的詩句不僅道出了自然萬物生長的道理,也是對修一夫婦美麗人生的詮釋。他們崇尚自然、順應四時,精通耕作、熱愛生活,孜孜不倦不緊不慢地培育著人生的果實。
日本人向來崇拜自然萬物,并把自然界的一切奉若神明,因而從自然界中所汲取到的情感體驗也自然而然地會與人間世態相聯系,自然美也作為日本民族審美的基點被貫穿到人生的審美之中。從草本植物萌芽、成長、開花結實的生命旅程中,感受生命的輪回與流轉;日月星辰的變換規律和風花雪月的瞬時即逝,則強化了生命短暫無常之道理,與日本“物哀”的審美意識一脈相承。正是由于與自然萬物的相生相戚,日本民族對于生命的認知更接近于對自然的體悟。如彭修銀在《東方美學》[5]中所闡述的那樣,在日本人的自然觀里,對宇宙精神和個體生命的理解與探索,如植物的根干和枝葉的辯證思維。他們認為植物通過播種、發芽、成長或開花結果,不斷輪回,以維系生命,表現出對生的強烈意識和優雅的美。在時間的流逝中,葉落花謝,返歸于根部,成為滋養植物的養分。
影片中,兩位老人從建造這所房子開始,就種下了梅花、柿子、櫻桃、栗子樹,循著四季輪回去澆灌、施肥、松土、收獲。春回大地,草木生長,果樹開花結實;經由夏的怒放與孕育,夏去秋來,草木枯萎,風吹葉落;再經過冬的囤積醞釀,落葉腐爛滋養土地,土地肥沃為植物果樹提供豐富的養料……如此以往,循環往復,生生不息。人生也是這樣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與園子里的果蔬沒有分別。
一天,修一先生在菜地里拔完草后午睡,便再也沒有醒來,同園子里的植物一樣,曾經絢爛輝煌,如今葉落歸根。他走得很平靜,很安詳,雖然沒能和英子好好告別,但在兩個人的心中,早已準備好了這一天的到來。影片沒有刻意煽情,沒有烘托悲傷,只是輕描淡寫地像描繪日常一樣。在日本人的審美中,人與自然之間沒有絕對的距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死”是人“生”之后的必然,一個人從生到死不過是簡單輪回,更映出生生不息的自然規律,匯聚成了人類的永續發展。熱愛生活,尊重生命,順應自然,呈現出一種真實的美好。影片內容扎實,有超越生死的撫慰。
“生活流”電影向來立足現實社會,關注當下生活,捕捉社會中引起人們思考和共鳴的原始素材,進行藝術加工創作,再通過影像的方式呈獻給觀眾,讓觀眾透過影片觀照現實,對自身和社會進行反思,并作出積極回應和行動,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主義意義和人文價值。導演伏原健之在采訪中提道,以高齡老人為題材的作品,內容多半帶有晦澀、陰郁的基調,而《人生果實》想呈現一部讓人對暮年充滿憧憬、從容優雅老去的作品。正如導演所說的那樣,電影自始至終都在向我們傳遞一個信息:生活是美好的。在任何歲月、任何年紀,我們都應珍愛生活,尊重生命,守護內心的那份執著,朝著自己選擇的方向,緩慢而堅定地前行。在老去時,留給他人一份溫暖,收獲屬于自己的人生果實。
“風吹枯葉落,落葉生肥土,肥土豐香果。孜孜不倦,不緊不慢”,是對修一夫婦美麗人生的詮釋,也是對修一先生一生堅持自己的理想與信念的認同與肯定,更是我們各自經由時間塑造出的人生。
四、結語
《人生果實》從始至終都是圍繞津端修一和夫人英子的日常瑣事而展開,講述的是夫妻倆生活中最平淡的點滴,但并不顯得冗長乏味,既有詩意的美感,又有渾厚的意蘊,充滿對生命秘而不宣的深情表達。同時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多的啟發,引發人們對生活方式、自我認知和老去、死亡等話題的思考,值得細細品味。人生的果實,不急于一朝一夕收獲,而是選擇播下一顆堅定不移的種子,經年累月地調配土壤,在時間的緩慢浸潤里,讓果實自然地成熟。“生活流”電影別樣的藝術風格,碎片化的敘事更容易貼近觀眾的心靈,產生巨大的藝術張力。如克拉考爾所說的那樣,“生活流”電影,“所喚起的現實要比它實際上所描繪的現實內容更為豐富”。
參考文獻:
[1]張德林.“生活流”:現實主義藝術方法的一種表現形態[J].當代作家評論, 1988(3):107-113.
[2][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M].邵牧君,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98.
[3]朱立元.美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435.
[4]葉渭渠,唐月梅.日本人的美學意識[M].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25.
[5]彭修銀.東方美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本文系2021年度山東省藝術科學重點課題項目(編號:L2021Z0707016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濰坊學院外國語學院
3050500338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