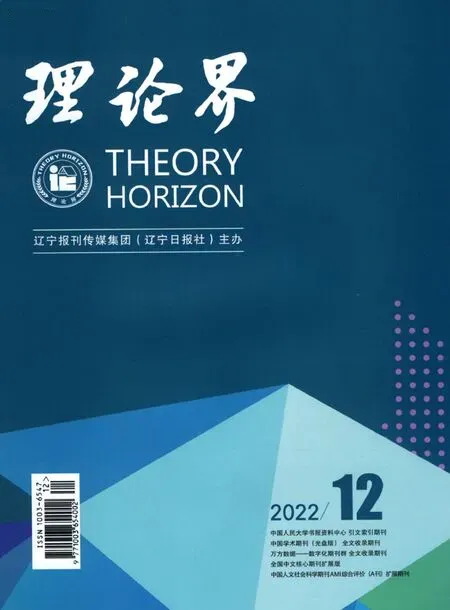反差視角下的《說岳全傳》牛皋形象研究
李 帥
明清長篇章回小說擅長運用反差來制造令人捧腹的可愛有趣的文學形象,武將形象亦在此列。他們身上往往兼具各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各種元素彼此沖突卻又交相輝映,在同一人物身上構成巨大張力,讓人頗感氣韻生動、親切有味。金圣嘆在點評《水滸傳》李逵時,已對這一現象有充分關注。他屢次使用兩個詞語——“天真爛漫”和“嫵媚”——來贊許李逵,可謂獨具慧眼。例如:“三字越可憐,越無理,越好笑,越嫵媚。”〔1〕“天真爛漫,不是世人害羞身份。”〔2〕“何等嫵媚,其疾如風。”〔3〕“偏寫他假處,偏是天真爛漫,令人絕倒。”〔4〕“天真爛漫”是說人心性單純,活潑自然,沒有矯飾與虛偽。“嫵媚”在《古代漢語詞典》里則解釋為“姿態美好”。《舊唐書·魏徵傳》里面李世民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5〕此處的“嫵媚”,就是此義。“嫵媚”和“天真爛漫”這種形容詞之所以能交匯在梁山好漢李逵身上,恰是因為金圣嘆發現了李逵各種特征之間錯位和反差所催生的可愛特點。正是這些看似不協調的因素共同造就了文學史上光彩熠熠的李逵形象,使其成為中國古代小說中武將可愛有趣一系的先驅。
如果說李逵導夫先路,顛覆了讀者對傳統武將形象的許多固化認知,那么《說岳全傳》里的牛皋則毫無疑問是運用反差書寫策略塑造武將可愛特征的另一座豐碑。反差書寫策略在牛皋身上有何種體現?秉承了怎樣的創作原則?承載了哪些文化內涵?目前學界尚未對這些問題給予充分關注與討論,本文將嘗試通過分析給出解答。
一
“反差”其實某種程度上是針對“刻板印象”而言的。“刻板印象”本是印刷術語,意指印刷鉛版,1922年記者沃爾特·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首次將其由印刷技術領域引入到了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用以描述和命名成見對人們認知世界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研究顯示,“刻板印象”意味著人們對某個事物會形成一種以偏概全的僵化固定看法,并將這種看法推而廣之,先入為主地認為這個事物或整體都會具有該特征,從而忽視個體差異。將刻板印象帶入武將故事的創作與閱讀過程,則往往會導致作者和讀者的閱讀期待視野變得狹窄,僅僅聚焦于他們莊嚴肅穆、殺伐決斷的共性側面。早期史書對牛皋形象的記載頗能體現這一點。以《宋史·牛皋傳》為例,這篇傳記意在著重凸顯牛皋兩點特征。第一點是他的驍勇善戰,比如:“金人再攻京西,皋十余戰皆捷。”〔6〕“皋追擊三十余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7〕第二點重在突出他的精忠愛國與赤膽忠心,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臨死時還在為不能實現南北一統、恢復中原而流露痛惜之情:“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尸,顧死牖下耳。”〔8〕質言之,早期史書中的牛皋形象特征符合人們對愛國武將勇猛精進、殺伐決斷的閱讀期待,但是與其他史書中的武將形象書寫相比,顯得共性有余而個性化不足,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認知特征。
從歷史位移到小說,牛皋形象漸變,這種變化至《說岳全傳》到達頂峰。隨著進一步加工改造,在原來史書突出的勇毅與愛國基礎上,蔓生諸多新特點,使其形象在可敬可畏基礎上擁有了更多可親可愛的柔性元素。而這些新特點之所以得以生成,恰是因為作者擅長使用反差書寫策略,從而有力打破了刻板印象對武將形象的束縛和制約,使其更加豐富多元。這種反差,大而言之,可分為兩類,本文將分而述之。
1.外在環境和人物抉擇的反差
孫紹振在談及塑造人物特征時曾言及“打出常規”一途:“情節的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規,或者說打入第二情境,使之顯出非常規心態,或者第二心態,把人物隱藏在深層的,甚至是潛意識的心態揭示出來。”〔9〕此處提到的“第二情境”在明清武將故事里,往往體現為具有生死考驗巨大壓力的外部環境。當這種外部環境與人物的面對方式構成張力,就會生發妙不可言的人物魅力。具體而言,按人物面對考驗所做出的反應,又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1)以硬碰硬
眾所周知,常人面對危險會進入恐懼、緊張、渴望自我保護等心理狀態,進而將這種內在狀態外化為一種舉止上的不敢輕舉妄動。我們不妨把這種謹慎狀態稱為“以柔克剛”或者“以靜制動”。然而,非凡之人自有非凡勇氣。文學史上,許多杰出人物形象都勇于跳出這種常規態勢,在極度緊張的情境下敢于打破禁忌,挑戰權威,為人物的心理刻畫與性格呈現宕開新格局。這種方式我們不妨稱之為“以硬碰硬”。其中第一個“硬”源于人物內心力量,凸顯的是人物強勢霸氣與奮不顧身的情感態度,第二個“硬”,是指外部環境的高壓與緊張。這在第十二回有最直觀體現。岳飛被逼之下槍挑小梁王,連宗澤都“心里卻有些慌”,整個武場氛圍異常緊張。就在張邦昌傳令要將岳飛斬首的千鈞一發之際:
底下牛皋早已聽見,大聲喊道:“呔!天下多少英雄來考,那一個不想功名?今岳飛武藝高強,挑死了梁王,不能夠做狀元,反要將他斬首,我等實是不服!不如先殺了這瘟試官,再去與皇帝老子算帳罷!”便把雙锏一擺,望那大纛旗桿上“當”的一聲。兩條锏一齊下,不打緊,把個旗桿打折,“哄嚨”一聲響,倒將下來。〔10〕
在武舉考場這種壓迫感強烈的嚴肅氛圍里,常人往往一舉一動都恨不得慎之又慎,因為只要稍有差池便有可能付出沉重代價。然而作者卻偏要寫牛皋的奮不顧身。為救好兄弟岳飛的性命,他甚至連造反都豁出去了。其無所畏懼的言行與現場壓抑威嚴的氛圍構成了一組巨大反差。這種突破常規的挑戰姿態和普通人的通常做法形成對比,為讀者了解牛皋心理狀態、展現其性烈如火與憨厚單純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2)舉重若輕
“重”在此處主要指外部環境的緊張危險和層層壓力,“輕”則指人物面對困難時的氣定神閑與不以為意。這在《說岳全傳》軍事戰爭描寫中有集中體現。自古而今,戰爭的嚴酷屬性導致人們往往不敢掉以輕心,而是嚴陣以待、以命相搏。然而,牛皋有時會持有一種近乎兒戲般瀟灑得有些夸張的方式在戰場上與敵人交鋒,與死神過招,甚至能在并不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取得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勝利。這在第三十二回有生動體現:
牛皋道:“常聽得人說:‘吃了十分酒,方有十分力氣。’快去拿來!”……牛皋雙手捧起來,吃了半壇,叫家將:“拿了這剩的那半壇酒,少停拿與你爺吃。”立起身來,踉踉蹌蹌,走下大堂。……牛皋也不答應,停了一會,叫:“快拿酒來。”……這牛皋吐了一陣,酒卻有些醒了睜開兩眼,看見一個番將立在面前抹臉,就舉起锏來,“當”的一下,把番將的天靈蓋打碎,跌倒在地,腦漿迸出。牛皋下馬,取了首級,復上馬招呼眾軍,沖入番營,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金節出關迎接,說道:“將軍真神人也!”牛皋道:“若再吃了一壇,把那些番兵都殺盡了。”〔11〕
在這緊張的戰場上,牛皋戰前放松,戰時迷糊,戰后也不后怕。以一種看起來稀里糊涂、傻人傻福的方式取得了輝煌戰績。這種兒戲態度某種程度上解構了戰爭的嚴酷性,同時游戲的意味則被放大和突出。而關于“游戲”,伽達默爾曾言:“游戲最突出的意義就是自我表現。”〔12〕“觀賞者不管其與游戲的一切間距而成為游戲的組成部分。”〔13〕并指出:“在觀賞者那里,游戲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14〕受此啟發,我們可將讀者視為這場戰爭的直接觀賞者和間接參與者,而他們得以參與其中的媒介則是“牛皋”,所以當牛皋以其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氣度、好運的加持意外取勝時,牛皋本體的自我表現與讀者自我的理想化呈現實現了某種程度的重疊。這意味著,他成了讀者的一個情感支點,更容易獲得讀者共情,也就更容易受到讀者的欣賞和喜愛。
2.外在身份與言行舉止的反差
一個人的外在身份通常與他的籍貫、年齡、輩分、家族、性別、職務、職業等息息相關。這些要素對個體的潛意識和行為有較大規范作用,也容易讓人生成刻板印象。但人是復雜的,人的性格是一個多元復合體,絕不是一個身份就可以涵蓋的。總有一些性格要在他的身份基礎上旁逸斜出,顯得出人意料。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小說,元雜劇也深諳此道。比如康進之《李逵負荊》寫剛下山的李逵陶醉于春光春色:“(云)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做笑科,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唱)恰便是粉襯得這胭脂透。(云)可惜了你這瓣兒,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兒去。我與你趕,與你趕,貪趕桃花瓣兒。”〔15〕在這里,李逵不忍心花瓣被冷落、踐踏,特意將它們放入流水中。就這樣,在這春天的一晌貪歡里,梁山好漢“鐵牛”不知不覺之間變成了內心細膩柔軟的護花使者。這與他通常粗豪的一面形成鮮明對照。《說岳全傳》塑造牛皋時,也注意吸收這類書寫經驗。不同處在于,《李逵負荊》中李逵的萌點放置到了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當中,而《說岳全傳》則轉移到人與人交往的社交領域,這尤其體現在他的親子關系上。比如第六十六回:
牛皋聽了,大哭起來。牛通怒哄哄地立起身,走上來指著牛皋大喝道:“牛皋!你不思量替岳伯父報仇,反在此做強盜快活,叫岳二哥受了許多苦楚!今日還假惺惺哭什么?”牛皋被兒子數說了這幾句,對二公子道:“當初你父親在日,常對我說:‘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今日果應其言!”〔16〕
牛通頂撞父親牛皋,對他大喝、指責,而牛皋并未勃然大怒,兩人的家庭地位仿佛顛倒了一般。不僅如此,牛皋還以自嘲方式反思批評了自己,化解了一場家庭沖突,顯得寬厚大度、幽默有趣。這種反差,其實是帶有可貴的反傳統意味的。封建社會家國同構,父權在家庭生活中至高無上,親子關系隨之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性。現實生活中,嚴父比比皆是,反映到文學作品里亦是如此。《紅樓夢》里面賈政和賈寶玉的貓和老鼠般的親子關系就很有代表性。賈寶玉怕極了賈政,在他面前大氣不敢喘,更別提頂撞。聽襲人說賈政要見他,他的反應是“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父權在家庭中不怒自威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相較而言,牛皋絲毫沒有封建家長那種固化的威儀,顯得平等親切了許多。
另外,這種身份與言行的反差還存在于牛皋和朋友的日常交往中。比如第十一回寫牛皋與眾兄弟進了校場,他記起旅店主人在他馬鞍后掛了一個口袋:
牛皋道:“妙啊!停一會比武,那有功夫吃?不若此時吃了,省得這馬累墜。”就取將出來,都吃個干凈。不意停了一會,王貴道:“牛兄弟,我們肚中有些饑了,主人家送我們吃的點心,拿出來大家吃些。”牛皋道:“你沒有得么?”王貴道:“一總掛在你馬后。”牛皋道:“這又晦氣了!我只道你們大家都有的,故此才把這些點心牛肉狠命的都吃完了,把個肚皮撐得飽脹不過。那里曉得你們是沒有的。”〔17〕
考武舉之前,牛皋肚餓,不假思索地以為拴掛在他馬后面的數十個饅頭和許多牛肉都是給他自己的,一口氣全吃完了,搞得弟兄們都沒的吃,完全不似一個成熟穩重的成年人,倒像一個幼稚貪吃、笨拙單純的頑童。之所以產生這種藝術效果,是因為作者此處是在運用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的反差制造一種“孩子氣”。所謂生理年齡指:“人自然生長的年齡。以出生后實際生活過的年數和月數計算。目前尚無真正清楚的標準,一般以人體的組織、器官、結構系統和生理機能的生長和成熟程度為指標。”〔18〕而所謂心理年齡又稱為“智力年齡”。“在正常個案中,智力是與實足年齡相等的。如某一年齡,智齡比實齡大,即較一般同齡人智力高;如某一兒童智齡較實際年齡低,即較一般同齡人智力低。”〔19〕從生理年齡角度看,牛皋已是成年人,人們通常認為他的行為應和他的心理年齡成熟度匹配。可是他有時偏像個孩子一樣魯莽不周、天真笨拙。這種錯位和反差,也是他顯得有趣可愛的重要原因。
二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作者正是有效運用外部環境、人物身份與本體個性之間的錯位制造反差,造就了牛皋形象的多重張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有反差張力不一定就可愛有趣。實際上,牛皋身上的種種反差如果稍有不慎很容易走到這種效果的反面,被處理成令人討厭的諸多缺點,比如:大敵當前卻喝得酩酊大醉,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瀆職;武舉考場上,他不守規矩,大喊大叫,也可以視為一種無禮;他跑去當綠林強盜,也可以說是一種離經叛道。所以,我們提出的問題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效果之間的邊界究竟在哪里?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作者至少有效把握了兩個關鍵性的書寫原則。
1.在反差中注意凸顯利他性的道德意識
牛皋很多沖動魯莽的行為顯得可愛,恰是因為他的這些舉動不是為自己謀利,而是在無私地顧全別人,換言之,他的很多行為有一種自發主動的利他性。比如,他在比武場大喊大叫,說出忤逆的話,行為動機是維護好兄弟岳飛的性命,將朋友置于自己生命之上,把自己搭進去也在所不辭。這個行為的本質是舍生取義,符合儒家理想人格。所以,他的魯莽沖動,就在不覺間位移到了傳統美德的至高點,是一種高尚行為。
這一原則在“牛皋剪徑”情節里也有體現。在岳飛與剪徑牛皋不打不相識時,牛皋意識到岳飛沒有武器,絕不肯占岳飛半分便宜:“岳大爺道:‘你若打得過他,便送些與你;如若打他不過,卻是休想!’那好漢(牛皋)怒道:‘諒你有何本事,敢來捋虎須?但你只一雙精拳頭,我是鐵锏,贏了你算不得好漢。也罷!我也是拳頭對你罷。’”〔20〕牛皋贏也要贏得正大光明,于是放棄了鐵锏,赤手空拳和岳飛搏斗,這種行為體現出他內心的坦蕩與光明。雖然強盜身份本身是不美好的,但是牛皋內心磊落,這個反差也就制造了新的萌點。也正是因為他頗具正義道德感,所以不良行為引發的后果惡劣嚴重程度就得到了有效遏制。比如,寫他剪徑當強盜,卻沒有寫他濫殺無辜,而僅僅是為了取得錢財去投奔岳飛而恫嚇了平民。他的缺點因此成為相對輕微的缺點。這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水滸傳》中對李逵形象的處理。《水滸傳》寫李逵第一次遇到心目中久仰大名的好漢宋江,想請宋江吃頓飯,苦于沒錢,于是去賭場賭博,賭輸了他的反應一反常態:
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么閑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里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閑常最賭得直,今日如何恁么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摟在布衫兜里,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閑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21〕
賭場輸了卻反悔賴賬本令人反感,但作者寫他反常行為的目的卻是請心中偶像宋江吃一頓飯。他今日的“不直”是建立在平日“直”的基礎上的,兩相對比,英雄好漢生活竟這般捉襟見肘,對待朋友的方式卻又如此真情實意,不由得讓人心生憐憫。所以雖然干的不是什么光明勾當,卻也容易獲得讀者的理解與寬容。
2.強化喜劇色彩,淡化悲劇色彩
我們在此不妨提出一種假設:試想,如果將牛皋寫為面對戰爭因縱酒而被敵人活活殺死,那么他的形象就恐怕不是輕松可愛而是可悲可嘆了,跟《三國演義》里面喜歡縱酒、性格大意、導致袁紹軍隊大敗的淳于瓊差不多,變成了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角色。又試想,將牛皋之死寫得像諸葛亮秋風五丈原一樣傷感,讀者可能會感到共情和感動,卻不會認為這是詼諧可愛的。《說岳全傳》作者之所以能避開這一問題,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頗為注意在涉及一些原本沉重嚴肅的命題時,選擇用喜劇色彩去淡化甚至抵消事件本身具有的悲劇意味。比如面對戰爭時,寫牛皋以兒戲般態度有驚無險取勝;又比如面對死亡,作者力避悲情。這在第七十九回“氣死金兀術,笑死牛皋”情節有所體現:
牛皋也是一跤跌下,恰恰跌在兀術身上,跌了個頭搭尾。番兵正待上前來救,這里宋軍接住亂殺。牛皋趁勢翻身,騎在兀術背上,大笑道:“兀術!你也有被俺擒住之日么?”兀術回轉頭來看了牛皋,睜圓雙眼,大吼一聲:“氣死我也!”怒氣填胸,口中噴出鮮血,不止而死。牛皋哈哈大笑,快活極了,一口氣不接,竟笑死于兀術身上!這一回便叫做“虎騎龍背,氣死兀術,笑殺牛皋”的故事。那兀術陰靈不憤,一手揪住牛皋的魂靈,吵吵嚷嚷,一直扭到森羅殿上去鳴冤。〔22〕
眾所周知,死亡在傳統文化里極具恐怖與消極意味:“古典藝術表現死亡多把它視為存在的一種喪失,是生命的終結,而藝術旨趣多是悲劇性的。”〔23〕然而,《說岳全傳》對牛皋死亡方式的處理,卻某種程度上偏離了人們對死亡的刻板印象。因為“死亡”有時候還可被理解為:“是具有倫理力量的性格心理的極致表現,更能流露出情感符號的價值觀和倫理觀,藝術家的道德尺度也借助于人物的死亡得以顯現。”〔24〕以此觀之,《說岳全傳》對“氣死金兀術,笑死牛皋”情節的構建也折射出作者的情感態勢與價值理念。作者讓牛皋騎在了金兀術身上,大笑而亡。“笑”本具有愉悅積極的情感色彩,而“騎”又可理解為一種壓倒性的勝利姿態,體現出當時語境下,宋人面對侵擾時渴望獲勝的心理訴求和家國情感。后面作者還寫兩人陰魂不散,一直扭打到森羅殿去鳴冤,這又有了歡喜冤家的喜劇效果。王國維曾言:“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25〕牛皋之死可謂完美契合了這種國民樂天心理。要言之,正是因為實現了這兩種心理的雙重滿足,牛皋之死才兼具了喜劇色彩,傳統“死亡”哀傷不祥的意味也隨之被沖淡乃至消散。他的死亡因此也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學死亡書寫里的一個異數,極具藝術魅力。
三
結構主義提出:“事物的真正本質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們在各種事物之間的構造,然后又在它們之間感覺到的那種關系。”〔26〕這提示我們既要關注文本各個元素自身獨立存在的性質,又要關注整體中各元素之間存在的有機聯系。這種微妙聯系,金圣嘆曾有所察覺,并將其納入《讀第五才子書法》中的“背面敷粉法”和“反襯法”予以揭示。牛皋形象亦可如是觀之。
一方面,種種反差突破了刻板印象束縛、大大增添了牛皋作為武將的獨特魅力,另一方面,也有效調節了將帥關系的對比,使我們看到,牛皋對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特別是岳飛形象的構建也能增色不少。學界對此已有清晰認識:“這一組將帥形象還具有鮮明的對比作用。比如岳飛英武正氣,牛皋粗豪狡黠;岳飛性格豐富,牛皋內心單純。岳飛‘以身許國、志必恢復中原,雖死無恨’,對朝廷和君王忠貞不貳。與之相比,牛皋對社會現實的認識要清醒得多,他甚至以‘大凡做了皇帝,盡是無情無義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騙,不受招安’這一尖銳的言語,毫無忌諱地道出了封建統治者的虛偽本質。兩人相映成趣,都是可愛而又可敬的英雄形象。”〔27〕除了牛皋和岳飛,《水滸傳》李逵與宋江、《三國演義》張飛與劉備,亦取得了這種因為組合而得以實現的一加一大于二的審美意趣和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