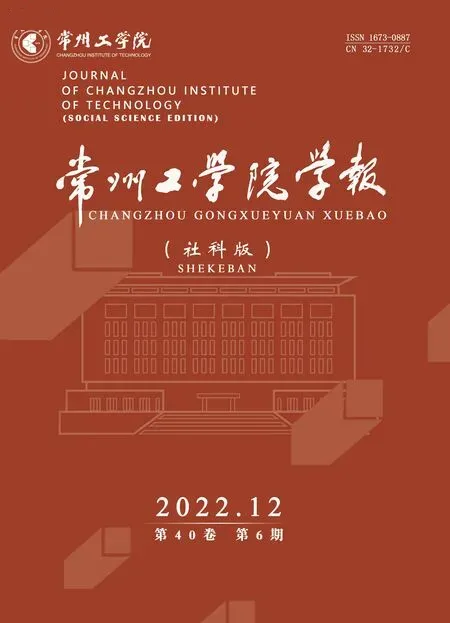建筑、身份認同與文化反思
——論《考工記》中“陳家老宅”的多重意蘊
李路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開封475001)
“陳家老宅”在《考工記》中仿佛一條線,貫穿整部小說的始終,串聯起眾多的人與事,同時又反映出當時上海的歷史。王安憶將鏡頭對準“陳家老宅”,以主人公陳書玉平凡而又獨特的生命體驗為線索,生發出對個人、歷史和文化的多重思考。“陳家老宅”這個獨特的空間和它周圍的人的命運緊緊相連,家人的風云流散和老宅無可避免的衰敗,表明二者共同的命運走向。而承載著歷史和文化的老宅無法幸存,甚至難以得到關注,又暗示著民族傳統文化的失落。至于在老宅中生活的陳書玉,一旦作為個體身份證明的老宅徹底坍塌,他就失去了合理的個人身份與價值的認證,這也是他不斷通過各種方法想要保全老宅的原因。通過一部《考工記》,王安憶把對歷史文化的反思、個體身份認同的困境徐徐展開。
一、人與屋命運的相互嵌合
《考工記》中人與屋的關系是相互嵌合的,王安憶通過書寫人、屋相互纏繞的命運,由此展開對整個社會歷史的思考。小說開篇就從這座老宅講起,回到上海的陳書玉在一片廢墟中看到自家的老宅,他對老宅的印象是萬事萬物都在變,獨這座老宅不變不移。在一片廢墟中格外顯出它肅穆的靜美,這是陳書玉回到上海后見到老宅的第一感覺。實際上,受戰亂的影響,這座宅子里居住的人早已風云流散,老宅也開始頹敗。陳書玉的一生是孤獨的,他游離在人潮之外,與親人疏淡,雖有幾個好友,但也在時代的裹挾下各自走散,唯一和他相伴的只有這座老宅。然而極為諷刺的是,曾經想逃離這座老宅的他,最終還是無可奈何地回到這里。
人的生存處境暗示著人物的命運走向,而人物的生存處境又和他的性格息息相關。陳書玉來自一個破落的世家大族,這樣的生活經驗造成了他封閉、怯弱和優柔寡斷的性格。他并非沒有離開老宅的機會,冉太太寄來的那張去香港的申請表,就是他逃離老宅的最好機會。只是他最終選擇留下來和老宅共度殘生,這其中必有其性格的原因。這樣的性格氣質無法和他生活的老宅脫離關系,空曠而陳舊的老宅加劇了陳書玉的不安,使他難以融入新時代的生活中,于是陳書玉和老宅的命運走向毫不意外地融合了。
老宅的來源已經不可考,至于他們家的歷史更是久遠得無法說清。記憶上的模糊性更增添了老宅命運的不確定性。就像身處時代洪流的人們,他們不知道未來走向如何,不過是順其自然罷了。閱讀王安憶的小說,我們可以發現,她總是將目光投向身處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的個體命運。不管是《長恨歌》中的王琦瑤,還是《考工記》中的陳書玉,王安憶總是通過對生活在上海的煙火氣息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的描摹,以達到弱化集體創造歷史感而突出個體參與歷史建構的目的。
小說中人與屋相互糾纏的命運,折射出王安憶樸素的哲學思考,即二者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房屋的存在價值由居住在其中的人體現;而人又通過房屋進行社會交往活動。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陳書玉和老宅的關系在生命的維度上是相互勾連的。“人和屋之間有著一種雙向建構性”[1],陳書玉不僅是房子的主人,更為重要的是老宅的結局隱喻了他的命運走向。所以,《考工記》中人與屋的關系不是彼此割裂的,王安憶巧妙地將眾人置于一個命運共同體中,共同體的核心自然是這座老宅。在王安憶的筆下,人決定了老宅的存在狀態,而老宅則反映了人的生存際遇。作家有意將二者放在一起敘述,由此勾勒出這一時期上海的風云流轉與人事變幻,并試圖反思小人物在時代潮流中的命運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圍繞著老宅,王安憶書寫了不同人物的命運。表面上看只有陳書玉和這座老宅的關系最為緊密,但實際上除卻陳書玉,“西廂四小開”中的其他三人也與老宅關系密切。朱朱,這個看起來和老宅關系最淺的人,因為他的妻子冉太太的緣故,夫妻二人和這座老宅產生了聯系。冉太太性格強勢,為人又有俠義之氣,在動蕩的歲月里,很需要這樣的人。與其說陳書玉對冉太太有超出朋友間的情愫,不如說陳書玉需要一個冉太太這樣的人將他從這座老宅中拯救出去。大虞,是和這座老宅互動較多的一個人物。作為一個木匠,他十分清楚這座老宅的價值,對老宅是如何營造的如數家珍,仿佛他才是這座老宅的主人,通過他的眼睛,讀者第一次看到了這座老宅的價值。從小說的題目“考工”來看,大虞首先道出了陳家老宅的營造史,通過他的眼光將老宅的文化價值與歷史價值發掘出來。奚子,這個在小說中出現次數最少且每次都很神秘的人物,在老宅的保護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由奚子引出“弟弟”和小李兩個人物,陳書玉在營救大虞的父親、朱朱以及老宅的保護中都是通過小李這個媒介完成了和奚子的溝通。至于更加神秘的“弟弟”,他更像是陳書玉的精神依賴。他的存在讓陳書玉飄忽不定的心安定下來,“對面的人,仿佛動蕩事實中的一個恒常,萬變中的不變,是他的依賴”[2]85。
“西廂四小開”的命運雖方向不同,但殊途同歸。陳書玉和大虞信奉著“順其自然”的人生哲學,在動蕩的歲月里,陳書玉希望擺脫這座宅子以求得生命的安全,然而他無論怎樣掙扎,也只能按照命運的安排“順其自然”地和老宅共生。大虞原本家境殷實,但因父親入獄,他散盡家產營救父親出獄,而他和譚小姐的婚事也因此告吹。朱朱也是因為政治錯誤而經受了牢獄之災,出獄之后冉太太帶著他們一家移居香港。至于奚子,他本來好好地做著官,可是因為政治斗爭他只能出門避禍。命運的無常他們無力改變,在時代的洪流中除了順其自然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他們在認清了生活的本質后,只能按照既定的軌道前行。在毫不留情的歲月面前,身處洪流中的人只能被裹挾著前進,即便過著各不相同的生活,但卻有著相同的人生體悟和心境,縱是兵荒馬亂,也只能妥協順受。從這個意義上講,人物的命運和老宅的命運相互嵌合、相互映射,都帶有無可挽回的悲劇色彩。
老宅和陳書玉如何在時代的風云變化中“生存”是王安憶寫作的一個主題。老宅和陳書玉在上海這個時空里見證了時代的繁華與落寞,經歷了生活中的苦痛與磨難,最終人與屋的命運實現了合流。陳書玉和老宅成為了時代洪流中的“常”,在上海社會“變”的情況下,老宅和陳書玉的“常”就顯得十分不合時宜。即便陳書玉為拯救老宅不斷奔走,可是依然無法避免被拋棄的現實。王安憶在《長恨歌》中表達了一個同樣的生存主題,王琦瑤作為上海中的“常”,順其自然地生活,外部社會的“變”被她屏蔽,于是她也成為時代的棄兒。由人與屋的命運上升到身處時代浪潮中的個人的命運,王安憶通過這種方式反思身處現代社會的人應該如何處理與時代的關系。
二、傳統文化斷裂的隱喻
陳書玉的家族歷史和老宅的歷史共同營造了可供世人考證的傳統文化史,于是它在某種程度上就成為傳統文化的象征。老宅在歷史的風雨中逐漸凋零破敗,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中又該如何存續。于是,王安憶在小說中安排了一條修葺老宅的線索,是否應該修以及如何修?王安憶借助陳書玉的行為向讀者傳達出傳統文化在現代文明中進退失據的狀況。
這座老宅在小說的開篇就突兀地出現在讀者面前,在月光下的廢墟中傲然挺立,仿佛時間獨獨在它的身上停止。作者賦予老宅一種遺世獨立的姿態,固執且不愿流俗。讀者第一次對這座宅子的歷史有所了解是通過祖父之口:“一日興起,帶陳書玉走遍樓上樓下,指示門扉上的雕飾,原來都有源頭,源頭都是八仙。……祖父說,這宅子的原主當是京官,因其宅基正北正南……”[2]33通過祖父之口,讀者知道了這座老宅的淵源,對其基本的形制有了基本了解。而讀者真正對這座老宅有詳細的認知是通過大虞的視角,王安憶借大虞拜壽這件事,對老宅進行了細致的描摹刻畫。這座老宅結合了西洋建筑的技法,又帶有中國傳統的文化底蘊,尤其是門頭上的八仙浮雕。“頂上一列脊獸,形態各異,琉璃的材質;檐口的瓦當,瓦當上的釘帽,前端的滴水,全是釉陶。前一夜下了雨,今日太陽出,于是晶瑩剔透,光彩熠熠。”[2]41-42通過大虞這個專業的木匠向讀者證實了這座老宅所具有的文化底蘊和厚重的歷史。
由人類建造的房屋絕非一個簡單的物質實體,在建造的過程中就已經投射了人類的情感,并且由于它參與了人類的歷史活動,這些建筑自然就成為具有人類屬性的產物。擁有厚重歷史的老宅就有了象征意義,即它發揮著符號指示功能,傳達著作者的概念、觀念和情感。所以,一方面老宅作為傳統家族禮教的精神內核,通過其精美的外部結構和久遠的歷史呈現出來;而老宅又通過它獨有的建筑特色和器物浸潤著人的精神內涵,并將傳統文明傳承下去。另一方面,老宅作為傳統文明的具象載體,對它的觀照和感知即表明作為現代人的陳書玉對傳統文化的認可,他選擇留在老宅或許就是出于這個原因。但時代的浪潮撲面而來,歷史的動蕩讓他深感恐懼,這座宅子就像一只“未落地的靴子”懸在他的頭頂,這座有著文化和歷史底蘊的宅子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大虞對陳書玉說擔心他家的宅子,這句話里不僅有對陳書玉處境的擔憂,更是作者透過大虞之口傳達出對傳統文化前路未知的憂慮。
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原始和傳統的文化遭到質疑和否定。新的社會在一體化的建設中,以階級話語采用強制性的制度將人與老宅及老宅文化強制剝離,老宅在歷史的車輪下不斷遭到碾壓。最直接的體現是,老宅無法挽回地變老變舊變得暮氣沉沉。不僅如此,外部的社會也在擠壓老宅的生存空間。老宅外的廢墟又重新建起了房子,下雨和刮風推倒了,再又重起。“每一次重起,屋脊都要高半尺,屋腳則向前跨一步,于是巷道越來越窄”[2]30,“東墻人家則推進蠶食,左右擴充,又加蓋房頂,建一座鴿棚,鴿子屎滿地皆是,腥臭不堪,喂食的飼料再引來鼠類……攘外必顧此失彼,而如今,顧此失彼,幾近全線崩潰”[2]113。可以看到不論是宅子本身的存在狀態還是外部環境給予老宅的生存空間,都清楚地表明老宅頹敗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此外,文中兩個人物的死亡也預示著老宅的結局,映射著老宅代表的傳統文化不被重視瀕于斷裂的境況。首先是和老宅同生共存的祖父,他的一生都是在老宅度過的。陳書玉說祖父從來都是與世隔絕的,不管世事如何,只講悠然自得。這樣的祖父宛然一個在桃花源生活的人,這宅子就是祖父的“桃花源”,代表著傳統文化的最后棲息地,祖父的逝去暗示著文化傳承的斷裂。大虞相隔10余年再來老宅,此時透過大虞的目光,讀者看到的老宅是“院墻房屋,呈傾倒之勢,四合過來,壓迫了視野。門樓上的磚雕風蝕得厲害,變成一種灰燼的顏色”[2]246。通過前后兩次的對比,老宅前途黯淡的命運清晰地傳達給讀者。陳書玉依然渴望挽救老宅衰頹的命運,他和大虞約定,只要修宅子就請大虞出山做大木匠。陳書玉再三強調要請大虞做木匠,是因為老宅古老的建筑技藝瀕臨失傳,修復技藝傳承的斷裂也預示著修復老宅的前途一片灰暗。這座承載著歷史與文化的老宅,它的命運晦暗不明。修復老宅的事情因為各種原因無限期地延宕下去,而且大虞毫無征兆的去世更像是一個預言——老宅再無修復的可能。陳書玉在靈前哭得像個孩子,他的痛苦一來像奚子說的那樣,兄弟如牙齒,緊緊相依,缺了一顆就都松動了;另外就是因為大虞死了,老一輩懂得“攻木之本”的大木匠沒了,修葺老宅的愿望就此成為幻想。大木匠驟然離去,釜底抽薪似地摧毀了修葺大計,使得陳書玉的希望就此告破,徒留象征著傳統文化的老宅日漸破碎卻無力挽回。
修葺房屋活動的失敗,不僅隱喻了故事的悲劇性結局,而且也表達出王安憶對“懷舊”活動的質疑。“渴望以‘修復’的方式來留住歷史或者重現歷史,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行為。”[3]《考工記》中這座身兼歷史和文化價值的老宅只留下斷壁殘垣,僅有一座刻著“煮書亭”的石碑立在門前,仿佛一座墓碑祭奠著傳統文化斷裂以及難以承續的遺憾。“尋根思潮后,王安憶小說一個最醒目的審美特征就是一個舊字,舊的街道、記憶、故事、傳聞和鄉間歷史,紛紛涌入她的小說藝術世界。”[4]“陳家老宅”就是一個這樣的存在,作為歷史見證者的老宅最終破落成“上海鍋底”,它的歷史和破敗言說著它的陳舊,而這“陳舊”中包含著精神和文化的遺產,所以它的破敗隱藏著王安憶對傳統文化斷裂的隱憂。
三、個體身份認同的困境
老宅在風暴中坍塌化成齏粉,生活在老宅中的陳書玉暴露在眾人面前。“文明突然坍塌了一塊,就可以看到平時隱藏著的一些縫隙。”[5]80這縫隙里藏著的就是煢煢孑立的陳書玉,舊時代的庇護轟然倒塌,在新的時代里他茫然無措,“他們好像是在一個文明或者社會的看不見的夾縫里”[5]82。小說的前半段,陳書玉想極力拋卻自己和宅子的聯系,除了這座宅子帶給他的孤寂感,還有就是他敏銳地發現這座宅子可能給他帶來危險。而到了小說的后半段,陳書玉各處奔走只希望能修復老宅,讓宅子保存下來。為了遠離危險他愿意拋棄老宅,而為了保留老宅他愿意放棄老宅。這看似矛盾,實則不然,放棄老宅不僅出于對老宅的保護,更是出于對個體身份認同的需要。
在那個動蕩的歲月里,“西廂四小開”中的大虞、朱朱、奚子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危險,唯獨他,這個帶著一座如此危險的宅子的陳書玉在這場動蕩中安然無恙地生存下來。各種各樣的方式都除不盡他,但當老宅坍塌毀滅的時候,他再也無法完成個人的身份認同,就連那個“城市平民”的身份都無法保存下來。他就像是一個“除不盡的余數”,一個我們這個社會的公約數無法除盡的人。陳書玉和這座宅子好像異類,對于他們出生和生活的地方來說是異類,對于我們這個正常的社會來說也是異類,他們仿佛陷落在文明或者社會深處的裂隙里。
陳書玉被遺忘在時間的縫隙里,這是因為作者有意設計了兩個敘述時間。首先是老宅里的時間緩慢流淌幾至停滯,它似乎預知到了自己的命運,所以不愿前行或者磨蹭地賴著不走。其次是外部的時間仿佛奔流的江水,浩浩蕩蕩一往無前,社會前進的浪潮沖擊著老宅和身居其中的陳書玉。而陳書玉仿佛被困在其間,他想融入發展的社會但又懼怕和它接觸,最終的結果是躲回讓他心安的老宅。在這老宅停滯的時空中,他看著外面社會化的浪潮,焦慮和恐慌又隨之而來。他連同這座老宅就夾在這時間的縫隙之中,被擠壓、被侵蝕直至化成齏粉。他的情況有點像魯迅筆下的“歷史中間物”,不管在怎樣的歷史語境下,都難以找到一個被大眾認可的合理身份。不管是做老師時的“城市平民”,還是退休之后的“區級政協委員”,這些身份都不能撫平他內心的焦慮。我們必須承認,迎面而來的新時代勢必會將這些舊人物拋棄在時代的洪流中。一個從未使用過的身份讓陳書玉有踩在空中樓閣上的虛幻感,一不小心就會跌落。所以他才努力從具體可感的老宅中獲得身份認同的安定感,老宅是他從舊時代走來的明證,也是他存在的意義。
陳書玉最根本的特點是“無”。一方面是指他努力隱身于時代,另一方面則是說他對時代總是采取一種游離的態度。作為“無”的陳書玉不單與時代若即若離,還必須與日常生活保持一段距離,這從他簡單的人際關系中可以窺見。60歲的陳書玉退休,學校敲鑼打鼓地送他回家。“看著他的背影在窄巷中越走越遠,孑然一身,人們發現,對于這個共事多年的身邊人,錯過了許多了解的機會,誰知道他經歷過或者正經歷著什么呢?”[2]243宅子給他提供隱藏的庇護所,他可以自然地拒絕與社會對話,他在自覺地排斥和這個新時代融合。他的交際似乎僅限于“西廂四小開”群體,一個缺少人際交流的人如何能夠在社會中完成身份認同呢?于是陳書玉和他的宅子一起陷入了時代的裂隙中。
此外,作者模糊了老宅的歷史,最為直觀的表現是家中的長輩也無法說清老宅和這個家族的關系。陳書玉聽著這些模糊的歷史,就像聽別人家的故事,毫無觸動。陳書玉對老宅的感情是復雜的,年輕時想逃離,中年時他因老宅可能帶來的危險想要拋棄老宅,到了晚年他又為修復老宅四處奔走。修復老宅并給予它一個合法身份,陳書玉想通過這種方式重新得到認可。為了使老宅獲得合法身份,就必須弄清老宅的歷史,那些傳說的家族史、老宅史不能夠成為佐證。為此陳書玉開始翻閱舊報紙,他希望從這些舊報紙中找到家族一星半點的歷史,從而為老宅獲得合法地位助力,可是在那些發黃破舊的報紙堆里找不到那些“相傳”的歷史。上海的正史與陳書玉的家族史隔著十萬八千里,那是別人家的故事,和陳書玉毫不相干。于是他只能從這座宅子留下來的一些老物件追尋家族的歷史,房契、祖父甚至曾祖的幾封短簡、幾頁豆腐賬、若干舊照片、一張文憑,他通過這些碎片拼湊他的家族史。
他在追尋著過去,試圖從過去的歷史中印證老宅的來歷,從而證明自己身份的合理性以及身份的來源,這是他立足的根本。他從未想過在當下為自己安排一個被社會認可的身份,一個被歷史漏掉的人,不敢期望在當下獲得身份的認同。即便他在“弟弟”的安排下獲得了新的身份,但和他一起參加活動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多是一些舊人物。他們的“談資不外懷想當年,數點今朝,有許多感慨,又有許多訴求”[2]244。只一個“舊人物”就限定了陳書玉難以在新社會中找到身份,人際關系的淺淡使他游離在社會的邊緣,他無法在這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安定下來。所以他急需一個身份,而他只能從這座老宅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在這漫長的歷史中老宅的身份來歷都已經不可考,所有的信息都是傳說和流言,虛假的歷史信息無法安放陳書玉這顆迷茫的心,他連同這座老宅都是被社會拋棄的“邊緣者”。所以當老宅在風暴中化為齏粉之后,陳書玉的身份就更加難以確認了。
四、結語
王安憶在《考工記》中設置了一個貫穿全文的“陳家老宅”,通過老宅這個空間意象傳達出作者對身處時代潮流中的小人物命運的思考,以及對傳統文化在現代文明中生存狀況的考察。老宅的命運和圍繞在它身邊的人的命運相互嵌合,他們無力抵抗時代的洪流,只能順其自然地生活。于是他們作為生活中的“常”最終被社會中的“變”所拋棄,而陳書玉為修復老宅所做的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則更顯其中的悲劇色彩。老宅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征,被眾人遺忘在角落,它的頹圮預示著傳統文化在現代文明中的失落。正像《小鮑莊》中撈渣的死亡一樣,暗示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生存境遇,這正是王安憶對文化尋根的思考和對傳統文化斷裂的隱憂。在《考工記》中陳家老宅作為陳書玉身份認同的一個象征,它的徹底坍塌表明陳書玉陷入了身份認同的困境。在新的社會語境中,陳舊的難以得到認可的老宅和垂垂老矣的陳書玉終究一起陷入時代的洪流中。從《長恨歌》到《考工記》,王安憶都以上海為書寫背景,且在其中完成了對人、事、物關系的考察以及對命運、文化的思考,這體現了她作為作家的責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