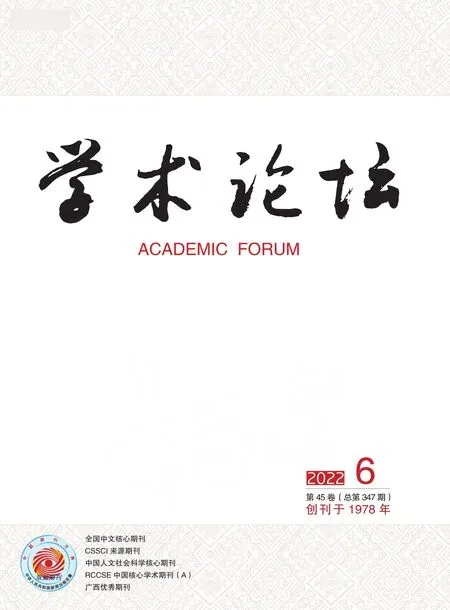敘事身份的內涵、意義與建構方式
尚必武
21世紀以來,敘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研究迅速升溫,成為敘事學乃至文學、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焦點話題。德國兩位敘事理論家比吉特·諾依曼(Birgit Neumann)和安斯加爾·紐寧(Ansgar Nünning)指出:“敘述與身份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已經成為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①NEUMANN B, NüNNING A.Ways of self-making in(fictional) nar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d identity[M]// NEUMANN B, NüNNING A, PETTERSSON B.Narrative and identity: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critical analyses.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2008:3.一方面,諸如保羅·約翰·埃金(Paul John Eakin)、詹姆斯·L.巴特斯比(James L.Battersby)、邁克爾·班伯格(Michael Bamberg)、喬治·布特(George Butte)、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等眾多理論家紛紛加入關于敘事身份的討論,并彼此之間展開激烈的爭論與交鋒,使得敘事身份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另一方面,學界出現了多個與敘事身份相關的概念,如自我敘事(self narrative)、生命敘事(life narrative)、故事化的自我(storied self)、敘事的自我建構(narrative self-making)等,使得敘事身份的討論愈加撲朔迷離、紛繁蕪雜。本文從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的敘事身份觀出發,試圖界定敘事身份的三個基本內涵,即身份的敘事、敘述身份和被敘述的身份。在此基礎上,筆者重點討論三個問題:為何身份離不開敘事;為什么說人類是敘事人,即人類為什么要講故事;敘事如何建構身份。
一、保羅·利科的困惑:為何身份離不開敘事
法國著名哲學家保羅·利科曾坦言自己在完成洋洋灑灑的三卷本《時間與敘事》后,被敘事身份這一問題所困而不得其解。利科說:“在完成《時間與敘事》第三卷之后,我遇到了一個問題。在長期游走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后,我問自己是否存在一種根本的經驗可以整合這兩大敘事。我提出的假設是,無論是對個體還是歷史群體而言,都可以在敘事身份的構成那里尋求歷史與虛構的融合。”①RICOEUR P.Narrative identity[J].Philosophy today,1991(1):73-81.實際上,利科的困惑并非個案,眾多哲學家都曾被敘事身份這一問題所困擾。根據安德烈亞·德西奧·里蒂羅伊(Andreea Deciu Ritivoi)的考察,“很長時間以來,哲學家們被個體身份(personal identity)這一問題所困擾,西方傳統上所提出的各種方法都難以應對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人類生物性條件所內在的變化性”②RITIVOI A D.Identity and narrative[M]// HERMAN D, JAHN M, RYAN M-L.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New York: Routledge,2005:231.。
從詞源學上來說,身份(identity)具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是自我,即拉丁文ipse,英文self,德文selbst;二是相同性,即拉丁文idem,英文same,德文gleich。在漢語中,身份等同于“身分”,一般用來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資格。根據《辭海》的解釋,身分又具有三個不同的含義:身份;模態、姿態;物品的質量③陳至立.辭海:第7卷[M].7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3848.。鑒于身份含義的多樣性,美國敘事理論家邁克爾·班伯格指出:“身份指的是在諸如性別、年齡、人種、職業、群體、社會經濟地位、族裔、階級、民族、國家或區域國土等不同的社會和個體維度上區別和整合自我的努力。”④MICHAEL B.Identity and narration[M]// HüHN P, MEISTER J C, PIER J, et al. Handbook of narratology.Berlin: De Gruyter,2014:241.國內學者聶珍釗認為,從起源上來看,身份有先天獲得的與后天獲得的兩種類型:“人的身份是一個人在社會中存在的標識,人需要承擔身份所賦予的責任與義務。身份從來源上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與生俱來的,如血緣所決定的血親的身份。一種是后天獲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⑤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264.當我們在討論身份的時候,通常會把目光放置于人在后天獲得的身份,并關注其社會意義。譬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身份政治:對尊嚴和認同的渴求》一書中指出:“身份如今有多種含義,有些情況下僅指社會類別或角色,還有情況指的是自己的基本信息(如‘我的身份被盜’)。這類含義的身份一直存在。”⑥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M].劉芳,譯.北京:中譯出版社,2021:14.福山認為,在現代,身份統一了三個不同的現象,“一是激情,渴望得到承認的普遍人性。二是內在自我有別于外在自我,且內在自我的道德賦值高于外部社會。這直到早期現代的歐洲才出現。三是不斷演變的尊嚴概念,承認不再只為某個狹隘的階級所應得,而不是人人應得”⑦同⑥37.。
為什么包括哲學家在內的多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都對身份這一問題感興趣,但同時又被這一問題所困擾?在利科看來,把握敘事身份的困難首先在于個體身份的模糊性。身份概念混淆了該詞所包含的兩個意義:作為自我的身份(identity as self)和作為相同性的身份(identity as sameness)。利科認為,身份暗含了與多元性(plurality)相對的獨特性(uniqueness),指向身份的相同性含義。在這一層面上,身份有四個維度:一是對相同性的一種重新認同(re-identification of the same);二是一種極端相似性(extreme resemblance),可以用一個替代另一個;三是超越非連續性的連續性(continuity over discontinuity),即不間斷的連續性;四是超越時間的永久性(permanence over time)⑧同①74.。就身份所指涉的自我含義而言,利科提出以下三個論點:一是自我認知是一種闡釋;二是在闡釋自我的所有符號和象征中,敘事可以作為一個優先的媒介;三是敘事這一媒介借用歷史和虛構,把生命故事變成虛構的歷史或歷史的虛構,甚至可以與那些混合了歷史和虛構的偉大人物的傳記相提并論①RICOEUR P.Narrative identity[J].Philosophy today,1991(1):73-81.。受利科影響,班伯格進一步指出:“任何關于身份的論斷都面對三個難題:1.面對不斷的變化,保持自我感的相同性;2.面對每個人都相同的他者,保持自我的獨特性;3.由自我(沿著自我到世界的適應方向)和世界(沿著世界到自我的適應方向)構成的代理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agency)。”②MICHAEL B.Identity and narration[M]// HüHN P, MEISTER J C, PIER J, et al. Handbook of narratology.Berlin: De Gruyter,2014:241.在某種意義上,敘事似乎成了解決上述三個難題的關鍵。在利科看來,所謂的敘事身份指的是“人類可以借助敘事功能的中介來獲得某種身份”(the sort of identity to which a human being has access thanks to the mediation of the narrative function)③同①.,也即是說,敘事是人獲得身份的中介(mediation)或途徑(means)。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就不難理解諾依曼和紐寧的觀點:“當然,處于敘事身份概念核心的是敘事。在敘事心理學上,敘事不僅被看作是文學形式,更被看作是組織人類經驗的一種根本方式,是建構現實模式的一種工具。”④NEUMANN B, NüNNING A.Ways of self-making in(fictional) nar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d identity[M]// NEUMANN B, NüNNING A, PETTERSSON B.Narrative and identity: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critical analyses.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2008:3.
問題的關鍵在于,為什么身份離不開敘事?利科的解釋是:“身份的問題被有意作為一個敘述的結果(the outcome of narration)提出來。根據我的觀點,敘事建構了個體被稱之為敘事身份的持久特征,在建構某種屬于情節的動態身份時,創造了故事主角的身份。因此,我們在主要在情節中尋找永恒與變化的中介,然后再把它移交給人物。這種通過迂回情節的優點是提供‘不一致的一致性模型’(the model of discordant concordance),根據這個模型可以建構一個人物的敘事身份。”⑤同①.可見,利科把身份與敘事的問題轉至了敘述與身份的問題,甚至直接把身份看作是“敘述的結果”(the outcome of narration)。對此,利科重點以傳記為例加以說明。利科認為傳記與敘事身份有著頗為密切的關系,他說:“當人類的生活被用來闡釋那些人們講述的關于他們自己的故事的時候,它們不是變得更具可讀性嗎?當這些‘人生故事’被用于從歷史和虛構(戲劇或小說)那里借來的敘事模式——情節的時候,它們不是更讓人容易理解嗎?自傳的認識論地位似乎可以確認這一直覺。”⑥同①.換言之,我們在討論敘事身份的時候,實際上不可避免地討論了敘述身份。因此,敘事學界常常會出現把敘事身份與敘述身份并用甚至是混用的情況。譬如,《勞特利奇敘事理論百科全書》納入了“身份與敘事”(identity and narrative),而《敘事學手冊》一書則收入了“身份與敘述”(identity and narration)。用敘事學術語來說,在建構身份的過程中,敘述行為主要涉及特定時空中的作者、敘述者和人物。班伯格說:“敘述這一言語活動涉及在時空中將人物排序,是身份建構的一個‘優選文類’(privileged genre),因為它要求通過手勢、姿勢、面部表情、眼神與話語的協調把人物放置于時空中。此外,無論是虛構敘述還是事實敘述,都傾向于‘人類的生活’(human life),一些超越了可報道或可講述的事情,是生命或值得生活的事情。因此,敘述可以讓說話者/作家將說話自我/寫作自我同說話行為分開,以一個反思位置去看待作為一個人物的自我。”⑦同②.
敘事身份并不是敘事(narrative)和身份(identity)的簡單疊加。在敘事學意義上,敘事包含兩個重要的維度,即故事與話語。在敘事文本之內,故事世界的主角是事件的行動者即人物,而話語世界的主角是事件的講述者即敘述者;在敘事文本之外,人物、敘述者以及敘事文本自身都是作者創作的產物。在討論敘事身份這一話題時,我們最終需要回到人物身份、敘述者身份、作者身份以及它們與敘事之間的關系。在不同類型的敘事文本中,作者、敘述者、人物的身份既可能重合,也可能不重合。綜合作者、敘述者、人物、敘事文本四個主要元素,筆者認為敘事身份大致包括以下三個基本內涵:第一,身份的敘事(narrative about identity),即敘事的本質是講述關于人物身份的故事,敘事文本是我們研究人物身份的基本對象;第二,敘述身份(narrating identity),即通過敘事獲得身份,敘述行為是建構身份的手段,在敘述行為使得作者和敘述者實現自我身份的建構;第三,被敘述的身份(narrated identity),即身份是敘事建構的結果,人物的身份在敘述中得以再現。
在敘事身份這一話題上,最核心的問題莫過于誰的敘事?誰的身份?從總體層面上來說,答案是人類的敘事和人類的身份。在人類學意義上,人類被稱為是“敘事人”(homo narrans)或“ 講故事的動物”(storytelling animal)。筆者擬在本文第二部分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從個體層面上來說,敘事之于身份的建構大致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我”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在講述過程中建構了“自我”身份,這在非虛構敘事尤其是傳記敘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等同于敘述者和人物,即他們是同一個人,具有相同的身份。第二種方式是“我”在講述他人的故事,在講述過程中,辨識或認同了“自我”身份,這在虛構敘事中較為常見。在這種情況下,作者不等同于人物和敘述者,即他們不是同一個人,具有不同的身份。第三種方式是“我”在講述關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講述過程中,建構了亦真亦假、相互沖突的“自我”身份,這在“自小說”中較為常見。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在名義上等同于人物和敘述者,即他們在字面意義上被宣稱是同一個人,但實際上又不完全是同一個人,具有既相同又不同的身份。筆者擬在本文第三部分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二、“敘事人”“ 講故事的動物”:人類為什么要講故事
如上文所及,從宏觀層面上來看,敘事是人類的敘事,敘事所建構的是人類的身份。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一文的開篇,羅蘭·巴特寫道:
世界上敘事作品之多,不計其數;種類浩繁,題材各異。對人類來說,似乎任何材料都適宜于敘事:敘事承載物可以是口頭的有聲語言、是固定的或活動的畫面、是手勢,以及所有這些材料的有機混合;敘事遍布于神話、傳說、寓言、民間故事、小說、史詩、歷史、悲劇、正劇、喜劇、啞劇、繪畫(請想一想卡帕齊奧的《圣于絮爾》那幅畫)、彩繪玻璃窗、電影、連環畫、社會雜聞、會話。而且,以這些幾乎無限的形式出現的敘事遍存于一切時代、一切地方、一切社會。敘事是與人類歷史本身共同產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從來不曾存在過沒有敘事的民族;所有階級、所有人類集團,都有自己的敘事作品,而且這些敘事作品經常為具有不同的,乃至對立的文化素養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敘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學,它超越國度、超越歷史、超越文化,猶如生命那樣永存著。①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M]//張寅德.敘述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
巴特的上述論斷直指敘事的普遍性,認為敘事以各種形式、各種文類、各種媒介得到再現。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尤其強調敘事之于人類歷史和人類身份的重要性,因為所有民族、所有人類集團都有自己的敘事,敘事與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而且就像人類的生命那樣永存于世界。如果將巴特的論斷進一步引申下去,那么就會涉及人類為什么要講故事這個問題。
在《人類為什么要講故事——從群體維系角度看敘事的功能與本質》一文中,傅修延試圖結合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把敘事看作為人類抱團取暖的一種行為。在傅修延看來,靈長類動物之間的梳毛是一種具有“前敘事”性質的溝通行為,其目的在于形成相互忠誠的盟友;隨后興起的八卦逐漸實現了通過敘事而結盟的目的,把擁有共同世界觀的人組織成同一張社會網絡;后來發展的圍火夜話也同樣使得人群相互靠攏,共同抵御黑暗。正是通過敘事,人類獲得了群體感。通過對梳毛、八卦、夜話和語音等四種不同敘事樣式的討論,傅修延的主要目的是“闡發敘事交流對人類群居生活的意義”①傅修延.人類為什么要講故事——從群體維系角度看敘事的功能與本質[J].天津社會科學,2018(4):114-127.。他指出:“國內敘事學在西方影響下偏于形式論,一些人甚至把研究對象當成解剖桌上冰冷的尸體,然而敘事本身是有溫度的,為此我們需要回到人類祖先相互梳毛的現場,聽取人類學家對早期講故事行為的種種解釋,從而深刻認識到敘事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抱團取暖的行為。萬變不離其宗,人類許多行為都和群體維系有復雜的內在關聯,只有牢牢地把握住這種關聯,我們今天的研究才不會迷失方向。”②同①.傅修延倡議從敘事的源頭追溯敘事之于人類的重要性,通過敘事把握人與人之間的群體性關聯,由此破解人類為何要講故事的奧秘。
倘若沿著傅修延的建議,根據人類學家的分析路徑來考察敘事之于人類的意義,我們可以發現敘事與人類身份之間的天然聯系。生物學家一般將人類命名為“智人”(homo sapiens),而人類學家則將人類稱為“敘事人”。在《敘事人:口頭文學的詩學與人類學》一書中,約翰D.奈爾斯(John D.Niles)說:“只有人類具有這個近乎不可思議的宇宙形成的或世界建構的力量。該事實太容易被想當然了。超出對語言或其他符號系統的使用,講故事是界定人類的一種能力,至少將我們關于人類經驗的知識拓展之歷史的過去和有時人種志所揭示的令人驚訝的領域。通過講故事,一個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的生物種類可以成為一個有趣的物種敘事人:原始人不僅僅成功地與自然界達成了和解,尋找到足夠的食物和住所來生存,而且還學會棲居于適應不在當下的時間和夢中事物的地點的心理世界。通過這些象征性的心理活動,人類獲得了把自己創造為人類的能力,也因此改變了此前未知的自然界外貌。”③NILES J D.Homo narrans: the poetics and anthropology of oral literature[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3.奈爾斯直接把人類稱之為“敘事人”,認為敘事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特征,人類通過敘事獲得世界建構的能力,進化成一個有趣的物種。與奈爾斯的觀點類似,延斯·布羅克邁爾(Jens Brockmeier)和多納爾·卡堡(Donal Carbaugh)認為,人類身份這個概念與敘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人類身份這個概念——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人類身份的可能性——與敘事和敘事性的概念是聯系在一起的”④BROCKMEIER J, CARBAUGH D.Introduction[M]// BROCKMEIER J, CARBAUGH D.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01:15.。從學理上而言,人類之所以要通過故事講述來建構自己的身份,不僅是為了結盟的需要,而且還因為他們可以通過敘事來辨識自己,即人類通過講述關于自我的故事而識別和認同自己。歷史上,人類通過敘事來建構和強化自己身份的例子屢見不鮮。譬如,猶太人就在《圣經》中的關于以色列人的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建構并獲得了自己的獨特身份。
奈爾斯認為人類是“敘事人”,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lntyre)認為人是“ 講故事的動物”。在《德性之后》一書中,麥金太爾寫道:“人在他的虛構中,也在他的行為和實踐中,本質上都是一個講故事的動物。他不是必然的,但通過他的歷史,成了一個渴望真實性的說故事者。不過,人的關鍵問題不是關于他們自己的原創作者的問題,假如我首先能夠回答‘在哪個故事或哪些故事里,我能發現我自己那一部分?’這問題,我就能夠回答‘我要做什么?’這個問題,我們進入人類社會,也就是帶著一個或多個被委以的角色——進入那些指派給我們的角色——并且,為了能夠理解他人對我們的反應如何和我們對他人的反應是怎樣被理解的,我們不得不了解角色是什么。”⑤麥金太爾.德性之后[M].龔群,戴揚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5:272.在麥金太爾看來,人類不僅是有故事的,而且還是說故事的,盡管他們所說的故事未必一定就是真實的。入乎故事之內,人類可以通過識別故事中的角色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出乎故事之外,人類能夠以特定的角色進入社會,并做出相應的行動。講故事固然使得人類獲得了建構世界,與自然界達成和解,創造了自己的能力,那么作為敘事人的人類究竟又是在講述什么呢?在筆者看來,人類的經驗(experience)構成了故事講述的主要內容,也是人類認識和建構自我身份的一個重要基礎。對此,趙毅衡有過精辟的論述。在《廣義敘述學》一書中,趙毅衡指出:“敘述,是人類組織個人生存經驗和社會文化經驗的普遍方式。”①趙毅衡.廣義敘述學[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1.
從遠古時代起,敘事成為記載和再現人類經驗的一個重要方式。杰里米·布魯諾(Jerome Bruner)認為,人類主要就是用敘事來組織自己的經驗。布魯諾說:“我們主要以敘事——故事、借口、神話、做或不做的理由等來組織我們的經驗和我們關于人類發生事件的記憶。”②BRUNER J.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J].Critical inquiry,1991(1):1-21.換言之,經驗都是人類敘事的核心。布魯諾的這一觀點在自然敘事學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論述。在《走向自然敘事學》一書中,莫妮卡·弗魯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參照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觀點,將自然敘事等同于口頭敘事。她指出:“口頭敘事(更確切地說,自發的會話講述的敘事)在認知上接近于人類經驗的感知范式,這些范式即便在更為復雜的書面敘事中也起著作用,哪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故事的文本構成會發生劇烈的變化。”③FLUDERNIK M.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M].London: Routledge,1996:9.弗魯德尼克用“人類經驗”來強調敘事的屬性,強調“經驗性”構成了作品的“敘事性”,她認為所謂的經驗性“反映了與人類存在和人類關切的具身性的認知圖式”④同③.。在弗魯德尼克看來,自然敘事構成了人類所有敘事的原型。弗魯德尼克實際上把故事講述作為一個過程來看,認為故事講述的目的與功能就在于再現敘述者過去的經驗。通過敘事講述,敘述者先是生動地再現這一經驗,繼而評價這一經驗,并且把經驗的意義與講述的語境結合起來。需要指出的是,弗魯德尼克所提出的關于自然敘事學的五種認知框架即行動(action)、講述(telling)、體驗(experiencing)、觀看(viewing)和反思(reflecting),都與人類的經驗及其敘事中介相關。人類的經驗可以通過一系列事件和反應來再現,因而人類的經驗實際上也是敘事的話題所在。弗魯德尼克指出:“再現人類經驗是敘事的中心目的,該目的既可以通過低層次敘事性的行動報道來實現,也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混雜了講述、觀看和經驗模式的形式來實現。”⑤同③51.
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在《講故事的人》一文中提到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歸來之后的士兵們沉默不語的現象,而這一敘事危機背后所隱藏與投射的是他們經驗的匱乏和身份的危機。本雅明說:
一夜之間,不僅我們對外在世界、而且精神世界的圖景都經歷了原先不可思議的巨變。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種現象愈發顯著,至今未有停頓之勢。戰后將士們從戰場回歸,個個沉默寡言,可交流的經驗不是更豐富而是更匱乏,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十年之后潮涌般的描寫戰爭的書籍中傾瀉的內容,絕不是口口相傳的經驗,這毫不足怪。因為經驗從未像現在這樣慘遭挫折:戰略的經驗為戰術性的戰役所取代,經濟經驗為通貨膨脹代替,身體經驗淪為機械性的沖突,道德經驗被當權者操縱。⑥本雅明.講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科夫[M]//阿倫特.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96.
從靈長類動物之間梳毛的前敘事,到作為所有文學敘事原型的自然敘事,從巴特關于“所有階級、所有人類集團都有自己的敘事作品”的敏銳觀察,到奈爾斯關于人類是“敘事人”以及麥金太爾關于人是“講故事的動物”的論斷,再到本雅明關于“講故事的人”所遭遇的經驗挫折,都說明故事講述是人類所特有的能力,人類通過講述故事建構了自己的身份,辨識了自己的存在。盡管隨著時間的變遷和媒介的革新,故事講述的形式愈加豐富多樣、千變萬化,但對人類經驗的再現始終都是敘事的核心。倘若人類失去了可以敘述的經驗,人類的身份和存在就會遭遇危機。
三、傳記、小說、自小說:敘事如何建構身份
在《反對敘事性》一文中,英國哲學家蓋倫·斯特森(Galen Strawson)明確表示自己反對關于敘事性的兩個命題:心理學敘事性命題(psychological narrativity thesis),即關于人類經驗本質的描述性命題;倫理學敘事性命題(ethical narrativity thesis),即關于我們應該以敘事的方式生活的范式性倫理命題。在斯特森看來,這兩種命題至少有四種組合關系:一是準確的描述性命題和錯誤的范式性命題,即我們認為自己是高度敘事的,但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二是錯誤的描述性命題和正確的范式性命題,我們不認為自己天生就是敘事的,但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過一個美好的生活;三是描述性命題和范式性命題都是正確的,即所有正常的、非病態的人類在本質上都是敘事的,敘事性對于美好的生活至關重要;四是描述性命題和范式性命題都是錯的,即人類并非只能以一種好的方式來體驗生活,世界上存在非敘事的人類,也有非敘事的好生活方式①STRAWSON G.Against narrativity[J].Ratio,2004(4):428-452.。斯特森區分了兩種類型的“自我經驗”(experience of oneself),即一個人在總體上主要把自己看作是人類時的自我經驗,以及一個人主要把自己看作是內在的心理實體或某種自我時的自我經驗②同①.。實際上,斯特森根據個體在時間上的存在又把自我經驗分成了兩種類型:歷時自我經驗(diachronic self-experience)和片段式自我經驗(episodic selfexperience)。歷時自我經驗指的是一個人把自我看作是在過去或在未來的東西;片段自我經驗指的是一個人沒有把自我看作是在過去或在未來的東西。歷時自我經驗一般被默認是敘事路徑,而片段自我經驗被認為是非敘事路徑。鑒于兩種類型的自我經驗之間的對立關系,人們通常認為如果自我經驗是歷時的,那么它就不是片段的;如果自我經驗是片段的,那么它就既不是歷時的,也不是敘事的。在斯特森看來,“一個片段性強的生活是人類的一種正常的、非病態的生活形式,實際上也是人類一種好的生活形式和繁榮途徑”③同①.。斯特森由此拒絕心理學敘事性命題和倫理學敘事性命題。
斯特森的觀點在敘事學界引發了較大的關注與爭議。巴特斯比這樣總結斯特森的論點:
斯特森論文的總體觀點分成兩個主要部分,而每個部分又包含兩點內容:(1)辯護他所稱之的自我經驗的片段式方法,在這一方法中,自我是與過去和未來都脫節的‘現在’現象,批判他稱之為自我經驗的歷時方法,在這一方法中,自我被理解成從過去到未來的時間中穩定的現象;(2)辯護自我再現的非敘事形式,批判自我再現的占據主導地位的敘事形式。斯特森研究個案的目標在總體上是去重塑討論自我和再現之間關系的條件和前提。④BATTERSBY J L.Narrativity, self, and self-representation[J].Narrative,2006(1):27-44.
換言之,斯特森的根本立場是自我經驗的再現但并不是依賴于敘事方法。在埃金看來,斯特森關于片段式自我經驗/歷時自我經驗之分存在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通過激發連續的身份承擔非連續的身份,沖淡了非連續身份觀;第二,沒有確定經驗的敘事觀是時間存在的歷時風格的特有屬性。與斯特森的觀點相反,敘事是所有人都可以獲得的資源,無論他們是否相信連續的身份或非連續的身份⑤EAKIN P J.What are we reading when we read autobiography[J].Narrative,2004(2):121-131.。與巴特斯比和埃金的觀點略有不同的是,費倫則認為斯特森關于片段式自我經驗和歷時自我經驗的論述具有一定的道理,并且試圖進一步拓展這一論點。費倫以其個人經歷為例,認為自己的身份不僅是片段式的而且也是多重的。當自己在通過“誰過去在哪里”(who was there then)的問題來思考“誰現在在這里”(who’s here now)問題的時候,與其說是被連續性給擊中了,倒不如說是被非連續性給擊中了。此外,費倫還認為“誰現在在這里”這個問題也包含多個可能的敘事①PHELAN J.Who’s here?Thoughts on narrativ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imperialism[J].Narrative,2005(3):205-210.。在此基礎上,費倫進一步提出兩個論點:第一,放棄敘事身份的普適觀點意味著減弱了敘事的力量,但這并不意味著敘事對于自我理解不再重要了,而僅僅意味著敘事的重要性因人而異。第二,對敘事身份命題產生更多的共情,因為斯特森既忽略了敘事身份是一個包含多元性的整體,也忽略了每個人是否都會敘事所塑造出來的身份感到滿意②同①.。
作為特殊種群的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人類獨特的敘事能力,而作為個體的人與他人之間的身份差異,則主要在于具有不同的人生故事。人生故事的呈現離不開敘事的作用,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討論的話題最終回到了敘事及其功能。什么是敘事?敘事何以具有建構身份的能力?在《敘事學詞典》中,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把敘事界定為“一個或多個虛構或真實事件(作為產品、過程、對象和行動、結構與結構化)的再現,這些事件由一個、兩個(明顯的)敘述者向一個、兩個或多個(明顯的)受述者來傳達”③PRINCE G.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extended and revised version)[Z].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58.。很顯然,在普林斯那里,敘事的核心就是事件。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敘事具有兩個重要維度——故事(story)與話語(discourse),前者關乎的是“什么”(what),后者關乎的是“怎么”(how)。一個人有怎樣的故事,就表明其有怎樣的身份;一個人有怎樣的故事,以及怎樣講述其故事,就會相應地建構怎樣的身份。
敘事是建構自我身份的一個重要路徑。我們在生命的不同時刻會發生很多不同的事件,而在講述生命故事時,我們一般會策略性地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進行選擇性的真實/虛構報道,建構自己喜歡/不喜歡抑或積極正面/消極負面的自我。敘事給予了個體以力量,“提供了控制其身份的能力,通過她所講述的故事,策略性選擇如何講述哪些事件”④RITIVOI A D.Identity and narrative[M]//HERMAN D, JAHN M, RYAN M-L.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New York: Routledge,2005:27.。通過講述不同的事件,敘述者或人物最終辨識了自己的身份,確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這種意義上,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指出,每個人都會以敘事的方式活著,結果“敘事就是我們,敘事就是我們的身份”(narrative is us, our identities)⑤SACKS O.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his hat and other clinical tales[M].London: Duckworth,1985:110.。敘事能夠給個體經驗賦予一定的結構與秩序,具有建構世界的能力。在被敘事建構起來的世界中,敘述者和人物認同了自己的位置,同時也投射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并對自我產生一定的意義。在諾依曼和紐寧看來,“我們的經驗和知識不是簡單地被給的或自然有意義的,相反它們必須被排序、言說和闡釋,即被敘述出來——才變得有意義。當我們在講故事的時候,我們給混亂的事件一定的規則和秩序,給異質的生活經驗以一定的結構”⑥NEUMANN B, NüNNING A.Ways of self-making in(fictional) nar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d identity[M]// NEUMANN B, NüNNING A, PETTERSSON B.Narrative and identity: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critical analyses.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2008:5.。
在論述敘事之于身份建構的重要作用時,利科把敘事作為一個獲取身份的中介,并重點考察了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兩大類型。如果把歷史和虛構放置于文學敘事領域,我們大致可以分為傳記敘事、小說敘事、自小說敘事三種類型。在傳記敘事中,“我”講述“我”自己的真實故事,力求真實;在小說敘事中,“我”講述了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明示了虛構性;介于二者之間的是自小說,“我”講述了關于“我”自己但又不是“我”自己的虛構故事,亦真亦假。
傳記敘事以自我敘述(self-narration)/自我敘事(self narrative)的形式為主,作者、敘述者和人物都是同一個人。在這一文類中,寫作自我(writing-I)通過敘述自我(narrating I)講述了被敘述自我(narrated I)的故事。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作者、敘述者和人物的身份融合。比如,在富蘭克林的《我的自傳》中,作者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傳記敘事中,自我敘事的重要作用在于“彌合了過去的經歷自我與現在的敘述自我之間在時間與認知上的間隙”①NEUMANN B.Narrating selves, (De-)constructing selves?Fictions of identity[M]//NEUMANN B, NüNNING A, PETTERSSON B.Narrative and identity: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critical analyses.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2008:57.。敘述自我把被敘述自我在重要時刻的事件按照一定的次序加以報道,實現了人生的故事化(life as storied)。用班伯格的話來說,就是把“把重要時刻嵌入重要事件,把重要事件嵌入一段經歷,然后把經歷變成人生故事”②MICHAEL B.Identity and narration[M]//HüHN P, MEISTER J C, PIER J, et al. Handbook of Narratology.Berlin: De Gruyter,2014: 245.。敘事之于自我的意義不僅在于在自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建立了鏈接,彌合了敘述自我和被敘述自我在認知與情感上的間隙,而且在于在講述的過程中認識和發現了敘事與自我身份的意義。諾依曼指出:“構成了我們身份的經驗、知識和記憶并不是簡單被給的,有自然的或積極的意義,相反它們必須被通過講述和闡釋而變得有意義。這一闡釋過程必然要使用敘事。在敘述過程中,我們給經歷賦予順序,塑造了我們的意圖,想象了我們的未來。”③同①54.一旦生活被中斷或失去其原有的連續性,我們就會遭遇身份危機,而通過敘事則有助于我們重新發現自我、審視自我。自我敘事是恢復、認知或審視身份的重要手段。以色列著名敘事理論家施勞米什·里蒙-凱南(Shilomith Rimmon-Kenan)曾說過一段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1998年夏天,里蒙-凱南在英國倫敦和家人一起度過了一個月后,準備自己再待上兩個月做課題,結果突然被診斷出“眼睛肌無力”(ocular myasthenia),只好中斷了課題,和家人一起返回了以色列。回憶起這段經歷,里蒙-凱南說:“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致命打擊’(a death blow),然后就是‘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回想起來,似乎對我而言,這種斷裂感主要由三個條件導致的:閱讀和寫作,職業必要性,以及存在的激情,都已經變得幾乎不可能了。”④SHLOMITH R-K.The story of ‘I’: illness and narrative identity[J].Narrative ,2002(1):9-27.在自我敘述的過程中,敘述者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進而開始辨識和認同自己的身份,接受原先生活中那個被中斷的自我。在這種意義上,埃金說:
傳記不僅僅是我們在書里讀到的東西,而且是作為一種身份話語,通過我們一天天講述自己的故事,一點點地傳遞出來,傳記建構了我們生活的結構。盡管我們不會過于思考自我敘述的這一過程,因為我們經過多年的實踐,已經把自我敘述做得如此之好。但是,當這一身份故事系統斷裂的時候,我們就會意識到它在組織我們的社會世界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⑤EAKIN P J.What are we reading when we read autobiography[J].Narrative,2004(2):121-131.
在小說敘事中,作者與敘述者和人物不是同一個人。作者以虛構的形式,講述了他人的故事。通過不同的視角和聲音,小說再現了不同場合下圍繞人物所發生的事件,講述了何人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出于何種原因發生了何事。敘事以建構世界的方式建構了人物的身份。通常情況下,作者會充分借用文類規約與敘事策略呈現作者、人物和敘述者的獨特身份。敘述者會在事實軸線上作出偏離事實真相的報道,在倫理軸線上作出錯誤的判斷,在認知軸線上作出不正確的闡釋,由此暴露出其不可靠的敘述者身份⑥PHELAN J,MARTIN M P.The lessons of ‘weymouth’: homodiegesis, unreliability, ethic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day[M]//HERMAN D.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88-109.。人物也會因其不同的地位、世界觀、立場等而被塑造出不同的面貌,或引發讀者的同情,或招致讀者的憎惡。鑒于在認知、情感和價值觀上的差異,作者、敘述者、人物之間存在一定的敘述距離。在敘述過程中,作者可能會認同,也可能會反對敘述者與人物的行為與立場。因為對故事資源和敘事策略的使用,作者也會由此表現出具有不同敘事格調的身份,貼上明顯的具有自我風格標簽的身份。譬如,我們會說海明威是采用簡潔凝練的“冰山體”寫作的作家,馬爾克斯是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家,狄更斯是現實主義色彩濃郁的作家等。
介于傳記與小說之間的文類是自小說。在該文類中,敘述者“我”和作者擁有同樣的名字,并宣稱會講述關于自己但又不是真實的故事,從而建構起既帶有真實性但又令人懷疑的真實身份。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的《百萬碎片》(A Million Little Pieces,2003)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作品中,敘述者和人物與作者詹姆斯·弗雷有相同的名字。弗雷曾是一名癮君子和酒鬼,他講述了自己如何在經歷各種挫折和痛苦之后,成功地戒掉毒癮和酒癮的勵志故事。盡管該書宣稱是弗雷的回憶錄和個人傳記,講述了自己戒毒戒酒的真實故事,但實際上弗雷在該書中杜撰了部分內容,并不完全都是真實的。譬如,其中一個頗有爭議的部分就是弗雷在書中寫道曾入獄87天,而實際上他在警察局只被關押了不到5個小時。通過這樣亦真亦假的故事講述,弗雷建構了自己曾經是癮君子的身份,并以戒毒戒酒成功的新面貌出現在公眾面前。盡管弗雷所講述的關于自己經歷的故事存在一定的虛構,但并沒有根本影響他是戒毒戒酒的成功者這一主要身份。在這種意義上,作為自小說文類的《百萬碎片》也實現了其關于弗雷敘事身份的功能。正如巴特斯比所指出的那樣,敘事身份命題的內涵“我們的身份是我們建構的關于我們自己的故事的功能”①BATTERSBY J L.Narrativity, self, and self-representation[J].Narrative,2006(1):27-44.。
就敘事身份的意義與啟發價值而言,從宏觀的總體層面上來看,敘事使得人類擁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即“敘事人”或“講故事的動物”,進而在人類學意義上成功地與其他的動物區別開來。從微觀的個體層面上來看,不同的人生經歷以及不同的人生故事使得人類擁有各自不同的身份,從而使得自我區別于他人。更重要的是,人類通過敘事不僅建構了自我身份,而且最終理解了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從而實現對道德意義的訴求,達到倫理化的目的。正如趙毅衡所指出的那樣:“敘述不可能‘原樣’呈現經驗事實。在情節化過程中,主體意識不得不進行挑選和重組。生活經驗的細節之間本是充滿大量無法理解的關系,所謂‘敘述化’,即在經驗中尋找‘敘述性’就是在經驗細節中尋找秩序、意義、目的,把它們編成情節,即構筑成一個具有內在意義的整體。一旦情節化,事件就有了一個因果一時間序列,人就能在經驗的時間存在中理解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因為獲得了事件中的意義,敘述就起了一般的陳述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敘述是構造人類的‘時間性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語言形式。情節將特定事件的諸種要素連為一體,構成道德意義。”②趙毅衡.廣義敘述學[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15.
實際上,人類不僅是講故事的動物,而且還是聽故事的動物。我們不僅渴望他人可以聽自己所說的故事,而且天然地也是他人故事的傾聽者。人類為什么對關于不同身份的人物的故事感興趣?從根本上來說,原因是我們希望通過傾聽他人的故事來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擁有一個更好的人生故事。對此,不妨引用麥金太爾的觀點加以解釋。在《德性之后》一書中,麥金太爾這樣評述人類聽故事的意義:
正是通過聽許多這樣的故事——邪惡的后母,丟失的小孩,善良但被錯誤引導的國王,養育孿生兄弟的狼,最年輕的兄弟們沒有得到遺產但卻在這個世界上獲得了成功,年紀大的兄長們在放蕩的生活中浪費了他們的遺產,離鄉背井和豬生活在一塊——兒童領會到或沒有領會到一個孩子是什么,一個父親或母親是什么,而這一切都是這個戲劇中的那些角色,兒童們就降生在這種戲劇中;而這一切也就是這個世界的這些方面,兒童們就處在這個世界中。受虐待的兒童的故事,憂慮的口吃者,這在他們的行為中就如在他們的言詞中一樣,而你都把這些故事默記在心。因此,除了通過作為最初的戲劇資源的那些故事,我們無從理解包括我們自己的社會在內的任何社會。神話,就它的原始意義而言,是心中的事物。維柯是正確的,喬伊斯也是正確的。所以從英雄社會到它的中世紀的繼承者的道德傳統當然也是對的,根據這個傳統,說故事在教育我們成為有德的過程中,起了一個關鍵作用。①麥金太爾.德性之后[M].龔群,戴揚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5:273.
四、余 論
在2005年10月份出版的《敘事》雜志上,主編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就敘事學界所熱議的敘事身份話題撰寫了題為《誰在這里?關于敘事身份與敘事帝國主義的思考》的編者按。費倫指出,敘事身份命題是“在更廣闊的敘事轉向語境下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因為這是我所提出的‘敘事帝國主義’(narrative imperialism)的一個例證,研究敘事的學子有占領越來越多研究領域、對我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式投入越來越多的力量的沖動。這種擴展主義沖動是自然的——它源自我們對研究對象的激情——它也常常是理由充足的:在很多情況下,敘事和敘事理論有助于豐富新的研究領域”②PHELAN J.Who’s here?Thoughts on narrativ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imperialism[J].Narrative,2005(3):205-210.。針對敘事身份命題的熱度,費倫認為這是一個關注的現象,并將之看作為敘事帝國主義的一種表現,諸如敘事身份命題等的敘事學拓展有助于深化和豐厚新的研究領域。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10年,敘事身份命題依然是敘事學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究其緣由:第一,這與當代文學對身份問題的關注密切相關,正如比吉特·諾依曼所指出的那樣,當代文學“沉迷于身份問題”③NEUMANN B.Narrating selves, (De-)constructing selves?Fictions of identity[M]//NEUMANN B, NüNNING A, PETTERSSON B.Narrative and identity: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critical analyses.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2008:66.;第二,與敘事轉向后,敘事的普適性和有效性得到廣泛的認同有關,即敘事不僅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同時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在《敘事學手冊》中,班伯格針對如何進一步研究敘事身份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敘事能否真正構成一個探究生活和身份的優先領域需要進一步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第二,用敘事方法來研究混合或帶連字符的身份構成了近期社會科學研究潮流中一個有趣的新進展,涉及討論的問題有公民權、文化排外性、想象的共同體、歸屬感的象征再現,以及全球化的一般過程;第三,疾病和創傷經歷通常被看作是連貫性和連續性的中斷,對自我感的形成和(傳記的)身份以及我們的主體感都提出了挑戰;第四,日漸多元的不同敘事方法和路徑,不禁讓人疑惑,對于研究主體性、自我和身份的最初的敘事方法還是否存在一個共同核心(a common core)④MICHAEL B.Identity and narration[M]//HüHN P, MEISTER J C, PIER J, et al. Handbook of Narratology.Berlin: De Gruyter,2014:250.。班伯格的上述四點建議切中肯綮,既涉及敘事身份命題的本體,又涉及敘事身份研究的跨學科領域與視角,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
筆者試圖在班伯格的基礎上,補充提出關于敘事身份未來研究需要注意和思考的三個問題,作為本文的結尾。第一,敘事身份研究中的“敘事”屬性與地位問題需要被進一步理清。敘事如何既是我們研究的對象,也是建構身份的手段,同時也是理解和評價身份的一種方法?第二,敘事的身份建構研究與敘事的世界建構研究之間內在關系的問題。敘事在建構故事世界的同時,也建構了人物的自我身份。問題在于敘事所建構的故事世界如何凸顯人物的身份,而人物的身份又如何影響故事世界的穩定性?第三,超越傳統意義上敘事身份研究限定在人的身份這一范疇,可以有效擴展至國家、種族、團體的敘事身份。敘事如何既可以有助于一個國家、民族或種族建構自己的身份,又可以幫助讀者來理解一個國家、民族和種族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