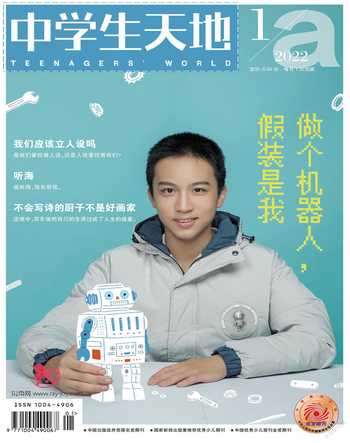燈之思
饒晨晗
似乎思月即思鄉(xiāng)。“月是故鄉(xiāng)明”,年年歲歲,見著月兒便道思鄉(xiāng),是自古以來的老傳統(tǒng)了。
我呢,不怎么思月。鄉(xiāng)情里最深沉一處,是老家門前的一盞燈。
一盞光線昏黃的小燈,簡單地罩了綠漆鐵片,懸在對門的屋檐下,垂下一條細(xì)細(xì)的燈繩。傍晚時分,各家小孩總要爭著去夠那繩子。年復(fù)一年,有一部分孩子先長高,先能夠著燈繩,點(diǎn)上燈——再后來,他們便長大離開了。
那是一盞很樸實(shí)無華的燈,在晚飯后亮起。鄰居們搬了各家的椅子凳子坐到燈下,圍坐成一個臨時院落嘮家常。燈光不是很亮,只能鋪開一小片淡黃微醺的光。一般是各家的老人先開口,綿綿地拉長聲音,細(xì)說一些被人淡忘的故事。小孩子們靜不下來,在燈光下跳啊跑啊,像一群不安分的羊羔。悶熱的空氣里,幾只蚊蠅偶爾撞進(jìn)光織的網(wǎng)里打轉(zhuǎn),帶著腥味的海風(fēng)遠(yuǎn)遠(yuǎn)地吹過來,捎來遠(yuǎn)海和停靠在碼頭的漁船的消息。當(dāng)時居然也不覺得熱,只覺得燈光亮得可愛,海風(fēng)吹得可愛,大人們臉上的笑意、老人們細(xì)細(xì)軟軟的方言聲、孩子們無拘無束的玩鬧也可愛。在那個小小的世界里,一個暫時搭建的、似乎與所有世俗隔絕的世界里,萬物都蒙上了一層朦朦朧朧的燈光,都那樣可愛。
小時候,我曾跟著爺爺奶奶在老家住過一段時間。老家門前的小燈,在漫長的歲月里替我保留了我的童年。
海邊的白天總是拉得太長,入夜又叫人猝不及防。大概和海聊天聊過了頭,往往是到點(diǎn)了,日頭才恍然大悟地落下山去,投入大海的腹中,去做一個光怪陸離的迷夢。冬天的晚飯,常常是閉著門吃的,凜冽的寒風(fēng)實(shí)在大得嚇人。吃完后,憋足了勁兒將門勉強(qiáng)打開一條縫,才發(fā)覺天色不知道什么時候已經(jīng)黑了。隨后小燈就亮起來了,藤椅板凳都擺出來了,我一步兩級地跳下門口的臺階,穩(wěn)穩(wěn)著陸在奶奶的懷里。
從那時候起我才知道,光是有味道的。而門前小燈的味道,是爺爺?shù)乃疅熚丁?/p>
長長的煙筒里飄出微腥的煙霧,裊裊地彌散在朦朦朧朧的燈光里。我時常覺得水煙里不只有煙草的味道,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滄桑和沉靜。在爺爺?shù)乃疅熚独铮衣勔姖皲蹁醯暮oL(fēng)、高聳的燈塔和晚歸的漁船,爬滿老碼頭和攔海壩的重重疊疊的小螺、在巖石間毫無頭緒地爬來爬去的巖蟹、張著嘴鼓著眼睛在漁網(wǎng)里掙扎的魚,還有我相信卻從未親眼見過的那些故事……它們?nèi)诨诠夂蜔熿F里,涌動著、打著旋兒飄飄忽忽,把我?guī)У揭粋€神話的夢境里。
老家很少入夢,這盞再普通不過的小燈卻一次一次闖進(jìn)我的夢里,掀開記憶斑斕的一角。
后來很少再看見這種老式的小燈。看見了,便將在心里某一處埋藏得遙遠(yuǎn)的記憶打撈上來,默默再倒放一遍,就好像我還沐浴在那樣的燈光下。
3440501908260